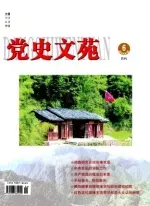為毛澤覃守靈的紅軍妹
■卜 谷
泥土?xí)裨崛伺c事,淡漠和遺忘也會(huì)埋葬人與事,但歷史不會(huì)埋葬人與事。
——題記
她出生在江西瑞金一個(gè)貧苦農(nóng)民之家,為生計(jì)所迫,19歲那年當(dāng)了紅軍。她曾跟隨原紅軍獨(dú)立師師長(zhǎng)、毛澤東的弟弟毛澤覃打過(guò)游擊,還當(dāng)過(guò)原中華蘇維埃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huì)(蘇區(qū)中央局軍委)主席項(xiàng)英的機(jī)要員兼保姆;她曾不顧死活,在白軍的槍口下為毛澤覃擦洗遺體;她“躲山”被捕槍決時(shí),連遇3顆臭彈,大難不死,虎口余生;她“文化大革命”中被誣陷為出賣毛澤覃的叛徒,被荒唐判處死刑,執(zhí)行槍決當(dāng)日竟神奇遇赦;她嫁過(guò)5個(gè)男人,最終還是難逃守寡的命運(yùn);她獨(dú)居深山,為毛澤覃守靈77年,可當(dāng)墓地打開(kāi)時(shí),她看到的竟是一座空墳!
她就是中國(guó)最老的紅軍妹——張桂清,至今依然活著,103歲。
在蘇區(qū)中央局軍委工作三年結(jié)識(shí)了毛澤覃
順著箬別溪走,溪流越來(lái)越大,河面越來(lái)越闊,就走到了江寬水闊的綿江,就走到了瑞金縣城。
1931年初的綿江清澈見(jiàn)底,那一天上午,19歲的張桂清在綿江邊為傷員洗繃帶。當(dāng)時(shí),藥品十分緊張,用過(guò)的繃帶洗干凈還要反復(fù)使用。岸上傳來(lái)護(hù)士長(zhǎng)的叫喚聲,說(shuō)醫(yī)院的領(lǐng)導(dǎo)叫她立即回去。進(jìn)到辦公室,院長(zhǎng)微笑著說(shuō)的這句話,讓她一下子懵了。
“你被選調(diào)到蘇區(qū)中央局軍委工作。”
由一個(gè)醫(yī)院領(lǐng)導(dǎo)引領(lǐng),經(jīng)過(guò)數(shù)位哨兵盤問(wèn),張桂清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情,踏進(jìn)了那片葉茂蔽天的神秘所在。經(jīng)過(guò)報(bào)告,他們跟著一位軍人由側(cè)門進(jìn)入一幢灰色的屋宇,從此以后,張桂清就留在葉坪工作,擔(dān)任時(shí)為軍委主席的項(xiàng)英的保姆兼做些機(jī)要工作,幫助項(xiàng)英的妻子張亮,照顧他們的兒子——小狗。
在蘇區(qū)中央局軍委工作并不孤單,軍委和紅一方面軍總部有十幾個(gè)女同志,其中有項(xiàng)英的妻子張亮、朱德的妻子康克清、毛澤覃的妻子賀怡,隨后也認(rèn)識(shí)了這些大姐的丈夫。
賀怡的丈夫毛澤覃也因工作、生活關(guān)系,經(jīng)常出入軍委駐地。那天,張桂清一邊帶著小狗一邊支撐竹篙架曬衣服,賀怡與一青年軍人路過(guò),二人主動(dòng)上前幫忙支撐竹篙架曬衣服。賀怡指著那個(gè)青年軍人介紹,“他就是我的老公——毛澤覃”。
毛澤覃像所有正規(guī)軍人遇到首長(zhǎng)那樣雙腳“嘭”地一并,身體挺直,行了個(gè)很好看的舉手禮,然后跨前一步伸出雙手與張桂清握手。張桂清張皇失措,過(guò)了一會(huì)才反應(yīng)過(guò)來(lái),伸出手去。
毛澤覃身材高大英俊,兩眼炯炯有神,雙手像兩團(tuán)火充滿熱力,緊緊地握住了張桂清剛才洗過(guò)衣物冰涼的雙手,有一股電流迅速傳遍張桂清全身。她覺(jué)得全身熱流涌動(dòng),臉頰發(fā)燒發(fā)燙通紅通紅,許久許久都平靜不下來(lái)。這一握,給張桂清留下了永遠(yuǎn)的印象。過(guò)去,雖然常見(jiàn)過(guò)別人握手,但還沒(méi)有人與她握過(guò)手,而且是用兩只手。這是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
張桂清就這樣認(rèn)識(shí)了毛澤覃。以后,她每次看到毛澤覃都會(huì)想到那次握手,都會(huì)面紅心跳不好意思,都會(huì)聯(lián)想得很多很多。此后,無(wú)論他在哪里出現(xiàn),她都會(huì)不由自主地把目光系在他身上。
清晨的樟樹(shù)林,蒙蒙的,蕩漾著濃濃淡淡乳白色霧氣,霧氣里飄浮著一股清爽的樟香。嘹亮的軍號(hào)聲,日日在霧氣中回響,樟樹(shù)林下是平敞開(kāi)闊的操場(chǎng)。
張桂清每天在號(hào)音中起床,在號(hào)音中參加操練。漸漸地,張桂清融入了紅軍總部的生活之中。
隨著越來(lái)越緊的槍聲,項(xiàng)英夫妻倆決定,兒子小狗先送到群眾家寄養(yǎng)。張桂清很茫然,張亮走了,小狗送人了,自己今后怎么辦?部隊(duì)還要不要自己,自己不帶人又能干些什么呢?
張桂清清楚記得,“最后一次與賀怡見(jiàn)面也很突然。那天,我正帶著小狗在屋檐下玩耍,一個(gè)戴著斗笠的人朝我們走過(guò)來(lái),到了面前摘下斗笠突然喚我一聲,竟是賀怡,更黑更瘦,我都有些不敢認(rèn)了”。
賀怡是專門來(lái)向張桂清告辭的,拉著她的手說(shuō)了很久的話,囑咐今后一定會(huì)再相見(jiàn)。淚水伴著雨水,張桂清與賀怡相擁而泣,天上的雨越下越大。
賀怡與張桂清的這次告別以及告別時(shí)的囑托,隨著時(shí)間的久遠(yuǎn),越來(lái)越清晰地銘刻在青年張桂清心里。張桂清是個(gè)實(shí)在的人,她記住了這些告別,也記住了與賀怡的友情。
張桂清為毛澤覃擦洗遺體
兵行如水,避高而趨下。紅軍主力離開(kāi)后,中央蘇區(qū)的形勢(shì)急劇惡化,日益緊張。
張桂清沒(méi)有隨中央分局去于都南部的禾豐地區(qū),她與張亮、小狗分手,即編入了毛澤覃領(lǐng)導(dǎo)的紅軍游擊隊(duì),跟著毛澤覃一路向閩贛省突圍。
那一段時(shí)間,白軍占領(lǐng)、進(jìn)攻的消息一個(gè)接一個(gè),人心惶惶,加上日日奔走行軍,吃喝拉撒都困難,更別說(shuō)洗澡換衣服,每個(gè)人身上都有一股濃濃的味道。上級(jí)決定,疏散一些地方干部、老弱病殘、婦女,以及不愿意留下的人,好幾百人就迅速分散了。
張桂清也屬于疏散人員,有點(diǎn)發(fā)蒙,不知道怎么辦,回到屋里看見(jiàn)別人起身走了,也準(zhǔn)備起身就走。這時(shí),一個(gè)高大的身影出現(xiàn),是毛澤覃匆匆過(guò)來(lái)。
“小張妹子,我抽空來(lái)送你一下。”毛澤覃還沒(méi)站定就急急地說(shuō),“你不能這樣隨隨便便回去,以后一定要學(xué)會(huì)保護(hù)自己。要把軍裝脫掉,不要讓村里的人知道你當(dāng)過(guò)紅軍;還要把辮子接長(zhǎng),不能讓別人一看你就是蘇干;你還要改過(guò)一個(gè)名字,以后說(shuō)話要把普通話口音改掉,完全說(shuō)本地話;還有一些生活習(xí)慣也要完全與本地村民一樣;要很快和村民們熟悉,好成一家人,關(guān)鍵時(shí)候村民們就會(huì)出來(lái)保護(hù)你……你一定要保護(hù)好自己,等紅軍主力回來(lái)時(shí),我們都平平安安活著再見(jiàn)。”
“姐夫,我改一個(gè)什么名字好呢?”客家人很講究取名字的,取得好,好一生,取得不好,不好一生。張桂清原名叫張愛(ài)蘭,她覺(jué)得這個(gè)名字少了點(diǎn)什么,很希望毛澤覃為她改一個(gè)名字。
“就叫做張桂清吧,桂花的桂,清水的清。”毛澤覃不假思索,順口就來(lái)了一個(gè)。
取名字很關(guān)鍵,按客家規(guī)矩被取名的人是要請(qǐng)酒的。張桂清請(qǐng)不起酒,她從箱子里掏出早已經(jīng)準(zhǔn)備好的一雙布草鞋、一雙襪底。那是一雙相當(dāng)結(jié)實(shí)的襪底,每只襪底上還用紅絲線繡了一顆心,心的中間是一顆紅五角星。她雙手把襪底遞給毛澤覃以表感激之情,聲音因?yàn)榧?dòng)而有點(diǎn)顫抖,說(shuō):“姐夫,你要長(zhǎng)命百歲,打仗時(shí)要注意保護(hù)自己。”
毛澤覃接過(guò)草鞋、襪底,抬腳比量了一下,大小正合適。隨口應(yīng)答:“妹子,你放心,我是時(shí)時(shí)可死,步步求生。”
開(kāi)口一句話便說(shuō)到平日最忌諱、卻又不能不時(shí)常想到的那個(gè)“死”字。她的心顫抖了一下,還想說(shuō)什么。那邊有人在一連聲地喊:“秘書長(zhǎng),毛秘書長(zhǎng)——”分手在即,張桂清想與毛澤覃緊緊地握個(gè)手,可是毛澤覃伸出厚實(shí)的大手,拍了拍張桂清的肩膀掉頭就走了。邊走邊大聲說(shuō):“記住,等紅軍主力回來(lái)時(shí),我們?cè)僖?jiàn)啊——”
毛澤覃遠(yuǎn)去的背影消失在綠樹(shù)叢中。
“時(shí)時(shí)可死,步步求生。”張桂清咀嚼著這句話,一個(gè)人呆呆地站了許久。
天色突然轉(zhuǎn)暗。她重重地嘆了一口氣,掏出一面小鏡子對(duì)自己進(jìn)行了簡(jiǎn)單的化裝。根據(jù)毛澤覃講的自我保護(hù)辦法,她在剪短了的頭發(fā)上接了兩條長(zhǎng)長(zhǎng)的辮子。
天漏了一般,梅雨淅淅瀝瀝地下著,寒侵入骨。
1935年4月的春雨是個(gè)慢性子,無(wú)休無(wú)止地下著,陰沉沉的云團(tuán)遮蔽了日光、月光、星光,像在醞釀一個(gè)陰謀。
“砰”地一聲屋門大開(kāi)。幾個(gè)白軍士兵在保長(zhǎng)的帶領(lǐng)下闖入屋子,這伙白軍一身泥濘卻興奮異常,個(gè)個(gè)大呼小叫,說(shuō)是剿“匪”立了天大的功勞。要她立即動(dòng)身去認(rèn)尸,看打死的人是不是大名鼎鼎的毛澤東的弟弟毛澤覃。
張桂清心中一驚,眼淚在眼眶里打轉(zhuǎn),腿腳抖得都邁不動(dòng)步子。幾個(gè)士兵特別兇,不管三七二十一,把她推出房門,拽著她的胳膊行走如奔。
張桂清逐漸清醒過(guò)來(lái),她不相信白軍打得死毛澤覃,一定是白軍搞錯(cuò)了。
小道十分泥濘,張桂清越走越快,走得比白軍還快。總覺(jué)得心里不托底,她急于去看個(gè)究竟,一路飛濺的泥漿糊住了她的腳面、褲面。她渾身透濕,冰涼冰涼,一直冰涼到心底。
那一段時(shí)間,各路白軍在軍事上四面出擊取得節(jié)節(jié)勝利,吹牛皮的事情也就層出不窮,有的白軍部隊(duì)膽子更大,為了報(bào)功,竟然敢到處宣揚(yáng)說(shuō)當(dāng)場(chǎng)擊斃了項(xiàng)英、陳毅,云云。為了搞清楚擊斃的人是否真正的毛澤覃,進(jìn)而邀功請(qǐng)賞,白軍特意派人去抓張桂清來(lái)黃鱔口的白屋子認(rèn)尸。
“那個(gè),你仔細(xì)看看,是毛澤覃嗎?”
尸體擱在白屋子屋場(chǎng)的大禾坪上。這是村民陳德寶、陳忠建的屋背,江聲球的家門口。當(dāng)時(shí),白軍的團(tuán)部就設(shè)在村民陳忠建家中。圍觀的村民有邱達(dá)輝、陳德寶、陳忠建、江聲球、邱世連等,還有一些婦女、孩子。尸體上纏著碧青的生長(zhǎng)著綠葉的藤條,一道一道如繩索一樣捆綁得結(jié)結(jié)實(shí)實(shí),兩根毛竹在藤條當(dāng)中一穿,像本地抬野獸一樣抬出大山的,一只光腳丫微微翹起來(lái)。
白軍連長(zhǎng)掏出手槍,將子彈上膛,槍口頂住張桂清的腦殼。
當(dāng)她輕輕揩去那人臉龐上覆蓋的厚厚血凝時(shí),只見(jiàn)兩眼仍睜著,黑亮的眼珠放著光。張桂清心里一咯噔,以為他還活著,驚叫了一聲,過(guò)一會(huì)兒才確信,他真的死了。真是毛澤覃,還是生前那個(gè)高大、青春、瀟灑的毛澤覃!她擦拭去他脖頸、手臂、腳裸上的泥污,脫下他腳上的布鞋。果然,鞋里墊著那雙她親手做的襪底,只是這雙襪底已經(jīng)完全被鮮血浸漬成黛紅色。
她的心一抖,淚如泉涌,摻和著雨水,“吧嗒吧嗒”打落在毛澤覃蒼白的臉龐上。
張桂清忘記了害怕,一下一下,用手輕輕地把毛澤覃微睜的眼睛合上,又使勁地將他臉上一層厚厚的硝煙銹痕揩去,把他嘴里的泥血洗抹掉,把頭發(fā)上的草屑污泥污血清洗掉。
整理好衣領(lǐng)、衣袖,平靜的毛澤覃猶如熟睡。張桂清開(kāi)始為毛澤覃洗手,那是一雙寬大、蒼白、長(zhǎng)著厚繭的手掌,這雙手曾經(jīng)非常有力,給她留下深刻印象和久久的溫暖。
如今,這雙大手就擺在面前,像睡夢(mèng)中一樣失去了力量,張桂清仔仔細(xì)細(xì)地擦洗著毛澤覃的雙手,把每一道皺折、傷痕中的縫隙都擦洗得干干凈凈。然后,她的雙手緊緊地握住毛澤覃冰涼冰涼的雙手。
一雙女性的布滿厚繭的小手,一雙男性的骨骼嶙峋的大手;一雙黝黑有力的小手似剛勁的藤索,一雙白皙的大手似一團(tuán)綿軟的棉花。兩雙手久久地握著、握著,雨水冰涼冰涼,那雙小手怎么也無(wú)法把熱力傳輸給那雙大手。
雨,竟意外地停了。這是他們兩人的第二次握手,也是他們?cè)谶@個(gè)世界上的最后一次握手……
張桂清的心在流血。
確定了年輕的尸體是毛澤覃后,白軍連長(zhǎng)和士兵們爆發(fā)出了一陣陣狂笑,相拽相擁著轉(zhuǎn)身去喝慶功酒了。
白軍拍下毛澤覃的遺像,用刺刀把他的頭顱割了下來(lái),送到縣城去請(qǐng)賞,爾后將毛澤覃的無(wú)頭尸體拋棄在竹林荒野中。
當(dāng)天下午,張桂清見(jiàn)到中共地下黨員邱達(dá)輝,說(shuō):“被打死的人,確實(shí)是毛主席的親弟毛澤覃,我認(rèn)得的……”邱的公開(kāi)身份是偽保長(zhǎng)。
張桂清說(shuō),當(dāng)晚夜里,邱達(dá)輝、陳德寶(中共紅林村第一任黨支部書記)等人悄悄聚合到張屋坪的荒野上,就地挖了一個(gè)坑,將毛澤覃的無(wú)頭尸體秘密掩埋在一片竹林間(另一傳說(shuō)他的尸體埋在縣城和尚墳,現(xiàn)已蕩然無(wú)存)。那是一座平冢,無(wú)墳頭,無(wú)碑石,無(wú)標(biāo)志,大地幾乎沒(méi)有留下一點(diǎn)痕跡。
靖衛(wèi)團(tuán)逼全村人看她生小孩
重重疊疊的山脈,把一座座村莊擠壓得很小很扁。白軍的擠壓如乳白色的濃霧,從山那邊彌漫過(guò)來(lái),密不透氣。風(fēng)聲一日緊似一日。
張桂清第四個(gè)老公,是在躲山時(shí)亂撞“撞”到的。羅家和原是鄉(xiāng)蘇維埃團(tuán)支部書記,才21歲,比張桂清小2歲,生得相當(dāng)英俊,人也很精明,能跑能打,是游擊隊(duì)的主力成員。新來(lái)乍到的張桂清,躲山時(shí)常得到羅家和幫助,對(duì)他頗有好感。之后,兩人結(jié)成夫妻,成了游擊隊(duì)中的第七對(duì)夫婦。
滅頂之災(zāi)禍,在一個(gè)清晨降臨。
那是一個(gè)白霧茫茫的早晨,霧靄在陽(yáng)光中漸漸消散。作為一個(gè)有經(jīng)驗(yàn)的游擊隊(duì)員,羅家和從來(lái)沒(méi)有放松過(guò)警惕性。在以往的斗爭(zhēng)中,白軍常利用清晨進(jìn)行偷襲,他在游擊隊(duì)里也就養(yǎng)成了清晨早起轉(zhuǎn)移、隱蔽的習(xí)慣。
可就在此時(shí),村前突然傳來(lái)幾聲犬吠,靖衛(wèi)團(tuán)的部隊(duì)趁著山嵐包圍了村子,直向羅家和、張桂清的住所撲來(lái)。
白軍在屋子里外搜索了幾遍,開(kāi)始折磨張桂清。
“你,你是交待還是看著你老婆去死!”白軍排長(zhǎng)踢了羅家和一腳,喝問(wèn)道。
那排長(zhǎng)并不是在嚇唬人,也不多啰唆,轉(zhuǎn)頭向一白軍發(fā)出命令:“立刻先把這個(gè)女人槍斃掉!”可連開(kāi)3槍,竟都是臭彈。
白軍排長(zhǎng)叫兩個(gè)士兵把張桂清拖起來(lái),那個(gè)執(zhí)行槍斃的士兵不服,走過(guò)去粗魯?shù)叵崎_(kāi)她的衣服看,張桂清的肚子已經(jīng)很凸,顯然是懷著孩子。
“難怪,這是個(gè)大肚婆呀,槍殺大肚婆天理不容,難怪槍里面盡是臭彈。”
那兩個(gè)扶起張桂清的白軍說(shuō)道,你的命真的蠻大,以后會(huì)蠻有福氣。
白軍排長(zhǎng)是個(gè)職業(yè)軍人,他很生氣,從地上撿起那白軍扔掉的步槍。“這槍打不死大肚子,一般人也打不死?!”說(shuō)著,把槍口一抬胡亂對(duì)著張桂清的丈夫羅家和就扣動(dòng)板機(jī)。
“砰”的一聲,一股鮮血濺了排長(zhǎng)一身一臉。臭彈竟然不臭了,所有的人嚇了一跳,白軍排長(zhǎng)更是驚得半晌開(kāi)不得聲,眾白軍好似碰到了鬼,一個(gè)個(gè)面色大變,驚慌失措。
“呸呸,霉時(shí)倒運(yùn),霉時(shí)倒運(yùn)!”色厲內(nèi)荏的白軍排長(zhǎng)抹了一把臉,手上全是熱腥熱腥的血水,胸襟處濕漉漉一大片血漿。
篤信風(fēng)水的靖衛(wèi)團(tuán)團(tuán)長(zhǎng)歐陽(yáng)光想到了一個(gè)最陰險(xiǎn)的計(jì)謀。
孕婦不是很兇煞么,那好,他要讓全村人來(lái)親眼看張桂清生小孩,讓全村人來(lái)分解孕婆子的晦氣、兇煞氣,那么孕婆子的晦氣、兇煞氣不攻自滅。另外,這棵大檫樹(shù)不是神樹(shù)么,就讓神樹(shù)來(lái)煞煞張桂清,也讓張桂清的晦氣、兇煞氣來(lái)煞煞神樹(shù)的神氣。
幾遍鑼響,胡竹段村的男女老少都被召集在神樹(shù)前的大坪上。張桂清被架著經(jīng)過(guò)烏壓壓的人群,她有點(diǎn)奇怪,難道要開(kāi)會(huì),要被當(dāng)眾拷打?
正狐疑間,幾個(gè)士兵上前,當(dāng)眾去扒她的上衣,她緊緊地護(hù)住衣服,左擋右遮,衣服一塊塊撕成片片落在地上,她的上身露了出來(lái)。
“大家快看呀,你們知道她是誰(shuí)吧,她就是你們胡竹段村人,羅家和的老婆,上三鄉(xiāng)有名的美女……”
張桂清不停地咒罵著,拽緊褲腰。白軍淫笑著又扒她的褲子。她又踢又咬,雙手死死地抓住褲腰不松手。不料一個(gè)白軍繞到她身后,抽出刺刀插入褲內(nèi),用力一割,只聽(tīng)得“嘶”的一聲,褲帶斷了,褲子連襠到褲腳割裂;又一刺刀下去,另一只褲腿也被割裂。張桂清拽在手里的只有一塊破布,雪白的下身全部裸露無(wú)遺。
眾目睽睽之下,幾個(gè)白軍開(kāi)始往張桂清身上一道一道勒繩子,越勒越緊的繩索,把她高高凸起的大肚子勒逼得明顯癟下,這是最野蠻的人工墜胎。
一陣一陣的疼痛從腹部向全身發(fā)散。這時(shí),張桂清明白了敵人的用意,是要害自己,害自己的孩子。在大庭廣眾面前,全裸的張桂清疼痛得厲聲尖叫,拼命掙扎,直到暈死過(guò)去。
大坪前一條清鱗鱗的小溪,都是冰涼冰涼的山泉,白軍拎了一桶溪水,嘩地從頭到腳潑在她身上,張桂清又從昏迷中凍醒。
白軍實(shí)施的人工墜胎繼續(xù)進(jìn)行,張桂清無(wú)力地咒罵著。道道繩索越勒越往下,大肚子越勒越小,腹部絞痛,連呼吸都相當(dāng)困難,猛然,她感覺(jué)巨痛襲來(lái),胯下一熱,大小便失禁。她又昏死過(guò)去。
突然,一個(gè)紫紅的胎兒順著血路掉在了地上。
張桂清第五次嫁人
整不死的人,怎么也整不死,整不死就還要往死里整。
1937年冬,周身傷痕累累的張桂清被抬進(jìn)縣城的大牢。第二天,她便奇跡般地坐了起來(lái),看著身邊那個(gè)剛出生的孩子,一聲不吭,一動(dòng)不動(dòng),青一塊紫一塊的身上冰涼冰涼沒(méi)有一絲熱氣,不知道是什么時(shí)候死的,也不知道活過(guò)沒(méi)有。
為了懲罰張桂清,靖衛(wèi)團(tuán)團(tuán)長(zhǎng)歐陽(yáng)光叫獄卒給她帶上手銬腳鐐,拴在牢房的柱子上,一天到晚不能動(dòng)彈。
不能動(dòng)彈的張桂清把屎尿都屙在身上地上,一時(shí)間,身上地上到處黏糊糊的,臭氣薰天。
幾天過(guò)去,張桂清天天不進(jìn)食,下身還不停地流血水,可她硬是捱著、撐著、掙扎著,奄奄一息就是不肯死。屋子里生出的蒼蠅烏云般地飛來(lái)飛去,管牢房的牢頭辦公桌和廚房灶臺(tái)上也爬著蛆蟲(chóng)。
獄卒和其他犯人都忍受不住,于是,奄奄一息的張桂清被抬走了,慢慢地,她竟回過(guò)陽(yáng)來(lái)。
終于回家了,張桂清回到魂?duì)繅?mèng)縈的娘家。不久后她又成親了,第五任丈夫名叫邱漢華,是一名紅軍傷殘兵,但基本生活還是勉強(qiáng)能夠自理。
結(jié)婚是一種奇怪的結(jié)合,要么撿到一個(gè)包袱自己背著,要么自己是個(gè)包袱讓別人背著。這回,張桂清是撿到了一個(gè)大大的包袱。
張桂清并不孤寂。長(zhǎng)長(zhǎng)的回憶,也是一種生存方式。面對(duì)青冢土堆,張桂清偶爾也帶上珍藏著的那雙襪底——毛澤覃犧牲時(shí)穿著的那雙襪底。
不知不覺(jué)中,張桂清已經(jīng)生育了一子一女,埋頭一心過(guò)她的苦日子。
1956年底的一天,邱漢華的咳嗽突然加重,開(kāi)始發(fā)燒,嘴唇都干裂了,暈暈地睜不開(kāi)眼睛。這不是過(guò)去常患的小毛病,邱漢華第二天便撒手人寰。剛剛才過(guò)了幾年寬松日子,從此張桂清肩上的擔(dān)子就更重了。
要養(yǎng)活兒子邱世機(jī),張桂清必須一邊參加生產(chǎn)勞動(dòng)掙工分,一邊幫別人接生掙工分,白天晚上不停地忙碌。可別小看接生這活計(jì),她每次都能帶回來(lái)幾個(gè)雞蛋,關(guān)鍵時(shí)刻還能靠這幾個(gè)雞蛋換點(diǎn)活命錢。
解放初,張桂清擔(dān)任過(guò)短暫的村干——婦女主任,不久被派到縣人民醫(yī)院婦產(chǎn)科學(xué)習(xí),主要是學(xué)習(xí)接生。久而久之,這一村子的人和四周許多村子的人都是她接的生。
張桂清是出賣毛澤覃的“叛徒”?
張桂清的命運(yùn)再次逆轉(zhuǎn)。
“四類分子”邱錘子向大隊(duì)書記揭發(fā):張桂清是個(gè)假老同志,偉大導(dǎo)師、偉大統(tǒng)帥、偉大……我們最最最最敬愛(ài)的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嫡親老弟毛澤覃就是她出賣的!
石破天驚,如同爆炸了一顆原子彈,整座紅林山震動(dòng)了,整個(gè)安治公社乃至整個(gè)瑞金縣震驚了。過(guò)去,人們只風(fēng)聞毛澤覃犧牲在瑞金,卻不知道他具體犧牲在哪里,更不知道他究竟是怎樣犧牲的。
這句話,像被點(diǎn)燃的山火遇著了風(fēng),火借風(fēng)勢(shì),風(fēng)助火力,迅速越過(guò)安治公社,在整個(gè)瑞金縣蔓延開(kāi)來(lái)。像蚯蚓一樣,她被人從地底下掘出來(lái)了。
主席的胞弟毛澤覃被叛徒出賣致死,叛徒的蹤跡已經(jīng)暴露,可能是一個(gè)女人……
身邊一個(gè)簡(jiǎn)單的女人,立即成了一個(gè)復(fù)雜的謎團(tuán)。這重大消息如重磅炸彈,炸彈的碎屑、碎片紛紛揚(yáng)揚(yáng),散落處無(wú)不高度緊張,無(wú)不非常重視。不久,就成立了由省、地、縣、公社、大隊(duì)五級(jí)革命委員會(huì)抽調(diào)精干人員組成全稱為“瑞金縣毛澤覃同志犧牲情況專案調(diào)查組”,后來(lái),也簡(jiǎn)稱為“縣毛澤覃烈士專案組”。細(xì)致縝密的調(diào)查緊鑼密鼓地開(kāi)始了。
懷疑一切,打倒一切;不能懷疑一切、打倒一切。都是那時(shí)的口號(hào)與行動(dòng)。
瑞金縣各級(jí)革命組織,紛紛對(duì)“四類分子”做出革命的宣判,經(jīng)常批斗來(lái)批斗去真麻煩,他們決定從肉體上消滅他們,讓這個(gè)世界純潔。
選來(lái)選去,決定處以極刑的3人是:張桂清、邱錘子、邱青山。
1968年9月25日上午,是張桂清、邱青山、邱錘子被處以死刑的日子。
在一片驚愕的目光中,吆喝聲、狗吠聲漸次傳來(lái),一群男男女女武裝基干民兵成散兵狀,將三名死刑犯以及五六名陪斬者五花大綁押赴刑場(chǎng)。
作為一個(gè)老資格的“叛徒”,張桂清走在隊(duì)伍最前面。“時(shí)時(shí)可死,步步求生。”數(shù)十年前毛澤覃的話似乎在耳邊響起……
對(duì)于死,張桂清一點(diǎn)也不害怕,她知道,無(wú)論怎樣,反正結(jié)果都一樣。
在赴死的路上被推搡前行,張桂清想站穩(wěn)一點(diǎn),她的雙腿膝蓋后部遭到猛烈撞擊,“撲通”一聲,重重地跌跪在地上。
“撲通”“撲通”——
接連兩聲,另兩個(gè)死刑犯也先后跪下,三個(gè)人一字兒排開(kāi)跪在地上。張桂清跪在中間,左邊跪著邱青山,右邊跪著邱錘子。
突然,整座山場(chǎng)寂靜了,寂靜得沒(méi)有一絲一毫聲音。張桂清的頭被按下垂,臉龐幾乎貼著地面,她看見(jiàn),離臉面很近的地面上,幾只螞蟻在匆匆爬行,就像幾個(gè)士兵在匆匆行走……
“澤覃,保佑我。”張桂清像在對(duì)螞蟻說(shuō)話,“我來(lái)和你們一起做伴了。”
“砰——砰——”兩聲槍響,滾燙滾燙的鮮濺了張桂清一身。
她突然感到奇怪,自己應(yīng)該是已經(jīng)死了,怎么還會(huì)有知覺(jué)呢?接著,她完全清醒了,知道今天是來(lái)陪斬,明天才是自己的死期。
張桂清覺(jué)得是毛澤覃在冥冥之中顯靈,保佑了自己。
這樣,張桂清又多活了一天,一天就是一世。
紅林大隊(duì)的殺人行動(dòng),是從張桂清等三人赴刑場(chǎng)開(kāi)始,也是從張桂清這里被制止。
“就是要 ‘立即執(zhí)行’我的那天,”幸存者張桂清說(shuō),“中央來(lái)了 ‘公示’傳達(dá)到村里,說(shuō)是不可以殺人了,誰(shuí)還要?dú)⑷司鸵肪繗⑷苏叩呢?zé)任。”
中央的“公示”下來(lái)后,大規(guī)模亂殺人的行為暫時(shí)被制止了。
陪斬那一夜,張桂清身上沾著許多別人的血污,昏昏沉沉被架回牛棚,第二天被立即釋放。
回到家中的張桂清終于透了一口大氣,在她看來(lái),冥冥之中,是毛澤覃在關(guān)鍵時(shí)刻保佑著自己。
出賣毛澤覃的“叛徒”奇跡般解脫
專案組的足跡遍及湖南三湘四水、城鄉(xiāng)村野、工廠街道,調(diào)查工作十分辛苦,進(jìn)展也十分喜人。
結(jié)合毛澤覃戰(zhàn)友藍(lán)盎子的回憶、紅軍戰(zhàn)士何富慶的敘述以及湯濟(jì)南一干人的回憶,已經(jīng)形成了一個(gè)完整的黃埂窩紙寮戰(zhàn)斗情節(jié)鏈:毛澤覃確實(shí)是在黃埂窩紙寮戰(zhàn)斗中犧牲,整個(gè)戰(zhàn)斗就是一個(gè)時(shí)間短促的遭遇戰(zhàn),可能根本就不存在叛徒。
為什么一定要有叛徒呢?這也許原本就是一場(chǎng)沒(méi)有叛徒的戰(zhàn)斗。
莫道讒言如浪深,莫言逐客似沙沉。千淘萬(wàn)漉雖辛苦,吹盡狂沙始到金。張桂清是清白的,毛澤覃的犧牲與她并無(wú)干系。
幾多波瀾,幾經(jīng)曲折,一場(chǎng)圍繞著張桂清是叛徒的漫長(zhǎng)調(diào)查,從起點(diǎn)到終點(diǎn),轉(zhuǎn)了一個(gè)360度的大圈又回到起點(diǎn)。調(diào)查的事傳播得迅速而又廣泛。由于民情風(fēng)俗的禁忌,盡管周圍的人大都知道調(diào)查一事,唯獨(dú)被調(diào)查人張桂清,卻從開(kāi)始到結(jié)束都不知情。風(fēng)風(fēng)雨雨,峰回路轉(zhuǎn),全部屏蔽。
這樣最好。
毛澤覃的墳塋竟是一座空墳?
晨星淡淡,張桂清的心有點(diǎn)莫名的忐忑。
張桂清早早地守候在晨風(fēng)里。聽(tīng)說(shuō),要新建毛澤覃的陵墓,動(dòng)工那天,她有些魂不守舍。其實(shí),不需要來(lái)那么早,來(lái)那么早也沒(méi)用,但她睡不著,還是來(lái)了。來(lái)看究竟的人很多,村民、村領(lǐng)導(dǎo)、鄉(xiāng)領(lǐng)導(dǎo),對(duì)所有的人,這都是個(gè)謎。
市里有關(guān)部門的領(lǐng)導(dǎo)陸續(xù)來(lái)了,正式的儀式開(kāi)始了。
眾人的眼睛都盯著那片青冢土堆,泥土里,不知道會(huì)有什么。
飛舞的鋤頭在掀開(kāi)紅土,也在掀動(dòng)歷史。
張桂清守望了77年的那堆紅土被掘開(kāi)了,還冒著一絲絲熱氣!
張桂清情不自禁,雙腳一下往前挪動(dòng)了幾步,她要急于看清,那墳?zāi)估锏降茁癫刂鯓拥拿孛埽】蓮埞鹎蹇匆?jiàn)的,卻是一片紅土!她的心砰砰直跳,再定睛一看,眼前的確是一片實(shí)實(shí)在在純凈的紅土。“挖呀,再往下面挖呀!”揮動(dòng)的鋤頭終于停止。她雙膝一軟跪倒在那掬松軟的紅土上,不甘心地用雙手挖掘起來(lái)。可是,紅土里面還是紅土,紅土的深處仍然是紅土,除了血一般的紅土,什么也沒(méi)有!
張桂清的頭腦里一片空白,十指仍深深地?fù)冈诩t土地中。淚水汩汩流淌,灑落在這片不知吸吮過(guò)自己多少淚水的紅土上。莫非,自己忠貞不渝廝守了77年的毛澤覃的墓地,就是一片紅土——一座空穴!?
一片紅土——一座空穴,意味著什么?
77個(gè)春秋,耗在這塊土地上。空穴是否是空守,不空穴就是不空守?值得,還是不值得?
三枚未燃盡的檀香,徐徐冒著青煙。張桂清望著紅土,淚流滿面地喃喃自語(yǔ):怎么回事,我曉得你一直都在這里躺著,一直都在保佑我。可是,你難道不是躺在這里嗎?
“噼噼啪啪——”遷墳的儀式照常進(jìn)行,紛飛的鞭炮紙屑在天空飛舞,漸漸歸于平靜。
紛飛的思緒停不下來(lái),一遍一遍,張桂清在梳理對(duì)這青冢紅土堆的記憶。當(dāng)初,說(shuō)的是在這一大片竹林里,這一大片竹林是怎么慢慢地縮小,縮成了這一小掬土堆,又變成的空穴呢……她的心被掏空了。
像被雷擊了一般,突然間,張桂清老年癡呆的癥狀就明顯起來(lái),記憶鏈的斷裂使人迷茫異常,她有時(shí)連自己的兒子都不認(rèn)識(shí),有時(shí)連自己是誰(shuí)都不知道。而另一些記憶鏈則無(wú)比頑固地連接著,她盲目地走著,繞來(lái)繞去,又會(huì)走到那片墳地。她聽(tīng)不見(jiàn)別人說(shuō)話,也不與人說(shuō)話,但她會(huì)自言自語(yǔ):毛澤覃、賀怡……完全沉浸于一個(gè)自我的世界。
張桂清深深意識(shí)到,他的靈魂已經(jīng)溶入這片大山、這片紅林,別的什么都不重要。一生一世,她的心不變,情亦不變。
山野之風(fēng),熱烘烘地拂過(guò)她的心田。張桂清鎮(zhèn)靜不下來(lái),卻似窄小幽深的箬溪水般澄澈、坦然、無(wú)奈,一個(gè)百歲女人的坦然和無(wú)奈。
青草綠了又黃,黃了又綠。
度過(guò)了戰(zhàn)爭(zhēng),度過(guò)了“文革”,度過(guò)了艱辛,度過(guò)了平淡,度過(guò)了5次婚姻,度過(guò)了102個(gè)春秋……她誠(chéng)實(shí)地活著。這個(gè)世界,不能只有誠(chéng)實(shí),除了誠(chéng)實(shí)之外,還得有點(diǎn)防范,否則你就無(wú)法也無(wú)權(quán)誠(chéng)實(shí)。
年屆103,張桂清生活圈子原本很小,如今更加縮小,自己的生命除了與活在周邊的幾個(gè)人有關(guān)、與死在周邊的幾個(gè)人有關(guān)之外,與所有別的人都無(wú)關(guān)。張桂清已經(jīng)很蒼老而恬淡了,布滿了折皺與黑斑的臉上,沒(méi)有任何表情,一只眼睛失明,另一只曾經(jīng)黑亮黑亮的眸子,摻雜著幾重重翳蒙。才幾月不見(jiàn),她的反應(yīng)也變得更加遲鈍,更加深地進(jìn)入了老年癡呆狀態(tài),她的記憶一片模糊,或者說(shuō)是更加專注。但是,她眼睛里面仍有一種憂郁,一種意外的平靜,那是看透了人生才有的憂郁和平靜。
山很深,林很密,冷風(fēng)熱風(fēng)在山林間滑翔,在一個(gè)百歲女人的指縫間悄悄地走過(guò),不知來(lái)自哪里去向何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