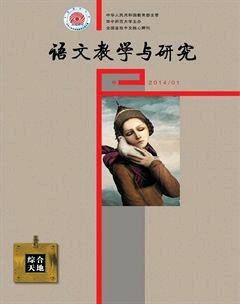也談語文課的玩
2012年2月8日《中國青年報》的專題《語文課可以變得很好玩》一文,報道了蘇州某中學史金霞老師好玩又高效的語文教學,不久,筆者又讀到了針對這一報道所寫的兩篇不同意見的文章:《語文課不可以這樣玩》與《再談語文課不可以這樣玩》,思慮良久,覺得語文課還是貴在一個“玩”。
有人提出“泛語文課”與“非語文課”兩個概念,認為“泛語文課”注重文本內容和精神,忽視了語言表達形式;而“非語文課”已經不是語文課,走出了語文,走向了“廣闊的天地”。這樣的課不像語文課,使我們的語言表達能力越來越弱,“誤盡天下蒼生”。
我們的語言表達能力越來越弱,是不是由于語文課未能集中于語言表達形式,是不是因為當前的“泛語文課”或“非語文課”越來越多,值得商榷。漢代司馬遷沒上過多少語言專業課,可是一部《史記》氣貫長虹;唐代李白、杜甫、白居易等一批詩人都沒能上過多少“專業的語文課”,他們的詩句卻像一杯杯醇厚的美酒,千古芳香;更近一點看,魯迅、郭沫若兩位名家在大學里種的都是醫學的地,但他們的田里卻長出了文學的豐碩美果。
“汝果欲學詩,功夫在詩外”,莫言小時候輟學在家放牛,一人孤獨地看天上白云;童年時代饑餓難耐,偷吃生產隊一個蘿卜差點被開會批斗;當別人讀經典的時候,他“聽閱”過成千上萬家鄉傳奇式的民間故事;史鐵生年輕時下肢癱瘓,接受上千次穿刺治療;海倫·凱勒幼小雙目失明,一生渴望三天光明。艱難的經歷使他們成為語言表達的巨人。現在的孩子人生經歷越來越貧乏,既不是為了人生而學語文,也不是為了藝術而學語文;是為了考試,中小學的老師為了各種各樣的考試,不得不戴著鐐銬跳舞;學生們為了多考一點分,不得不戴著鐐銬學跳。在這種狀況下,教者上再多的“真語文課”,學生的語言表達能力也難以真正提高。
錢夢龍先生說過,語文學的終極目標是人學,是教育人培養人的一門學問;優秀語文老師熊芳芳提出了“生命語文”的觀點,他們都追求把語文課上到學生的內心深處,讓語文課真正觸動學生的靈魂,使孩子們從心靈深處熱愛祖國的語言文化,從而喚起他們學習語文的興趣和熱情。對語文充滿興趣和熱情的學生怎能學不好語文!正如《語文課可以變得很好玩》一文中所說:“在史金霞所負責的班級里,學生們的語文成績并沒有因為語文講課的‘不拘一格而受到拖累,因為‘好玩愛上語文課的學生們常常會拿到全校的最高分,而班級高考平均分也是第一名。”如果你是史金霞老師的學生或學生家長,你喜不喜歡這樣的老師,答案當然是十分肯定的。要知道當今有許多課雖教者費盡心血,或“聲光電”現代化手段樣樣皆俱,或分組討論互相質疑熱熱鬧鬧,可學生就是既不感到好玩也考不出高分,與史老師的課相比,究竟誰在“誤盡天下蒼生”,答案是不言自明的。
有人認為史老師班上學生語文成績很好,是因為他善于讓學生課外閱讀。既然如此,那么所有的語文老師都像史老師那樣給學生列閱讀書目,督促他們讀書,引導他們寫隨筆,寫感想。學生的語文成績是不是就會大幅提高呢?現實是很多語文教者喊破了嗓子,教導學生讀名著、“吃大餐”,可學生往往連教科書上的自讀課文都懶得一讀。由此看來,這位史老師之所以能“得益于課外”,正因為他“得法于課內”。
如果一位教者學識淺薄,對語文教學沒有刻苦鉆研的上進之心,僅僅為迎合學生“好玩”而故弄玄虛,那么他能哄騙學生多長時間,他所教學生語文成績能有多好?教育的行家們是心知肚明的,孩子的心明鏡似的,你糊弄一兩節課尚可,時間久了,學生便會看透你的本質,那時你的課就不是越來越“好玩”,而是越來越上不下去。
“玩”,雖一字但意無窮,葉圣陶先生談及兒童的成長教育時,強調孩子從小要學會“玩”,著名導演張藝謀在談《紅高粱》獲獎感言時的第一句話就是“玩玩”。一位教者要能“玩”好課,那他首先必須有廣博的學識、強烈的事業心、勇于創新的精神。其次,他必須以常人雙倍的精力備課,備教材,備學生,備社會人生……當今能在這種狀態下“玩”課的人不是太多而是太少,教者把各自的課上得“太真”、“太專”。正如楊振寧教授分析中國的自然科學離“諾獎”越來越遠問題時所說:“中國的高校太專業化了,扼殺了學生創新能力。”大學這樣,中小學莫不如此。語文與史學、哲學、美學以及其他一切學科形成的是一個互相聯系、互為因果的知識能力系統,如果教者能在研究這一系統背景下展開語文教學,這樣的“玩”真是難能可貴。
陸文兵,江蘇金湖中等專業學校語文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