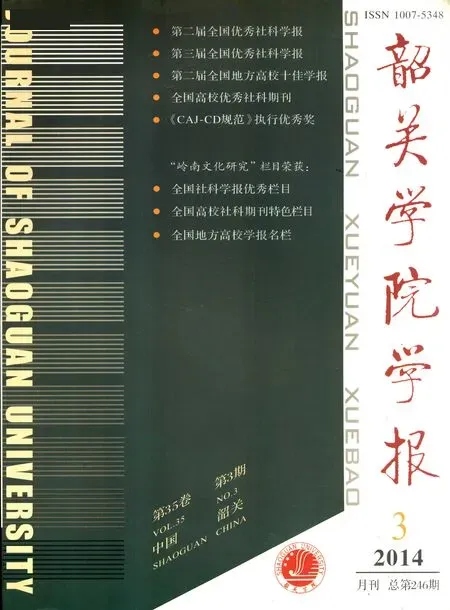古漢語處置句同“以”的關系及基本結構格局
鄧昌榮
古漢語處置句同“以”的關系及基本結構格局
鄧昌榮
(韶關學院文學院,廣東韶關512005)
古漢語處置句與以字式的關系甚密,處置類和致使類兩類處置句都與以字式存在繁衍、類推關系。其中處置類與工具方式類以字式有密切聯系;致使類則和致使義以字式功能相似。它們之間的這種聯系,是由漢語特有的兩種基本結構格局決定的。
以字式;處置句;致使;繁衍類推;自動與使動
處置式是指施事對“將、把”等介詞后的名物處置以某種動作的句式。處置式的產生和演變是“漢語語法走向完善的標志之一”[1]415。因此處置式一直是漢語學界研究的熱門話題。以往對處置式的研究,主要包括兩大內容:
一是從歷時角度,研究處置式的產生及其演變過程。對于處置式的產生,學界大體同意王力先生的看法,認為“大約在第七世紀到第八世紀之間”[1]411。對其演變過程,則看法不一。其中影響較大的主要有以下兩類:
一類是單源說。持此看法者,有的認為純粹動詞“將/把”用在“Vj/VB+O1+V2+O2”①為表述方便,文中一些概念分別用符號表示,動詞“將”:Vj;動詞“把”:VB;動詞/動詞短語:V/Vp;名詞/名詞短語:N/Np;賓語:O;補語:C;加括號的項,如“(+C)”,表示其中的成分可出現也可不出現。這樣的連動式中,逐漸虛化為工具語,又從工具語繼續語法化而導致處置式產生。有的認為“以”字式是處置式的更早期形式,而后來的將字句、把字句,則不一定是從動詞“將”或“把”構成的連動式演變而來,“只不過是隨著語言的不斷發展,介詞的替換而已”[2]。日本漢學家太田辰夫先生也認為中古處置式的“把/將”字式大多能用“以”替換[3]。
另一類是多源說。最有影響的是梅祖麟先生的研究。梅先生將中古處置式分為甲、乙、丙三種類型,并分別考證其不同來源。甲型為雙賓語結構,又可細分為三小類:“處置給…/處置作…/處置到…”,其演變途徑雖不盡相同,但都與上古“以”字相關。乙型則與受事主語句關系密切,“去掉了‘把’或‘將’,便是受事主語句;反之,受事主語句加上‘把’字或‘將’字,就形成處置式。”丙型是旁支,不是主流,大致是通過省略“VB+O1+V+O2”中的“O2”而來[4]。這一研究盡管還有可商榷之處,然而匠心獨到。此后,許多學者都在此基礎上致力于探討處置式的不同來源,多源研究基本取代了單源研究。
二是從共時角度,研究處置式的類型。在這方面,多數研究者仍以梅先生的研究為基點,或探討處置式的新類型及其形成機制,或探討更科學的分類標準。看法不少,而分歧不大。
前賢時學對處置式的研究可謂碩果累累。筆者只是沿著前人開辟的道路,擬就古漢語處置句②拙文不言處置式,而說處置句,是因為一般認為,由虛詞將/把等構成的有處置作用的句式才是典型的處置式,而“以”字類不屬于此列。因此姑且稱之為處置句。同上古“以”字的關系再作一個探討。
一、處置句同“以”的關系
“以”是古漢語用法較多且較靈活的虛詞,常用作介詞、連詞;即使作實詞,也有幾種意義和詞性。這些意義有的是詞匯義,有的是結構義。正是這種靈活多樣的語義和用法,決定了它與其他詞構成“以”字結構(下簡稱“以字式”)后,也可表示下面多種語義關系:
A組:(主語)+以+(N1)+V+(N2)
(1)君王不以鞭棰使之。①本文使用的材料除注明的以外,皆錄自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韋昭注《國語·卷十九吳語》。
(2)莫如此以環瑱通相問也。
(3)以人為鏡,見成敗;以水為鏡,見形而已。
(4)將以伐齊。
(5)越人分為二師,將以夾攻我師。
(6)孤將以舉大事。
(7)吾何面目以見員也?(以何面目)
(8)天若不知有辠,則何以使下國勝。(以何)
(9)春秋皮幣、玉帛、子女以賓服焉。(以春秋皮幣、玉帛、子女)
這組以字式,“以+(N1)”是動作行為的方式或工具;“V+(N2)”是動作行為的目的或結果。“以”相當于“用、拿或把”。(1)-(6)例的“以”,尚未完全虛化,與動詞構成連動式;(4)-(6)例省略了“N1”。后三例的“N1”置于“以”前,意義顯然已趨虛化。盡管如此,這組以字式與其后Vp構成的語義關系則相同,都表示動作方式與所及目的之間的聯系。
B組:V1+以+V2+N
(10)求以報吳。
(11)行賂以亂軍。
這組以字式,“以”通常被訓為連詞“而”,用以連接有先后順序的兩種行為,后一行為往往是前一行為導致的目的或結果。其實,這個“以”與A組省略賓語或賓語前置的“以”用法相類。例(10)為“求(之)以報吳”;例(11)為“以行賂亂軍”。
C組:以+使動詞+施事
(12)三歲于沮、汾以服吳、越。(以使吳、越歸服)
(13)三軍皆嘩扣以振旅,其聲動天地。(以使軍威大振)
(14)用命孤禮佐周公,以見我一二兄弟之國,以休君憂。(以使我們能與同姓諸侯國相見,使國君消除憂患。)
(15)今齊侯任不鑒于楚,又不承共王命,以遠我一二兄弟之國。(導致我們同姓諸侯國關系疏遠。)
這組以字式,“以”后是一個使動詞,使動詞后的“Np”是施事或當事,“使動詞+Np”則是被某一條件致使的結果。于是,“以”便在這種結構模式中被賦予了“致使”義。若刪去“以”,動詞雖仍有使動義,但只能一般地表示行為的連續;加上“以”,前動作致使后行為產生某種結果的趨向就被凸現出來了。
甚至在施事或當事隱去的情況下,“以”字仍能在隱含使動意義的結構中被賦予“致使”義。例如:
D組:
(16)大夫種勇而善謀,將還玩吳國于股掌之上,以得其志。
(17)越大夫種乃倡謀曰:“吾謂吳王將遂涉吾地,今罷師而不戒以忘我,我不可以怠也。……”
(18)闕為石郭,陂漢,以象帝舜
(19)譬如農夫作耦,以刈殺四方之蓬蒿,以立名于荊。
(20)今會日薄矣,恐事之不集,以為諸侯笑。
(21)使淫樂于諸夏之國,以自傷也。
(22)越人分為二師,將以夾攻我師。
(23)乃不待旦,亦中分其師,將以御越。
(24)寡人其達王于甬句東,夫婦三百,唯王所安,以沒王年。
(25)王總其百執事,以奉其社稷之祭。
這類以字式的“以”后,大都留有一個使動作發生的施事遺跡。如:
大夫種勇而善謀,將還玩吳國于股掌之上,以(施事)得其志。
“以(施事)得其志”就是“以(之)得其志”。這類結構中的“以”字,都含“致使”義,可用“使、讓”替換;Vp前隱含的施事,可以在句中其他位置出現,也可以不出現。因此,這組句子一般都可以進入以下變換矩陣,而基本意義不變:
以得其志→以(之)得其志→使(之)得其志
以忘我→以(之)忘我→使(之)忘我
以怠→以(之)怠→使(之)懈怠
以自傷也→以(之)自傷→使(之)自傷
以夾攻我師→以(之)夾攻我師→使(之)夾攻我師
以沒王年→以(王)沒年→使(王)沒年
以御越→以(之)御越→使(之)御越
以為諸侯笑→以(之)為諸侯笑→使(之)為諸侯笑
以立名于荊→以(之)立名于荊→使(之)立名于荊
以象帝舜→以(所筑之臺)象帝舜
→使(所筑之臺)像帝舜陵墓
以奉其社稷之祭→以(之)奉其社稷之祭
→使(之)奉其社稷之祭
值得注意的是21例,“使”、“以”分別用于上下句,“以”的致使義比其他各例更明顯。此外,在這類以字句中隱含的“Np”大都是兼語,所以,若刪去“以”,其語義關系大致不變:“得其志”猶“其得志”;“忘我”即“(吳)忘我”;“象帝舜”猶“(所筑之臺)像帝舜陵墓”;“立名于荊”即“(吳)立名于荊”。當然,缺少“以”,這種結構自然也就沒有了強調“前一動作致使產生后一行為結果”的意味。這說明不僅“以”字在這類結構模式中獲得了“致使”義,而且又將致使義反作用于結構。在筆者所收集的語料中,甚至還有直接表致使義的“以”:
(26)傳曰:“王縊,申亥以其二女殉而葬之。”
此“以”,可用“使、讓”替換;且不可刪去,若刪去則不成句(*申亥其二女殉而葬之)。這類例句,雖鮮有,但至少給人們提供了詞義演變的一些信息:詞在結構中被賦予的意義,久而久之,完全有可能被轉為詞匯義。這并非孤例,在其他古文獻中亦有類似用例:
(27)以能問于不能,以多問于寡。(論語·泰伯)[5]261
(28)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孟子·梁惠王上)[5]441
這兩例與(26)例相似,“以”可直接被“使/讓”替換,是使動句。若刪去“以”,則是自動句。
以上四組以字式,不是相互對立的,而是互為條件、逐步推演的。A、B兩組可為一類,具有使用某一工具或方式導致某一目標或結果實現的作用,這是以字式最常見的用法。可名之為“方式類以字式”。而某一行為使某一目標或結果得以實現,又總是離不開主、客觀因素的致使,于是,用在這類結構中的“以”字便常與使動詞結合,并因此而獲得了結構賦予的“致使義”,由此逐漸繁衍出了C組及D組以字式。可稱之為“使動類以字式”。
這兩大類以字式,又分別與處置類和致使類兩類處置句有密切聯系。請看:
處置類處置句:
(29)昔天以越賜吳,而王弗受。(將越賜給吳。)
(30)勾踐愿諸大夫言之。皆以情吿,無阿孤。(把實情相告。)
(31)今王非越是圖,而齊、魯以為憂。(把齊、魯兩國作為憂患。)
(32)以其私卒君子六千人為中軍。(把親兵君子六千人組編為中軍)
這組處置句顯然是從處置義以字句推演而來。因為方式或工具常常是被處置的對象,因此“以”字也就常與具有處置作用的動詞(如例句中的賜、告、為等)結合,“以”便獲得了介詞“把”的固定義,句子就具有了明顯的處置功能。再以下列圖示明之:

盡管例句中的方式類以字式尚不能跟處置類以字式構成一一相對的格局,但是它們隱含意義的密切聯系則是不容忽視的。
致使義處置句:
(33)吳為不道,求殘吾社稷宗廟,以(之)為平原,不使血食。
(34)有父母耆老而無昆弟者以吿。
(35)以(之)焚其北郛焉而過之
例(33)-(35)是一組致使義處置式。既然“以”在使動類以字式中能獲得致使義,那么,從理論上說,它也同樣可以在致使義處置句中獲得致使功能,“以”也可以分別用“把”和“使/讓”來變換。請看下列變換矩陣:
以(之)為平原
→使/讓(吾社稷宗廟)夷為平地
→把(吾社稷宗廟)夷為平地
有父母耆老而無昆弟者以吿
→使/讓有父母耆老而無昆弟者來告孤
→把有父母耆老而無昆弟者告(孤)
以焚其北郛焉……
→使/讓其北郛焚燒后……
→把其北郛焚燒后……
顯然,上述變換矩陣是可以成立的。致使義處置句與使動類以字式一樣,“以”后都有一個或隱或顯的兼語,刪去“以”其基本意義都大致不變。這說明使動類以字式跟致使義處置句存在相互類推的關系。而類推能力正是人類的基本認知能力之一,“人們正是依靠這些基于體驗之上形成的主要認知能力和認知方式,逐步形成了概念結構,并在此基礎上創造出各種語法構造。”[6]
事實上,古今不少學者對“以”字這種由類推導致的致使功能已有一定認識。例如:
《戰國策·秦策一》:“向欲以齊事王,使攻宋也。”高誘注:“以,猶使也。”
《左傳·文公三年》:“莊叔以公降拜。”
《孟子·公孫丑上》:“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5]445
楊伯峻先生言:“‘以’有‘助使’義。意謂管仲助使其君(桓公)稱霸天下,晏子助使其君(景公)名揚諸侯。”[5]445
若“以”前有助動詞,“以”的這種助使功能會更突出,如:《孟子·梁惠王下》:“然則小固不可以敵大。”馬建中說:“‘小固不可以敵大’者,猶云‘小故不可以之敵大’也。”[7]“以之敵大”就是使之敵大。
處置句何以能跟以字式產生這樣的聯系呢?筆者認為,這是由漢語句式的基本結構格局決定的。
二、處置句的基本結構格局
徐通鏘先生認為:“根據一種語言有定性范疇的特點,我們認為漢語語義句法的基本句式是自動和使動。”[8]徐先生曾轉引過呂叔湘先生對漢語句式兩種結構格局的描寫:

呂先生雖未明確指出它們具體是什么格局,卻以此例肯定了漢語句式存在兩種不同格局。徐先生明確指出這就是漢語的兩種基本句式:a為自動句,b是使動句。
徐先生指出:“從語義上說,使動是漢語語義句法的一種重要句式,它和自動句的語義差異主要是:自動句對受事產生的影響是明的,處于動字前的位置,如:‘中國隊大敗南朝鮮隊’的‘中國隊’,……使動句的力量是‘暗’的,句中沒有出現相關的結構成分,如‘南朝鮮隊(大)敗了’,不是南朝鮮隊自己愿意‘敗’,而是有一種力量使它‘敗’,只是這種力量沒有‘明’說出來,在這種情況下,有定性的受事移至句首,形成所謂受事主語句。”[8]這段話至少讓我們得到了以下兩點啟示:
第一,使動句與自動句是漢語語義句法中相互對立的兩種基本句式。自動句的主語是施事;使動句則是受事,因為使動句的顯性主語其實是受制于隱性施事的。
人們之所以對自動句習以為常,卻忽略了與之對立的諸如“中國隊大敗南朝鮮隊(中國隊使南朝鮮隊大敗=南朝鮮隊大敗)”之類的使動句,是因為使動句與自動句的對立在現代漢語中已成遺跡,或只有少量存在(如豐富業余生活之類),人們已經不大去關注處于“暗”處的結構成分。然而,在古漢語中自動與使動的對立則是成系統的。例如:
(36)宋小而齊大,夫救小宋而惡大齊,此人之所以憂也,而荊王悅,必以堅我也,我堅而齊敝,荊之所以利也。(韓非子·說林上)
(37)鄭皇戌使如晉師,曰:“……子擊之,鄭師為承,楚師必敗。”彘子曰:“敗楚服鄭,于此在矣,必許之。”(左傳·宣公十二年)
(38)群公子皆鄙,唯二姬之子在降。
(39)大國無厭,鄙我猶憾。(左傳·成公十八年)動詞“救”、“惡”、“敗”,形容詞“堅”,名詞“鄙”,分別用在自動句和使動句中。“救小宋”、“我堅”、“敗楚”、“群公子皆鄙”是主動句,“惡大齊”、“堅我”、“楚師必敗”、“鄙我”是使動句。漢語的名、動、形容詞大多能形成這樣的對立。而且非唯名、動、形構成的句式如此,其他詞構成的句式亦如此。無論句型怎樣千變萬化,而支配這種變化的基本結構格局卻不會輕易改變。上文討論過的以字式和處置句在語義上都存在這兩種對立。如以字式的A、B兩組像“君王不以鞭棰使之”、“行賂以亂軍”之類的句子都是自動句;C、D兩組像“三軍皆嘩扣以振旅”、“闕為石郭,陂漢,以象帝舜”之類的句子都是使動句。處置句同樣存在這種語義對立。如33例:“吳為不道,求殘吾社稷宗廟,以(之)為平原,不使血食。”就是這兩種基本結構的語義對立。
中古、近古的將/把字式處置句也有這種對立。例如:
(40)心將潭底測,手把波紋裹。(皮日休詩)[1]411
(41)莫將天女與沙門,休把眷屬惱人來。(變文)[1]411
(42)偏又把鳳丫頭病了。(紅樓夢)[1]414
(43)將那一艙活魚都走了。(水滸傳)[1]414
例(40)是主動句,(41)是主動與使動語義的對立,(42)和(43)都是使動句。這種現象正說明了“語言現象的易變性和結構格局的穩固性”[8]。
由此可見,盡管漢語句式在發展演變,但始終離不開潛在的兩種基本格局的影響。上古“以”字在處置句中能獲得致使義,主要就是由漢語這種特有的基本結構所賦予。久而久之,這種結構義也有轉化為詞匯義的可能。
第二,從表層結構來看,自動和使動同形,但從深層語義結構來看,它們卻同形異構。“有很多語法規則在歷史上卻是從這種使動結構中脫胎而來的。”[8]
處置句就是如此脫胎而來。當以字后的“Np1”是受事時,“以+(Np1)+V+Np2”便是自動結構,如:“昔天以越賜吳”。由于“以”的提賓強調作用,它的語義主要指向受事“越”。“昔天以越賜吳”就是“昔天賜越予吳”,“以越賜吳”顯然是自動結構的一種變異。而當以字后的“Np1”是兼語時,“以+(Np1)+V+Np2”則是使動結構,如:“以(之)為平原”,就是“把/使(吾社稷宗廟)夷為平地”。這是外力“吳”致使“NP1”變成“NP2”,動詞“為”的語義主要指向“NP2”。所以,“以(之)為平原”,是使動結構的一種變異。
一般而言,以字式處置類大多可變換成自動結構,而致使類則大多能與使動結構變換。這正說明不管漢語句式怎樣千變萬化,而其基本結構格局則是基本穩固的。
[1]王力.漢語史稿[M].北京:中華書局,2003.
[2]陳初生.早期處置式略論[J].中國語文,1983(3):201-205.
[3]太田辰夫.中國語歷史文法[M].蔣紹愚,徐昌華,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241-242.
[4]梅祖麟.唐宋處置式的來源[J].中國語文,1990(3):190-207.
[5]楊伯峻.古漢語虛詞[M].北京:中華書局,2000.
[6]王寅.認知語法概論[M].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6:11.
[7]宋紹年.馬氏文通研究[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226.
[8]徐通鏘.自動和使動——漢語語義句法的兩種基本句式及其歷史演變[J].世界漢語教學,1998(1):11-65.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spositional Sentences of Ancient Chinese Language and“Yi”Along with Basic Structural Analysis
DENG Chang-rong
(College of Literature,Shaoguan University,Shaoguan 512005,Guangdong,China)
By demonstrat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ispositional sentences of Ancient Chinese Language and the“Yi”structure,this essay shows that the two kinds of dispositional sentences-dispositional and causativeboth have analogy logic with“Yi”structure.One kind is dispositional verb which has close connection with the“Yi”which is used to show an disposition;the other is causative verb which has similar function with“Yi”which is used to show a cause.This kind of relationship is caused by the two basic structures of Chinese language.
“Yi”structure;dispositional sentences;bring about;the autonomous and the causative
H109.2
A
1007-5348(2014)03-0079-05
(責任編輯:吳有定)
2013-12-28
鄧昌榮(1954-),女,湖南衡山人,韶關學院文學院副教授,主要從事漢語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