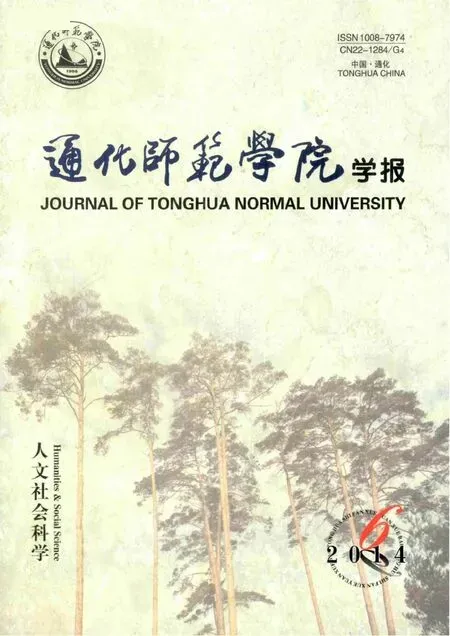“底層文學”的創作誤區
王學勝,袁 華
(通化師范學院 文學院,吉林 通化 134002)
“底層文學”的創作誤區
王學勝,袁 華
(通化師范學院 文學院,吉林 通化 134002)
“底層文學”的作品在學術界的質疑聲中大量涌現,仔細解讀這些作品之后,我們不難發現“底層文學”的作家們在創作中走入了誤區。諸如作品中底層生存環境與現實的偏離、情節的“失真”和人物的“空殼化”等。
底層文學;誤區;偏離;失真;空殼化
如何最大化地接近底層,應該是作家在創作中努力實現的目標。學者安敏成就非常推崇魯迅關于寫實主義的觀點,對于魯迅所提出的:“多講別人,是寫實主義”的觀點,安敏成認為,魯迅的觀點是樸素的和意義深遠的。通過它,魯迅完成了社會關系與“寫實主義”的結合,他暗示,文學經驗參與者之間的關系,“我”“你”和“他”或“她”分別構成了小說的作者、讀者和人物,決定了選擇哪種文學模式。如果我們還未洞悉底層的面貌,那個“本真”的底層離我們仍然遙不可及時,我們不得不在“社會關系”中來面對“底層文學”的問題。惟其如此,底層才有意義,底層才能去除空虛的、缺乏厚重的假想與闡釋。我們才會重視底層的復雜性。而現在我們關于底層的表述有簡單化的傾向,這顯然有把底層作“本質主義”定義的原因。細讀“底層文學”的作品,我們發現較為成功的底層生活的書寫來自于精英階層對“底層”的描述:精英與底層之間的巨大差異讓書寫在想象中順利前行。比較而言,精英作家筆下的作品雖然還有很多不盡人意的地方,但底層的自我書寫則問題重重。
無產階級、平民、勞苦大眾這些在過去階級時代頻繁被使用的階級術語,很多時候被替換成 “底層”的“等價物”。今日中國,雖然階級已經不復存在,但階層卻不可避免地凸顯出來。在學者的視野中,作家就被劃分為精英與草根兩個階層,精英作家和草根作家都離不開文學創作的傾向性的問題。雖說精英作家身上擺脫不了階層差別的利益性制約,甚至作家筆下的底層生活根本無法擺脫某種意識形態的附著。可叫人欣慰的是,即便作家的世界觀不那么靠譜,也并不必然帶來其創作中的傾向性,就一定會偏離對底層的悲憫和尊重。馬克思曾就此做過深入的研究,他認為作家的創作有可能突破自身世界觀的局限,這在現實主義作家當中尤為明顯。作家在作品中表現出來的對某種現象或事件的看法,很可能有別于他所一直堅持的觀點或傾向,即世界觀與作品效果二者之間的巨大差異。恩格斯在該問題上的見解與馬克思達成了共識,他在給瑪·哈克奈斯的一封信中明確表達了現實主義可以突破作者思想的局限而展露出來,巴爾扎克就其打破了自身的政治偏見和階級情感,從而走向了現實主義的“最偉大勝利之一”。馬恩的論述從理論上讓我們看到了底層之外仍然存在著書寫真實“底層”的可能。而 “文革”時代的“工農兵創作”則從創作實踐中給我們的“底層文學”創作提供了負面的教材。
一、作品中底層生存環境與現實的偏離
像大家熟悉的那樣,近期進城務工的農民成為了“底層文學”熱衷的書寫對象。數量龐大的書寫農民進城打工的作品中,充分地關注了這些農民的權益保護、社會福利保障以及子女受教育權力等問題。研讀一下這些作品,我們就會發現一個問題:關于城市邊緣人群的書寫大多都夾雜著對城市的道德審判,這種滲入其中的道德主義意識,讓這些“底層文學”作品失去了客觀與公允。大部分的以進城農民工為主人公的小說常常夸大城市居民的自私、冷漠和虛情假意,美化進城務工人員的忠厚、熱心和勤勞儉樸。即便有部分進城農民做出違法之事,也是由于城市道德敗壞對他們的污染同化導致其精神的扭曲。
《太平狗》是2005年陳應松推出的一部中篇小說。小說講述了程大種帶著他的趕山狗太平去武漢打工,最后慘死在黑工廠,而土狗太平雖然瞎了一只眼睛,瘸了一條腿,丟了半條尾巴,最后還是奇跡般地回到了神農架的家中。在這個悲慘的故事中,城市像地獄一樣出現在讀者的面前。即便是程大種的姑媽亦是人情冷漠,罵起程大種來如同潑婦,即便是年節也不讓兒女前來探望。如果說作為個體,這倒是可以讓人接受的,因為每個個體的生活方式和對待親人的態度是存在差異的。城市當中肯定存在激烈的競爭,然而并未達到像小說表述的那樣可怕,到處是弱肉強食,能置人于死地的黑工廠畢竟是很少的。但是小說由于把黑工廠作為主人公程大種生存的環境,城市似乎變成了一個暗無天日的魔窟,似乎進城的農民工只有被騙進高墻內如奴隸般工作,得病之后,由于無人照顧,只能在床上任由老鼠啃噬,直到病死。小說為了情節發展的必要,同時也是要反映出現實中曾經發生過的黑磚窯事件,但是就目前披露的新聞事件而言,那些黑工廠所用的工人大多是智障人群或聾啞等殘疾人。因此小說在進行藝術加工時,雖然突出了程大種所遭受的苦難,但是卻制造了城市隨處是危機的假象。因此整篇小說中,陳應松有把城市妖魔化之嫌。這種妖魔化在其他“底層文學”作品中也比較常見,一般把鄉村看作是凈土,把城市描繪為罪惡之源。
我們必須承認程大種的經歷或許存在真實的可能,但它不具備代表性。為了程大種在小說中恐怖經歷能夠自然地發展,陳應松把城市和鄉村描繪成了惡與善完全對立的兩極。城里人,有錢人永遠都是無情的、卑鄙的、殘忍的。在限定的歷史空間內,作家所處的社會環境及其早年的生活經歷,對某些事物抱有的特殊情感等因素往往會左右他在撰寫作品時的心態,作家的價值取向和審美追求在此得到展現。陳應松曾直接表達過自己討厭富人階層和中產階級,他說他厭惡城市和富人,在電影和小說中,他們經常居住在華麗的住所當中,電影中演員的表演都是不真實的,感情是不真摯的,城市和富人的心態是不正常的,甚至是變態的。而農民和小人物的情感才是真實的,痛苦與幸福都是催人淚下和優美無比的。
意識中鄉村道德與城市道德水火難容,導致大部分作家選擇用極端的形式來進行道德描寫。其中尤鳳偉、孫惠芬和荊永鳴可謂其中代表。他們的作品往往在歌頌鄉村道德淳樸的同時,抨擊了城市道德的失序。這三名作家在表現進城務工農民題材的小說中,尤鳳偉所創作的《泥鰍》堪稱丑化城市道德的代表。小說沒有從進城務工者自身去尋找道德淪喪的原因,而是把責任完全歸咎于城市。《泥鰍》中的蔡毅江,原本只是搬家公司中一名靠力氣吃飯的搬運工,但是一次貨車司機緊急剎車事件讓他的睪丸被撞碎,被工友送到醫院后,因未被及時救治而喪失性功能。于是他帶領一伙人強奸了當事的女醫生,并逼迫女友寇蘭去做小姐,自己則當上了替工商局收稅的蓋縣幫老大。王手的中篇小說《鄉下姑娘李美鳳》中的主人公農村女孩李美鳳為了能夠使用老板家的浴室洗澡,不惜淪為老板泄欲的工具。更可悲的是,李美鳳并不把這種侮辱當作什么了不起的事,反而認為身體白天打工賺錢,晚上閑著也是閑著。最后因為老板兒子在車禍中喪生,老板一家把喪子之痛都發泄到她的身上,誣陷她偷了兒子的錢,讓她進了警察局。類似的境遇,在尤鳳偉的《泥鰍》中也能讀到:純潔、質樸的陶鳳和寇蘭,都計劃著進城后用雙手賺錢養活自己,沒想到最后前者被逼瘋,而后者淪為了出賣肉體的妓女。
綜上所述,對城市進行“丑化”在很多“底層文學”中流行。數量之多,已經不能讓我們相信這僅僅是個別的例外。誠然,城市當中肯定存在卑劣的壞人,而且部分城市居民往往對進城的農民抱有一種天生的歧視,但這絕不是一種普遍的現象。然而,由于許多作家有意無意地泛化處理,透過這些“底層文學”就會構建一種假象:是城市道德的沉淪造成了進城務工人員的苦難和不幸。可是我們又如何解釋同樣發生在鄉村的罪惡呢?把蔡毅江放在農村,我們很難相信報復心如此之強的性格會忍氣吞聲地迎接外界的戕害。由此可見,無論是小說還是小說外,受了傷害便不顧一切去打擊報復的行為,都只能是非典型性的個案。
不可否認,現實生活中確實存在著很多一時無法解決的矛盾,矛盾的激化會把一系列的磨難推給底層民眾的生活,“對底層苦難的表現同時伴隨著仇恨與暴力,”[1]然而這并不能讓我們接受對于城市進行歪曲化的書寫以及為實現此目的不符合情況的“胡思亂想”。或許大多數作者對城市作出偏離現實的“妖魔化”的處理是為了提高文本的閱讀快感,即便是這樣,也不能如此毫無顧忌地刻畫極端,何況這樣做的后果必然會削弱作品的批評力量,而且還以對城市的“惡意中傷”為代價。“包容或正視那些來自邊緣的異議的敘述,并不意味著慫恿、鼓勵某種極端社會情緒和‘革命’的滋生。 ”[2]
二、情節的“失真”
新世紀以來,我國城市化的快速發展和經濟的突飛猛進的同時,我國的貧富差距越來越大,尤其是城市與鄉村、精英階層與底層百姓群體之間的收入差距日益嚴重。農村無保人群、城市失業、半失業以及城市邊緣人等社會底層在艱難的生活境遇中忍受著、掙扎著、盼望著,尤其是中國經濟產業結構調整時期,社會矛盾也相當尖銳。同時,我們國家和政府越來越重視農業、農村和農民的問題,農業大量的剩余勞動力很大程度上解決了城市用工荒的難題,于是每年正月一過,大量的農民涌入城市尋找賺錢的機會。但是,這些農民工普遍受教育程度較低,只能從事城里人不愿意從事的體力勞動或服務性行業,他們只能處于城市的底層。無論是城市的失業、半失業人群,還是這些農民工,他們生活中的苦難和悲劇都成為眾多作家書寫底層的熱點。苦難的極端化書寫就在這樣的背景下得以產生并大行其道。
農民工從人情味濃厚的莊稼院來到鋼筋混凝土鑄造的“城市牢籠”,“他們雖然工作、生活于城市,可是生活習慣、思維方式卻保留著在家中式的印記。”[3]這必然引發一些矛盾和沖突。但是沖突的設計要水到渠成方可,如果人為痕跡過于明顯,必然會降低作品的批判力度,淪落為獵奇媚俗之作。如劉慶邦的《守不住的爹》中的一段情節顯然就不合情理,叫人無法接受。爹一心想找個女人,讓小青和小龍有個娘,有個完整的家,這倒是符合邏輯:無論從照顧孩子的角度,女人更細心些;還是從性生活和情感的角度都能讓人信服。可是爹把一個暗娼領回家,把小青和小龍都攆到二嬸家去睡,然后整宿地嫖,最后由于付不夠嫖資,被那個叫喬阿姨的女人坐在堂屋里一頓臭罵,這和小說的前后情節及人物形象不太匹配。
事情很明顯,小說中過分渲染了底層生活的細節并做了“性趣化”處理。當然劉慶邦的作品不是情色文學,對性愛細節的刻畫只是點到為止。這種情節虛假的情況也出現在胡學文等其他作家身上。
胡學文的小說《命案高懸》中就采用了情節突變的敘事技巧。小說的主人公是一個名字叫吳響的鄉村地痞,他是一個喜好女色的光棍,因為有把力氣,一股匪氣,而且六親不認,副鄉長毛文明任命他為護林/坡員,并享受村干部待遇。而吳響也利用他的這種小權利,為自己占女人的便宜創造各種條件。小說在開篇就描寫了吳響試圖勾引尹小梅的場景。為了得到尹小梅,他故意裝作沒看見,等尹小梅牽牛越過圍欄進草場吃草,才去當場抓住把柄。可是倔強的尹小梅并沒有讓他得償所愿,惱羞成怒的吳響為逼其就范把她押到鄉政府副鄉長毛文明處關了起來,沒想到尹小梅卻再也沒能活著走出鄉政府。到此,小說的第一次突轉出現。但是此處情節便有故意夸張之嫌:首先小說中我們未發現尹小梅的身體有疾患的伏筆;其次開篇也并未表現出來尹小梅長的多么漂亮。這就讓我們對尹小梅的死因充滿疑問:既不是突發疾病而死,也排除了鄉政府工作人員強暴未遂殺人滅口的可能,如果單單就想教訓教訓她,無論從哪個角度來說,尹小梅的死對毛文明都沒有好處,他的目的只是為了讓尹小梅服軟。隨后的吳響從一個可以說是“狗仗人勢”的流氓,轉變為一個富有正義感的形象,開始奮不顧身地去調查尹小梅死亡的真相。如果不是胡學文故意用來對比基層權力機構對待底層百姓還不如地痞流氓的話,讀者無法接受吳響反差如此巨大的舉動,我們也很難相信是為了塑造豐滿人物的需要。胡學文指出:“我對鄉村情感上的距離很近,可現實中距離又很遙遠。為了這種感情,我努力尋找著并非記憶中的溫暖。”[4]可是胡學文展現“溫暖”的方式卻很特別,因為他選擇了一個良心泯滅的光棍無產者“吳響”來描寫這種遠離的情感,著實叫人生疑。令人遺憾的是至此情節的虛假依然在繼續:小說的結尾黃寶因為后悔沒給妻子尹小梅伸冤,先撒錢后跳河自殺了,這顯然有悖常理。如果黃寶既不貪財也不怕死,為什么不去調查妻子的死因呢?有什么還有比選擇死亡更苦更難的嗎?作家這么處理更多的只是故意加重悲劇的慘烈程度罷了。
上面我們提及的作品中,大都描寫了生活中的陰暗面,可是我們不能忘了,生活中還有溫暖和亮色的一面。比如最美女教師張麗莉舍身救學生,最美警察李博亞為救乘客被火車軋斷雙腿等等,可謂不勝枚舉。然而,“底層文學”的這些作品中回避了陽光的一面,除了要博取讀者對底層民眾生活的同情之外,還隱含著另一層含義:寫不出優秀的,就寫怪異的。為了市場占有率的提高,為了讀者能夠買賬,好多作者不惜去搜羅一些怪異的、離奇的、罕見的內容寫入作品。批評常常從實際利益出發促生了城市妖魔化書寫的流行。一句話,如此樣態的創作與批評是不折不扣的小眾文學圈子的合謀。一些“底層文學”只是把陰暗公開呈示一番而不加褒貶,會貽誤眾生。因為我們無法體會到有尊嚴的生命和純凈的心靈,無法讀出帶有正義追求的真理及人類的共同價值。
三、人物的“空殼化”
脫離原型,把人物完全變成作者的影子,情況會如何呢?賈平凹在2007年出版的《高興》是這方面一個很好的例子。客觀地說賈平凹是當代作家中,最具實力的小說家之一,他的一曲《秦腔》讓我們看到了他勾勒農村底層的生存百態的能力。《高興》原本可以成為賈平凹得心應手之作,但是由于他刻意地追求創新,雖然逃離了“底層文學”目前熱衷的苦難敘事,但是由于筆下的劉高興,已經不是那個發小“劉書禎”,完全變成了是撿破爛的“賈平凹”,讓這部《高興》失去成為“經典”的機會。小說中劉高興是一個頗有些書生氣的拾荒者。他穿戴干凈、齊整,見城里人不卑不亢,他拾破爛用的板車上還時常放著一只蕭。即使是見到讓很多司機都發憷的交警,他也未表現出任何慌亂,他甚至還和交警搭訕,幾句不失身份的恭維之后,交警笑著拍著他的肩膀讓他走。在這部整整62章的長篇小說中,我們幾乎找不到劉高興有什么突出的缺點,幾乎盡是美德。相反,五富、石熱鬧和黃八等人身上,卻有很多底層人民的缺點。吝嗇的五富把錢看得比什么都重要,舍不得錯花哪怕是一毛錢。好逸惡勞的石熱鬧,一直裝瘸利用行人的同情心來乞討為生,即使是劉高興給他錢去買燒餅,他也沒花那三元錢,而是要來了一張餅。在劉高興需要他向警察說明自己不是殺五富的兇手時,他卻悄悄地躲了起來。
小說中對劉高興性欲望的書寫,也顯得比一般的底層民眾要“清高”得多,因為他不會去找妓女來解決身體里膨脹的欲望。即便是他心儀的妓女孟夷純也是如此的“脫俗”——賣身救兄的行為可以稱得上是當世的“鎖骨菩薩”。劉高興極力地控制著自己的欲望,似乎超越了人物自身的可能,畢竟是孟夷純當街親了他之后,他也沒有想去馬上去占有她的想法和行動,讀者會相信如此虛假的強大和純潔嗎?我想大家都不會懷疑這是作者強加給人物的道德感使然。當一位作家試圖塑造某種傳聲筒式的人物,而無視現實生活中活生生的人的欲望和需求時,拋開人物的自身的行為邏輯時,只能是對書寫對象的漠視和扭曲。
劉高興的人格高尚,他把一只腎臟獻給了城里人,他遵守交通規則,他隨時隨處注意自己的言談舉止,以獲取所有人的尊重。他恪守著道德的底限,不收臟物,不掙來路不明的錢,在五富死后得知黃八替自己和五富墊付了一百元的房租,非要把一百塊錢硬塞給黃八。為了表明劉高興的不同,賈平凹還讓他的主人公嘴里不時出現些哲理名言,以表明劉高興是有修養和高雅的人,盡量去適應城市。劉高興還經常勸五富不要對城市充滿仇恨,要學愛這個城市,只有這樣西安城才能接納你。如此的人物特點和現實主義文學中提倡的高大全英雄形象是多么類似啊。可惜,他們都太沒有“人情”味了,太過虛假。為什么底層人民一定要漠視金錢和抑制身體的欲望才會被認為美好;為什么底層人民只能忍讓和奉獻?他們應該有憤怒、不滿及正常人所應該普遍具有的一切情感。遺憾的是,在劉高興的藝術形象里,早早就設定了基調:知足常樂的“好人”與“有素質的人”,表面上似乎保持了人物的特點,但實質上卻沒有留給人物能獲得生長和發展的自由,相反,他從始至終都是為作者的既定意圖服務的工具。劉高興實際上是賈平凹指導底層人民應該如何生活的一個符號。通過小說,賈平凹在向底層滲透一種生活哲學——做一個脫離低級趣味的人。
讀小說《高興》時,我想到了陳應松在2002年寫的《松鴉為什么鳴叫》。這兩部作品都是描寫底層生活的作品,由于《松鴉為什么鳴叫》很大一部分是寫伯緯的“背尸”和“救人”的場景,沒有像陳應松另外的幾篇作品小說那樣經常被提起。小說《高興》中也有一段劉高興背著五富的尸體回家鄉的描寫,相比較而言,我覺得《松鴉為什么鳴叫》寫得更為出色。伯緯遵守了對一起去修路的王皋的承諾——如果王皋死了,就要背他回家。就是這樣一個半開玩笑的話,成了伯緯歷盡千辛萬苦把王皋的尸首背回村里的精神支柱,當然這里面還有共患難的友情和同鄉之情。伯緯在深山老林中背著王皋的尸體往家里趕,一路上渴了喝山泉水,餓了啃生苞谷和洋芋,在經歷了失足差點跌入懸崖、黑熊的對視、松鴉的追趕等一系列磨難之后,終于把王皋的尸首運回了家。雖然王皋的尸體已經不是完整的了,但這不能怪伯緯,因為缺失的半個腦袋本來就是在工地被炸藥崩沒的。陳應松對伯緯背尸回家一路上的描寫可謂句句到位,無論是伯緯一邊走一邊跟王皋的尸體說話,求王皋不要在他背上作怪,還是對王皋尸體在夏天的高溫下產生的尸脹進行的細膩刻畫,都顯示出陳應松不俗的寫實功底。然而反觀《高興》我覺得就要稍微遜色一些。從醫院中謊稱去拍片把五富的尸體偷出來,接著騙出租車司機說五富喝醉了,一直到火車站被警察發現,過程都比較簡單,我想這肯定不是賈平凹的想象的能力不足,而是因為他預先設定的基調決定的:他不想表現過多的苦難和悲傷,那樣就和把主人公叫“劉高興”的巧妙設計相違背了。賈平凹不是忽略苦難,而是更多地想展現底層在面對苦難時的樂觀,這自然無可厚非,但是“劉高興”的形象中有太多的在城市謀生的農裔作家的影子,這就壓制了在苦難時刻應有的表達。如果在偷運尸體的敘述中再多些筆墨,可能更會彰顯底層生活的苦澀,還能和“高興”的標題更強烈地構成一種“欲哭無淚”的張力效果。
因而,當一位作家僅僅描寫底層人民的眼淚,或者只是贊頌底層人民的某種美德,都是不尊重他人生存狀態與情感方式的行為。我們需要謹記這樣的事實:一個人,無論他的知識、地位、財富如何,他身上都參雜著善與惡、簡單與復雜、陽光與灰暗、高貴與卑賤。正如前面所說,底層人民的生活有質樸、節儉、重情義的一面,也有自私、貪婪、膽小等小農意識嚴重的一面。他們有著對世界的復雜感受和認知,他們都是俗人,并不像官方意識形態所宣傳的那樣沒有缺點。因而,我們需要關注底層人民,但不需要毫無節制地贊美,更不能掏空了底層人物,而把作家自己的靈魂附體在其身上。如何理解并尊重底層人民的生活,而不是想當然地“改寫”,這恐怕是作家面對底層生活時的最大挑戰。
讀了一些“底層文學”作品之后,我們不難發現,描寫底層社會生活的“底層文學”既不是文學的一種現實性突破或現實性轉向,也并不比其他范式的文學做出了更多的詩性突破,因此它根本就不是新的文學曙光。相反,由于它正在走向一種玩味和展覽,正在發展成一種新興的公共寫作 (局限于小眾群體)。作為一種較為新型的文學范式,“底層文學”憑借介入現實的穿透力量,依然是很多評論者和作家熱衷的對象,盡管如此它直到現在還沒有顯示出某種詩性的優越和主題傾向。
“底層文學”將底層民眾的生活環境、生活經歷和人物形象的主觀臆造,雖然或許會吸引一些讀者的獵奇心理,卻缺乏對底層民眾一種負責任的書寫與尊重。對于這樣過度夸張地呈現的底層生活狀態,對底層生活缺乏了解的“底層文學”讀者就會以為,這就是現實,這就是真實。如果缺少了對這種生活的追問和批判,必將誤導人們去接受甚至模仿生活中的丑陋和卑劣,于是,鄉間陋習、城市丑惡、變態人格、陰暗心理都會在生活中自由自在地生長。
[1]陳曉明.“后人民性”與美學的脫身術——對當前小說藝術傾向的分析[J].文學評論,2005(2).
[2]劉繼明.我們怎樣敘述底層?[J].天涯,2005(5):29.
[3]張謙芬.90年代以來鄉村書寫中的城市背影[J].文藝理論與批評,2005(4):67-69.
[4]胡學文.《命案高懸》創作談:高懸的鏡子[J].北京文學·中篇小說月報,2006(8):121-123.
(責任編輯:章永林)
Creation Misunderstanding of"Underlying Literature"
WANG Xue-sheng,YUAN Hua
(College of Literature,Tonghua Normal University,Tonghua,Jilin 134002,China)
The"underlying literature"works caused large numbers academic questions,after careful reading these works,we found that the"underlying literature"writers had gone into the creation misunderstanding, such as the deviation of underlying living environment and reality,the"distortion"of plot and"emptyshell"character in the works.
underlying literature;misunderstanding;deviation;distortion;empty-shell
I021
A
1008—7974(2014)06—0059—05
2014-06-30
王學勝(1978-)吉林長春人,文學博士,講師。研究方向:當代文學理論與文學批評。
吉林省教育廳“十二五”社會科學研究項目:“底層文書”批判。項目編號:吉教科文合字[2014]第385號;通化師范學院博士扶持基金項目:新世紀以來的“底層文學”研究。項目編號:2014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