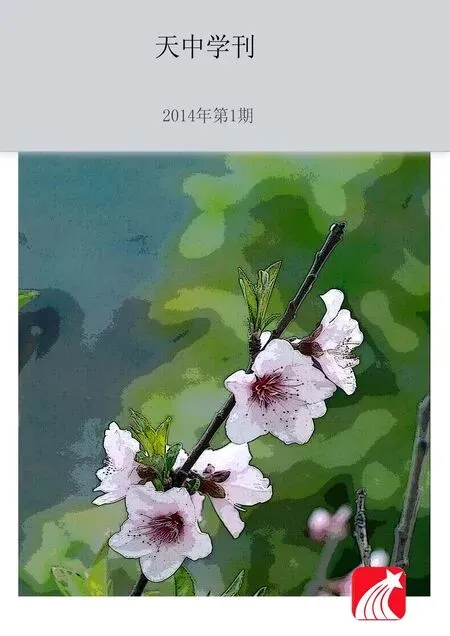“揚州夢”故事的文本流變及其文化意蘊
歐陽春勇
?
“揚州夢”故事的文本流變及其文化意蘊
歐陽春勇
(南開大學 文學院,天津 300071)
與唐代詩人杜牧相關的“揚州夢”故事,在歷代詩評、詞作、小說和戲曲中,有豐富多樣的文學表現形式,梳理、比對各代之流傳文本以及故事的演變軌跡,可以看到故事演變背后的文化推手。
杜牧;“揚州夢”故事;演變;文化意蘊
杜牧“揚州夢”故事寫我國唐代詩人杜牧的風流韻事,得名于其《遣懷》詩:“落魄江南載酒行,楚腰腸斷掌中輕。十年一覺揚州夢,占得青樓薄幸名。”[1]1376詩出以后代不絕書,在小說、戲曲等體裁中均有文本流傳,故事地點也不局限于揚州。杜牧“揚州夢”故事以才子佳人和愛情香夢深深打動后人,幾經歷代文人的雕琢和渲染,不僅成就了內涵深厚的知名典故,堪與黃帝的華胥夢,莊子的蝴蝶夢,盧生的黃粱夢相提并論,其流變中的文化意蘊也耐人尋味。
一、“揚州夢”故事的文本流傳
《遣懷》詩筆帶香艷脂粉氣息,在貌似冷靜平淡中,抒發作者懷才不遇的憤懣不平,同時也表達了對過往歲月荒唐之行的懺悔之意。杜氏此《遣懷》詩之后,其同代人于鄴專就杜牧“逸游之事”以小說形式寫了一篇《揚州夢記》,一邊對杜牧風流艷事娓娓道來,一邊穿插進杜氏詩歌,如《兵部尚書席上作》《遣懷》《題禪院》《嘆花》等,讀之倍感真切。該文也成為此后各種敷衍杜牧“揚州夢”故事的祖本,同代以及后世詩評詞作和小說集中多有對之轉引、節錄或稍作補充的文字,如孟棨《本事詩·高逸第三》、高彥休《唐闕史》卷上之《杜舍人牧湖州》、丁用晦《芝田錄·杜書記平善》、《太平廣記》之《杜牧》、王讜《唐語林》之《杜書記平善》、張君房《麗情集·湖州髫髻女》、毛滂《東堂詞》之《調笑令·詠苕子》、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后集之《杜牧之》、計有功《唐詩紀事》之《杜牧》、辛文房《唐才子傳》之《杜牧》、馮夢龍《情史》之《情豪類·杜牧》以及《情憾類·杜牧》。上述種種文本記載杜牧風流之事,雖簡繁有別,題名不一,但基本構成了杜牧“揚州夢”故事的流變脈絡。
杜牧“揚州夢”故事不僅在詩詞、小說中傳頌不衰,在戲曲文本中更是大放光彩。如元朝知名作家喬吉所著《杜牧之詩酒揚州夢》、明代卜世臣所作傳奇《乞麾記》、清代嵇永仁所作傳奇《揚州夢》、清代黃之雋所撰雜劇《夢揚州》(又名《杜牧》)、清代陳棟所作雜劇《維揚夢》、清代佚名作者所著雜劇《夢揚州》,還有“小留香館”藏本京劇《揚州夢》等。
除了詩評詞作、小說和戲曲之外,杜牧“揚州夢”故事還作為知名典故廣泛運用在詩詞、小說和戲曲等各種文體的作品中。如黃庭堅《鷓鴣天》詞:“甘酒病,廢朝餐。何人得似醉中歡。十年一覺揚州夢,為報時人洗眼看。”[2]94倪瓚《【雙調】殿前歡·聽琴》:“十年一覺揚州夢,春水如空。”[3]1421《醒世恒言·杜子春三入長安》:“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人間敗子名。”[4]837清代岳端所作傳奇《揚州夢》,雖非杜牧之事,但卻采“十年一覺揚州夢”詩句標題。杜牧“揚州夢”故事廣為傳播,由此可見一斑。
二、“揚州夢”故事的演變軌跡
故事在流傳之中往往伴隨著文體的演變,杜牧“揚州夢”故事首先由其本人之詩歌得名,隨后在同代人于鄴之小說中初具規模,進而在各代文人墨客中引起共鳴,作為典故被廣泛使用,尤其在戲曲文學中煥發異彩,其演變軌跡清晰可循。
(一) 故事情節的演變
杜牧“揚州夢”故事在各種文體中流播,因載體體裁不同,故事的敘述也相應發生著流變。杜牧《遣懷》詩追憶了自己昔日詩酒縱情、放浪形骸的荒唐生活,抒發了青春虛擲、功業未成的人生感嘆。囿于七言絕句的詩體形式,詩歌言辭暗含的故事不得展開敘述,只能點到為止,這也為此后杜氏“揚州夢”故事的鋪衍敘述留下了廣闊空間。
杜牧“揚州夢”故事的敘述在于鄴的小說《揚州夢記》里首次發生質的飛躍,詩歌中濃縮的意象“江湖載酒”“楚腰纖細”和“青樓薄幸”得以鋪展,于氏小說主要選取杜牧幕職牛相時揚州狎妓,赴宴李愿宅索討紫云,尋芳湖州時十年相約三事使詩歌畫面開始具象化。杜牧“揚州夢”故事由此具備了必要的情節內核,敷寫文人浪漫風流的特質,但是情節顯得疏散,故事的敘述呈板塊拼湊狀,像是文人逸事集錦,缺乏連貫的線脈,當然在情節的推進發展中塑造人物性格也就無從談起。在其他小說中,杜牧“揚州夢”故事亦多未超出這一敘述狀態,至多也是內容上有所轉引、節錄或是稍作補充。如孟棨《本事詩·高逸第三》節選了杜牧赴宴李愿宅索討紫云,文前增加杜牧游城南至文公寺遇禪僧感其玄言而詠《贈終南蘭若僧》詩之事。高彥休《唐闕史》卷上之《杜舍人牧湖州》、張君房《麗情集·湖州髫髻女》、馮夢龍《情史》之《情憾類·杜牧》則只載其尋芳湖州時十年相約之事。《太平廣記·杜牧》、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后集之《杜牧之》及辛文房《唐才子傳》之《杜牧》記取其游逸三事,例同于鄴《揚州夢記》,只是文字稍有出入。丁用晦《芝田錄·杜書記平善》、王讜《唐語林》之《杜書記平善》則僅取其幕職牛相時揚州狎妓之事。《唐詩紀事》則是簡要輯系詩歌與本事,敘述自是蜻蜓點水。
杜牧“揚州夢”故事的敘述在戲劇文學中得以長足發展。首先,元人喬吉雜劇《揚州夢》開始圍繞其題目正名“張好好花月洞房春,杜牧之詩酒揚州夢”[5]125作整體構思,敘述不再是杜牧逸事的生硬拼湊,而有了一以貫之的表現主題,劇中幻設夢境,聯系杜牧《張好好詩并序》,把張好好與“揚州夢”巧妙地綰合在一起,對于氏《揚州夢記》有所發展。其次,清人陳棟雜劇《維揚夢》,比之喬作,夢中設夢,情節更奇。故事敘寫杜牧幕職揚州,夜夜流連妓院歡娛,不以功名為念。不料此事驚動梓潼元皇帝君,遂派朱衣使者對之重演呂洞賓邯鄲道上故事,讓其夢中遍嘗幕客心酸。杜牧醒悟,后來居官,獲贈相好紫云。故事敘述因為夢中設境,更顯波瀾。但雜劇終究限于體制,不能盡情鋪敘,而清人嵇永仁傳奇《揚州夢》敷衍此故事,以三十二出之篇幅則已能極盡敘寫變幻之能事。本傳奇構思精嚴,將于氏《揚州夢記》所寫杜牧風流三事全部囊入,但又敘述自然連貫,不見拼接痕跡。其中寫杜牧與韓歌娘及紫云合賺司徒李愿,情節一波三折,既驚險又風趣。寫杜牧與民女綠葉之悲歡際遇更是敘述宛轉,高潮迭起。劇中增設齊小二與陰大郎兩小人從中撥弄,使得才子佳人遇合美事受阻,情節由此鋪陳,更顯搖曳多姿,生動引人。
(二) 形象的演變
通過文本載體的演變,杜牧“揚州夢”故事不僅在敘述上由片狀湊合趨于統貫表達,由相對簡單走向較為復雜,敘事因素得到不斷加強,情節更加曲折,而且人物形象也在發生著演變。
首先,形象數目的增設。杜牧《遣懷》詩用凝練的語言表達寄情詩酒青樓快意的同時,更多傾向于對自身政治抱負落空的一種深衷隱痛,詩人形象藏于言辭背后。到于鄴小說《揚州夢記》,杜牧形象具體可感,另外節度使牛僧孺、司徒李愿、歌妓紫云、湖州刺史某乙、鴉頭母女等人一并隨故事陳現。此后,其他小說均未超出這些既寫形象。至戲曲文學中形象數量更為豐富。喬吉雜劇《揚州夢》演敘杜牧婚娶歌女張好好之事,比之小說,張好好、媒人員外白謙及豫章太守張紡等為新增人物。黃之雋雜劇《夢揚州》寫杜牧娶女又增出一妓紅雨。陳棟雜劇《維揚夢》寫杜牧與紫云遇合之事,劇本添出梓潼元皇帝君、朱衣使者等。嵇永仁傳奇《揚州夢》篇幅最長,人物自然較為繁雜,新增韓歌娘、巫醫婆、溫庭筠、李商隱、齊小二、陰大郎、史憲城,可謂文人歌妓、武夫儒將、賭棍屠夫、巫婆老鴇,三教九流,一應俱全。
其次,形象身份的坐實。杜牧《遣懷》一詩,詩人形象隱含句中。于鄴以及其他小說,女主人公基本不出紫云和湖州鴉頭女范圍,湖州刺史某乙有的則落實為崔君(或坐實為崔元亮),閑居李司徒則有指實為李愿。戲曲劇本中,女主人公有張好好、紫云、紅雨以及命名為綠葉的鴉頭女,孔子有言:“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6]206文本給形象指名加姓,落實身份,不言而喻,可以起到加強作品的真實效力之用,告知讀者實有其人,確有其事。
最后,形象內涵的變化。杜牧,新舊《唐書》有傳,只是均附于《杜佑傳》后,《舊唐書》云:“(杜)牧好讀書,工詩為文,嘗自負經緯才略。”[7]3986《新唐書》云:“(杜)牧剛直有奇節,不為齪齪小謹,敢論列大事,指陳病利尤切至。”“于詩,情致豪邁。”[8]5097正史所載自有根據,由此可見杜牧性情。但唐人尚文好狎,狎妓、攜妓、蓄妓尤其成為文人風雅生活的重要內容,或被視為高人一等的社會地位之象征,風流俊爽、自視甚高、仕途失意的杜牧有此好尚,就更是不足為奇。其《遣懷》之作,便是對這種冶游生活情帶悔痛的詩性追憶。孫書磊《中國古代歷史劇研究》指出:“后世文人歷史劇作者因認同甚至激賞前代文學家的志趣而鐘愛該文學家及其作品,并進而產生欲將其人其作結合起來加以表現,以求與古人神交的強烈沖動。于是,演繹歷史上文學家作品創作的本事的歷史劇便應運而生。他們通過在歷史劇中演繹前代文學作品的本事,實現志趣上的古今對接。”[9]134當然,以文人為題材進行創作的作者不限于后世,而且此種題材作品也不僅是歷史劇,杜牧“揚州夢”故事流傳文本就是很好的明證。可是,故事撰構畢竟會染上作者的意志,難免借他人酒杯澆自己塊壘,因此,杜牧“揚州夢”故事形象不可避免地由真實走向虛構。
由此而來,故事主人公杜牧的形象也在嬗變之中。其《遣懷》詩側重情懷感嘆,缺乏故事意味,不便論其形象。于鄴《揚州夢記》,通過杜牧幕職放蕩、赴宴詠妓和湖州約聘三個片段,就已勾勒出杜牧疏野放蕩、風流俊逸、知恩圖報、剛直有節的生動形象。其他小說文本中,杜牧這一形象基本未變動。在戲曲文學里,杜牧形象發生了較大流變。喬吉《揚州夢》中,杜牧雖仍是風流才子,甚至好色之名驚動皇帝,但因激賞張好好才貌而對之鐘情癡迷后,誓言哪怕縱有奢華豪富家,倒賠妝奩許招嫁也絕不丟下與其美滿恩情,并以實際舉動展現出專情癡狂的才子形象。嵇永仁傳奇《揚州夢》中,杜牧除了秉承才華超眾、風流瀟灑的特質外,又平添了幾分政治家的雄才韜略和道學家的冷血酸腐。黃之雋雜劇《夢揚州》中杜牧則是偽裝道學的風流名士形象。而陳棟雜劇《維揚夢》中,杜牧不僅風流疏狂、放蕩不羈,也有雅量熱腸、浪子回頭金不換的品性。
三、“揚州夢”故事演變的文化意蘊
歷史上的杜牧雖有其人,卻只有一個,自其以生花妙筆寫出膾炙人口的《遣懷》絕句后,“揚州夢”故事便得到同代及后世文人的不斷敷衍。盡管各種文本無不著眼于杜氏逸游之事,喜談風月,以致“揚州夢”一詞幾近成為“風月繁華”的代稱,但在不同作家的各自文本中,杜牧形象及故事內涵又各有不同。不同時代不同作家筆下的杜牧“揚州夢”故事,其實都是撰者根據自己的生活體驗對之作出的獨特理解,寄托著各自的情感。而人是歷史的存在物,不可能將自己完全拋離歷史,作者在借歷史之人物故事表達自己的主張和感受時,總會不自覺地讓作品打上其時代文化的烙印。從唐朝至清代,杜牧“揚州夢”故事演變的背后“推手”或說反映的文化蘊涵,清晰有致。
先看唐代。呂興昌《奔騰與內斂——盛唐詩歌》曾言:“有唐繼隋奄有天下,其文化精神一方面接受江左之清新優雅,另一方面則承襲北朝而遠祧兩漢之質樸雄壯。兩者相互映襯影響,匯成新流。此外,就軍事經濟而言,大唐乃當時世界性之大帝國,生于其間,無形間似有一份莫名的信心活躍胸中。”[10]158其文人士子,感染泱泱大唐氣象,遂適性任情,真誠坦率,毫不避諱世間功名利祿、聲色歌舞,行動服從生命本真原則。他們既沒有之前魏晉文人苦苦思索自身生命價值的那份沉重,也沒有以后宋明理學“存天理,滅人欲”之絞索羈勒,無須遮掩“人生得意須盡歡”的放縱狂歡。于鄴小說《揚州夢記》可稱是這一文化生態的經典映像,其所塑造之杜牧是生性風流、不拘小節的翩翩才子。在任職掌書記時,他依然幾無虛夕地出入秦樓楚館,盡興宴游;在身為持憲之侍御史時,他又是自請赴宴,開懷暢飲,當著眾賓對妓紫云凝睇良久,甚至點名索妓,惹人哄堂大笑,仍能即席賦詩,“意氣閑逸,旁若無人”[11]7。在湖州尋美,水嬉之日,他“閑行寓目”于云集如堵的茫茫人海,終于鐘意年十余歲之鴉頭少女,定下“十年之約”,可當才子姍姍來遲之際,又能瀟灑吟詩,慨然“厚為禮而遣之”。可見唐人筆下的杜牧,絕妙地體現了那個時代之人率性任真的品性和豁達爽朗的氣度。于氏撰述杜牧“揚州夢”故事的字里行間,折射出唐代文人士子的生活風范,洋溢著時代風潮的精神氣韻。
次說宋代。宋太祖選擇重文輕武路線作為王朝的基本國策,又因宋朝連遭外族入侵,邊地失守,盡管其科舉制度改革更有利于文人發展,但較之唐代,文人精神卻趨向整體滑坡,變得謹微內斂。從現今所見宋代記載杜牧“揚州夢”故事之小說文字來看,其多是節錄于鄴《揚州夢記》,像是進行文獻整理,缺乏對其風流生活的創造熱情,這無疑反映出宋代文士精神氣度沒有了唐代的張揚奔放,但并不表示宋代文人對杜牧“揚州夢”故事內涵缺乏認同。恰恰相反,他們對杜牧本欲成就非凡功業,實際卻落得虛擲光陰的懊惱與悔恨深有感懷,所以在詩詞中多有吟嘆。如曹勛詩《上塘值清明》八首之一:“不作揚州夢,何能賈客留。壯懷今斷斷,世事任悠悠。”[12]21117陳子高《大年流水繞孤村圖》詩:“少游一覺揚州夢,自作清歌與寫成。流水寒鴉總堪畫,細看疑有斷腸聲。”[13]392王千秋《憶秦娥》詞:“揚州夢覺渾無跡,舊游英俊今南北。今南北,斷鴻沈鯉,更無消息。”[14]44姜夔《月下笛》詞:“揚州夢覺,彩云飛過何許?多情須倩梁間燕,問吟袖弓腰在否?怎知道、誤了人,年少自恁虛度!”[15]85
再言元代。元蒙統治者崇尚武力,輕賤文士,漠視儒學對其穩固統治的積極作用,入主中原后曾長達八十余年停止科考,即使后來恢復開科,但在選取及用人標準上的嚴重民族歧視政策,讓眾多滿腹詩書、胸懷韜略的文人士子喪失仕進之路而顛狂絕望。另則,宋元已降,商業經濟逐步繁榮,市民階層隊伍壯大,符合其欣賞趣味的通俗文學發展較快。《元史·刑法志》條例規定:“諸亂制詞曲,為譏議者,流。”[16]2685“諸妄撰詞曲,誣人以犯上惡言者,處死。”[16]2651在此背景下,疏離政治、不關時事的愛情故事自然成為雜劇作家首選題材而使其創作蔚然成風。當然,正如丹納在《巴爾扎克傳》中所言:“精神著作的產生不能只靠精神,整個人對它的產生做出了貢獻。他的性格、他的教育、他的生活、他的過去和現在、他的情欲、才能、德行和惡習,他靈魂的行為的每一部分都在他所思考和寫作的東西上留下了印痕。”[17]34喬吉對杜牧“揚州夢”故事在人物、情節、結局、意涵上的創造性改編,寄予了作者自己的身影,也可說在杜氏身上找到了契合點。如其散曲《折桂令》云:“文章杜牧風流……老我江湖,少年談笑,薄幸名留。”[18]230作為封建社會的底層儒生,喬吉自然無法超越“金榜題名”和“才子佳配”情結,雖然其《揚州夢》中,杜牧不是狀元及第,但也位居高官。雜劇的情節誠然不是史實,事實上杜牧與張好好有各自的人生軌跡,彼此擦肩而過。作者濃墨重彩讓他們在《揚州夢》中團圓,說穿了無非是一場“白日夢”式的自我迷醉,這正反映出傳統文士囿于時代局限對為官入宦、嬌妻美妾的終極追求不能超拔,何況是在有“九儒十丐”之排位的元代,缺失性心理補償的創作沖動就更是異常強烈。
明代,商品經濟活躍,市民隊伍壯大。在哲學層面,陽明心學及其眾多分化學派給予晚明個性解放思潮以強大動力。卜世臣《乞麾記》傳奇,劇本雖已亡佚,但據目錄之書介紹,可知其演杜牧風流韻事,綴合杜詩“欲把一麾江海去”句及其乞守湖州之事為劇名。呂天成《曲品》評云:“發揮小杜之狂,恣情酒色,令人頓作冶游之想。”[19]247卜世臣生活約在明萬歷年間,散曲之作喜為艷曲,猜想此劇定在一定程度浸染上晚明社會淫靡風習。
清朝,嚴酷的文字獄讓文人噤若寒蟬,所謂“羅網滿地欲何之,文字藏機劇可危。鸚鵡洲邊休作賦,鷓鴣嶺下莫題詩”[20]124。嵇永仁傳奇《揚州夢》、黃之雋雜劇《夢揚州》、陳棟雜劇《維揚夢》盡管不約而同地敷衍杜牧“揚州夢”故事,取向亦各有不同,但無疑都融入了各自的幕府生活期遇和體驗。嵇氏青少年時即恃才優游,又為人慷慨不拘小節,雖胸懷經世之學,卻數困場屋,帶著懷才不遇的失落、生活貧困的焦灼而創作以獲牛僧孺恩遇的杜牧為主角之《揚州夢》,劇中寄予對知己的無限向往和深情渴望可以想見。黃氏亦是多年科場不幸,盡管學識淵博,但為生活所迫坐館入幕,幸遇幕主陳元龍賞識,甚至所作雜劇亦是由其資助刊刻。黃作除了把杜牧狎妓當成名士風流韻事來描寫外,甚至將牛僧孺派人暗中保護杜牧狎妓之行當成德政歌頌。黃之雋感念知遇之恩于劇中隱隱可見。陳棟相較二人更為不幸,他屢應鄉試而不中,又苦于多病,幾乎以藥代飯為生,也曾游幕,但終郁郁不得志而含恨離世。陳棟雜劇《維揚夢》敷寫杜牧夢中遍嘗幕途惡況,醒來碎硯擲筆,求取功名,后來歷官清要,獲贈美姬紫云。現實為幕的悲慘遭際于劇中隱然顯現,心中理想期待借文字虛幻滿足。
綜上所述,杜牧“揚州夢”故事由其《遣懷》詩作發端,歷經各種文體,在歷代文人筆下不斷演化,并被烙上各自時代的特殊文化蘊涵。此故事流傳甚廣,影響很大,究其原因,無不和中華民族的文化精神和傳統的文人審美心理息息相關。傳統文人輕狂,期許甚高,杜牧“揚州夢”故事非常契合中國文人的內在心理,因此,該故事擁有了強大的生命力。可以說,文化土壤的源泉不竭,其被演繹的動力就會不止。
[1]何錫光.樊川文集校注[M].成都:巴蜀書社,2007.
[2][宋]黃庭堅.黃庭堅詞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3]隋樹森.全元散曲[M].北京:中華書局,1989.
[4][明]馮夢龍.醒世恒言[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
[5][元]喬吉.杜牧之詩酒揚州夢[M]//王季思,主編.全元戲曲:5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0.
[6][宋]朱熹.四書集注[M].長沙:岳麓書社,1987.
[7][后晉]劉昫,等.舊唐書[M].北京:中華書局,1975.
[8][宋]歐陽修,等.新唐書[M].北京:中華書局,1975.
[9]孫書磊.中國古代歷史劇研究[M].南京: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
[10]蔡英俊.意象的流變[M].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2.
[11][清]吳曾祺.舊小說(復印本)[M].上海:上海書店,1985.
[12]傅璇琮,等.全宋詩[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13]盧輔圣.中國書畫全書:2冊[M].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09.
[14]馬興榮,等.全宋詞:廣選·新注·集評[M].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7.
[15][宋]姜夔.姜夔詞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16][明]宋濂.元史[M].北京:中華書局,1976.
[17][1]劉彥君.欄桿拍遍——古代劇作家心路[M].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95.
[18][元]喬吉.喬吉集[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8.
[19][明]呂天成.曲品校注[M].吳書蔭,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6.
[20]徐坤.論清代雜劇的個人化傾向[J].求是學刊,2006(2).
〔責任編輯 劉小兵〕
歐陽春勇(1979―),男,湖南寧遠人,博士研究生。
2013-12-05
I206
A
1006?5261(2014)01?0024?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