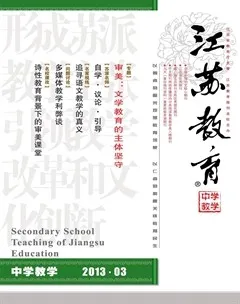志于道,游于藝
“中國文脈,是指中國文學幾千年發展中最高等級的生命潛流和審美潛流。”余秋雨教授的新作《中國文脈》開篇便闡釋了這樣一個觀點。事實上,這種“最高等級的生命潛流和審美潛流”,在明清之前就是一股詩的潛流,從《詩經》伊始,一以貫穿了中國文學的整個發展脈絡。因此,談到詩歌教學,如何將這種“生命”意識與“審美”意識貫徹于課堂,便成了詩性教育探討的話題,其實,概而言之,也是詩性教育的底色。
一、操千曲而后曉聲——提升獨到的文化鑒賞力
詩歌,是文學體裁中最具情感沖擊力的一種文學樣式,它可以具有情節、畫面感,也可以給人以理性的震撼。如果說語文審美課堂像中國園林的造園藝術,那么現代詩歌的教學更像是其中那東渡扶桑、被日本人舶去的“枯山水”。
中國園林講究氣韻,山不在高,水不在深,陋室有文化精神就成為心向往之的圣殿,這樣的語文課堂如同中國畫講究飛白、點染,引日光穿林做影子秀,隨清風搖曳送遠香。日式的“枯山水”集結著中國的園林文化,但繁花落盡,四大皆空,如用流沙剔除了真水的元素,高度濃縮的形式比江南園林更抽象、更具符號化,成為一種直指本質、禪意深厚的審美形式。宜品,不宜游;宜茶,不宜娛,帶著濃厚的思辨色彩。
因為高明的詩人不僅用創造性的藝術思維和創造性的藝術語言去概括生活和表現生活,而且也深深懂得這是把握讀者欣賞心理、調動讀者的創造性思維去再創詩境的必然要求,可謂拙樸中暗藏機巧,淺顯中隱匿深邃。
這就要求教學者擁有強大的文化氣場:吸納、積淀、深厚己身。所謂“落花無殘”,就是平時所學的無用之用,很可能成為大用。聞道踐行,深廣的理解力、嚴密的分析力,可以讓教師敏銳地去捕捉學生的思維潛能,及時地去引導、闡發,去還原他們的精神能量,正如曾鞏所說的“學似海收天下水”。
但相對于文化的吸納,更重要的卻是“操千曲而后曉聲,觀千劍而后識器”——提升獨到的文化鑒賞力。
讀書固然要破萬卷,但不是紙上談兵,詩歌教學具有思辨性,因此,教師首先要是文化的鑒賞者,具有文化的鑒賞力。詩歌教學的審美性,是從“意旨”走向“意味”。它不僅是知識的傳承,更是思維品質的培養,孔子說:“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這句話,有牢記的價值。
二、丹可磨而不可奪其色——舒張自然天成的心性
詩歌,是一種極其優美的文學樣式,它以形象示人,但我們在教學中,往往不知不覺地走進一個誤區,就是把意象一個個剝離開來,再將其寓意一一對號入座。殊不知,這種肢解與拆卸,使詩失去了原有的光澤和神韻,唯借助著技巧與功能來賣弄風情,詩情被蕩滌無存。而學生的學習,往往是用一種坦白的、好奇的、富于冒險的心情去探索、發現與吸納。課堂教學若只以機械、枯燥的程式去傳達知識,那精神上的審美何在?
心性的培養應該是道德的,也是審美的。當中需要學問,更需要雅韻與風味,所謂“丹可磨而不可奪其色,蘭可燔而不可滅其馨”是焉,課堂教學不但不能“奪”與“滅”,更應“增”與“添”,去還原個體生命意識覺醒的美感,這種覺醒的美感,是還原師生的性靈,讓其與天地精神共往來。
例如:高一的一堂語文課,上的是白居易名篇《琵琶行》。授課教師沒有從常規的朗讀、分析、欣賞、評價展開,而是對學生改寫的《琵琶行》進行賞析。下面便是從眾多學生作品中選出的兩首:
《琵琶行》改寫
琵琶聲聲錯,客飲瀟瀟然。
屈指迎仙樂,繞耳賞玉環。
移船邀相見,久現半妝顏。
一曲同命人,無語淚闌干。
《琵琶行》改寫
秋風瑟瑟掃落葉,月影凄凄訴離別。
忽聞江面琵琶聲,錚錚似憶故人情。
慢捻急挑切切彈,春光玉柳塞外風。
江州司馬筆下走,千古流傳《琵琶行》。
看了學生的這兩首作品,我們完全可以相信,再和他們談論什么寫作背景、琵琶女的身世、全文的主旨,都已經是多余,對學生而言,他們對于整篇文章已經完全了然于胸,否則他們根本無法用嫻熟的筆調寫下這樣的文字,傳遞出詩人的情懷。
我們要尊重學生的閱讀初感。這種初感也許是淺顯的、有疏漏的,但只要不是曲解,沒有南轅北轍,便孺子可教。在詩歌教學中,重要的是理解文本所特有的筆法和感情,但這種個性常被技巧所淹沒。對于初學者,最大的難點就是如何跨越思維的定勢、固有的范式和經驗。本著心性的直覺去感知與解讀,這種感知與解讀是需要“膽”與“識”的,是值得我們尊重并予以鼓勵與激發的。
舒張自然天成的心性,是走出教學的程式、道統,既不放縱、也不平庸,要有“淘汰俗情,漸及清望,互相唱詠,以見性靈”的情趣,不為物累、知書達理。這樣的課堂教學好就比蘇州園林的主人,他們大多歷經宦海沉浮,耗盡青春志氣,最后在仕途榮辱不再牽絆的時候老去。所以蘇州園林的節奏必定舒緩,色彩必定如繁華落盡盡顯素雅本色。
三、山高不阻野云飛——還原精神的好奇心
留白,傳統繪畫的一種極高境界,講究著墨疏淡、空白廣闊,以留取空白構造空靈韻味,給人以美的享受。一堂好課,應該有“留白”的空間,培養學生思維的張力,還原學生的好奇心,使其游走在詩賦詞句間,能感受四壁合圍的天空之寥廓和水面在四岸包圍下的舒展,正所謂“竹密何妨流水過,山高不阻野云飛”。
歷代的詩詞大家,都十分講究文學意境的含蓄婉折。講求“象外之象、景外之景”,他們寫而不“滿”,言外有義,句式變形,運筆迂曲,使詩歌包含了弦外之音、韻外之致,并以此來激發讀者廣泛的聯想和豐富的想象,產生了虛實相生、有限中寓無限的藝術效果。自古以來“詩無達詁”,讀者品讀意旨的方向也許是一致的,但由于學識、閱歷的不同,心理感受有可能會大相徑庭。
遺憾的是,我們在教學中唯恐“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總想著要傾囊相授,或者也知道“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才是教育的境界,但一旦走入教學情境,便不自覺地想要去窮盡我們的認知。例如,在上“現代詩欣賞與寫作”公開課時,我選用了張紹民的《從前的燈光》一詩進行鑒賞。閱讀中,學生已然讀出了其中的人情美、人性美以及母愛的光輝,對于中學生詩歌鑒賞的教學預設其實已經生成,但我未能忍住,還是將我課前準備的五個角度的賞析內容高調地講了一遍。課后反思,才發現不是不可以深入講析,而是錯在“不憤而啟”“不悱而發”,看似好心的行為,無意中卻容易養成學生思維的惰性。
園林中的“留白”,絕不是孤立地讓景物保持殘缺之美,而是意圖構筑整個景境的無盡之思,使得景有所歸而意在言外。同樣,中國的很多詩歌作品,形式非常簡單,但內涵卻相當深刻,像岑參的那兩句:“山回路轉不見君,雪上空留馬行處。”王維《終南別業》的頸聯:“行到水窮處,坐看云起時。”看似什么也沒說,但詩人的情致已自然流露于言語之外了,這就是無言之美的境界。無言之美,是一種力量,它如孔子說的:“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在無聲中見其博大;無言之美,是一種境界,它又如老子所說:“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在順其自然中無為而教、無為而學;無言之美,更是一種智慧,“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在效果上以期實現“明刑至于無刑,明賞至于無賞,百職不戒而舉,萬事不勞而成”,以“無為”達到“無不為”的目的。課堂教學不也如此嗎?
如果學生無疑,聰明的做法是設疑,引導他們打開思路,但更聰明的做法是存疑,如沈郁菁老師所說:“有疑則思,有思則學,學而又問,問則疑消疑釋。”存疑,是課堂教學的留白,可以讓學生利用身邊的豐富資源,去打開一條通向自覺認知的快捷通道,而遠離思維的僵化與惰性,探幽發微,去獲取思維的敏銳性、還原精神的好奇心。
園林是“多方勝境,咫尺山林”的藝術,是一花一世界、一葉落而知天下秋的哲學境界,在濃縮的亭臺軒榭中去體味山野林泉的空寥,在精神上給人們提供了足夠具象的空間。對鑒賞者來說,園林的空白之處恰恰是留有余味的韻腳,等待進一步的補全。而詩歌教學的留白之美,就如寂靜的衰草枯楊,唯有通過想象方能了解當年歌榭舞場的喧鬧;片斷的頹壁殘墻,需要通過歷史才能還原它曾是宮室苑囿的繁華。不同的知覺體驗和知識背景,帶給學生迥異的審美想象和感受,但這種感受是超越了知識與技巧的,是教學之外的一個更廣闊的空間。
有一種園林的審美意境,被稱為“九宜”,即“宜月、宜雪、宜雨、宜煙、宜春曉、宜夏、宜秋爽、宜落木、宜夕陽”,若以此來形容詩性教育、語文的課堂審美,我想,一堂課中應是做不到包羅“九宜”的,但若能做到九之一二、或者三四,甚至跳出“九”,創出自己的“十”,乃至“十一”,便是一種悠游的審美之境了。
(作者單位:江蘇省蘇州市第十中學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