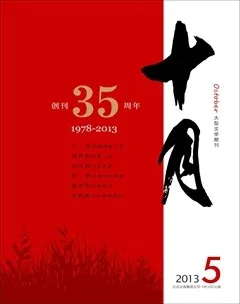一點光亮,一點輕靈(創作談)
2013-12-29 00:00:00吳文君
十月
2013年5期
時隔多年,我早不記得父親給我買的第一本讀物是什么了。不過,還記得《木偶奇遇記》,那個愛惹事,老讓老木匠傷心的木偶,一說謊鼻子就會長起來;還記得《綠野仙蹤》——好像也叫《尋找奧茲國》,看完這本書,我悶悶不樂了很久,為什么多蘿西、稻草人、鐵皮人千辛萬苦找到的奧茲國國王竟然是個什么用也沒有的膽小鬼,豈不是白找了?那年我是九歲吧,喜歡西方文化的父親只給我書看,他也解答不好我的問題。不久,我就不滿足他給我買的書,開始讀他的書。——以為看更多的書,可以聰明起來,終于能夠找到什么。說不定是一枚很大的果子呢?而且只屬于我?
所以,我是看著父親的書,看著西方讀物長大的。天知道我看懂了多少。那個時候,看書只是幫我消磨掉用之不盡的時光,從沒有顯現出什么值得說的用處。直到有一天,我寫起了小說。沒有人教過我小說該怎么寫,我自己也不知道。我有很多話想說,卻沒有地方說,直到找到小說這個途徑。我試著寫了一個短篇,寄給《北京文學》。那年我已經三十歲。隨后,又寫了一個短篇,又寄給《北京文學》。這兩個小說都發表了,也給我寫下去的勇氣和信心。雖然這之后半成品、廢品開始不斷出現,我深為苦惱,對自己能否寫作產生了懷疑。
還好我堅持了下來,直到今天。也許現在可以說了,父親的那些讀物,給了我最初的文學啟蒙,培養了我的直覺。從第一個小說開始,我就依靠直覺在寫,寫我對生活的直接印象。直覺是我對現實世界最真實的觸摸,而真實,我則認定它是文學的一個基本標準。……
登錄APP查看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