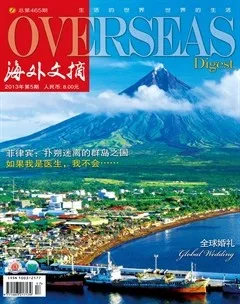法棍情結

巴黎的四月,萬物靜謐,法國三色旗在微風中輕輕飄動。這是一個周六的早晨七點,一個睡眼惺忪的少年在面包房買了一個牛角面包。
一個六十多歲的白胡子男人走進來。他穿著雨衣和黃卡其褲子,頭上戴著一頂有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標志的棒球帽。“女士,早上好,我要一個法棍面包。”售貨員的微笑隨即變成疑惑,因為這個男人手上已經抱著很多法棍了。十分鐘后,男人回到了他的住所,來到書架和油畫裝飾的客廳,iPad中飄出爵士樂。他把法棍放在一個橢圓形小桌子的桌布上,從一個扁平的紅色盒子中抽出一把野餐刀。
這是紐約康奈爾大學歐洲歷史研究所所長斯蒂芬·卡普蘭教授。桌子上是他一名學生的厚達800頁的論文,研究的正是卡普蘭教授的專業領域——面包。墻上掛著他的一部作品的海報,畫中的他胸前滿滿地抱著法棍,題字是“法國和它的面包——一段酷愛史”。
面對前來拜訪的我,卡普蘭教授自然也是拿出他最鐘愛的面包來招待。他用手指節骨敲擊法棍,把它放在耳邊說:“如果面包完全烤好了,敲它的一端,發出的聲音應該像鼓一樣清脆。”突然,他的臉色暗了下去:“這個面包沒有完全烤好。”
五十年前,還是學生的他來到巴黎,坐在位于巴黎第六區拉丁區盧森堡公園的長凳上,吃起他生命中的第一個法棍面包。他還記得他是如何為這種法式面包的味道所驚艷的,這和工業制作的美國白面包相比簡直是天壤之別!今天,他已經是法式面包領域的世界級學術權威,努力維護它們的品質。長棍面包是法國文化的一個如此重要的組成部分,因此,法國政府已經兩次因為他關于面包的政治、社會和宗教意義的論文給予他嘉獎。
在為他的書《尋找面包》進行關于“巴黎最好的面包房”調查研究的過程中,他和妻子瑪麗-克莉絲汀選出了600家面包房,每天花五小時品嘗面包,這一過程耗時六個月。“瑪麗-克莉絲汀增重了七公斤,因為她總是吞下面包,而我總是把試吃后的面包吐在袋子中。”他指向一個面包表面的斜紋凹痕,“這種刀痕不僅僅是裝飾,它們的存在使得氣體能在烘烤的過程中跑出去,避免長棍面包從內部撕碎。”
“我現在做的事情不一定很衛生……”他把長棍面包放在嘴邊,輕輕朝著它呼氣,“喝紅酒的人也會這樣做。他們把紅酒倒進杯子中旋轉,讓它和空氣混合,更好地釋放香氣。對白面包呼氣,它們也會變得更香。”
我聞了聞法棍面包,朝它吹了一口氣,溫暖的氣息使面包散發出堅果的香味。教授說:“我們不是品紅酒的那幫故弄玄虛的嚴肅家伙,最終標準永遠是味道,必須確保面包在食物中的地位。我們因此擁有了一套標準,可以據此就法棍進行專業的信息交流,比較它的不同類型。”
他把法棍切成小段,把鼻子深深地埋進柔軟的面包中。“有些法棍面包有馬鞭草、黑櫻桃、檸檬和蘑菇的香味。面包屑最好是琥珀色,而不是完全的白色。除此之外,蜂窩狀的小槽也是高質量的標志。大小不一的氣孔證明,面粉是按照規定發酵并正確捏出的。”
他仔細地咀嚼著一塊面包皮,高度集中的注意力使他的眉毛上揚。“我喜歡淡淡的焦糖味。這種味道比較沒有魔力,不會使我像法國意識流作家馬塞爾·普魯斯特一樣,在幻想中回憶起和法國電影女星碧姬·芭鐸開始一段愛的冒險前吃的法棍面包。”
太驚人了!我從來不曾夢想,這樣一小塊樸實無華的白面包竟然能在人腦中激起這樣的波浪。教授的眼睛閃著戲謔的光芒,然而他的語調仍是客觀樸實的。顯然,他堅信,一個烘制良好的法棍面包能夠重新喚醒心靈角落瀕于遺忘的記憶。
他切開的那個“沒有烤好的面包”遭到了他無情的批評,我不敢向他請求讓我嘗一塊。之后,他用流利的法語打著電話,拿起他的夾克,對我說:“一會兒我帶你去參觀法式面包的圣殿。”
我們來到巴黎享有盛譽的“多米尼克·賽布隆(Dominique Saibron)”面包店。一進門,我們就被陣陣新鮮面包的撲鼻香氣和黏黏甜甜的糕餅所環繞:沿墻擺設的松木架子,平放的面包,圓圓的面包球,表面撒上面粉的成束垂直放置的法棍。“面包,面包,面包!我愛它!”卡普蘭教授興奮地說。
迎接我們的是一個深色頭發的男人,系著焦糖色圍裙,上面繡著面包店的名字“多米尼克·賽布隆”,鞋子上滿是白色的面粉。這個51歲的男人曾是多家美食餐館的首席糕點師,后來他擁有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面包店,每天接待的顧客達2000人。賽布隆先生已經在日本開設了15家分店,努力使日本美食家也慢慢適應這種“小麥文化”。
“面包入口時感覺非常輕軟,能夠激起食欲。”教授說,“我喜歡黑櫻桃、甘草、甜薯和干杏的味道,加上一點香料,哇!”我小口啃著一塊面包,就是白面包的味道,然而不是那種工廠生產出來的單調乏味的面包。我繼續咬著,我的味蕾反應出水果和香料的味道。我不能做到像教授那樣準確地描述這種感覺,我只知道我想吃更多。我問賽布隆先生:“您的秘訣是什么呢?”
“我只遵循‘訂貨型生產’原則使用面粉。”他說,“我和我的磨坊工一起去田里看小麥,按不同比例混合不同的種類。我會用它們做出法棍的式樣,并從中選出最好的比例組合。”每年的收成都不一樣,他的小麥混合比例也不盡相同。“味道才是重中之重。為了烘制出美味的白面包,必須使用高品質麥子磨出的上好面粉。我使用的面粉百分百由小麥制成,沒有任何其他成分。”
“另外,要烘制出美味的白面包,必須要有足夠的耐心。”制作面包的工藝耗時五個半小時,包括捏面粉、兩次發酵過程、成形和烘烤。法國法律規定,打著“傳統”旗號的法棍面包不能含有任何化學物質,在任何時候都不能被冷凍。
我跟隨他來到滿地面粉的面包房后部。學徒阿克塞爾正從捏面機器中拿出生面團,為每份稱重,做出長條狀,把法棍面包按一定間距放在尼龍布上。一個白色塑料瓶里裝著蜂蜜色的粘稠物質,賽布隆先生稍稍掀起它的瓶蓋。“這是我自制的發酵面團,它的成分有蜂蜜、肉桂、姜、八角、香草和肉豆蔻。酵母和鹽也不可缺少,但是用量比其他面包師用的要少。”賽布隆先生透露,在他的配方中,生面團的發酵時間比較長,鹽是來自法國東北部的高品質海鹽。我們來到面包房前部。16歲的學徒提奧用一個金屬盤小心地端出還沒有烘制的法棍面包。接著,他把面包放進一個多層烤箱中,把熱乎乎的已經烤好的面包放進一個柳枝筐中。
“為什么面包如此重要?”我問。答案很明顯,賽布隆先生聳了聳肩:“沒有面包就不能開飯,少什么也不能少面包!在巴黎,兒科醫生甚至會建議嬰兒吮吸面包。”1789年面包價格的上漲,是巴黎人民攻占巴士底獄的原因之一。今天巴黎甚至會調整市內面包師的休假時間,以便巴黎人即使在每年八月的休假高峰期也不需要跑很遠就能買到他們的“生命之泉”——面包。
在法國首都一年一度的“最佳法棍面包”比賽中,賽布隆先生于2010年獲得了第三名,2012年他沒有參加,冠軍是塞巴斯提安·莫威。他的面包店贏得了第一名,并獲得了向愛麗舍宮提供一年面包的特權。莫威先生為總統所嘉獎的法棍面包是每個巴黎人都能承受的美味,每個僅需1.05歐元。此外,每個公民都擁有在任意一家面包店買到半根法棍面包的權利。
第二天是個周日。我坐在咖啡館的露天椅子上。教堂的鐘聲敲響了,蔬菜商開始賣第一批法國草莓,游客們閑步走過,當地衣著鮮艷的波西米亞人和年輕的巴黎女士構成了一道道亮麗的風景線。
一個纖瘦的服務員給我端來黑咖啡和一個長方形的盤子,里面放著草莓果醬、無鹽黃油和切成一塊塊的半個法棍面包。我為這個法棍面包漂亮的表皮驚嘆不已,隨即決定運用新獲得的知識,在面包上吹上一口氣,享受著面包的香氣。坐在旁邊的一對芬蘭夫婦向我投來了訝異的目光。我聞著這象牙色的面包,嗯,甜瓜的味道。又一次把鼻子埋進去的時候,我在母親廚房中把面團碗舔得干干凈凈的記憶瞬間清晰起來。
我抬起頭,擦去鼻子上的面包屑。芬蘭人還在盯著我看。我無視他們疑惑的目光,也不管黃油和果醬,一口口咬著我的法棍面包。表皮發出孕育著希望的噼啪聲,給面包內部的香草香味釋放出足夠的空間,我的味蕾不禁歡欣雀躍。
在人行道上,我看著以急躁著名的巴黎人安安靜靜地站在面包房前,閑聊或是讀著報紙。是啊,如果只需支付一個法棍面包的價錢,誰會不樂意為這種每天都可享用的奢侈排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