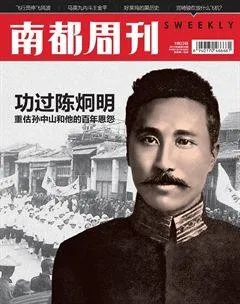好萊塢的黑歷史
1937年,美國華納兄弟電影公司一改往常以城市和女性電影為主的風格,野心勃勃地推出了《左拉傳》,講述了法國文壇巨匠左拉的一生經歷。這部片子重點描述了在普法戰爭期間,猶太軍官德雷福克斯被誣陷為向德軍出售機密情報時,左拉為他奔走平反的故事。電影一經推出就大獲成功,獲得了10項奧斯卡提名,最終奪得了最佳影片、最佳劇本和最佳男配角三項大獎。
然而,《左拉傳》卻有一個很詭異的地方:盡管德雷福克斯是片中的重要角色,但“猶太”這個詞卻從未在對白中出現;在原劇本里,“猶太”這個詞一共出現了4次,其中3處都被刪掉了,只有保留著最后一處——當法國司令審視軍官名單時,德雷福克斯的名字旁邊寫著“宗教:猶太教”,這一幕出現了一秒半。
這是遺漏錯誤嗎?還是某種抗爭的表現?《左拉傳》完美體現了上世紀三十年代好萊塢對納粹主義和反猶主義的態度:一貫屈從,偶有反抗。
近年來,包括尼爾·加布勒在內的電影大師和學者們對那段歷史的各個層面都進行了研究和揭露,不過,最近有兩本新書——本·厄蘭德的《合作:好萊塢集團與希特勒》(哈佛出版社)和托馬斯·多赫蒂的《好萊塢與希特勒,1933-1939》(哥倫比亞出版社)——的出現都打著“揭開好萊塢的黑歷史”的旗號,直指好萊塢曾與納粹進行過“深度合作”,引發了學術界的大論戰。
那么,究竟事實是怎么樣的呢?
納粹德國的審查策略
“美國人的表現手法是如此自然,遠比我們先進”,1935年,納粹宣傳部長約瑟夫·戈培爾看完《一夜風流》后在日記里寫道。當時的美國電影,包括音樂劇,在德國都非常流行。美國電影通常都非常通俗,而且極具娛樂性,而納粹時期的德國電影人則傾向于表達憤怒。這令戈培爾對美國電影的欣賞顯得十分諷刺:畢竟,他對電影業的期許是宣傳納粹意識形態,他將猶太藝術家和工人驅逐出了德國電影工業,迫使后者加入美國電影公司。
納粹將每一部電影都視為對他們純潔性的潛在污蔑。厄蘭德引用了若干納粹官員之間的對話,他們認為《金剛》(巨型猿人與北歐長相的金發美人)冒犯了德國人民“健康的種族感情”,而《泰山》(沒穿上衣的野人跟白人女性)呢?最終,《金剛》得以上映,而《泰山》則被禁播。同樣地,《疤面人》、查理·卓別林的《摩登時代》還有女星瑪蓮娜·迪特里茜,后來的所有電影也因為種種原因禁播。一旦戈培爾手下的宣傳部發現哪部美國電影中有猶太演員或者猶太工作人員,就會拒絕引進這部電影。
按理說,這些審查只影響到電影在德國的輸出,但有一個人卻能影響到好萊塢的生產端,那就是納粹德國特派領事蓋奧格·基斯林。1933年,基斯林抵達洛杉磯。如果他認為某部即將開拍或者已經拍完了準備試映的電影包含了“污蔑德國”的因素,他就會給好萊塢公司的老板寫一封信,詳細地指示應該剪輯掉哪些鏡頭。比如說,在看完1937年福克斯電影拍的《蘭瑟間諜》的試映后,他就寫了一封信,不是給福克斯,而是給“海斯辦公室”(威爾·海斯主持下的“美國電影協會”,以高壓政策而聞名):“這部電影會讓德國觀眾對制片公司產生非常糟糕的負面情緒,可能會導致一系列問題,損害到我們共同的利益。”他還暗示說,如果不刪改的話,這部電影將會在德國遭到禁播。于是,在《蘭瑟間諜》上映之前,他提到的若干修改意見就被全部接納了。
基斯林還抗議過其他一戰背景的電影——《寒夜鐵窗》(Captaured!)發生在一個德國監獄營里,而《重歸之路》(The Road Back)的原著則是被納粹深惡痛絕的《西線無戰事》同系列小說。1937年,當環球影業無視他的建議而執意拍攝《重歸之路》時,基斯林給劇組演員和工作人員寄去郵件,警告他們說,他們未來拍攝的任何電影都會在德國遭到禁播。這封威脅信被媒體刊登出來,在美國民眾中引發一陣嘩然,最終德國外事辦公室不得不再三向美國國務院保證,不會再有人對美國平民做出這樣的威脅。不過,基斯林還是基斯林,他還是保持著他的老樣子。
為什么這些制片公司要聽他的話呢?他們并未像戈培爾一樣留下日記,因而我們無法參透他們當時的想法。但多赫蒂和厄蘭德兩人都認為,其中一個明顯的原因,是因為這些制片公司想要保住德國市場,盡管威斯康辛-麥迪遜大學教授蒂諾·巴里奧的研究表示,當時德國的市場其實還沒有英國市場大。華納在1934年就離開了德國,因為納粹黨襲擊了他們當時的駐德代表(一個英國籍猶太人)。到1936年,只有派拉蒙、米高梅和福克斯還在向德國輸出電影;而且,這些公司還無法立刻收回他們的票房,那些錢被凍結在德國銀行里。
那么這樣就說不通了。商人逐利是天性,在無法拿到錢的情況下,為什么還要聽命于德國人?當時是不是還有其他勢力壓迫著他們低頭?
傳說中的“海斯辦公室”
很多人都不知道海斯辦公室的誕生是制片公司自己的決定。1922年,他們意識到,作為一個發展蓬勃卻丑聞纏身的新興產業,他們需要一個組織代表他們去華盛頓表達自己的意見。于是他們組成了美國電影協會(the Motion Picture Producers and Distributors of America),由前郵政總長威爾·H·海斯擔任主席,與此同時,他們還建立了一個道德規范,以應付國內外審查。
一開始,這些都只是裝飾性的規定。直到1934年,全美教會組織“全國道德聯盟”宣稱好萊塢及其品位低下的產品污染了美國年輕人的精神與靈魂,并威脅抵制好萊塢出品的任何電影,除非好萊塢肯接受一個“產品標準”,對其出產的電影進行政治和道德的雙重審查,以符合一定的規范。后來這個產品標準被稱為“海斯法典”,而海斯又任命信徒喬瑟夫·I·布林為總審查官,而后者恰恰是一個反猶主義者。在被任命之前兩年,布林曾在給朋友的信中寫道,他無法容忍那些擁有好工作卻只懂榨取錢財的人,而那些人之中95%都是猶太人,“他們可能是地球上渣滓中的渣滓”。

布林的規定中,大部分都關乎性跟語言,不過也有這樣一個規定:“任何國家的歷史、機構、杰出人物和公民都需要被公平地呈現。”這個規定定義之含糊,可以被解讀為,但凡提及某個外國的一丁點不妥之處,一部電影就可能被禁。于是布林和基斯林的工作在1934年就有了重合。布林會在電影開拍之前就通讀每一個劇本,并且運用“公平”原則限制或取締任何涉及納粹德國的電影。
在上世紀30年代中期,一個名叫艾爾·羅森的經紀人渴望成為制片人,他試圖為一個叫做《歐洲瘋狗》的電影籌集資金。這個電影講的是希特勒攀升至權力高點過程中一個德國猶太人家庭的消亡,從1933年起,劇本就已經在好萊塢中流傳,但沒有制片公司愿意接這個項目。結果,反而是布林看到了這個劇本,他立刻就將此視為一個嚴重的事件。他還特地為此寫下長篇大論,節選如下:“如今,猶太人已經占據了這個國家的電影工業的很大一部分,而我們有理由相信,猶太人作為一個階層,是這些反希特勒影片的幕后支柱,他們利用娛樂電影作為自己意識形態的宣傳工具。整個電影工業都因此而遭人利用。”
就用這個理由,他封殺了這個電影,以及其他許多這樣的電影。
直到戰爭爆發,布林都一直持續給制片公司施壓,要求他們不準提到納粹主義。1938年,米高梅電影公司試圖改編雷馬克的反納粹小說《三個同志》,而布林強烈要求把背景時間設置得更早一點,“這樣我們就不會被說成是在描述納粹暴力或恐怖主義了”。簡單來說,他的原則很簡單:不管納粹事實上有多殘暴,為了確保電影能“公平”對待外國,電影中絕對不能顯示出納粹的殘暴。
布林有時候會跟基斯林一起合作,而更多的時候,他是一個人做這些事情的。毫無疑問,他比基斯林更有權勢:擁有《海斯法典》的幫助,布林可以嚴重打擊一部電影在美國的市場,所以他對好萊塢的制約力是顯而易見的。
至于基斯林,他在好萊塢一直待到1941年6月羅斯福總統跟德國斷絕外交關系。在其任期上的8年里,基斯林給好萊塢帶來了不少麻煩,但不管是他,還是權力更大的布林,都不是電影公司老板們最大的恐懼。
永不停息的恐懼
后世的大人物們從東歐漂洋過海來到美國,他們一無所有,甚至沒有父親(他們的父親要么已經亡故,要么就是失了蹤)。他們渴望金錢和別人的尊敬,于是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東西來努力:沿街叫賣廢品,皮毛或者手套。然后,1905年街邊“五分錢娛樂場”興起之后,他們有了新的機會。路易斯·B·梅耶爾、薩繆爾·戈德溫、阿道夫·朱克、卡爾·萊姆勒、杰西·萊斯基和華納四兄弟分別成立了自己的公司,以一種即使是現在的IT業人士都會驚嘆的速度發展并崛起。然而,在“他們的帝國”(尼爾·加布勒語)之外,他們非常安靜并且順從,他們生怕自己犯下哪怕一點點小錯誤,他們害怕自己的權勢或者財富被奪走。
這才是他們最大的恐懼。
這種恐懼并非無所根據,因為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反猶主義已經在全美蔓延開來,在紐約和其他城市,大街小巷里都有著納粹或者支持德國的標志。在某些地方,猶太人被認為是大蕭條的罪魁禍首;不少憤怒的團體更是將猶太人對電影工業的把控視為不可容忍,并用各種手段予以攻擊。
所以,這些制片公司老板們把自己包裝進美國精神和美國夢之中,如加布勒所說,他們把電影包裝成理想國:“美國父親都很強大,家庭和睦,人民美好、勤勞、善良而且無私。”在那個美國里,沒有猶太角色的生存之地。
在這種長久的妥協和偽裝后,他們陷入了一種錯覺之中,那就是,他們必須讓基斯林和布林這樣的人決定他們的電影應該怎么拍。因為他們是猶太人,所以他們不能制作反納粹電影,也不能制作關于猶太人的電影,否則就會被視為有某種政治意圖或者結黨營私。哪怕是世界上其他地方的電影人都已經紛紛對納粹和反猶主義予以抨擊,這些好萊塢的猶太老板們卻是最后一個這樣做的。他們既悲劇又荒謬的立場,才是好萊塢被迫受制于納粹的根本原因。
原載于:紐約客 原題:HITLER IN HOLLYWOOD 原作者:DAVID DENB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