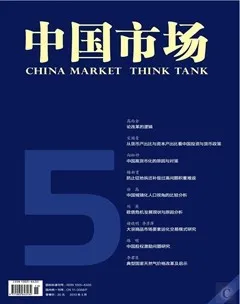防止征地拆遷補償過高問題積重難返

摘要:隨著中國經濟高增長和城鎮化的雙引擎快車,征地和拆遷逐步成為社會熱議的突出矛盾之一。目前,不少地區特別是東部地區和大城市及其郊區,部分被征地、被拆遷方索要補償要求過高以至于損害公共利益已成現實。這造成了經濟發達地區本地人與新移民之間、回遷戶與釘子戶之間等利益沖突日益明顯。征地拆遷補償要求過高,導致一些建設項目撤銷或爛尾樓甚至是“鬼城”的出現,造成了被征地拆遷方、開發建設方與當地經濟社會發展“三輸”的結局。同時,征地拆遷補償要求持續上漲壓力更加劇對國有農場土地的蠶食,助推了強大食利者集團的形成。從長遠來看,對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產生了不容忽視的負面影響。引導征地補償適度集中并流向生產性投資等措施值得堅持與實施。是防患于未然,還是坐等問題積重難返,取決于我們的認識與行動。
關鍵詞:征地拆遷;補償過高;經濟利益矛盾
中圖分類號:F292;F301
一、補償要求過高有成為征地拆遷主要矛盾之勢
無論是發展非農產業、建設基礎設施還是城市改造,都離不開征地、拆遷環節;乘著中國國內經濟高增長和城鎮化的雙引擎快車,中國房地產業已經迅猛成長為中國經濟的一大骨干產業:1992年,中國商品房銷售面積為4288.86萬平方米,銷售額426.59億元,占當年中國GDP總量(26937.3億元)的1.58%;[1]到2011年,中國房地產開發企業當年竣工房屋面積已達8.9244億平方米,竣工房屋價值21796.4億元,當年商品房銷售面積10.9946億平方米,銷售額59119.1億元,占當年中國GDP總量(471563.7億元)的12.54%。[2]幾乎與此同步,征地和拆遷也逐步成為社會熱議的突出矛盾之一。在許多案例中,失地農民和拆遷戶得到的補償過低,不僅令他們陷入生活困境,甚至釀成了一些惡性事件。有鑒于此,許多地方下了很大功夫對征地和拆遷工作進行了一系列調整,失地農民和拆遷戶所得補償水平顯著提高。正因為如此,在許多城市,破舊拆遷房價格大大高于同一地段新建中高檔房的現象已屢見不鮮。
然而,任何事物都是可能發生轉化的,昔日的被壓迫者可能成為壓迫者,征地拆遷中的矛盾也不例外。征地拆遷伊始本來就同時存在失地農民和拆遷戶補償過低、過高兩類現象,1990年代至前幾年,補償過低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而隨著失地農民和拆遷戶所得補償顯著提高,補償要求過高成為矛盾主要方面的幾率正同步日益提高。某些社會輿論先入為主地將被征地、被拆遷方視為利益受損的純潔無辜羔羊而一面倒地支持其提高要價,甚至不分青紅皂白地支持某些打著“維權”旗號的過激舉動,進一步促使此種問題來得更快、更普遍、更嚴重。
時至今日,在不少地方,特別是在東部地區和大城市及其郊區,部分被征地、被拆遷方索要補償要求過高以至于損害公共利益已成現實,遷戶為自己十幾平方米、幾十平方米的破舊危房、甚至是違章建筑索要數百萬、數千萬、乃至上億元驚人天價補償的事件不勝枚舉,而且有蔓延之勢:
上海某地一戶居民為其30平米老房拆遷索價5億元;萬達集團四川綿陽市涪城區南河片區舊城改造項目因當地居民補償要求過高而落空;山西平定縣森宇公司開發的森宇坐標城樓盤因建設規模過大、高利貸集資和拆遷高補償而爛尾;歌手左小祖咒為其岳父卞仕方房產而發起的“抗拆”風波……這些事件一次又一次凸顯了拆遷要求過高正日益向中國征地拆遷中的主要矛盾發展,一些失地農民和拆遷戶不勞而獲從社會財富中取得了過大份額,以至于造就了新的社會不公和腐化墮落,不僅導致越來越多的發展項目受阻甚至完全落空、失敗,造成被征地拆遷方、開發建設方與當地經濟社會發展的“三輸”局面,而且由此產生的社會沖突風險和矛盾也在顯著上升。
二、解剖輿論非理性偏袒釘子戶過高補償要求:左小祖咒案例
在歌手左小祖咒為其岳父卞仕方房產而發起的“抗拆”風波中,拆遷戶補償要求過高和輿論先入為主非理性偏袒的問題就相當突出。在這次2012年10月23日引爆的事件中,左小祖咒本人對采訪的新華社記者明確說:“‘釘子戶’的目的就是為了賺錢,未經我的同意就是不能拆。我只是想維護我的家庭應該得到的利益。”[3]通觀事件經過,當地此次拆遷并非無法可依,也非執法不嚴,作為拆遷指導辦法的2009年常州市武進區政府頒布的《常州市武進區征地房屋拆遷補償和安置辦法》(武政發[2009]96號)詳細規定了住宅房拆遷補償與安置的標準,甚至連屋內一只水龍頭的補償價格為8至10元也有規定,在此次拆遷執行中,村委登門丈量房屋后一個星期,業主就可收到拆遷結算單,其中會詳細計算列舉房屋補償價、屋內的裝修及附屬設施補償、搬家補助費等各項拆遷補償。[4]矛盾的焦點在于左小祖咒夫婦為其岳父開出的拆遷補償條件過高,且不準拆遷方入戶實測房屋面積,以至于當地政府難以接受;由此引起的輿論風潮更使雙方騎虎難下。
關于左小祖咒提出的拆遷補償條件,網上盛行的說法有兩種,其一是700萬元;其二是1700萬元外加三套房屋;而據《社會觀察》雜志記者采訪負責該地拆遷工作的勝西村黨支部書記蔣中行稱,蔣中行根據自己的拆遷經驗,判斷卞仕方家兩棟合計600多平方米的房子拆遷補償約在57萬左右,但是卞仕方要求一口價100萬,雙方就沒有繼續談下去了。[4]鑒于當地其他與卞仕方情況相近的村民拆遷結算單上顯示補償是24萬多元,兩次找村委“談判”后拿到36萬元補償,即使是心有不足也只是指望能拿到40萬元,而且截至2012年11月7日,當地40戶村民中已經有33戶達成了協議并實行清理,[4]這說明當地給出的補償標準并非不合理,卞仕方要求一口價100萬元確實過高。一些輿論甚至為盛傳的700萬元補償要求搖旗吶喊,更充分暴露了一些社會公眾對征地拆遷事務抱有先入為主的非理性偏袒。
引發此次事件的卞仕方房產位于常漕南路武南殯儀館以西約200米處,屬于農房,用事件發生地常州市武進區房地產市場行情衡量,盛傳的700萬元補償要求遠遠超過了合理水平。查閱新浪常州房地產門戶網站上當時當地各樓盤項目標價,不難看出,700萬元要價可在武進市區購買數百甚至上千平米商品住宅或兩套左右豪華別墅。茲列舉當地12處有代表性的房產項目物業類型、地址、主力戶型、價格如下:
常發御龍山,新盤,物業類型為普通住宅、別墅,地址在武進人民路、定安路、玉塘路,別墅起價280萬元/套,左小祖咒要價可購買兩套半。
上林國際上林君悅,在售,物業類型為普通住宅、別墅,地址在橫林鎮公園路,起價5000元/平米,左小祖咒要價可購買1400平米,折算該小區主力大戶型10套。
得園,在售,物業類型為別墅,地址在遙觀鎮宋劍湖旁,均價8000元/平米,左小祖咒要價可購買875平米,折算約兩套。
星湖丹堤,在售,物業類型為別墅、酒店式公寓、商鋪,地址在西太湖攬月灣,450~1000萬元/套,左小祖咒要價可購買一套半。
天目湖城市廣場,在售,物業類型為普通住宅、別墅、酒店式公寓、建筑綜合體,地址在天目湖迎賓路,均價11000元/平米,左小祖咒要價可購買636平米,折算60平米主力戶型10套半。
天潤國際花園,在售,物業類型為普通住宅,地址在滆湖路科教城(離左小祖咒岳父家不甚遠,更改規劃后的地鐵終點所在地),均價5600元/平米,左小祖咒要價可購買1250平米,折算143平米主力大戶型8.7套。
九州紅墅嶺,在售,物業類型為別墅,地址在太湖灣旅游度假區,起價13000元/平米,左小祖咒要價可購買538平米,折算一套456平米戶型別墅后還可剩余107.2萬元。
新城香溢瀾橋,在售,物業類型為普通住宅、別墅,地址在火炬路與光電路交匯處,均價6500元/平米,左小祖咒要價可購買1077平米,折算320平米別墅3套以上,或高層130平米戶型8套以上。
甲殼蟲工坊,在售,物業類型為普通住宅、商鋪,地址在武進體育館對面,均價5000元/平米,左小祖咒要價可購買1400平米,折算75平米主力戶型近19套。
綠地香頌花園,在售,物業類型為普通住宅、公寓,地址在聚湖路南,均價6300元/平米,左小祖咒要價可購買1111平米,折算123平米主力大戶型9套有余。
聚湖雅苑,在售,物業類型為普通住宅,地址在長江路與312國道交叉處,起價4880元/平米,左小祖咒要價可購買1434平米,折算174平米主力大戶型8套有余。
天安數碼城,在售,物業類型為寫字樓、商鋪、建筑綜合體,地址在常武南路紅星美凱龍對面,均價5500元/平米,左小祖咒要價可購買1273平米。①
綜上所述,憑借這樣一處地段并不好的普通農房,700萬元拆遷要價可以換來當地品質較好、檔次較好的綠地香頌花園小區3套123平米大戶型(合計232.47萬元),外加市區天安數碼城850平米鋪面。如此要價,是否屬于天價,是否遠遠高出了合理水平,是否構成了對征地方的不勞而獲的不合理剝奪,答案顯而易見,更何況這樣的農房拆遷戶通常能夠另外得到一處宅基地補償。許多媒體和評論員支持這樣的要價,離實事求未免太遠;而這樣的不合理要價卻可以得到掌握話語權力者如此普遍的支持。
三、征地拆遷補償要求過高制造經濟社會矛盾
目前,至少在東部地區和大城市及其郊區,征地、拆遷補償已經成為當地居民期盼的飛來橫財,許多失地農民和拆遷戶拿到了巨額補償,以至于大城市及其郊區的拆遷戶已經成為購買進口豪華車的生力軍。2011年初,中國汽車流通協會調查發現,2010年北京銷售的8萬輛進口車中一半賣給了北京和各地的拆遷戶,特別是北京拆遷戶。當時調查人員在擴建后的北京南苑機場一帶發現,機場周邊村莊豪華車數量眾多,密度特大,進而發現那一帶拆遷戶拿到兩三千萬元補償者司空見慣。[5]由于缺乏相關統計,我們目前還難以準確估算征地拆遷補償總額和人均補償金額,但眾多類似購買豪華進口車之類的跡象足以從側面印證,征地拆遷補償水平已經相當高。
勞動是一切財富的最終源泉;在征地和拆遷中,被征地拆遷方并沒有為建設直接付出勞動,征地和拆遷補償歸根結底是非農產業生產者及其消費者、商品房購房者、城市新移民向失地農民和拆遷戶的財富轉移,這種財富轉移規模過大,無異于對非農產業生產者及其消費者、商品房購房者、城市新移民等群體的壓榨盤剝,在經濟方面的負面效果自不待言,而且必然因其不公而造成社會矛盾。畢竟,土地增值歸根結底源于這塊土地及其鄰近地區基礎設施的建設、非農產業的發展和人口的增長,由社會共同勞動創造的土地增值收益倘若由被征地方、被拆遷方獨享或取得大部分收益,既不合理也不公平。而且,土地市場價值增量中還有相當一部分源于嚴格的土地管理制度,這種嚴格的土地管理制度又是為了確保國家糧食安全以及宏觀經濟與社會穩定所必需,以免過多農地被占用而貽禍于子孫乃至當前,把這部分市場價值增量劃歸被征地拆遷方更不合理;但在市場體制下,發展中國家政府越是有效率,越是實施嚴格的土地管理制度,土地房產被征用拆遷一方就越有條件索取高額補償。在某些情況下,上述矛盾甚至會以相當激烈的方式爆發出來。隨著被征地拆遷方補償水平的提高,這種矛盾沖突的頻率和烈度也將趨向上升。盡管流行觀點主張大幅度提高被征地拆遷方分享土地增值收益的份額,甚至由被征地農民獨享土地增值收益,從而根本顛覆現行的土地制度,但我們不能因為征地拆遷補償收益過低問題以前較為普遍、現在仍然存在就看不到走向另一個極端將制造的更多、更大的矛盾和沖突。
在現實生活中,在經濟發達地區的本地人與新移民、外來工之間源于拆遷補償過高的經濟利益沖突已經明顯上升。與外來移民、特別是外來勞工必須勞心勞力以求站穩腳跟不同,本地居民因占有先天地利而能獲得較多的資本增值收益,特別是土地、房產增值收益;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本地居民往往更容易獲得相對輕松的崗位。這種局面有其必然性與合理性。但假如本地居民無需勞動即可獲得的資本增值收益太多,而外來工待遇又不合理,看不到向上提升的希望,窮畢生之力也無望圓住房夢,這種經濟利益之爭就會浮現。新世紀以來10余年我國流動性過剩,資產市場泡沫橫飛,這已經成為我們面臨的現實問題。如果我們偏頗地強調“增加居民財產性收入”,強調“拆遷者權益”,即使能夠收獲部分占據優勢地位者一時的喝彩,卻必然損害“沉默的大多數”,畢竟拆遷戶的補償最終都要由后來者埋單,而后來者絕大多數是普通的工薪階層。接納外地新移民最多的廣東省近年之所以連續發生本地居民與外來工之間的暴力沖突群體性事件,根源即在于此。
新移民、外來工是征地拆遷補償過高的受損者,而我國已經步入新的大規模人口流動時期,城鎮化人口中恰恰有很大一部分源于新移民;城鎮化的進一步發展將推動這一比例繼續上升。在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中,居住地與戶口登記地所在的鄉鎮街道不一致且離開戶口登記地半年以上的人口高達26139萬人,接近美國全國人口總數;其中市轄區內人戶分離的人口為3996萬人,不包括市轄區內人戶分離的人口為22143萬人。同2000年人口普查相比,居住地與戶口登記地所在的鄉鎮街道不一致且離開戶口登記地半年以上的人口增加11700萬人,增長81.03%;其中不包括市轄區內人戶分離的人口增加10036萬人,增長82.89%。不考慮已經取得移入地戶籍的人口,僅將不包括市轄區內人戶分離的人口定義為新移民,其人數(22143萬人)也占2010年末我國城鎮人口66978萬的33%。[6]換言之,征地拆遷補償過高,結果是使得1/3的城鎮居民成為現實和潛在的受損者。若再考慮到已經取得移入地戶籍的新移民中也不乏“房奴”之輩,這類受損者人數之多,更不容忽視。我國城鎮化已經取得了長足進展,2011年末城鎮化人口比例51.3%,[6]首次突破50%大關,且中央政策指導思想是將城鎮化作為下一階段經濟發展和擴大內需的主要動力之一,過高的征地拆遷補償要求則給這一戰略埋下了經濟和社會安定雙重隱患。
不僅如此,由于少數“釘子戶”補償要求過高,導致建設工程受阻遲遲不能開工,或基本完工后留下梗阻地段多年無法收尾,這樣的案例在全國各地都已經屢見不鮮,涉及住宅、商業、道路等多種建設項目。在這種情況下,受損者不僅是新住戶,大多數接受條件的回遷戶合法權益也嚴重受損,多年無法回遷,蒙受巨大經濟損失和生活上的嚴重不便,與少數釘子戶之間的矛盾也相應滋生,即使釘子戶最終要求得逞,也已經無法在原來的社區立足,只能遷走。在虛妄地美化釘子戶為“維權英雄”的偏頗輿論壓力下,許多地方政府被綁架而不敢作為,致使這種矛盾常常發展到相當激烈的程度,以至于發生暴力沖突:
由于釘子戶李桂君等少數幾家作梗,河北省衡水市原精工機械廠家屬院改造項目多年無法實施,有最終落空之虞,數十家回遷戶被迫在外流落5年多,經濟損失慘重,生活極為不便,激憤絕望之余,他們于2012年12月1日集體闖入李桂君家打砸。
廣州楊箕村舊村改造于2010年6月份開始動遷,規劃2011年年中開工建設新村,全村1405戶村民2014年年中全部回遷。然而,動遷至今2年已經兩年半,楊箕村舊村改造項目仍然在少數“釘子戶”阻撓下停留在拆遷階段:2012年12月,仍有8家“釘子戶”。不足村民總數1%的“釘子戶”令99%的村民回遷遙遙無期,已簽約村民負擔的住房租金不斷上漲,村民兒童長年起早摸黑從四面八方趕到村旁臨建的小學上課,更有100多位老人在等待回遷期間相繼去世。正因為大多數村民合法權益嚴重受損,上千名楊箕村民于2012年12月16日聚集村口,拉起抗議橫幅,要求仍然留守的8戶人家搬遷。
這類事件的絕對數量已經不容忽視,且其增長趨勢難以停止。在目前偏頗的輿論環境下,加之房地產市場價格已經大幅度上漲,由于類似原因而爛尾的項目有增多之勢,絕望回遷戶與釘子戶之間的沖突也必將趨向上升。
不是依靠辛勤勞動,而是依靠拆遷得來的巨額橫財使得不少拆遷戶迅速養成了揮霍的生活方式,甚至徹底腐化墮落。早在1980年代后期、1990年代初,珠三角經濟的發展就使不少當地居民因被征地、拆遷而暴富,其中相當一部分人缺少技能而無法獲得高薪工作機會,又因為暴富而鄙視辛苦的一般勞動,于是坐食征地、拆遷的補償而終日無所事事,其子女也多為因家庭不勞而獲暴富頗多而無心向學之輩,最終坐吃山空,等而下之者還成為吸毒等犯罪行為的高發群體。目前,因征地、拆遷補償導致家庭、社區關系扭曲惡化的事例更是屢見不鮮。
四、征地拆遷補償要求過高導致“三輸”結局
部分人為征地拆遷補償索價過高而導致被征地拆遷方、開發建設方與當地經濟社會發展“三輸”的案例已經為數不少,而且還在日益增多,無論是東部發達地區還是中西部欠發達地區,都不例外。
就當前而言,“三輸”主要表現在過高的征地拆遷補償導致一些建設項目撤銷或爛尾。
典型如萬達集團放棄四川綿陽市涪城區南河片區舊城改造項目。2009年10月,綿陽市政府與萬達集團簽訂框架協議,萬達集團擬投資60億元參與綿陽市涪城區南河片區舊城改造,開發建設包括百貨、酒店、餐飲、娛樂、住宅等綜合業態的綿陽萬達廣場,占地218.2畝。但當地居民拆遷補償要求過高,經過拆遷摸底匯總,拆遷要價高達29億元,幾乎占計劃投資總額的一半。盡管萬達集團董事長王健林生于綿陽,如同大多數中國人一樣有回報家鄉的情結,非常看重南河片區改造項目,但面對超過項目承受能力的拆遷補償要價,經過半年摸底、協商,萬達集團最終不得不于2010年三四月間最終決定放棄南河片區項目,并一度打算撤出綿陽。
在這類因拆遷補償要求過高而導致建設項目撤銷的案例中,當地居民喪失的不僅僅是在可預見的未來大幅度改善居住條件的機會,進而只能繼續居住破舊、雜亂環境中的小房子中,而且也喪失了可預見的更好的就業機會,因為改造后的舊城區或城中村能夠吸引層次高得多的企業機構入駐,當地居民不管是到這樣的企業機構就業,還是自己成立公司為其提供服務配套,都有近水樓臺之便。即使是那些已經搬遷到較好地段居住、只是把此處舊城區或城中村房屋出租的居民,他們也損失了大大提高租金收入的前景,而且因不確定性而降低了他們持有的這些舊房屋在市場上的流動性。因為舊城改造項目雖然已經被放棄,但當地許多業主對拆遷和房價上漲的預期卻已經大大提高,而且難以降低,買方則因為開發商放棄改造項目而對此抱有較低預期,這類舊城區或城中村房產成交流通的難度由此大大提高。時間拖得越久,當地城市發展越快,周邊地區建設改造水平越是提高,這類錯失改造機遇的舊城區或城中村就越難改造,因為業主預期價位與買方預期價位落差會在這個進程中進一步拉大,改造該地區的獲利空間日益壓縮而令投資者卻步,最終結果是這片舊城區或城中村向貧民窟方向發展。
而且,在這類情況下,社會輿論越是一邊倒地聲援拆遷戶索取高要價“維權”的主張,業主預期價位與買方預期價位落差就越大,潛在投資者越覺得政治性風險大而卻步,這片舊城區或城中村向貧民窟方向發展、固化的幾率也就越高。即使某些業主感到自己原來預期價位過高而意欲降低至合理水平,也有可能被這類非理性輿論氛圍綁架而無法采取自主行動。
更糟糕的是,拆遷補償過高而對違章建筑處罰不嚴,這樣的政策組合必然造就個體理性而集體非理性的結局,因為這樣的政策組合從一開始就激勵了城中村居民大量修建違章的“親嘴樓”、“握手樓”,并盡力加高。城中村居民借此貌似可以立于不敗之地:不改造時能獲得大量租金收入,改造時要求按面積獲得1.3倍乃至3倍補償,可頓成富豪。但這樣一來地方政府和開發商因無法承擔巨額成本和虧損前景而喪失了改造的能力,只能轉向開發新區,這樣的城中村也就只能加速向貧民窟淪落了。
建設項目征地拆遷補償過高,即使勉力為之,結果也很有可能是爛尾,令被征地方、拆遷戶所得承諾淪為泡影。由于油畫家、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朱維民的一篇微博,山西平定縣森宇公司開發的森宇坐標城樓盤爛尾事件引起了全國性關注;在分析森宇公司資金鏈斷裂原因時,負責此案善后的平定縣委常委、政法委書記楊艷紅就指出,除了受整個經濟形勢影響和攤子鋪得太大之外,森宇公司實際控制人李小虎承諾的拆遷補償過高也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原因—— “別的開發商拆遷補房比例一般是1比1.3,李小虎竟是1比3,平定那么多開發商算著都賠錢,可他敢干。”過高的拆遷補償也許能夠招來一時的喝彩,但在氣泡不可避免的破滅之后,拆遷戶就不得不面對現實了。在森宇公司一案中,根據媒體報道,當地社會傳言被拖累的除了4000多戶拿不到房子的購房人,還有近2000家拿不到本金及利息的集資戶,2000多回遷無望的拆遷戶,加上被拖欠工程款的施工單位、供貨商、拿不到工資的森宇員工,合計涉及幾萬人,近萬個家庭。而根據楊艷紅介紹的情況,初步查明,截至2012年4月28日,森宇坐標城項目共收入預售房款6.1億元,銀行貸款1.3億元,尚欠銀行貸款1.3億元、城市基礎設施費2400萬元、人工費7200萬元、稅金6320萬元、土地費4280萬元。只有2.9億元支付了工程款。根據收入支出情況,尚有3.2億元(不包含銀行貸款1.3億元)資金不能查明去向,目前該公司資金賬戶余額為零;而要把森宇坐標城房子交到購房人手中,整個資金缺口有4.75億元。如果森宇公司不鋪那么大攤子,不開出那么高的無法兌現的征地拆遷補償,也就無需訴諸利息高達2分、3分乃至4分的非法高息集資,這一切悲劇也就可以避免了。
五、征地拆遷補償要求持續上漲壓力加劇中國“鬼城”問題
雖然中國的城市化進程正在凱歌行進,且政府已將城鎮化列為驅動經濟社會發展的頭號引擎,但除了玉門等一批資源枯竭的老資源型城市之外,中國還有一批城市的某些局部已經出現了“空城”景象。盡管尚未達到美國底特律市那種十足“鬼城”的程度,但空空蕩蕩的小區在全國許多城市已不鮮見,更出現了鄂爾多斯康巴什新區這樣整個城區建筑和園林苑囿豪華卻荒無人氣的“鬼城”。
中國“鬼城”之所以出現,在相當程度上是持續十年之久的房地產牛市的產物。正是在持續的房地產牛市中,不僅房地產業界,整個中國社會都形成了房地產價格持續上漲的預期和觀念,房地產開發商、銀行、政府、拆遷戶等有關各方基于上述觀念而采取的行動最終造就了一批空城,其中,通過影響開發商和政府的預期與決策,征地拆遷補償要求大幅度上漲的壓力對此施加了不可忽視的作用。
由于征地拆遷補償及其要求大幅度上漲,許多城市的決策者和開發商情愿舍棄人口較多、因此空置風險較低的老城區,轉向人口稀疏得多、空置風險也因此高許多的新區。因為舊城區和城中村征地拆遷補償要求過高,如果仍然堅持改造舊城區、城中村,開發商就有虧損之虞,當地黨政領導則要冒出現“釘子戶”鬧事而影響甚至中斷其政治生命之險。
同時,基于對房地產價格和征地拆遷補償要求持續大幅度上漲的預期,不少地方政府決策者擔心日后建設項目會因補償要求太高而無法開展,即使感到吃力也要硬著頭皮先把新攤子鋪開,而且規模盡可能求大。許多決策者不是看不到此舉對地方財政的壓力,也不是看不到陡然鋪開這么大的攤子建設新區很有可能造就一片嶄新的空城,但他們相信隨著城鎮化推進,源源流入的新移民終將填滿今天的空城;但今天倘若不鋪開這么大的攤子,固然可以避免眼下的空城問題,但日后想要建設的時候政府和開發商的財力恐怕已經跟不上征地拆遷補償要價漲幅了。
加上“土地財政”和其他因素的作用,共同造就了中國百城競建“國際化大都市”的奇觀。有報道稱,截至2008年,全國共有直轄市、省轄市、地級市、縣級市221個,其中竟有183個提出要建成“國際化大都市”,占上述城市總數的82.4%,占全國667個城市總數的27%。與此同時,“空城”問題也開始出現并蔓延開來。
六、征地拆遷補償要求持續上漲壓力威脅國有農場土地
征地拆遷補償要求持續上漲的壓力必將而且已經驅使許多地方政府和企業將眼光投向國營農場,因為國營農場都是國有土地,倘若用于工商業、房地產等項目開發,無需經過高成本、費時費力而且政治風險難以預期的向農民征地程序。由于國有農場生產率高,人均耕作面積較大,征用同樣多的土地,與向農民征地相比,受影響而需要補償的人數相對較少,也更容易安置。
對于征地補償要求過高的農民而言,這樣一種個體理性選擇也存在幾個方面的潛在負面后果,其中比較突出的一點是有危及大城市“菜籃子”之虞,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加重當地通貨膨脹壓力。因為國有農場是我國農業生產的一支生力軍,由于耕作大面積連片耕地,建立了統一的水利灌溉、交通運輸等系統,其技術裝備水平和生產效率均非一般小農所能企及。2004-2011年間,國有農場總產值從977.9億元上升至2803.9億元,全國農業總產值從18138.4億元上升至41988.6億元,國有農場占比從5.7%逐年上升至6.7%。②這個比例雖然絕對數字不算高,但國有農場勞動生產率和農產品商品率遠遠高于一般小農,其質量控制水平也遠遠高于高度分散的小農,這使得國有農場對城市農產品市場供應意義格外突出。特別是在一些大中城市,為了保障城市居民副食品供應,從建國初年起,國家就在各主要城市郊區選擇荒地設立了一批國營農場作為這些城市的“菜籃子”,經過數十年的辛勤耕作開辟,昔日荒地已成膏壤,在所在地城市蔬菜等副食品市場常常發揮著“四兩撥千斤”的調控作用。
單純從耕地總量數據看,“保護國有農場土地”之說似乎是無的放矢,因為我國國有農場耕地總面積近幾年是增長的,2004-2011年,國有農場耕地總面積依次為482.01萬公頃、503.81萬公頃、518.70萬公頃、530.81萬公頃、549.89萬公頃、559.83萬公頃、598.93萬公頃、611.63萬公頃,②逐年上升;問題是耕地總量增長掩蓋了其區域分布的變化,亦即東部和中部地區、城市郊區國有農場耕地明顯萎縮而東北、西北偏遠地區國有農場耕地擴張。盡管目前還查不到系統的調查統計,但根據筆者實地所見,東部和鄰近城市的國有農場土地近年來被形形色色的“開發”項目蠶食甚多,而這些地方的土地正是生產力最高的。在有的大城市近郊國有農場,筆者乘車行進上十公里,沿途房產、工業項目連綿不絕;這些樓盤可能品質甚佳、風物優美,但當筆者意識到這是建在國有農場、昔日的“菜籃子”基地上時,不能不感到一陣陣心悸。根據相關資料和親身見聞,可以判斷,近年增加的國有農場耕地主要分布在東北和西部較為偏遠的地區,而這些地區土地的生產力不能與遭到蠶食的東部、鄰近城市的國有農場土地相比,而且更多地用于種植生產糧食、棉花、油料、糖料之類大宗作物,較少也不甚適合向大城市供應新鮮蔬菜,而這正是城市居民每天生活不可缺少的。全國國有農場數目在2004-2011年間之所以從1928個一路減少到1785個,③原因之一就是東部和中部地區、城市郊區國有農場耕地萎縮。在“開發”的熱潮中,在征地拆遷補償要求持續上漲的壓力下,盯上城市郊區“菜籃子”的地方和機構還將進一步增多。
七、征地拆遷補償要求持續上漲可能形成強大食利者集團
從長遠來看,征地拆遷補償過高必將對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產生不容忽視的負面影響。實體經濟部門、特別是物質生產部門是一個國家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根基所在,而從1980年代泡沫經濟時期的日本,到1990年代以來的香港、臺灣,再到近10年以來的溫州,房地產價格過高過度抬高實體經濟部門經營成本、導致產業空心化的后果已為世人所熟知,更不用說房價問題在今日中國大陸已在相當程度上發展成為事關社會穩定的政治問題,而過高的征地拆遷9b06cfab3085b3446388b6acd68da39e補償歸根結底必然要體現在房地產價格上。不管打著何種貌似“正義”的名義,指望維持、甚至進一步提高本來已經相當高的征地拆遷補償而不提高房產價格,那只不過是不可能實現的空想。如果在征地拆遷索取過高補償的進程中形成了一個強大的食利者集團,那就更有窒息經濟社會進步之虞。一旦中國房地產市場泡沫開始破滅,僵硬的、向下剛性的征地拆遷補償要求還將妨礙市場及時調整的靈活性,從而加大泡沫破滅的沖擊。是防患于未然,還是坐等問題積重難返,取決于我們的認識與行動。
八、結束語
無論是公共事業建設,還是商業性開發,我們確實應當給予失地農民和拆遷戶合理的補償,但這絕不等于要鼓勵他們過上不勞而獲的寄生性生活,更不等于要給予他們遠遠超過市場行情的天價補償。任何財富歸根結底來自勞動創造,鼓勵財富如此轉移的社會注定不可持續。中共十八大報告提出,要“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而提高“勞動報酬比重”與過高的征地拆遷補償是不相容的。
正因為如此,2010年,國務院法制辦公布《國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與補償條例(第二次公開征求意見稿)》之后,很多人要求規定補償上限,以防止過度補償。最終在2011年1月公布的《國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與補償條例》在第十九條、第二十條對此作了規定,力求兼顧避免拆遷暴富與侵害拆遷戶合法權益。其中,第十九條規定:“對被征收房屋價值的補償,不得低于房屋征收決定公告之日被征收房屋類似房地產的市場價格。被征收房屋的價值,由具有相應資質的房地產價格評估機構按照房屋征收評估辦法評估確定。對評估確定的被征收房屋價值有異議的,可以向房地產價格評估機構申請復核評估。對復核結果有異議的,可以向房地產價格評估專家委員會申請鑒定。房屋征收評估辦法由國務院住房城鄉建設主管部門制定,制定過程中,應當向社會公開征求意見。”
第二十條規定:“房地產價格評估機構由被征收人協商選定;協商不成的,通過多數決定、隨機選定等方式確定,具體辦法由省、自治區、直轄市制定。房地產價格評估機構應當獨立、客觀、公正地開展房屋征收評估工作,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干預。”
在征地補償方面,中共十八大報告提出,要“改革征地制度,提高農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就總體而言,適度提高農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是正確的,但現行土地制度的基本框架不宜顛覆,因為現行土地制度本質上更有利于農民進入非農產業贏得可持續的發展機會。在中國現行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下,一個村集體被征用土地所得貨幣補償有義務在整個集體內部公正分配,或留作發展基金;由于承擔成本和獲得補償的是同一主體,因此,只要保證村集體內部的廉潔,就能落實內部公平和發展需求,由此招致的農民集體內部矛盾也相對較少。同時,現行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為被征地農民創造了更多的機會以平等身份進入正規經濟部門就業,或持續分享其收益,或兼而有之。因為現代工商實業項目啟動資本門檻較高,單個普通農民所得征地貨幣補償通常達不到這一門檻,難以憑所有者身份進入被征地后發展起來的正規經濟部門,加之知識、技能方面存在欠缺,不少被征地農民往往只有兩個選擇:要么是做點“提籃小賣揀煤渣”式的小生意在非正規經濟部門謀生,要么是進入正規經濟部門打雜。但在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下,只要當地集體經濟管理者具有一定行動能力,沒有選擇將征地收入分光吃凈,而是留下足夠數量的發展基金,這個集體就能夠跨越啟動現代工商實業項目的資本門檻,為其成員贏得以所有者身份分享正規經濟部門收益的可持續的機會,而具有這樣身份的被征地農民也有更多的機會在正規經濟部門贏得體面的收入就業機會,以及培訓提高技能的機會。而且,以中國之大,各地發展狀況千差萬別,不少地方農民征地補償已經相當高,在土地增值收益中所占比例已經不低,更重要的是引導征地補償適度集中并流向生產性投資,為失地農民提高自身素質和創造新的體面收入勞動就業機會而提供條件。
注釋:
① 見新浪樂居常州武進區,http://data.house.sina.com.cn/cz/sech/754-0-0-0-0-0-0-0-0-0-0-0-0-0-0-0-0-0-0-0-0-1.html。
② 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鑒-2009[M]. 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09: 466,495;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鑒-2012[M]. 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12: 466,495。
③2004—2011年歷年國有農場數目為1928個、1923個、1896個、1885個、1893個、1818個、1807個、1785個。數據來源為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鑒-2009》第480頁;《中國統計年鑒-2011》第493頁;《中國統計年鑒-2012》第495頁。
參考文獻:
[1]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鑒-2011[M]. 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11:195,197.
[2]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摘要-2012[M]. 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12:58—59.
[3]楊紹功.網傳音樂人左小祖咒房屋 “被強拆”事件調查[EB/OL].[2012-10-27].http://news.xinhuanet.com/local/2012-10/27/c_123877141.htm.
[4]唐逸如.獨家調查:“左小祖咒”老家拆遷始末[J].社會觀察,2012,(12).
[5]蘇暉.拆遷戶買豪車就是炫富[N].汽車商報,2011-12-21(4).
[6]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摘要-2012[M]. 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12:39.
(編輯:周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