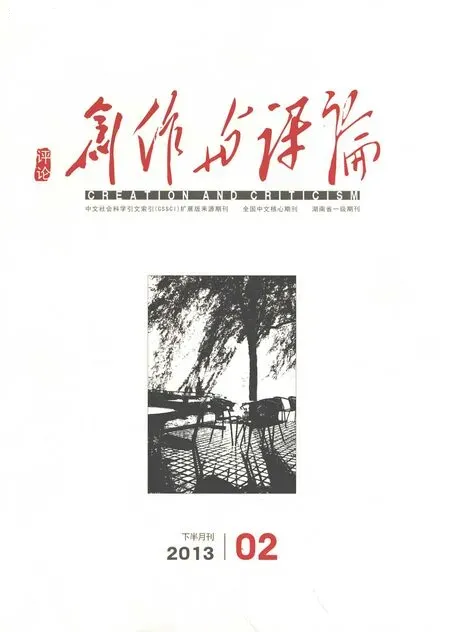中西繪畫的造型語言比較:以書入畫與以線造型
○ 魏紅珊
沃林格爾認為,造型藝術的出發點乃是線型之抽象。回顧早期東西方繪畫,繪畫都是從運用線條勾勒形象開始的。就歐洲而言,早期希臘繪畫中的“線條”給我們留下至深的印象。愛琴文明時代的克里特“迷宮”壁畫,其線條運用得精美絕倫,令人驚嘆不已!希臘瓶畫也以線造型。在中國,線條一直是國畫表現語言之基礎,線條之重要性于國畫可謂彌足珍貴。而且,經過“筆墨”傳統的洗禮,線條于中國繪畫已獨領風騷,自具美學風范。若將其與西方繪畫中的線條作一番比較,是十分有趣的。
除中世紀之外,傳統西方繪畫的線條無不嚴格地服從造型的要求,是一種描繪性的線條。15世紀,佛羅倫薩抒情畫派大師波提切利放棄了當時意大利畫家競相追逐的塊面造型方法,有意用線條描繪形象。在他的作品中,線條流暢蜿蜒,充滿韻律之美。然而,波提切利筆下的線條又并非僅考慮形式韻味的唯美主義的線條,而是緊貼對象真實體積和運動,隨形體的體面變化而自然形成。法國新古典主義繪畫大師安格爾把這種描繪性的線條發展到了極致。他的鉛筆素描畫《帕格尼尼像》是偉大的音樂家帕格尼尼的一幅肖像。其用線粗細長短參差變化,細膩與奔放雜糅并陳;長線如提琴拉出的柔穩長音,短線如飛跳弓拉出的叮咚之聲。而且,任一線條與形象的輪廓和人體運動的節奏吻合。使其線條剛柔并濟、絲絲入扣,自然如行云流水。
同樣,中國畫之用線當然也始于表現形象的需要。不過,在實現造型的功能之外,線條的審美獨立性卻與日俱增,已成為一種獨具東方韻味的線條美學。東晉畫家顧愷之的線條就被人們譽為“春蠶吐絲”,在發揮其描繪性的同時,顯示了中國畫家對線條風格的追求。
在唐代以前,早期中國畫的線條運用都還是粗細基本一致的“高古游絲描”、“琴弦描”或“鐵線描”。到了盛唐畫家吳道子那里,線條開始有了粗細的變化。吳道子之所以備受后人推崇,不僅由于他塑造了許多撼人心魄的人物形象,更重要的是他對線描藝術表現力的獨特感悟和發掘。吳道子空前提高了中國畫運用線條的表現力,他的線條在運筆的急緩節奏中摻入了粗細轉折的變化,被人形容為“莼菜描”。其筆力勁放,磊落逸勢,有“吳帶當風”之美譽。可憾其真跡無一件傳世,唯有一件宋代的紙本摹作《送子天王圖》,可讓人一睹其畫風。這是后人根據他所創作的一幅壁畫的粉本臨摹下來的。作品描繪了佛祖釋迦牟尼降生的故事,故又名《釋迦降生圖》。畫面很有動感,得益于線條的氣勢。現傳北宋最杰出的宗教人物畫家武宗元(?-1050)的白描畫《朝元仙仗圖》所用線條即為“莼菜描”,深得“吳帶當風”之意趣。作品描繪南華天帝君和東華天帝君率道教眾神前去朝覲道教最高神祇——元使天尊——時的儀仗行列,所繪神仙共87人。1939年,中華書局影印出版了由徐悲鴻收藏的《八十七神仙卷》,僅殘缺最前一名神將。當為武宗元畫稿的進一步加工,用線更纖細綿密,技法更趨成熟。畫中人物雖排列密集,但高下參差的形象安排和流動飄逸的衣紋、飾帶化解了構圖的呆板,化靜為動,使朝覲隊伍看上去有緩緩前行之感。至此,中國畫線條的表現力和風格化趨勢便進一步顯露出來。
北宋畫家李公麟(1049-1106)在前人的基礎上開創了“掃去粉黛,淡墨輕毫”的白描畫風。他的畫不著色而全憑變化多端的墨線,輔以淡墨微染來表現對象。這種風格上承吳道子,下啟趙孟頫,最終確立了線條的獨立審美價值,對宋元白描花鳥畫、元明清白描人物畫均有重要影響。
至南宋,梁楷創立“減筆人物畫”,如其笑傲王侯的灑落、狂放性格一般,他的畫寥寥數筆便能收到神氣粲然的效果。如《太白行吟圖》用幾條簡括、粗豪的墨線,就把李白那種才思橫溢、縱酒放歌、“斗酒詩百篇”的詩仙氣度刻畫得入木三分。《六祖斫竹圖》描繪六祖慧能斫竹的情景,用線分別狀貌,自然貼切,人物衣衫用“折蘆描”繪出。梁楷“減筆”畫的神韻在于逸筆草草,以一當十,代表了中國畫由以形寫神到以意寫形的轉變,為元明清大寫意繪畫風格的形成和發展提供了范例。
晚明人物畫家陳洪綬(1598-1652)所作人物畫造型奇特,用線遒勁,尤有“易圓以方,易整以散”的形式風味,開辟了一條“寧拙勿巧,寧丑勿媚”的藝術道路,令畫壇為之一新。其用線頗富刀刻味,是為了適應白描與版畫的結合。他與徽州版刻名手黃子立合作的版畫《水滸葉子》、《博古葉子》等形象生動,流傳廣遠。至此,線條自身的美學獨立性漸趨成熟。
叔本華曾說:一切藝術都希望達到音樂的狀態。對西方人來說,音樂是聲音的形式,是聽覺中的旋律和節奏;而對中國人來說,音樂卻是生生不息的陰陽變化,是自然世界無窮無盡的天籟。中國音樂在表現工具與技巧上未曾達到西洋音樂的高度。中國古人對“樂”的感悟,常常并不通過音響的結構組織來表現,而是直逼其內在旋律——這種旋律是大自然節奏與主體心靈應和無間的產物——沒有什么力量推動古代中國人去創制如鋼琴一類的大共鳴樂器;中國樂理也從來不像西洋樂理那樣精密復雜。然而,這些先天不足卻通過書法的“舞”得到了補償。作為獨一無二的中國傳統藝術,書法推動中國畫將線條從造型手段升華為美學對象,由此建立了別具一格的東方“線條美學”,從而與西方造型藝術的“塊、面、體”的美學拉開了距離。我們知道,西畫固然也運用線條,但那是面和體的結構或對象運動的形態反映。中國傳統繪畫不僅主動地以線造型,而且盡其所能地發揮線條獨立的審美表現力,表現線條的韻味和意趣。這也正是它之所以能與書法建立聯系的直接原因。
中國畫的用筆方式經歷了“以書入畫”的過程。書法在中國傳統藝術體系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它實際上是中國繪畫跨越時空、溝通視聽的橋梁。在靜態線形的另一頭是“舞”——流轉于時間中飛揚的舞蹈——書法正是直接受啟于“舞”;而“舞”又伴隨著永恒的樂之動感——旋律和節奏。唐代張旭見公孫大娘舞劍器而悟草書,書與舞相通;吳道子觀裴將軍舞劍而畫法大進,畫亦與舞相通。如果說書法是空間化的舞蹈,那么通過書法,中國畫的線條就是視覺化的音樂。
書法的審美形態突出地體現了時間藝術向空間藝術延伸的特點。線條運動時留下了書寫過程的信息,視覺地展現出時間結構。姜夔說:“余嘗歷觀古之名書,無不點畫振動,如見其揮運之時。”①對其他空間藝術門類來說,運動感只是一種暗示,但書法藝術卻通過連續不斷的線條運動,幾乎把這種暗示推向了一種臨界點,時間即將侵入空間的邊界了。
書法掙脫了視覺形象的復雜性,以單純的線條,以線的速度和方向顯示了“運動”最純凈的視覺性,成為我們在空間維度上感知運動的最單純的形式。書法雖然屬于空間形態的藝術,卻有著時間藝術的屬性。這種屬性主要體現為筆勢,即運筆的過程與運動軌跡。就創作來說,是時間帶領空間運動;從鑒賞來說,是空間暗示時間的軌跡。用筆中的提按、頓挫、縱橫、起止、轉折、回環、順逆、輕重、疾徐、澀滑等等,構成了筆勢的內容。不過,真、行、草、篆、隸各種書體表現時間性的程度并不是平均的,其中,草書的運動感和對時間性的表現最為強烈,因而成為最具表現力的書體。張懷瓘說:“草與真有異,真則字終意亦終,草則形盡勢未盡。或煙收霧合,或電激星流;以風骨為體,以變化為用……或寄騁縱橫之志,或托以散郁結之懷;雖至貴不能抑其高,雖妙算不能量其力。”②也正因其變化多端,草書成為“以書入畫”的直接媒介。
書法以其強烈的時間感和鮮明的運動感表現了書法家的情感起伏和心靈狀態,如音樂一樣對應著心靈運動的過程,同時還將情感和心靈的運動變成了穩定的視覺軌跡,它把音樂般的情感表現轉換成了平面中的線條節奏,喚起了豐富的時間體驗,完整地呈現出情感連續幻變的存在維度。每一根線條,都是書法家捕捉情感之幻影的敏感的神經;每一個字,都是迭涌交織的情感的波浪;每一幅作品,都是心靈深邃澎湃的大海。書法的美在于能任性逍遙,縱情揮灑,一“書”胸中逸氣。
書法之所以能夠取得藝術的位置,根本原因就在于它具有情感表現功能,能夠“達其情性,形其哀樂”③。故韓愈在《送高賢上人序》中有云:“有動于心,必于草書發之。”拋開由漢字的所指功能所決定的文字的內容不說,書法的情感表現功能主要是視覺的,具體落實為線條的起伏。任何一條徒手的線條都有特定的感覺狀態——飄忽的線條或能喚起靈動的心情;穩重的線條使人感到端嚴;遲滯的線條傳達了內心的糾結。每一根線條都敏感地傳導了“手”對“心”的牽動及“心”對“手”的控制,伴以微妙的情緒,又以此觸動觀者的心。正是利用了線條的表情能力,書法成為一種情感表現的視覺語言,有著十分率直的審美表現力,尤其能夠坦坦然表現書法家當下的情感且回味無窮。高明的書法應該如同純粹的器樂,單憑美好的曲調也能感動人。蘇軾說得好:“心存形聲與點畫,休暇復求字外意?”書法是一種抽象的藝術,它的情感效能屬于視覺形式,而不屬于文字內容。人們欣賞書法,不是從內容看形式,而是從形式看內容,是從文字形式來看內容的。
書法藝術的藝術效果是具體通過筆法、墨法、結體、章法實現的,其中,筆法和墨法通過“以書入畫”而與中國畫發生了關聯。筆法是書法家控制毛筆運動所運用的方法,而在觀者的眼中,則是毛筆的運動軌跡所留下的視覺效果。書法作為線條的藝術,最終是由筆法加以體現的。從書寫方面看,筆法包括執筆和運筆兩個內容;從欣賞方面看,筆法則轉化為觀者印象中的筆勢,包括線條的外輪廓、線條運行的速度和力度。筆法控制了線條的質感,其效果與許多因素相關,例如書寫材料的物理性質。唐代大書法家孫過庭論書,有“五乖五合”之說,其中專門提到“紙墨相發”之“一合”④,這說明“墨”的審美價值首先是與書法家控制紙、墨的能力息息相關的。不過,書法家的運筆卻是影響筆法效果最重要的因素。運筆有許多種方式,例如一般所謂的中鋒、側鋒、藏鋒、露鋒、方筆、圓筆,皆為毛筆運動使然,它們統統依賴于一些更顯著的運動,例如起止、提按、頓挫、轉筆、折筆、徐疾、輕重等等。其實,這所有的運筆方式都不外乎三種最基本的運動——使轉、提按和平動。
運筆不是一種平鋪直敘的機械運動,而是一種有變化的、充滿節奏感的運動,即運筆的快慢要有變化,有時快速,有時遲緩。姜白石說得好:“遲以取妍,速以取動,先必能速,然后為遲,若素不能速而專事遲,則無神氣,若專務速,又多失勢。”⑤從運筆的基本方式上說,速度主要產生于“平動”,即筆朝平行于紙面的方向上下左右地運動。不過,速度之疾緩快慢,總是跟用筆的提按輕重相聯系的,尤其是使用毛筆這種特殊工具時,就更是如此了。這就是所謂“輕重緩急”。在這里,緩急帶領著輕重,平行運動帶領著垂直運動。
力度也是筆法審美效果的重要內容之一。中國畫講“骨法用筆”,書法用筆更要講究“骨法”,即要求線條要有力量感,要“力透紙背”。但假如我們把“力”單單看成是用筆的輕重造成的,未免失之簡單。事實上,筆力產生于各種對立趨向的沖突和緊張之中,貫穿于用筆的使轉、提按、平動等全部運動方式的控制之中。所有這些控制方式都來源于書寫者從身體中調集起來的力量。因此,從根本上說,筆力是“全身力到”的結果,是書寫者的身體力量通過手臂到手腕、手腕到手指、手指到筆、筆到線條渾然天成的。
作用力和反作用力總是結伴而行,只有克服阻力,才能顯示張力。可以這么說,有力度的線條就是一種力量與另一種力量交鋒而最終獲勝一方的視覺軌跡。其間對立一方并不被徹底消解,其殘存的對立之勢成了加強勝者之勢能的一個有利因素。要求書寫者“全身力到”,就是為了在運筆的過程中造成阻礙運行的力量和克服阻礙的沖突感,這種沖突被直接落實到了筆和紙的摩擦之中,體現為平動時的左行右掣和右行左掣,提按時的欲提還按,使轉時的欲藏還露。
這樣看來,筆力必須在審美效果上使人感受到線條的視覺張力。這要歸結為書寫的運動節奏,所以,富有過程性的節奏感是筆法的中心內容。通過運筆的急與緩、輕與重、收與放、斷與續造成“力”的張弛效果,使一筆一畫都成為若斷還續、富有質感的形體,創造出“骨肉相稱,筋脈相通”的有機而實在的美。含而不露,委婉曲折,達到言有盡而意無窮,讓觀者借想象去思考領悟,產生心靈共鳴,方為佳構。
在書法藝術中,墨法是筆法的延續。一般來說,書法都不會運用渲染的方法。除了日本手島右卿“墨象派”書法等實驗性的現代主義書法外。這樣,書法所講的墨法就與中國畫所講的墨法有了很大的差異。當然,這并不是說二者沒有重合的地方。事實上,書法的墨法正是繪畫墨法的簡化,它將水與墨之間的關系變得單純化了。繪畫的用墨,需要講究干、濕、濃、淡、黑,需要潑墨和破墨,需要“墨分五彩”,而到了書法這里,統統簡化為一個“濃”與“枯”或“潤”與“燥”的問題。
墨法服從于筆法,是書法用墨的基本要求,而且還要連帶漢字的間架結構,所以,在書法中,用墨完全不是一個孤立的問題,而應該照顧整體節奏的需要。就用墨本身而言,好的墨法也總是富有節奏變化的,所謂“帶燥方潤,將濃遂枯”⑥說的就是這個道理。不過由于用筆的線性特征,在此,“水”的力量并不像在繪畫中那樣能夠恣意揮灑,因此,“潤”與“燥”或者說“濃”與“枯”,就被限制到了一個相對較小的變化幅度中,其變化也就顯得更加微妙,更加需要書寫者把握墨與水的關系尺度。古人有云“枯,不枯,中潤”,一個“中”字,的確將書法用墨的特點說到了實處。古代有不少既能體現墨韻又不掩蓋筆法風骨的作品,如王羲之《蘭亭集序》、蘇軾《黃州寒食詩》、李建中《土母帖》等,墨氣渾厚,有樸茂郁勃之致。
通過對書法審美內涵的經驗性分析,我們進一步了解到,樂、舞、書、畫在中國藝術美學中如何通過線條美學獲得了內在的聯系。這也是中國畫的線條獲得審美獨立性的依據所在。事實上,在中國畫這里,線條美學具有統領地位,墨法被統一于筆法,用墨的方法存在于用線之中。自五代南唐花鳥畫家徐熙開創了“落墨法”,勾勒填彩的花鳥畫傳統技法的地位便發生了動搖。所謂“落墨法”,即用墨帶水,連勾帶染地作畫,其運筆所遵循的就是線條的運動軌跡。這便是寫意技法的開端。中國畫家之所以稱自己的作品為“寫”而非“畫”,寫意成像其直接動因,不能不歸于這種線條美學的作用。
西方現代主義繪畫由于解脫了寫實主義的束縛,亦開始注重線條審美意味的獨立表現,這不能不說受到了東方視覺美學的啟發。畢加索曾經說,要是生長在中國,他很可能成為一名書法家。在現代主義畫家中涌現了不少線條藝術大師,其作品中的線條不再受到造型的限制,而起到了直接表達藝術家審美理想與情感的作用。畢加索、馬蒂斯的線條就達到了極其簡練和含蓄的境界。如馬蒂斯的大型繪畫作品《舞蹈》中的線條,一如風拂水面,自然成像,暢然快意。雖然極富美感,卻不招搖于市,而是服從畫面形色構成的有機整體,仿佛是從這個獨立自足的空間中自然生長出來似的,彈奏著心靈的弦音。
20世紀的西方現代主義繪畫沿著兩條道路前行:第一,對形式表現力的探索,主要體現于抽象傾向與表現主義潮流;第二,對非理性的追求,主要體現在從幻想風格到超現實主義的演進歷程中。由此構成了20世紀上半葉的現代藝術景觀。它們以各種形式,趨近于兩個共同主題:一是“反傳統”;二是通過抽象實驗來探索藝術的自律性。不過,要是我們認為,西方現代主義繪畫是徹底與西方傳統藝術美學背道而馳的產物,看問題就未免太表面了。就拿線條的運用來說,即使僅作直觀對比,我們也能發現,畢加索、馬蒂斯畫中那些并未喪失描繪性的線條更近于古希臘瓶畫的線條而不是中國畫的線條。如果說中國畫的線條與“人與物游”的動態表現緊密相關,那么,西方繪畫的線條就與其由來已久的“結構”意識緊密相關,而不論這種結構是屬于對象的描繪性結構還是屬于畫面的自主結構。蒙德里安說:“只有線條、色彩和相互關系的運用才能表現內在生命的全部感情和理智。”其作品以線條分割平面為特點,采用直線、矩形或方塊,把紅、黃、藍及黑、白、灰分割和組合為簡化的圖形。蒙德里安聲稱,這是要揭示出宇宙的終極實在。這種自我辯護固然利用了東方神秘主義的思想資源,但更使人嗅到了柏拉圖主義和黑格爾主義的氣息。就此,我們看到,無論從視覺經驗還是從觀念依據上看,西方現代主義繪畫美學依然在骨子里延續了西方傳統。
與其他現代主義畫家一樣,超現實主義畫家保羅克利總是在實驗形式的簡化能力,但卻不像馬列維奇和蒙德里安那樣為簡化而簡化,甚至也不像康定斯基那樣為取得情感效果而煞費苦心地進行抽象。他極力將藝術扎根于自然之中。這不僅是為其提供素材的那種自然,更重要的是一種自然品質;就像樹木生長和四季運轉是一種變化、一個過程,是從一個部分到另一個部分的遷延和繁殖。在他的作品中,點、線、面、體都不應該只是最后呈現于空間上的效果元素,而是在時間中不斷增進的過程要素。表面看來,這似乎與中國畫的“人與物游”有某種呼應之處。不過,中國畫創作講究“胸有成竹”,克利追求的卻是“用一根線條去散步”。二者的距離正在于此。他的創作并非先有一個明確的幻想,再拿繪畫形式去進行傳達,而是把視覺形式本身當成建構幻想的材料。馬拉美說,詩歌不是用思想和情感寫成的,而是用“詞語”寫成的。我們在克利這里看到了類似的情況。幻想隨著形式的顯現一道走向成熟,“詞語”變成了體驗的一部分、思想的一部分。他的作畫過程就真的是這樣,任由畫筆引出線條,讓線條帶領自己,讓形象自動呈現。最后,才在這些直覺的成果中引申出標題。這實際上是一種心理自動主義的創作方式。還沒等到法國超現實主義者來提倡,克利就提前付諸實施了。在他的畫中,線條成了一種行動,色彩成了一種活力,而不是刻意“抽象”的成果。如果說,我們在他的作畫過程中隱約看到了中國大寫意“潑墨”畫的影子,那也更多是一種貌合,因為中國畫家潑墨既出,接下來所用的功夫是在潑出的墨跡中運用想象,以便能畫出山水或人物。我們不難發現這其中有“天人合一”的思想在起作用。而克利卻是讓散步的線條自動繁殖,生成為非描繪的形式。在這里,我們看到了實踐著的存在主義,并以此為起點,最終走向了抽象表現主義和行為藝術。
中國畫的線條美學與客體形象處于一種若即若離的關系中:既要描繪對象,又要表現趣味,還要遵守格法。后者造成了中國線條美學的風格化和符號化,如從人物衣褶描繪中總結出來的“十八描”,當然難以做到西畫那樣要么完全遵從客體對象的描繪,要么完全遵從線條的自動呈現。但這些線條勾勒的繪畫形象畢竟又與描繪對象存在一定的關聯,是用某種線條程式適應對象表現的結果,反映了中國畫在形式層面上的“以大觀小”。由于沒有西畫那般對摹擬之物的執著,中國畫的線條顯示出一定的審美自主性,但又未免受到格法與程式的限制,妨害了靈活性與個性追求,因而與西方現代主義繪畫所追求的個性化的審美獨立是不相同的。
注釋:
①⑤(宋)姜夔:《續書譜》,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八藝術類。
②(唐)張懷瓘:《書斷》卷上,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八藝術類,書畫之屬
③④⑥(唐)孫過庭:《書譜》,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八藝術類,書畫之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