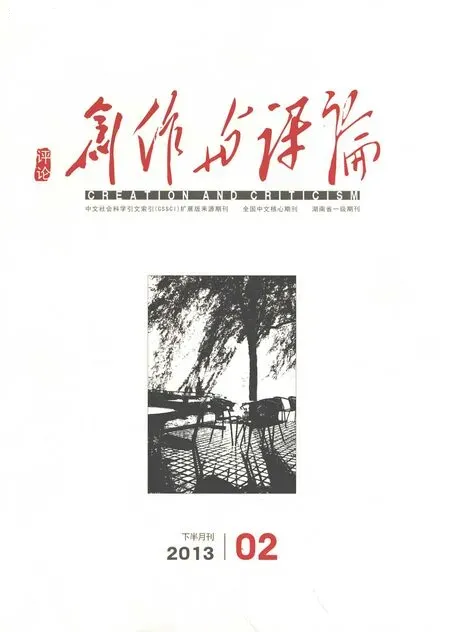文藝評論的作用及其實現方式
○ 艾斐
文藝評論作為文藝創作的一種評鑒機制和馭動力量,自有其不可替代的特殊功能與巨大作用。而文藝評論的效能凸顯和價值實現,則又惟在于它所秉具的理論品格、精神內蘊、時代韻律和科學素質。因此,我們在倡揚和提振文藝評論的同時,也必須賦予其足以擔當時代重任的粹質與能力,這就要求文藝評論在行使自己歷史使命的過程中一定要以清淳、敏睿、明達、深邃的品格和銜史、應時、務實、求真的資質走完全程,并不斷地有所提升,有所發展,有所開拓,有所創新。
一
文藝是一種精神構建,而任何精神構建在本質上就都是對以“人”為核心的社會生活的藝術反映。這就不僅使文藝本能地成為社會生活的審美體現與精神賡延,而且也天然地使之與時代、政治和現實社會生活發生著割舍不斷的血肉關連。
于此情況下,作為對文藝創作進行臧否評騭與方向引導的文藝評論,當然就更應須高屋建瓴地站在歷史、社會、時代和政治的高度,對其所評騭和引導的對象施以科學認知、宏觀把握、精神定位與正確馭動了。不如此,便不足以盡到文藝評論的責任,更遑論發揮文藝評論對創作的巨大推動作用與特殊觀照功能。而要如此,文藝評論本身則就必須賦有更高遠的基準、更宏闊的視閾、更敏銳的眼光、更精允的判斷、更清晰的洞察、更透徹的理喻、更深邃的鉤稽和更明睿的詮達。因為只有這樣,文藝評論才能夠做到像魯迅所要求的那樣“壞處說壞,好處說好”①、“剪除惡草,……灌溉佳花”②。
實際上,在任何時候文藝評論對文藝創作所應當起和能夠起的作用,就都是這樣。按說,這并不是什么難事,更不是對文藝評論的額外苛求,但在實踐中要真正做到這一點,卻往往是很難很難的,特別是在世俗化和功利心越來越浸染文化意識和馭控筆鋒走向的當今,要實實在在地做到這一點,就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事實上,一個時期以來文藝評論之所以會出現孱弱化和邊緣化的傾向,其主要原因就是它漸漸失去了本應稟賦的品格和功能,并因此而越來越不被信任和崇尚。
文藝評論,本來是要對文藝活動、文藝創作和具體作品的傾向與得失,進行具有權威性和說服力的評鑒與引導,并以理性的創造思維而賦予其以思想的內曜與美學的光彩,從而使創作主體從中得到啟迪和感悟,同時也引發受眾的文化自覺和促動讀者的閱讀欲望,進而在不同層次和不同范疇中對作者和讀者共同實現不同程度的提升與引導,并通過對作品的思想發掘和藝術詮釋而形成文藝作品的準確社會定位與恰切藝術定格。這種定位與定格,往往就是構成民族和時代文藝發展走向與軌跡的基本元素和主要標識。一個國家的文化史、一個民族的文化值、一個時代和社會的文化精神與文化魂魄,往往就是這樣形成和奠立的。想想看,如果只有《離騷》、《史記》、《紅樓夢》和《阿Q正傳》,而沒有對之的研究和論述;只有孔子、李白、曹雪芹和魯迅,而沒有對之的分析與評說,那么,這些作品和這些作家的價值與意義,乃至其在民族和世界文化發展中的地位與作用,還會像我們今天所認識到的這樣具有普遍性、深刻性和典范性么?其在文化史冊和民族心愫中的滲透力和影響力,還會像現在這樣廣泛、深刻而崇高么?答案無疑是否定的。
事實上,無論是文化史、文學史或藝術史,都是以評論家的具有事實依據、科學精神和卓拔見解的“定評”作為根據而逐漸書定的。評論家們不僅以自己的個性化和創造性勞動書定了炫示民族精神與照耀思想蒼穹的文化史,而且以特殊的方式與堅韌的耐力發現和磨礪了眾多原本并不為人所知的文化珠璣與藝術巨匠。像對《論語》和《離騷》之價值的認識,就是在一代一代的不斷發掘和提升中逐漸深化的;像對卡夫卡的小說和梵高的繪畫的認識與評價,也是在眾多評論家的不斷“發現”和深入探賾中逐漸得到提升的。特別是像徐渭這樣的大畫家,雖然今天早已是藝術天昊中的璀璨明星了,但如若沒有當年袁宏道的慧眼識珠和大力評薦,那就極有可能現在還會被埋沒在歷史的蒿萊與歲月的塵垢之中而不堪世銘和不為人知了。確乎,正是理論家袁宏道從散佚于民間那“煙煤敗黑,微有字形”的殘卷余幅中,才發現了青藤藝術的內蘊與真諦。
文化的價值不僅在于創造,而且更在于發掘、發現、認識、揚勵和不斷地創造性的磨勵與提升。文藝評論的作用正是這樣。莎士比亞戲劇,一開始就只是在鄉村戲班子里巡回演出,其受眾地域之狹小和影響范圍之逼仄,都足以使之成為不登大雅之堂的短命藝術,而正是評論家們的發現和薦舉,才使它名聲大震、不脛而走,并一步步地成為享譽世界的戲劇藝術瑰寶。《紅樓夢》的手稿甫一開始,也只是在民間秘密傳抄,寫作者唯為錄事、言情、抒意,傳抄者唯在好奇、謔趣、娛心,誰也沒有思考和追索它的社會意義究竟有多大,文學價值究竟有多高?舉凡這些,都是后來的評論家和研究者們一步步地將之發掘出來,并以之而啟示和引導讀者從中擷珠探寶、覓蹊采珍,直至發現和架構出一個無限風光任徜徉的大千藝術世界。魯迅只活了55歲,著作只有600余萬字,可時至今日,研究和評論魯迅的書籍與論文加在一起,其文字量又何止超過魯迅著作的十倍、百倍?也正是在這種世界性的魯迅研究與魯著評說中,才不但步步深入地解析了魯迅著作的精髓,而且也更漸入佳境地摶煉了魯迅精神的粹質。我們現在認知中的魯迅之崇高與偉大,其實就正是在這個過程中完成的。
歷史與現實總是睽隔著一定距離的,而對于文化創造和文藝創作來說,理論和評論就正是占取和彌合這種距離感的思想尺度與藝術材質。因為只有當歷史在歲月衍移中沉淀和過濾了現實的渾沌之后,其所熠射出來的才會是理論和評論的爝焰與光彩。人們對一個具體文化產品之價值的認識和接納,往往都會有這樣一個過程。對于文藝作品來說,即時的熱捧和一時的轟動,收視率的暴棚和市場上的走俏,都并不一定代表其價值的宏大與意義的崇高,而只有在時間的磨礪中所逐漸摶煉和熠射出來的凝重與光彩,才是其實際價值的真正體現。也正是在這個過程中,評論的效能才會尤為凸顯和倍加放大,并為文化產品和文藝作品的最終定位和定格鑄煉圭臬,以至勾劃和引導著文化與文藝的既定格局與未來走向。由此足見文藝評論對于文化創造和文藝創作所具有的既不可缺如又無以旁代的極端重要性。如果說創作者是以自己的作品直接再現生活和取悅讀者,那么,評論者則是要以自己的理性論騭和科學評價,通過鑒析作品而提升和引導作者與讀者。從某種特定意義上說,顯然理論和評論更重要。因為沒有理論的匡正和指導,作家就會陷于迷惘;而失去評論的扶掖與鑒析,創作則會撂荒。在文化創造和文藝創作中,任何主體的迷惘和客體的荒率,都會使作品本身及其社會效能陷于不可估量的銷鑠與紊亂,乃至走向悖論,出現負值,墜入思想的冰窖和精神的黑洞,造成創作力的下沉和收獲季的凋零。
這樣的例證并不鮮見。人們之所以要把創作和評論比喻為車之兩輪和鳥之兩翼,作家藝術家之所以要把評論家及其評論視為園丁和引擎,其原因正在于此。在一個健全的文藝生態環境中,創作和評論的任一失衡與傾覆,都會給實現文藝的繁榮與發展形成妨礙和阻滯。特別是在失去評論護佑和指引情況下的文藝創作,則無異于農民疏于對土地的耕耘和工人放棄對鑄鐵的淬冶。其后果無疑是不堪設想的。
二
我們肯定文藝評論的價值和作用,強調文藝評論的功能和意義,重視文藝評論對文藝創作的觀照性和指導性,當然并不是無前提和無條件的。這前提和條件對于文藝評論來說,就是要求它必須剴切、精當、明睿、卓拔,必須秉有先進性和科學性,必須充盈創新思維和領異精神,特別是必須能夠有效地對文藝創作起到匡正、啟悟、激勵、誡勉、引導和提升的積極作用。
這個前提條件很重要。只有它,才是文藝評論的精魂與樞機,才是文藝評論的全部價值和意義之所在,才是文藝評論之所以至關重要、之所以不可缺如和之所以功能獨特、作用無貸的全部理由和惟一根據。一旦失卻這個前提條件,文藝評論在本質上也就不再是文藝評論了,因為它既不具備文藝評論的原本品格和價值,又不能發揮文藝評論理應秉有的功能與作用。而這,對于文藝評論來說,則無異于是一種自我功能擯棄和主體價值否決。
文化評論是“評論”文藝創作和文藝作品的。而進行評論的目的,則是要給予文藝創作和文藝作品以準確的鑒診和正確的指導。這當然就首先要求文藝評論本身必須是正確的、先進的和具有睿慧眼光與高卓見解的了。打鐵先要本身硬,矮子何以攙巨人?而恰恰正是在這一點上,我們的有些文藝評論卻犯了大忌。它們要么見解平庸、思想灰黯;要么語辭晦澀,概念扭曲;要么以述充評,文不逮意;要么褒貶失當,結論褊畸,甚至還出現了什么“紅包”評論、人情評論、御用評論、權謀評論、唯美評論、超現實評論、技術主義評論和“去政治化”評論等等。這樣的所謂文藝評論,哪里還具有文藝評論的素質與品格呢?當然也就無法起到文藝評論所應起和能起的積極作用了!
文藝評論的質量和效能,只能取決于文藝評論家的情操、能力與水平。因此,要提高文藝評論的質量和效能,就必須不斷提高文藝評論家的思想水平、知識結構、認知能力、藝術素養和道德情操。為此,從文藝評論的現實情況和實際需要出發,我認為評論家在其評論過程和評論成果中至少應當從以下三個方面進行積累、淬冶和修練。
首先是要處理好文藝評論與文藝理論的關系。理論既是思想的依據,又是評論的根基。評論只有在理論的基礎上才能實現生發、升躍與延伸,才能趨于厚實、堅挺和新蔚,也才能有思想、有力量、有內涵。否則,評論就會被平庸和淺薄所彌漫,就會缺乏雋意和深度,就會成為生命力極度脆弱的涸轍之鮒和說服力十分有限的表面文章。正因為如此,所以歷來的大評論家就無一不是一身兼為理論家和學者,甚至還是翻譯的高手和創作的能手。而在這方面,恰恰是我們現在許多評論家的短板,并因此而使我們的文藝評論常常顯得評述多于論賾,陳言壅堵探蹊,冗敘替代思想,謬說冒充創新。這樣的文藝評論,實際情況是只有“評”,而沒有“論”;只有“學”,而沒有“思”;只有“膩”,而沒有“彩”;只有“玄”,而沒有“益”。而真正有思想、有力量、有情彩的文藝評論,則注定應該是理足評當、意懋思深、尋蹊探奧、臻于旨歸。
其次是要處理好文藝評論與政治和藝術的關系。曾幾何時,在文藝評論界興起一股風,就是遠離政治,只談藝術;阻斷傳統,傾慕“西潮”;告別“在場”,回歸自我。這導致我們的一些文藝評論在行文立意上不僅退出了現實,而且也規避了政治和睽隔了時代,悖逆了歷史,疏遠了人民。其所篩落下來的,也就只有新名詞轟炸、自我意識的無規則膨脹以及所謂的“新銳”概念和“前衛”思潮的漫天盤繞與胡亂糾結,乃致常常在恣肆汪洋的篇幅里和荒誕怪異的理念中所裹藏著的,卻僅僅是一個小小的和不可捉摸的空洞意概與猥瑣思骸。這無疑是蹈入了一個認識論的誤區。文藝創作要民族化、時代化、社會化,文藝評論當然也應當和必須具有民族化、時代化和社會化的品格與氣質。否則,評論與創作就會無法實現對接。對于西方文藝思潮當然不能無視,不能拒絕,但吸收則必須是有淘漉、有選擇,必須做到擇其優而為我所用,擷其用而對我有益。即使如此,中國氣派和中國風格也仍舊永遠都是我們文藝評論的時代標識與精神芯片。至于對政治的規避,那就更是一種思想的顢頇與認識的幼稚了。政治是融化在現實社會生活中的,人是社會生活的核心和主體,文藝創作是以“人”為描述和表現對象的,或者說是以寫“人”為旨歸的。那么,作為以評析和引導文藝創作為己任的文藝評論,又怎么能夠規避得了政治呢?這簡直無異于癡人說夢。正經說來,文藝評論只有認真研究如何才能更好地從政治和藝術兩個方面給予文藝創作以切實的和科學的謀劃與引導,才是正道。只有從政治上和藝術上對文藝創作進行全面觀照和有力馭動,才是文藝評論崇高的歷史責任與永恒的時代主題。
第三是要處理好文藝評論與作家和作品的關系。文藝評論的對象是文藝作品,而作品又是由作家藝術家們創作出來的。在作品中,常常是作家藝術家價值觀和審美觀的情韻表達與藝術流露。既然如此,文藝評論在評析作品時就不能不顧及到創作主體。事實上,也只有在將作者看做作品的背景和底片時,評論本身才會更全面、更準確、更有力。魯迅不僅說過“我總以為倘要論文,最好是顧及全篇,并且顧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處的社會狀態,這才較為確鑿。”③而且認為“要論作家的作品,必須兼想到周圍的情形。”④文藝評論的生命之源和價值之樞,也就唯在于它能對作品做出肯綮而科學的評析,并引導作家藝術家在明得失和知方略的高度自覺中不斷地得到提升和發展。而要實現這個目標,認真處理好與作家和作品的關系便顯得至為重要,其要點有三:一是全面考察和掌握作家與作品的相關情況和信息,并對之進行有機聯系與縝密分析,從中找出個性化和規律性的東西來;二是既要對作品負責,又要對作家藝術家負責,堅決做到有一說一,有二說二;好處說好,壞處說壞。既指出優長之處,促其擅揚;又指出不足之處,助其改進。既以理論的闡釋幫其提升認識,又用忱摯的誡勉勖其鼓足信心。在這個過程中,作家藝術家也同樣需要有足夠的真誠與耐心,尤其需要有虛懷和稚量,決不能只愿聽好的,不愿聽孬的,更不能媚取和誘發評論家的違心之論和不實之諛。三是評論家不僅有責任對作品進行評析和品鑒,而且也同樣有責任對作家藝術家進行理論引導和學術濡化,并使之在這個過程中不斷地增強和提高精品意識與創新能力,從而在作家和評論家的開誠相見、諧勉互促中共同構成繁榮和發展文藝創作的時代脈動與強大合力。
注釋:
①魯迅:《南腔北調集·我怎么做起小說來》
②魯迅:《華蓋集·并非閑話(三)》
③魯迅:《且介亭雜文二集·“題未定”草(七)》
④魯迅:《且介亭雜文二集·后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