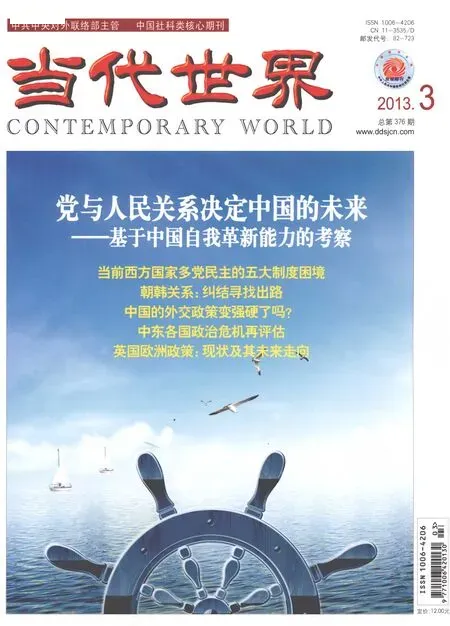從中國模式的智力援助到全球化時代新公共外交
——講述中國對非洲獎學金的故事
劉海方/文
從中國模式的智力援助到全球化時代新公共外交——講述中國對非洲獎學金的故事
劉海方/文
中文“留學生”一詞泛指所有留居國外學習研究的學生。從歷史考證,創造于隋唐時期,特指跟隨遣唐使進入中國、并在遣唐使回去后留下來學習的人。然而, 就整個世界范圍來看,大規模跨越國境的海外學習,卻絕對是20世紀的事情,是現代交通手段使得大規模的快速國際旅行成為可能之后的新發展;更重要的是,機制化的資金安排——即獎學金制度——使得赴國外求學得以實現。
1902年設立的羅德斯獎學金(Rhodes Scholarship)被認為是現代最老牌的獎學金,被后來雙邊或者多邊性質的國際獎學金制度所效法,即資助不發達國家學生到發達國家學習。獎學金制度開始興起之時,就是國際發展援助的核心內容之一,其基本理論基礎就是能力赤字——漸次獨立的非洲國家顯得尤為必需——麥克米連所謂的“變革之風”勁吹大陸的1960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只有五個類似大學的體制。知識和技術要實現從富國向窮國轉移,而獎學金制度正是使其實現的關鍵;與此同時,援助國的合法性來源,也是自己有某種比較優勢,可以供別人所欣賞和學習。
中國式智力援非的邏輯起點與展開
建國之初,中國政府最先制定的有關來華留學生的政策是首先與東歐五國達成互換留學生的政府間協議,所有來華留學生的渠道都是根據對等交換原則實現的。1956年,國務院批準了《關于接受資本主義國家派遣留學生來我國學習的修改意見》,向蘇東社會主義國家為主的一邊倒政策,開始轉變為同時向資本主義國家開放,而且亞非民族獨立國家作為提供來華留學獎學金的重點地區。
具體到對非洲國家,中國政府接受其留學生不完全是出于與派出國雙邊關系的考慮,因為一些國家還在獨立運動過程之中已經在向中國派出留學生了,這體現了中國政府在多個場合申明的態度:即為友好國家培養留學生是履行國際援助義務。1963年12月,在中央批轉教育部黨組《關于外國留學生工作會議的報告》中還指出:接受來華留學生不僅是我國應盡的國際主義義務,而且還有利于擴大國際反帝統一戰線。
從1956年第一批埃及同學來華開始,非洲同學逐年增加,到1960年,這個數字快速增加到95人。此后,汲取非洲留學生出現輟學的教訓,有關部門明確反思了價值觀念、生活方式、風俗習慣、宗教信仰差別給學校的教學和管理工作帶來的挑戰;1962年第一部關于來華留學生管理工作的法規性文件《外國留學生工作試行條例(草案)》中,提出了“精選少收、分別對待、統一管理、提高質量”的方針,且建議盡量勸說亞非民族獨立國家減少留學生。該條例還明確了對所有來華留學生的管理方針:“學習上嚴格要求,生活上適當照顧”和“政治上不強加于人”,至今仍然適用。
1966年“文革”爆發使得留學生工作被迫中斷,這一年14個國家共164位非洲留學生與其他國家留學生一起被告知暫時離開中國。1972年中國接受贊比亞和坦桑尼亞兩國派遣的200名鐵路留學生來華,系統學習各相關專業;1973年接受來華留學生工作得以全面恢復。隨著中國政府的國際戰略從“學習蘇聯”轉向“兩個中間地帶”和“三個世界”理論,20世紀70年代的獎學金名額開始明顯向非洲國家傾斜,實際人數與占總來華留學生比例都有大幅度增加。
從檔案文獻來看,中國政府當時對于亞非拉學生的培養目標是,除了對中國友好以外,要求專業知識、實際技能、身體健康都需達標;政治上則按照不同國家,對學生提出不同標準:馬列主義政黨國家,要求同學掌握馬列主義理論并與實踐相結合;民族主義國家的同學,則要求有反帝反封建、爭取民族獨立解放、為人民服務的思想。在專業選擇方面,非洲國家留學生與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學生是一致的,即由派遣國和接受國共同協商決定是否賦予留學生專業選擇權,這區別于對待資本主義國家學生的“積極慎重”的方針——由教育部和外交部等機構進行會商,嚴格地控制、審批所開放的專業。整體上對于留學生教育的目標是培養專業技能。1974年以后大規模對留學生推行開門辦學,其目的也是“為了貫徹以社會主義為工廠、理論聯系實際的方針,組織留學生進行在廠的教學實踐”。
當時同樣受意識形態驅動的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對非外交攻勢”分兩個層次行動:官員和層次低、但有望成為領導的階層。蘇聯對非的政策目標,就是精英培養,培養致力于共產主義運動的干部,斬斷與其西方宗主國之間的聯系,在非洲建立一個共產主義世界。20世紀50年代中期后,蘇聯重點轉向培養青年人,留蘇的非洲學生,來源大多數是工會成員,因為蘇聯認為工會是社會轉型的潛在力量。蘇東陣營訓練非洲工會干部的最大機構是1953年成立的布達佩斯工會學校,當時世界勞工聯合會總書記路易斯·賽揚(Louis Saillant)曾經概括該校的特征就是“一切為階級斗爭做準備”。東歐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和非洲本土如幾內亞達拉巴(DALABA)等非洲城市,也建立了類似的工人學校和培訓中心,講授課程也都以馬列主義詮釋的歷史、社會、殖民主義和經濟發展觀為主。根據美國衛生、教育和福利部的說法,僅1965—1966年間,在蘇聯境內受訓的非洲學生就達4000人,這一政策成為當時蘇聯對非外交的主干道。
總之,在這個初始階段,歐美世界對于獎學金制度的理念是培養出直接進入非洲國家各個機構的人力資源從而實行知識轉移,就能有益于非洲國家的發展。蘇聯的對非獎學金,沒有這樣明確關于發展的表述,而是以培養青年人建設非洲共產主義為鵠的。中國接待非洲留學生的目標,沒有蘇聯那樣明確的政治目的,而更體現出了中國文化的平和中正的特點,即便是意識形態影響最強烈的文革時期,對于留學生的培養目標強調的也是馬列主義與自己國家國情相結合的實事求是原則,而且“政治上不強加于人”的自愿原則貫穿始終。當時接待非洲留學生的,不是蘇聯那樣特別為他們量身打造的學校,也不是專門進行馬列主義政治哲學教育的特殊機構,而是教育中國自己的高中畢業以上層次的學生、分布在全國各地的高校,在接受留學生之前,其資質一般根據師資力量、課程設置、基礎設施條件等方面接受高教部的評估。在接受方針方面,中國政府的政策目標并不是“階級革命”,因此也不瞄準工會干部或者成員,而是把選擇權交給生源國政府,同時以學生在國內的先修學歷作為入學資格,體現了對于派遣國的充分尊重和信任,是與平等尊重和不干涉內政原則一脈相承的。
對于招收來華后的非洲留學生,和來自其他國家的留學生一樣,所有教學目標、管理原則都是邊學邊干的狀態下不斷調整的,具有非常明顯的實踐主義特征。因為國內建設的需要,這一時段來華學習的非洲留學生是以理工科專業為主體。學生的課程設置,能同一計劃的,就盡量與中國同學(文革時期是與工農兵學生)一起上課;不能同一計劃的,再單獨開課;當時的組織課堂的原則是小班教課,確定既教書、又教人的原則。相比于歐美的學制,在當時“教育要革命”的口號下,中國當時提供的學制相對較短。實際效果來看,當時非洲同學的印象是,較短的學制并不一定教學效果更差,中國的老師更負責任,而且始終貫穿著讓學生動手實踐的重點,與歐美老師講完課就走人的方式完全不同。
中國式智力援非的建制化與新目標
1976年1月,探索已久的來華留學生經費標準、醫療收費標準細則相繼頒布。因為發生了少數留學生畢業后不按時回國的情況,教育部在1976年10月下發了要求所有畢業生必須在1—2周內離境的規定。各高校的留學生工作也開始制度化管理,食、住、行、醫各方面都開始進行細則化的規章管理制度建設。為了保證質量,由駐外使館進行考試然后再招生的政策于1978年被提出;以1979年1月第二次全國來華留學生教育工作會議為契機,《外國留學生工作試行條例》得以修訂,明確了建立留學生學位制度,同時“堅持標準、擇優錄取、創造條件、逐步增加”成為基本招生政策,并將1978年的“先考試、后錄取”政策細化為:理工農醫等學科必須經過考試后根據標準錄取,文史哲中醫等專業本科留學生必須經過兩年漢語學習后方可進入專業學習。
1983年中國總理訪問非洲,全面提振了自1978年以來有所弛緩的對非工作,對非獎學金名額也一舉提升到230名。1984年12月,全國外國留學生工作會議再次召開,“智力援助”概念被首次正式提出,使其“與軍事援助和經濟援助一起三足鼎立”。
20世紀80年代末,為了解決非洲留學生的就學困難,教育部本著“高學制、短學歷”的精神、鼓勵各高校次年嘗試開辦英語、法語專業授課班。在這種國際化的努力之下,1996年非洲獎學金生從上一年的256人迅速增加到922人,自費生也增加到118人,使年度來華學生總數第一次超過1000人。數量迅速增加的趨勢到了2000年中非合作論壇成立以來更加明顯,尤其是2006年以來通過中非合作論壇平臺,中國政府兩次宣布提高對非洲國家的獎學金資助力度(即分別從年度2000人增至2009年的4000人和2012年的5500人),使得中國儼然成為一些非洲國家年度獲益人數最多的獎學金提供方。
關于來華留學生工作的目標定位上,20世紀90年代中期提出了新目標,即除了傳統上強調為輸送國培養專業人才和促進和加強與學生母國友誼以外,“提高中國高校的國際交流水平”開始作為新的目標被明確提出,“教育國際化”的目標作為新的推動力凸現出來,地方政府和院校因此把留學生教育納入發展規劃,制定了很多地方獎學金。除此之外,不同省、市還會有其他更為多元的訴求:例如北京市就把留學生教育視為是把北京“建成國際化大都市”和“深化改革開放”的指標,并因而從2001年開始對北京市有接收外國留學生資格院校教育管理工作進行評估,已達到“辦學條件、管理水平、教育質量與辦學效益”方面可持續發展的目標。伴隨新目標的提出,相應舉措不斷出臺:例如2003年建立起來的來華留學管理干部培訓制度,有的培訓班甚至搬到境外求取美國等國家的經驗;全國范圍內的來華留學生業務工作會議每年召開,以便互相交流經驗;以“全國智力援非工作會議”為題的系列會議自從2004年以來在全國培養非洲留學生(尤其是短訓生)的各高校輪流召開。
世界各國獎學金的老邏輯、新走向
獎學金這種曾經普遍通行的教育援助模式在全球都在悄然發生變化,特別是有關國際援助績效的阿克拉會議(2008年)和強調受援國自主權的釜山會議(2011年)以來,這種模式的優缺點在被不斷反思之中,焦點集中于外國受訓回來的學生是否能夠很快貢獻于發展中國家經濟建設急需的各個領域。對此援助模式質量和效果的廣泛關注,甚至已經開始動搖和改變一些雙邊、多邊援助方進行教育援助的模式,目前出現了真正新舊并置的格局:一方面,德、法等國每年還將用于教育的援助金額主要用于獎學金;另一方面,一些歐洲國家現在確實出現了要壓縮學生簽證的意圖,如英國的計劃就是將學生簽證壓縮25%,瑞典則第一次大規模改變援助政策,要求歐盟以外的學生都要交學費;與此同時,一些資助方則開始為發展中國家的學生提供在本土/本地區的培訓,即強調與本土研究者、領導人在一起學習、成長的重要性。
具體而言,德國和法國是經合組織(OECD)捐助國集團中最大的高等教育捐助者,每年各自投入10億美元以上。以2009年為例,德國獎學金受益學生中,來自北非和中東的有4328人,來自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有3762人。法國對于高等教育的援助主要集中于非洲法語區,2006年有2萬受益者,2008年在法非洲留學生總數高達11萬。
模式同德國法國一樣沒什么大調整的是美國這個世界頭號強國,主要還對研究生進行資助,包括外來留學人員。雖然并不是全球提供獎學金最多的國家,美國卻毫無疑問是全球吸引外國學生最多的國家,而且高等教育一直是其創匯最高的服務業出口部門,外國學生所繳納學費和生活支出,每年為美國GDP收入貢獻200億美元。
很長時間里,為非洲等發展中國家學生提供獎學金都是英國政府獲得巨額教育創匯的平衡點綴。最近,英政府明確宣布海外獎學金的目的有三個:支持國際發展、提高英國公共外交和影響力、增強英國作為高等教育的優秀中心的位置。聯邦獎學金是其最大的項目,2010年受益者為700名,來自于40個英聯邦國家,其中一半為非洲國家。英國政府最新的要求是,獎學金授予要更加靠近英國國際發展部(DFID)的發展戰略目標。這種強調專業化和發展導向的實用主義傾向,也遭到了一些英國學者的批判,認為應該鼓勵學習那些看似沒用的專業,如人文、語言、文化和藝術表達等。
近年來頻頻效法中國出臺種種對非新舉措的新興經濟體印度,甚至針對非洲新設立了印度—非洲獎學金,2010—2011年上半學年有33名非洲學生成為此新項目的受益者。
另一個金磚國家巴西,隨著2005—2010年的發展援助增加一倍達到30億美元,用于獎學金的開支每年也保持在5000—7000萬美元之間,加上用于學術和研究機構的獎金,每年已在1億美金以上。與非洲相關的巴西獎學金有幾個,2008年又推出新的計劃,即支持非洲國家數學和葡語教學計劃,理念是如果數學和語言能夠運轉自如,教育和科學方面的其他困難就更容易解決了。
至于繼承前蘇聯的俄羅斯,1992年3月接待非洲代表團時,俄羅斯政府還承諾繼續提供獎學金給非洲同學;但三個月后,俄羅斯政府發表公開聲明,因為經濟問題,希望非洲國家承擔自己學生的費用。莫桑比克、安哥拉和埃塞俄比亞這幾個傳統盟友,獲得獎學金也大大減少了。普京接替葉利欽掌權后,新外交政策開始強調與非洲國家強化互動;但在獎學金上一直沒有恢復原來的盛況,而是轉向通過國際組織支持世界全民教育,即投入提高兒童和成人識字率,這也意味著放棄傳統上支持高等教育和大量提供獎學金的政策。
南非是世界上第五大國際學生東道國,2010年接收了6萬多外國學生,70%國際學生來自于南部非洲共同體(簡稱“南共體”)地區,18%來自于非洲大陸其余國家。南非政府認為,擁有這么大規模的外國學生最大的收益就是,督促南非一直都有保持教育質量的壓力。南非為所有南共體國家學生提供補貼,補貼發到每個人手中;同時,這些學生和南非本土學生所交的學費是一樣的,也就是說南非國家同樣補貼他們。所有南共體國家學生進入研究生項目,就享受完全補貼了。
總之,不管是發達國家還是新興國家,作為對非智力援助的獎學金制度仍然呈現方興未艾的趨勢。日本和美國都不諱言以此網絡優秀人才的目標,在全球化人員流動的規模和頻率空前增加的時代,提升本國政府形象也成為獎學金的題中要義,不管是英美那種“全球高等教育中心”因而能贏得更多服務業產值的形象、還是作為發展中大國印度那種以赤腳大學“扶貧”的形象。
結論:怎樣講述中國的對非獎學金故事
自2008年開始,中國政府對來華留學工作的財政投入大幅增加,年度達到5億元以上。在世界上19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來華留學生中,2009年有12436名非洲學生來華求學,比2000年增加近八倍。值得注意的是,2005年是一個轉折點,這一年非洲的自費生超過了獎學金生,這得益于獎學金生的廣告效應,也得益于奧林匹克運動會前后的巨大宣傳效應,非洲青年人開始睜大眼睛“發現中國”。此后的所有年份,即便中國對非獎學金資助力度增加迅速,自費生的數額也都遠遠超過獎學金生的數額,顯示了非洲對于中國教育市場的旺盛需求。也就是說,非洲作為中國教育對外合作的對象,已經不僅僅應該從雙邊援助的角度上去理解,而應該增加教育服務市場的理解視角。那么,像英美兩國那種打造中國“國際化教育中心”的形象是當務之急了。
中國的教育機構的決策者和管理者應該對來自于非洲的這種需求旺盛增長的態勢更加關注和重視,與此同時,要改變國際輿論界往往因為信息不暢等原因而評價中國的獎學金“極為神秘”的現狀,加強輿論引導對于非洲留學生的認知,以及學術界關于非洲留學生的研究。近年來隨著公共外交社會化,終于有人提出“留學生交流”也是有可能作為外交活動的新主體、成為全球化時代的“公民外交家(citizen diplomat)”。
總體上來說,中國對留學生的認知,亟待走出僅是教育界話題的局限,將其置于國家外交布局的認知坐標下來討論。這不僅僅是因為在新的時代留學生身份更為多元、要求更為多樣;更重要的,中國人只有自己將留學生開始于獎學金生的歷史梳理清晰,才能對外講述清楚這項起源于比較純粹的國際主義的智力援助項目,包括其整個演變過程中的中國特色和對非洲等發展中國家做出的近期和遠期的貢獻,也才有可能為更長遠的打造中國作為全球教育中心的形象加分。而這項工作,同時也是創造性的新公共外交的基礎,自我認識清楚了,也就更知道怎樣跟世界打交道了,非洲也不例外。
(作者系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副教授)
(責任編輯:魏銀萍)
[1] 檔案號:20772201,卷2, 北大留辦《關于籌備接受留學生工作的意見》,1972年5月15日。
[2] Roger E. Kanet, “African Youth: The Target of Soviet African Policy”,Russian Review, Vol. 27, No. 2,1968, pp. 161-175.
[3] 北京大學留學生辦公室檔案:北京大學《關于留學生工作問題的請示報告》,1974年5月7日。
[4] 教育部1976年209號文件:《關于畢業或結業的外國留學生應按期離華的通知》,北京大學留學生辦公室檔案,卷號20776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