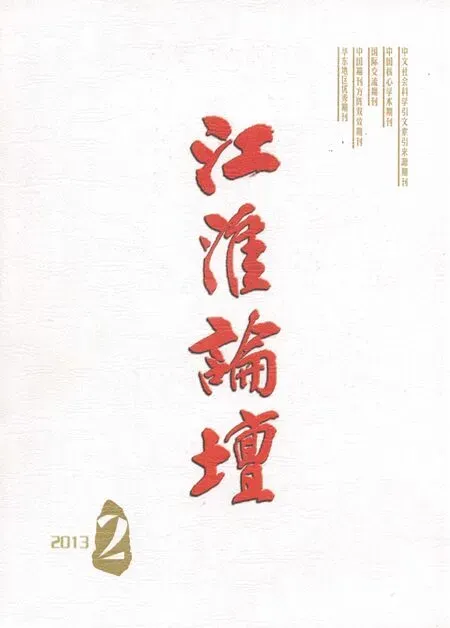中西比較詩(shī)學(xué)的對(duì)話危機(jī)及詩(shī)學(xué)話語(yǔ)轉(zhuǎn)型*
范方俊
(中國(guó)人民大學(xué)文學(xué)院,北京 100872)
當(dāng)代社會(huì)是一個(gè)強(qiáng)調(diào)對(duì)話的社會(huì)。在對(duì)話成為時(shí)代主潮的背景下,中西比較詩(shī)學(xué)的基點(diǎn)也一躍從“比較”轉(zhuǎn)向了“對(duì)話”,走向?qū)υ挸蔀橹形鞅容^詩(shī)學(xué)發(fā)展的必由之路。而中西詩(shī)學(xué)對(duì)話在大大拓展了中西詩(shī)學(xué)比較研究的視野及思路的同時(shí),自身也面臨著一系列的理論和現(xiàn)實(shí)問(wèn)題。走向?qū)υ挼闹形鞅容^詩(shī)學(xué)由此成為比較學(xué)界令人矚目的焦點(diǎn)。
一、中西詩(shī)學(xué)對(duì)話的緣起
中西詩(shī)學(xué)對(duì)話既是近代以來(lái)中西文化碰撞下的時(shí)代產(chǎn)物,同時(shí)也是詩(shī)學(xué)自身領(lǐng)域內(nèi)中西兩大詩(shī)學(xué)體系互為“他者”、反省自我的必然結(jié)果。
首先是中國(guó)傳統(tǒng)詩(shī)學(xué)在西方詩(shī)學(xué)沖擊下凸現(xiàn)出的“現(xiàn)代轉(zhuǎn)型”使然。中國(guó)傳統(tǒng)詩(shī)學(xué)是在自身文化系統(tǒng)內(nèi)生發(fā)的一套詩(shī)學(xué)體系,無(wú)論是在內(nèi)在的文化底蘊(yùn)還是外在的理論表述上都迥異于西方詩(shī)學(xué)。作為中國(guó)傳統(tǒng)文化的一個(gè)重要組成部分,中國(guó)傳統(tǒng)詩(shī)學(xué)一直受到中國(guó)學(xué)人的珍視。然而,進(jìn)入近代社會(huì)以后,隨著近代中國(guó)社會(huì)的急遽變化,中國(guó)傳統(tǒng)詩(shī)學(xué)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質(zhì)疑。這種情況的出現(xiàn)是與當(dāng)時(shí)整個(gè)時(shí)代氛圍密切相關(guān)的。19世紀(jì)中葉鴉片戰(zhàn)爭(zhēng)后,古老的中華封建帝國(guó)一下子從四方仰慕的天朝大國(guó)淪落為任人宰割的半殖民地,救亡圖存成為近代中國(guó)社會(huì)的時(shí)代主題。當(dāng)時(shí)一批具有先進(jìn)意識(shí)的先覺(jué)者已經(jīng)清醒地認(rèn)識(shí)到,中西方的巨大落差不僅體現(xiàn)于政治、經(jīng)濟(jì)、軍事層面,同時(shí)也體現(xiàn)于思想文化層面。1894—1895年中日甲午戰(zhàn)爭(zhēng)的失敗和戊戌變法的流產(chǎn)更讓他們痛楚地意識(shí)到,僅僅依靠軍事上的“船堅(jiān)炮利”和政治上自上而下的社會(huì)改良不可能挽救中國(guó),唯有借助思想文化的啟蒙,發(fā)動(dòng)民眾,實(shí)現(xiàn)近代中國(guó)自下而上的社會(huì)變革。由于中國(guó)舊有的文化傳統(tǒng)長(zhǎng)期陷于自我封閉之中,已不可能自主生發(fā)出時(shí)代迫切需要的近代思想意識(shí),人們只好“別求新聲于異邦”,向西方尋求先進(jìn)的思想文化真理。但這并不意味著中國(guó)文化就此走向“全盤西化”的道路,這一方面是由于先覺(jué)者們浸染于中國(guó)傳統(tǒng)文化太深,在感情上對(duì)她難以割舍,另一方面他們?cè)谝槲鞣轿幕畷r(shí)已理智地察覺(jué)到了它的不足。因此,他們引入西方文化并不是用它來(lái)替代中國(guó)的傳統(tǒng)文化,而是要借助西方文化的參照,實(shí)現(xiàn)中國(guó)傳統(tǒng)文化的近現(xiàn)代轉(zhuǎn)型。中國(guó)傳統(tǒng)詩(shī)學(xué)即是在上述歷史背景下于19世紀(jì)末20世紀(jì)初開(kāi)始自身的現(xiàn)代轉(zhuǎn)型的。早在1905年王國(guó)維在《論近年之學(xué)術(shù)界》一文中,在肯定了西洋新學(xué)語(yǔ)的輸入對(duì)于轉(zhuǎn)型中國(guó)傳統(tǒng)詩(shī)學(xué)的必要性的同時(shí),也分析指出,中西學(xué)術(shù)話語(yǔ)各有其片面性,不能盲目認(rèn)定西方的學(xué)術(shù)方式就是絕對(duì)地好,應(yīng)該借鑒西洋文學(xué)批評(píng)的長(zhǎng)處來(lái)補(bǔ)足中國(guó)傳統(tǒng)文學(xué)批評(píng)的不足。進(jìn)入20世紀(jì)30至40年代,隨著中西詩(shī)學(xué)比較研究的深入,以朱光潛、錢鐘書為代表的中國(guó)比較學(xué)者更加注意到在中西詩(shī)學(xué)的融通中“轉(zhuǎn)型”中國(guó)傳統(tǒng)詩(shī)學(xué),并取得了令人矚目的實(shí)績(jī)。建國(guó)后,由于眾所周知的原因,中國(guó)傳統(tǒng)詩(shī)學(xué)的現(xiàn)代轉(zhuǎn)型被迫中斷,中國(guó)的文學(xué)理論一古腦兒地倒向了蘇俄文論。改革開(kāi)放后,隨著西方現(xiàn)當(dāng)代文化的大量涌入,中國(guó)文論又一邊倒向了西方現(xiàn)當(dāng)代文論。于是,當(dāng)人們冷靜地審視當(dāng)代中國(guó)文論的現(xiàn)況時(shí),有關(guān)中國(guó)傳統(tǒng)詩(shī)學(xué)現(xiàn)代轉(zhuǎn)型的呼聲再次在中華大地上空響起。回顧中國(guó)文論近百年間經(jīng)歷過(guò)的風(fēng)風(fēng)雨雨,實(shí)現(xiàn)中國(guó)傳統(tǒng)詩(shī)學(xué)的現(xiàn)代轉(zhuǎn)型可謂是一個(gè)世紀(jì)性的主題,尋求與西方詩(shī)學(xué)的對(duì)話就成了中國(guó)傳統(tǒng)詩(shī)學(xué)實(shí)現(xiàn)自身現(xiàn)代轉(zhuǎn)型的必然抉擇。
其次是西方比較詩(shī)學(xué)界對(duì)于包括中國(guó)傳統(tǒng)詩(shī)學(xué)在內(nèi)的東方文化視野的吸納使然。美國(guó)學(xué)者厄爾·邁納(Earl Miner)在其《比較詩(shī)學(xué):文學(xué)理論的跨文化研究札記》一書中,令人信服地指出:東西方的原創(chuàng)型詩(shī)學(xué)體系都是在各自的文化系統(tǒng)中產(chǎn)生的,“跨文化”是比較詩(shī)學(xué)的最根本性的特征。眾所周知,西方奠基于亞里士多德(Aristotle)《詩(shī)學(xué)》之上的理論體系,盡管在不同時(shí)期、不同地域內(nèi)的表述方式上存在著這樣或那樣的差異,但從根本上講,它們是屬于同一個(gè)西方文化圈內(nèi)的詩(shī)學(xué)體系。相比之下,中國(guó)傳統(tǒng)詩(shī)學(xué)則完全屬于另一個(gè)與西方文化幾無(wú)直接關(guān)聯(lián)的異質(zhì)文化圈。巨大的文化差異過(guò)去曾使不少西方學(xué)者對(duì)中西詩(shī)學(xué)比較的可行性感到難以想象。然而,比較詩(shī)學(xué)的“跨文化”特征決定了比較詩(shī)學(xué)必須有勇氣去跨越不同的文化圈子,否則,比較詩(shī)學(xué)很難名副其實(shí)。而且,中西詩(shī)學(xué)間的巨大差異固然給中西比較詩(shī)學(xué)在整體研究上帶來(lái)了很大的困難,但它同時(shí)也為比較詩(shī)學(xué)研究走向深化提供了一個(gè)難得的契機(jī),因?yàn)橥耆胺俏鞣交钡闹袊?guó)傳統(tǒng)詩(shī)學(xué)不僅為西方詩(shī)學(xué)提供了一面反視自我的“鏡子”,而且更為難得的是,在許多方面中國(guó)傳統(tǒng)詩(shī)學(xué)都與西方詩(shī)學(xué)有著一種令人瞠目的互補(bǔ)性。顯然,缺少中國(guó)傳統(tǒng)詩(shī)學(xué)的參照,西方詩(shī)學(xué)無(wú)法奢談所謂的一般文學(xué)理論。正是從這個(gè)意義出發(fā),美國(guó)華裔學(xué)者劉若愚一生孜孜不倦地從事著向西方學(xué)界介紹中國(guó)傳統(tǒng)詩(shī)學(xué)的“鋪路”工作,得到了西方比較學(xué)界一些有識(shí)之士的贊賞與首肯。美國(guó)學(xué)者紀(jì)廉 (Guillen)曾贊同地表示:“在某一層意義說(shuō)來(lái),東西比較文學(xué)研究是,或應(yīng)該是這么多年來(lái)(西方)的比較文學(xué)研究所準(zhǔn)備達(dá)致的高潮,只有當(dāng)兩大系統(tǒng)的詩(shī)歌互相認(rèn)識(shí)、互相關(guān)照,一般文學(xué)中理論的大爭(zhēng)端始可以全面處理。”而邁納基于東西方文化視野的比較詩(shī)學(xué)研究也是得益于劉若愚的啟發(fā)。不過(guò),更能體現(xiàn)西方比較學(xué)界態(tài)度轉(zhuǎn)變的當(dāng)屬烏爾利希·維斯坦因(Ulrich Weisstein)。美國(guó)學(xué)者維斯坦因一向以治學(xué)嚴(yán)謹(jǐn)、持論公允為國(guó)際比較學(xué)界稱道,他早年撰寫的《比較文學(xué)與文學(xué)理論》一書被公認(rèn)為關(guān)于比較文學(xué)的權(quán)威性著作,然而就是在這本書里,他對(duì)東西方跨文化間的比較研究持懷疑與否定的態(tài)度,但隨著西方比較學(xué)界對(duì)于東方特別是中國(guó)的日益關(guān)注,他對(duì)自己的上述觀點(diǎn)作了反省,對(duì)未能在過(guò)去看到東西方文學(xué)比較研究的必要性感到后悔。通過(guò)與中國(guó)同行們的交流,他提出了“絕對(duì)的平行”的觀念,對(duì)那種沒(méi)有事實(shí)聯(lián)系的,非歷史的跨文化的比較研究持肯定態(tài)度。與此同時(shí),越來(lái)越多的西方學(xué)者認(rèn)識(shí)到與包括中國(guó)詩(shī)學(xué)在內(nèi)的東方詩(shī)學(xué)體系進(jìn)行對(duì)話的必要性。可以說(shuō),西方學(xué)者掀起的一輪又一輪的與東方詩(shī)學(xué)對(duì)話的熱潮,既得益于西方比較詩(shī)學(xué)界對(duì)東方視野的拓展,同時(shí)也是比較詩(shī)學(xué)渴望走向深化的歷史必然。
總之,正是相互間的“互見(jiàn)”及借鑒的需要使得中西詩(shī)學(xué)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對(duì)話之途。不過(guò),透過(guò)以上的分析,我們也清楚地看到,由于中西方所面臨的對(duì)話語(yǔ)境存在著明顯的分野,兩者對(duì)于對(duì)話的期望是不盡相同的。對(duì)于中國(guó)詩(shī)學(xué)而言,對(duì)話的最終目的是為了實(shí)現(xiàn)中國(guó)傳統(tǒng)詩(shī)學(xué)的現(xiàn)代轉(zhuǎn)型,以此來(lái)推進(jìn)當(dāng)代文藝學(xué)的建設(shè),誠(chéng)如黃藥眠、童慶炳在《中西比較詩(shī)學(xué)體系·序言》所表述的:“中西比較詩(shī)學(xué)正意味著一種返回原初詩(shī)意根基的舉動(dòng)。中國(guó)詩(shī)學(xué)與西方詩(shī)學(xué)相比較,固然要尋求二者的共通性與差異性,但根本目的并不在此。這個(gè)比較本身并不基于一個(gè)無(wú)所不在的視點(diǎn),而只能是基于中國(guó)詩(shī)學(xué)的前景這一特定視點(diǎn)。這一特定視點(diǎn)是由我們的‘成見(jiàn)’。我們總是基于自己的‘成見(jiàn)’,從自己的‘成見(jiàn)’出發(fā),超乎‘成見(jiàn)’而又返回‘成見(jiàn)’去比較的。中西詩(shī)學(xué)的比較,說(shuō)到底為的是中國(guó)詩(shī)學(xué)的前景。而這種前景并不能憑空猜測(cè),我們宜站在原初詩(shī)意根基上去眺望前景。所以奔向前景正意味著返回原初根基。因此,中國(guó)詩(shī)學(xué)是為解決自身問(wèn)題,為擺脫自身困境而求助于中西比較詩(shī)學(xué)的,這種比較實(shí)際上就是對(duì)中國(guó)詩(shī)學(xué)自身的原初詩(shī)意根基的尋找。”而對(duì)于西方詩(shī)學(xué)而言,對(duì)話的真正目的在于調(diào)整自身詩(shī)學(xué)體系的偏狹與不足,使之上升為一種更具普泛性及適用于更大范圍的共同詩(shī)學(xué)。毫無(wú)疑問(wèn),中西詩(shī)學(xué)在展開(kāi)平等對(duì)話的同時(shí),仍然存在著一個(gè)以誰(shuí)為主的問(wèn)題。我們決不應(yīng)該將對(duì)話的主動(dòng)權(quán)拱手相讓。這就要求我們?cè)趫?jiān)持與西方詩(shī)學(xué)對(duì)話中尋求傳統(tǒng)詩(shī)學(xué)現(xiàn)代轉(zhuǎn)型的同時(shí),必須對(duì)西方式的“共通性”、“一致性”保持一種民族性的警覺(jué)。一旦背離了上述立場(chǎng),將使我們?cè)谥形髟?shī)學(xué)對(duì)話中處于極其被動(dòng)的地位。事實(shí)上,當(dāng)前中西詩(shī)學(xué)對(duì)話中出現(xiàn)的一系列問(wèn)題已明白無(wú)誤地告訴我們:我們正陷入中西詩(shī)學(xué)對(duì)話的“危機(jī)”之中。
二、中西詩(shī)學(xué)對(duì)話的危機(jī)
對(duì)話,已成為當(dāng)今中國(guó)比較學(xué)界的一個(gè)熱門口號(hào)。應(yīng)該說(shuō),走出自我封閉,主動(dòng)尋求與西方詩(shī)學(xué)的對(duì)話,體現(xiàn)了中國(guó)比較學(xué)界可貴的自覺(jué)意識(shí)和令人稱道的國(guó)際眼光。但與此同時(shí),我們?cè)谂c西方詩(shī)學(xué)的對(duì)話過(guò)程中也出現(xiàn)了一些不容回避的問(wèn)題,其中最突出的就是我們究竟該如何來(lái)理解對(duì)話以及如何去實(shí)施對(duì)話,在這些方面,中國(guó)比較學(xué)界的應(yīng)答顯然不夠盡如人意,由此引發(fā)的中西詩(shī)學(xué)對(duì)話“危機(jī)”在所難免。
首先是理論層面的危機(jī)。如前所述,中西詩(shī)學(xué)對(duì)話是在中國(guó)傳統(tǒng)詩(shī)學(xué)實(shí)現(xiàn)自身現(xiàn)代轉(zhuǎn)型的特定歷史語(yǔ)境下凸現(xiàn)的,這就決定了我們參與其中的中西詩(shī)學(xué)對(duì)話的終極目標(biāo)必須是以實(shí)現(xiàn)中國(guó)傳統(tǒng)詩(shī)學(xué)現(xiàn)代轉(zhuǎn)型作為其最后的歸宿,然而占據(jù)中國(guó)比較學(xué)界的主導(dǎo)性意見(jiàn)卻是:中西詩(shī)學(xué)對(duì)話的目的在于相互間的“理解”和“溝通”。不可否認(rèn),中西對(duì)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促進(jìn)雙方“理解與溝通”的作用,但是,對(duì)于中西比較詩(shī)學(xué)而言,“理解與溝通”絕不應(yīng)是中西詩(shī)學(xué)對(duì)話的全部目的,甚至可以說(shuō)不是主要目的,因?yàn)橹形鞅容^詩(shī)學(xué)的最終目的不在于達(dá)致相互間的交流與溝通,而是以實(shí)現(xiàn)自身詩(shī)學(xué)建構(gòu)為終極指向的。從這個(gè)意義上講,中西詩(shī)學(xué)對(duì)話作為一種深化中西比較詩(shī)學(xué)研究的手段,其最終目的必定是服從于中西比較詩(shī)學(xué)的最終目標(biāo)的,因此,中西詩(shī)學(xué)對(duì)話的最終目的并不止于和西方詩(shī)學(xué)尋求“理解與溝通”,而是要通過(guò)與西方詩(shī)學(xué)的平等對(duì)話,最終實(shí)現(xiàn)中國(guó)當(dāng)代詩(shī)學(xué)的理論建構(gòu)。關(guān)于這一點(diǎn),錢中文曾正確地指出:“東西文化交流的目的,自然在于互通文化上有無(wú),形成文化互補(bǔ),但這不是目的的全部,而交流的深層意義還在于引入外國(guó)文化中的有用部分,用以激活本土文化,從而進(jìn)入創(chuàng)新,推動(dòng)整個(gè)文化的發(fā)展”。在他看來(lái),不唯文化對(duì)話是這樣,東西方文學(xué)理論的對(duì)話也是如此,所以,他把中西文學(xué)理論的對(duì)話概括為“誤差、激活、融化與創(chuàng)新”。令人遺憾的是,由于人們幾乎眾口一詞地把“對(duì)話”偏解為“理解與溝通”,鐘中文的上述主張一直未能引起中國(guó)比較學(xué)界應(yīng)有的重視,其中的緣由的確引人深思。多年來(lái),中國(guó)比較學(xué)界一直熱心倡導(dǎo)中西詩(shī)學(xué)對(duì)話,這個(gè)大方向無(wú)疑是正確的。不應(yīng)否認(rèn)人類之間存在著“一致”與“共通”之處,但一致性與共通性的獲得絕不能是以犧牲民族性、差異性為代價(jià)的。因此,中西詩(shī)學(xué)對(duì)話的當(dāng)務(wù)之急不是“總結(jié)不同文化體系長(zhǎng)期積累的豐富經(jīng)驗(yàn),從不同語(yǔ)境,通過(guò)對(duì)話來(lái)解決人類在文學(xué)方面的共同問(wèn)題”,而是恢復(fù)對(duì)話的應(yīng)有之義,向各種形式的話語(yǔ) “獨(dú)白”宣戰(zhàn),在多元對(duì)話格局中實(shí)現(xiàn)中國(guó)傳統(tǒng)詩(shī)學(xué)的現(xiàn)代轉(zhuǎn)型。由于中國(guó)比較學(xué)界一味強(qiáng)調(diào)中西詩(shī)學(xué)對(duì)話的一致性、交流性,而有意無(wú)意地忽視中西詩(shī)學(xué)之間的差異性和對(duì)話的建構(gòu)性,使得我們未能真正置身于中西詩(shī)學(xué)的對(duì)話當(dāng)中,中國(guó)詩(shī)學(xué)更多地是充當(dāng)了被西方詩(shī)學(xué)闡發(fā)、說(shuō)明的角色。
其次是實(shí)踐層面的危機(jī)。這是理論層面的危機(jī)在實(shí)踐層面的直接延續(xù)。由于中國(guó)比較學(xué)界把中西詩(shī)學(xué)對(duì)話偏解為“跨文化的理解與溝通”,于是,在尋求中西詩(shī)學(xué)對(duì)話的具體路徑上,除了強(qiáng)調(diào)中西詩(shī)學(xué)間的相互譯介外,尤其重視中西詩(shī)學(xué)間的雙向“闡發(fā)”。作為由中國(guó)學(xué)者首創(chuàng)的研究方法,闡發(fā)研究一直被視作與影響研究、平行研究相并列的一種基本的比較文學(xué)方法論。進(jìn)入20世紀(jì)90年代,它又引人注目地同中西詩(shī)學(xué)對(duì)話聯(lián)系在一起。中國(guó)比較學(xué)界樂(lè)觀地認(rèn)為:“‘闡發(fā)研究’是一種‘開(kāi)辟道路’式的研究,好比戰(zhàn)場(chǎng)上的先頭部隊(duì),擔(dān)負(fù)著開(kāi)辟道路、掃清障礙等任務(wù),為后續(xù)部隊(duì)打開(kāi)一條前進(jìn)的通道。闡發(fā)研究正是使中國(guó)文學(xué)真正介入國(guó)際性文學(xué)交流與對(duì)話,尋求中西融匯通道的最佳突破口,它創(chuàng)造了從術(shù)語(yǔ)、范疇到觀點(diǎn)和理論模式等多方面的溝通的條件,掃清了中西方相互理解的一些障礙,為中西比較文學(xué)開(kāi)辟了一條前進(jìn)的通道。”在他們看來(lái),闡發(fā)研究作為中西詩(shī)學(xué)實(shí)現(xiàn)對(duì)話的必由之路似乎是理所當(dāng)然的,但探究一下“闡發(fā)研究”的歷史流變及理論內(nèi)涵,上述的結(jié)論遠(yuǎn)非那么可靠。
事實(shí)上,早在20世紀(jì)初中國(guó)學(xué)者如王國(guó)維、吳宓、朱光潛等人已事實(shí)上開(kāi)啟了援用西方文學(xué)理論來(lái)闡發(fā)中國(guó)文學(xué)及文論的先河。不過(guò),“闡發(fā)法”作為一種特定的比較文學(xué)研究方法的正式提出卻是20世紀(jì)70年代以后的事。1976年,臺(tái)灣學(xué)者古添洪、陳慧樺在他們所編的《比較文學(xué)的墾拓在臺(tái)灣》一書的“序言”中大膽地把晚清以來(lái)中國(guó)學(xué)者 “援用西方文學(xué)理論與方法并加以考驗(yàn)、調(diào)整以用之于中國(guó)文學(xué)之研究”稱作是“比較文學(xué)中的中國(guó)派”。三年后,古添洪在《中西比較文學(xué):范疇、方法、精神的初探》一文中,明確地把援用西方文學(xué)理論從事中國(guó)文學(xué)及文論的研究命名為“闡發(fā)研究”。“闡發(fā)研究”提出后,立即遭致包括中國(guó)大陸學(xué)者在內(nèi)的國(guó)際比較學(xué)界的一致批評(píng)。原因很簡(jiǎn)單,因?yàn)椤叭魏我粐?guó)文學(xué)都不能沒(méi)有自己的民族傳統(tǒng),不要說(shuō)像我們中華民族這樣一個(gè)具有古老悠久文明的國(guó)家……完全以自己的民族文學(xué)的模式去衡量別的民族的文學(xué)不僅是不明智的,也是粗暴的……這反映了一種帝國(guó)主義的態(tài)度;反過(guò)來(lái),完全要按別的民族文學(xué)的模式來(lái)衡量自己的文學(xué)也同樣是幼稚的、卑怯的,這反映了一種民族虛無(wú)主義的態(tài)度和奴化心理”。 不過(guò),大陸學(xué)者認(rèn)為闡發(fā)研究的“癥結(jié)不在方法本身,而在于它的解釋者提出的界說(shuō)是錯(cuò)誤的,至少是不完全的”,認(rèn)為闡發(fā)研究不應(yīng)該是單向,而應(yīng)該是雙向的,即相互的,“是不同民族文學(xué)的相互闡發(fā)、相互發(fā)明……特別是在理論(或曰詩(shī)學(xué))的領(lǐng)域內(nèi),將不同民族的文學(xué)理論互相闡發(fā),對(duì)于文學(xué)理論的建設(shè)有特殊的意義”。 然而,盡管在理論表述上,大陸學(xué)者使闡發(fā)研究全面化、系統(tǒng)化了,但仍然沒(méi)有從根本上解決闡發(fā)研究作為一種方法論自身存在的難以克服的理論缺憾。闡發(fā)研究,無(wú)論是單向的還是雙向或多向的闡發(fā),究其實(shí)質(zhì)“是指用外來(lái)的理論方法去闡明本土的文學(xué)創(chuàng)造,即以形成于一種文化系統(tǒng)中的文學(xué)理論批評(píng)模子去分析處理形成于另一文化系統(tǒng)中的文學(xué)現(xiàn)象”,但問(wèn)題是用形成于其一特定文化模子內(nèi)的文學(xué)理論去“分析處理”另一文化模子內(nèi)的文學(xué)與文論在方法論上是否合理?“文化模子”是由美籍華裔學(xué)者葉維廉提出來(lái)的。在《東西方文學(xué)中“模子”的應(yīng)用》一文里,他指出:人類所有的心智活動(dòng),不論其在創(chuàng)作上或是在學(xué)理的推演上以及其最終的決定和判斷,都有意無(wú)意地必以某一種“模子”為起點(diǎn),“模子”是結(jié)構(gòu)行為的一種力量,決定人的運(yùn)思及行為方式。文化的含義更是人類結(jié)構(gòu)行為的意思,由于文化因人而異,因而形成不同的文化模子并由此形成文學(xué)模式的差異。因此,在進(jìn)行不同類型文化背景下的文學(xué)比較研究時(shí),不應(yīng)該用一方既定的文學(xué)“模子”硬套到另一文學(xué)之上,“模子”誤用將不可避免地產(chǎn)生歪曲及破壞性。單從方法論角度著眼,闡發(fā)研究是一種不折不扣的“模子”誤用。希望用闡發(fā)研究來(lái)為中西詩(shī)學(xué)對(duì)話“掃清障礙,開(kāi)辟道路”的做法是不現(xiàn)實(shí)的。中西詩(shī)學(xué)對(duì)話必須尋找新的路徑。
三走向語(yǔ)言闡釋之途
必須指出,理論及實(shí)踐層面的危機(jī)并非中西詩(shī)學(xué)對(duì)話危機(jī)的全部,甚至只能說(shuō)是當(dāng)前中西詩(shī)學(xué)對(duì)話危機(jī)的一些表征,另一種深層次的“危機(jī)”還遠(yuǎn)遠(yuǎn)沒(méi)有引起中國(guó)比較學(xué)界的足夠重視。仔細(xì)地審視我們有關(guān)中西詩(shī)學(xué)對(duì)話的討論,不難發(fā)現(xiàn),盡管人們對(duì)中西詩(shī)學(xué)對(duì)話的現(xiàn)實(shí)性與可能性、對(duì)話的基礎(chǔ)、對(duì)話的意義及前景等問(wèn)題發(fā)表了不少看法,甚至“話語(yǔ)”一詞也頻繁出現(xiàn)于專家們的論文中,但絕大多數(shù)的議論都無(wú)一例外地忽視了對(duì)話的語(yǔ)言性這一話題,而語(yǔ)言性恰恰是對(duì)話的根本性特征之一。其實(shí),西方的對(duì)話理論都十分關(guān)注對(duì)話的語(yǔ)言性特征,甚至直接把對(duì)話理論稱作“普通語(yǔ)言學(xué)”或“超語(yǔ)言學(xué)”,就是要強(qiáng)調(diào)對(duì)話研究不能忽視語(yǔ)言視角的參與,因?yàn)樗鼈儭把芯康亩际峭粋€(gè)具體的,非常復(fù)雜而又多方面的現(xiàn)象——語(yǔ)言”。毫無(wú)疑問(wèn),中西詩(shī)學(xué)對(duì)話的“危機(jī)”要從根本上予以消除,必須引入語(yǔ)言研究視角,借用德國(guó)哲學(xué)家馬丁·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的話來(lái)說(shuō),就是“走向語(yǔ)言之途”。
對(duì)于比較詩(shī)學(xué)而言,語(yǔ)言問(wèn)題從來(lái)沒(méi)有像今天這么重要過(guò)。盡管從一開(kāi)始比較文學(xué)就被界定為一種“跨語(yǔ)言的文學(xué)研究”,但語(yǔ)言問(wèn)題一直未能夠引起比較學(xué)界的足夠重視。自從比較文學(xué)法國(guó)學(xué)派的奠基人梵·弟根(Van Tieghem)把精通多種語(yǔ)言視作“比較文學(xué)家的必備之具”之后,盡可能多地通曉歐洲各國(guó)的語(yǔ)言就成了早期歐美比較學(xué)者們的一個(gè)共識(shí)。事實(shí)上,出于家庭背景或?qū)W術(shù)淵源上的原因,對(duì)于他們而言,同時(shí)掌握西歐幾個(gè)主要國(guó)家的語(yǔ)言如法語(yǔ)、英語(yǔ)、德語(yǔ)等幾乎沒(méi)有什么問(wèn)題,即便是再多上一二門歐洲其他國(guó)家的語(yǔ)言也是常有的事。正是在這種背景下,當(dāng)比較文學(xué)美國(guó)學(xué)派的勒內(nèi)·韋勒克(Rene Wellek)表示,包括比較文學(xué)在內(nèi)的文學(xué)研究“不必考慮語(yǔ)言上的區(qū)別”時(shí),也就絲毫不用奇怪了。可以說(shuō),歐美比較學(xué)者之所以如此忽視語(yǔ)言在比較詩(shī)學(xué)中的作用,一個(gè)很重要的原因是歐美諸國(guó)的語(yǔ)言間的親緣關(guān)系十分密切,同屬于一個(gè)統(tǒng)一的印歐語(yǔ)系,彼此之間沒(méi)有本質(zhì)上的差異,因此他們不可能去關(guān)注比較詩(shī)學(xué)中的語(yǔ)言問(wèn)題。然而,隨著中西比較詩(shī)學(xué)的展開(kāi),語(yǔ)言問(wèn)題的重要性與尖銳性突出地顯現(xiàn)出來(lái)。反映在中西詩(shī)學(xué)對(duì)話中,首當(dāng)其沖的就是中西詩(shī)學(xué)的話語(yǔ)問(wèn)題。
話語(yǔ)無(wú)疑是困擾當(dāng)今中西詩(shī)學(xué)對(duì)話的核心問(wèn)題。中國(guó)比較學(xué)界曾就中西詩(shī)學(xué)對(duì)話中的話語(yǔ)問(wèn)題展開(kāi)過(guò)熱烈的討論,并達(dá)成下述共識(shí):中西詩(shī)學(xué)對(duì)話如果完全采用西方的那一套話語(yǔ),如果只用這套話語(yǔ)所構(gòu)成的模式和規(guī)則來(lái)衡量和詮釋本土文化,那么大量最具本土特色和獨(dú)創(chuàng)性的活的文化就有可能因不符合這套話語(yǔ)的準(zhǔn)則而被摒除在外。另一方面,我們也不能用完全屬于本土的文化話語(yǔ)來(lái)和他種文化進(jìn)行對(duì)話。在筆者看來(lái),中西詩(shī)學(xué)對(duì)話不能完全采用西方詩(shī)學(xué)的一套話語(yǔ),這是顯而易見(jiàn)的。因?yàn)樾纬蓪?duì)話的最起碼條件是至少兩個(gè)聲音的存在,缺少中國(guó)自身詩(shī)學(xué)話語(yǔ)的參與,任何形式的中西詩(shī)學(xué)“對(duì)話”都不可能是一種真正意義上的“對(duì)話”,只能是西方詩(shī)學(xué)話語(yǔ)變著法的“獨(dú)白”。至于“我們也不能用完全屬于本土的文化話語(yǔ)來(lái)和他種文化進(jìn)行對(duì)話”的建議則有必要重新審視。試想中國(guó)詩(shī)學(xué)如果不用自身的詩(shī)學(xué)話語(yǔ),那么我們?cè)撚檬裁丛?shī)學(xué)話語(yǔ)去與西方詩(shī)學(xué)對(duì)話呢?看來(lái),問(wèn)題出在對(duì)詩(shī)學(xué)話語(yǔ)的理解上。
從本質(zhì)上講,“話語(yǔ)是指在一定文化傳統(tǒng)和社會(huì)歷史中形成的思維,言說(shuō)的基本范疇和基本法則,是一種文化對(duì)自身的意義建構(gòu)方式的基本設(shè)定。”由于話語(yǔ)總是在具體的言說(shuō)中才成其為話語(yǔ)的,因此,詩(shī)學(xué)話語(yǔ)在言說(shuō)中必然具體呈現(xiàn)為一系列滲透著本民族文化精神的基本概念、范疇或術(shù)語(yǔ),以及其特有的言說(shuō)方式和意義生成方式。固然從整體上著眼,中西詩(shī)學(xué)對(duì)話是中西兩個(gè)詩(shī)學(xué)主體之間的對(duì)話,但在具體的對(duì)話過(guò)程中,中西詩(shī)學(xué)對(duì)話又必然表現(xiàn)為中西詩(shī)學(xué)話語(yǔ)間的對(duì)話,因?yàn)槿魏涡问降膶?duì)話都是必須借助于具體的話語(yǔ)才能得以實(shí)現(xiàn)的。正因此,任何關(guān)于中西詩(shī)學(xué)對(duì)話的考察都必須是基于中西詩(shī)學(xué)話語(yǔ)之上的研究。應(yīng)該說(shuō),中國(guó)傳統(tǒng)詩(shī)學(xué)曾在自身的文化系統(tǒng)內(nèi)形成了一套獨(dú)具本民族特色的詩(shī)學(xué)話語(yǔ)系統(tǒng)。然而,進(jìn)入近代社會(huì)以來(lái),隨著西方詩(shī)學(xué)話語(yǔ)的大量引入,中國(guó)傳統(tǒng)詩(shī)學(xué)話語(yǔ)系統(tǒng)受到了無(wú)情的沖擊。在西方詩(shī)學(xué)話語(yǔ)系統(tǒng) “條理明晰”、“義界分明”等“現(xiàn)代性”特征得到極力渲染的同時(shí),中國(guó)傳統(tǒng)詩(shī)學(xué)話語(yǔ)體系卻被冠以“邏輯匱乏”、“概念含混”等惡名痛加貶斥,直至被徹底打入冷宮無(wú)人問(wèn)津,最終導(dǎo)致當(dāng)代中國(guó)詩(shī)學(xué)話語(yǔ)的“失語(yǔ)”。所謂“失語(yǔ)”,并非指當(dāng)代中國(guó)詩(shī)學(xué)沒(méi)有一套詩(shī)學(xué)話語(yǔ)系統(tǒng),而是“指她沒(méi)有一套自己的而非別人的話語(yǔ)規(guī)則。當(dāng)文壇上到處流行的現(xiàn)實(shí)主義、浪漫主義、表現(xiàn)主義、唯美主義、象征、頹廢、感傷等等西方文論話語(yǔ)時(shí),中國(guó)現(xiàn)代化文論就已經(jīng)失落了自我。她并沒(méi)有一套屬于自己的獨(dú)特話語(yǔ)系統(tǒng),而僅僅是承襲了西方文論的話語(yǔ)系統(tǒng)”。 不可否認(rèn),與西方詩(shī)學(xué)話語(yǔ)相比,中國(guó)傳統(tǒng)詩(shī)學(xué)話語(yǔ)確實(shí)存在著諸如 “條理欠明”、“義界不清”等方面的不足,但這并不能抹殺中國(guó)傳統(tǒng)詩(shī)學(xué)話語(yǔ)在直觀、形象、多義的詩(shī)意傳達(dá)中的過(guò)人之處,而這恰恰是講求義界分明、邏輯嚴(yán)整的西方詩(shī)學(xué)話語(yǔ)所無(wú)法比擬的。中西詩(shī)學(xué)話語(yǔ)可以說(shuō)是各有短長(zhǎng)、瑕瑜互見(jiàn),并且體現(xiàn)出一種驚人的互補(bǔ)性,一方之所“長(zhǎng)”,恰恰是對(duì)方之所“短”,這就為雙方的詩(shī)學(xué)話語(yǔ)對(duì)話提供了一個(gè)絕好的“契機(jī)”。從這個(gè)意義上講,當(dāng)代中國(guó)詩(shī)學(xué)話語(yǔ)固然要在借鑒西方詩(shī)學(xué)話語(yǔ)的基礎(chǔ)上實(shí)現(xiàn)傳統(tǒng)詩(shī)學(xué)話語(yǔ)的現(xiàn)代轉(zhuǎn)型,與此同時(shí),西方詩(shī)學(xué)話語(yǔ)也必須參照中國(guó)傳統(tǒng)詩(shī)學(xué)話語(yǔ)進(jìn)行必要的自我調(diào)整。事實(shí)上,西方社會(huì)從20世紀(jì)初開(kāi)始就已經(jīng)注意到了自身話語(yǔ)的“危機(jī)”,貫穿于整個(gè)20世紀(jì)的“語(yǔ)言轉(zhuǎn)向”都可以視作西方人試圖調(diào)整自身話語(yǔ)的一種不懈的努力。至于西方人能否在自身語(yǔ)境內(nèi)實(shí)現(xiàn)自我調(diào)整另當(dāng)別論,但西方人已經(jīng)確確實(shí)實(shí)地感受到了對(duì)自身話語(yǔ)進(jìn)行調(diào)整的必要性。這也反過(guò)來(lái)警示我們,不要對(duì)西方詩(shī)學(xué)話語(yǔ)過(guò)分迷信,要對(duì)本民族的傳統(tǒng)詩(shī)學(xué)話語(yǔ)充滿信心。否則,在中西詩(shī)學(xué)的對(duì)話中,我們將不得不再一次面對(duì)中國(guó)詩(shī)學(xué)話語(yǔ)的“失語(yǔ)”的尷尬。
中西詩(shī)學(xué)對(duì)話無(wú)疑要在雙方詩(shī)學(xué)話語(yǔ)之間展開(kāi)。既然中西詩(shī)學(xué)對(duì)話的深層次“危機(jī)”是對(duì)對(duì)話的語(yǔ)言性特征的忽視,那么破除“危機(jī)”的必然出路就在于突出對(duì)中西詩(shī)學(xué)話語(yǔ)的語(yǔ)言性分析。其實(shí),早在寫作《語(yǔ)法與表現(xiàn):中國(guó)古典詩(shī)與英美現(xiàn)代詩(shī)美學(xué)的匯通》、《語(yǔ)言與真理世界:中西美感基礎(chǔ)的生成》等文章中,葉維廉已經(jīng)注意到了對(duì)中西詩(shī)學(xué)話語(yǔ)進(jìn)行語(yǔ)言性探析的重要性。但由于他僅僅把語(yǔ)言視作思維的外在表現(xiàn)形式,故而他把中西語(yǔ)言的異質(zhì)性完全歸結(jié)于中西思維的差異性。值得注意的是,持此觀點(diǎn)的遠(yuǎn)非葉維廉一人,國(guó)內(nèi)比較學(xué)界也通常把漢語(yǔ)言與印歐系語(yǔ)言的差異性歸因于中西思維模式的不同。應(yīng)該說(shuō),從思維影響語(yǔ)言的角度說(shuō),語(yǔ)言是思維的表達(dá)工具本身無(wú)可厚非,但問(wèn)題是語(yǔ)言從來(lái)就不僅僅只是一種表達(dá)思想的手段,同時(shí)也是人類認(rèn)知世界的一種方式,這意味著人在運(yùn)用語(yǔ)言表達(dá)思想的同時(shí),語(yǔ)言從一開(kāi)始就參與了思想的形成。因此,在事關(guān)語(yǔ)言與思維的關(guān)系內(nèi)涵上,不應(yīng)該僅僅糾纏于究竟誰(shuí)決定誰(shuí)之類的無(wú)謂之爭(zhēng),而應(yīng)該關(guān)注二者事實(shí)上存在的同構(gòu)關(guān)系。明確了這一前提,我們才可能對(duì)與思維、語(yǔ)言密切相關(guān)的詩(shī)學(xué)問(wèn)題進(jìn)行深入的探析。比如人們?cè)谡劶爸形髟?shī)學(xué)的根本差異時(shí),總是要?dú)w結(jié)于中西思維方式上的差異,其推論過(guò)程通常是這樣的:中西詩(shī)學(xué)的差異取決于中西文化上的差異,中西文化的根本差異在于中西哲學(xué)的差異,而中西哲學(xué)的根本差異在于中西思維上的差異。關(guān)于中西思維的差異,人們又往往滿足于綜合性與分析性、模糊性與明晰性等諸如此類的描述性說(shuō)明。由于缺少必要的學(xué)理性的證明,常常使得上述的結(jié)論與斷言充斥著太多的主觀性與隨意性,由此推演出的中西詩(shī)學(xué)的比較論斷的說(shuō)服力可想而知。思維固然是看不見(jiàn)、摸不著的,但這并不意味著人們對(duì)于思維的認(rèn)知只能是個(gè)體感悟式的。事實(shí)上,由于語(yǔ)言與思維存在著無(wú)可辯駁的同構(gòu)關(guān)系,我們完全有可能借助對(duì)語(yǔ)言內(nèi)在組織形式的剖析達(dá)到對(duì)人類思維模式的理性認(rèn)知。我們突出對(duì)中西詩(shī)學(xué)話語(yǔ)的語(yǔ)言性特征的分析,其根本目的就是要闡明中西詩(shī)學(xué)差異的根本所在,并通過(guò)對(duì)中西詩(shī)學(xué)話語(yǔ)的分野、融合和轉(zhuǎn)換的揭示、歸納和總結(jié),為中西詩(shī)學(xué)深層次的理論對(duì)話的展開(kāi)創(chuàng)造必要的條件。由此,中西比較詩(shī)學(xué)研究將不可避免地告別慣常的文化或哲學(xué)比較模式,圍繞著中西詩(shī)學(xué)話語(yǔ)的分野、融合和轉(zhuǎn)換這一主軸,堅(jiān)定地走向中西詩(shī)學(xué)的語(yǔ)言闡釋之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