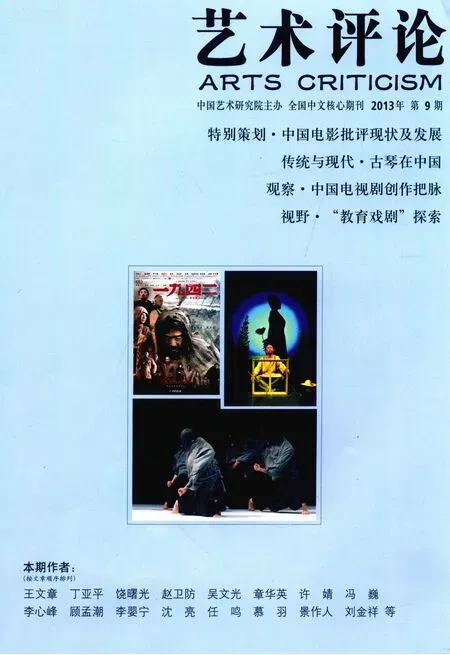中國當代藝術中傳統符號的玄幻迷局
周 青
在經歷了上世紀末、本世紀初過山車般的繁榮之后,中國當代藝術的困頓和落寞已經成為我們不能回避的現實狀態。在這種困頓和落寞的背景下,關于中國當代藝術的出路的思考,幾個依然是眾所周知、耳熟能詳的關鍵詞也許便是“傳統”、“民族化”、“本土化”等等,所謂“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不管是否真的理解和贊同,多數人對于中國當代藝術喧囂之后“原形畢露”的原因分析都集中在當代藝術缺乏獨立的民族性格和圖式,以及過于迎合西方視野下的對于中國認知的趣味和藝術市場資本投機。因此,解決的途徑和方案也就相對一目了然了,即必須立足自己民族和傳統的文化、精神、圖式及時代特征。于是,我們可以看到越來越多的藝術家的作品中開始出現各種各樣的似曾相識的傳統文化符號。之所以說似曾相識,是因為觀者在面對這樣的作品時會發現,這些傳統符號的形式及其在作品中的語境已經很在很大程度上游離于以往既定的狀態,藝術家賦予了這些符號非常個人化和令人困惑的時空環境。這給觀者的認知與闡釋都帶來了相當的困難。中國當代藝術生態便在這種傳統符號表征營造的似是而非、光怪陸離的圖像世界中陷入一個個視覺的玄幻迷局。
中國當代藝術中傳統符號的凸顯與喧囂
在中國當代藝術生態中,不論是架上繪畫、雕塑、影響還是其他藝術樣式,我們不難發現,對于傳統符號的運用從來沒有如此多樣、瘋狂和復雜。藝術家從之前的集體模仿和照搬西方藝術樣式又集體轉向對傳統文化藝術的發掘和挪用。我們既可以看到鋪天蓋地的古代神話及宗教題材中的神怪人物、裝飾性自然紋樣、祥瑞,也可以看到各種各樣的古代民間習俗及日常生活內容的符號。
其實,在藝術創作中,藝術家對于本民族、本地區傳統符號的運用是很自然的事情,任何藝術作品的產生都離不開傳統文化藝術土壤的滋養。站在人類美術史的視野來看,不論是上溯到古代兩河流域美術、古埃及美術及南美洲的瑪雅人藝術,還是文藝復興歐洲各個藝術樣式乃至其他任何時代、國家和地區的藝術,無不帶有鮮明的地區和民族傳統文化及藝術符號特征。以文藝復興為例,除了我們耳熟能詳的三杰達芬奇、米開朗基羅和拉斐爾之外,像威尼斯畫派、尼德蘭畫派等,都涌現出面貌各異的藝術精品。波提切利以其極具裝飾性而又略帶病態的線條詮釋了希臘和羅馬神話題材在文藝復興時代的新注腳。而長期在西方美術史中沒有得到應有重視的北歐尼德蘭畫家群體則用他們雄渾浪漫的筆觸和氣魄向我們展示了今天的荷蘭、比利時和盧森堡一帶勞動人民生活和勞動的壯闊詩篇。特別是包斯(H Bosch 1450 — 1516)的作品,場面宏大,形象眾多,藝術家把北歐的社會萬象、神話傳說融入到自己無限的想象力之中,充滿魔幻現實主義色彩。
所以說,中國當代藝術對于傳統文化藝術符號的運用不但無可厚非,而且是必須的。85思潮時期,星星畫派中的一些藝術家便有意識地使用傳統符號來承載特定的當代精神指向。上海畫家孫良的作品現實了藝術家對于楚漢文化尤其是具有濃郁浪漫主義色彩的荊楚文化的癡迷。號稱當代藝術F4之一的方力均的近期的作品,也從之前呆滯、木訥的大頭形象逐步轉向富有傳統氣息的宏大瑰麗場面,色彩艷麗的祥云、鳳鳥,烘托出一個個令人玩味的視覺烏托邦。如果說,上述藝術家對于傳統符號的運用在當時還屬于相對獨立的、有著一定思考和探索的個案,那么,隨著中國當代藝術市場泡沫的迅速破滅,以及人們對于中國當代藝術的反思,這種運用在中國當代藝術中正在呈現出一種急于求成、生硬拼湊的喧鬧態勢。
中國當代藝術中傳統符號運用的玄幻化傾向
符號,或者說圖式,是個寬泛的概念,是約定的代表某種事物或意義的標記,主要包含有兩層意思,一個是視覺層面的,一個是精神層面的。任何一個民族、地區的傳統文化藝術符號的形成,是在長期的歷史發展過程中,精神內質與視覺特征不斷自我發生、發展、豐富和調整的過程中逐步形成的。各個元素可以是具體的形,色,空間關系,也可以是某種觀念,是這些符號的授意者及創作者借以表達的媒介和途徑,它們集中反映了特定民族和文化的特征,是有著自我完滿特征和內在發展邏輯的。不論是光怪陸離的神怪宗教題材,還是豐富多彩的世間萬象,無不是統一于一個明確的意義和動機構架之中。
王廣義、方力均等人的巨大成功使中國當代藝術家們看到了符號的驚人力量,可惜的是,卻很少有人真正理解符號的應有價值和作用。中國當代藝術市場過山車般的變化和隨之而來的反思并沒有真正讓多數藝術家認真而有效地思考中國當代藝術的真正出路所在。在很多人看來,問題不是出在對符號的態度上,而只是那些呆滯木訥的大頭、文革知青圖式以及調侃式的政治波普等元素已經被藝術家過度投機使用從而使得藝術市場產生了疲憊效應而已,也就是說,需要做的就是重新選擇新的符號加以替代。
從表面上看,這樣的認識和理解并沒有錯。可問題是,如果沒有認清中國當代藝術曾經繁榮背后隱藏的巨大方法論危機,而僅僅從符號的角度來試圖延續或再現曾經的所謂成功,不但無益于中國當代藝術的真正自我重建,就連部分地重現曾經的市場輝煌也是不可能的。這個巨大的方法論危機就是:靠兜售片面的、甚至是有些扭曲和夸張的中國當代社會符號來獲得國外藝術機構和收藏家的青睞,其背后的直接推手便是藝術市場與藝術資本,當代藝術已經成為在民族歷史和文化承擔口號下謀求經濟利益和藝術頭銜的工具。
于是,傳統符號在中國當代藝術中的運用便出現了一種令人眼花繚亂的玄幻化傾向。這種玄幻化一方面是由于藝術家對于自己所選取的傳統符號不求甚解而導致的語義模糊,另一方面則是在前者的基礎上,作者無意甚至有意將傳統符號進行曲解和復雜化,將其組織到一個反復的、時空錯置的環境中,從而營造出一種所謂的夢幻或觀念性迷局的結果。我們可以看到傳統墓室中的鎮墓獸形象陪伴在性感女郎身邊,山海經中的奇鳥怪獸盤旋在燈紅酒綠的都市上空……這些作品讓由于視覺上的新奇性會很多人覺得眼前一亮,為之一振。中國當代藝術的這種玄幻化迷局讓多數的觀看者、批評者乃至藝術家本人在當前的藝術困頓態勢中都陷入了一種自欺欺人的突圍幻想之中。
傳統符號的理性審視與中國當代藝術的重建
在后現代這樣一個觀念性占了主導地位的時代,一方面,那些有著敏銳的洞察力和感知力的藝術家擁有了更大的施展空間,另一方面,也為不少善于藝術投機的人提供了有效庇護。不論某些藝術家的本意和思想深度如何的膚淺,也不論當代藝術的這些“玄幻迷局”如何生硬、空洞,好在中國傳統文化藝術語匯本身具有極大的內涵和闡釋空間,只要不是套用得過于離譜,它們所包含的中國(東方)式的感悟在與當下藝術的接觸和對話中仍然能夠自覺地形成某種契合,只是這種契合可能連藝術家本人都意識不到。同時,中國不甚完善的藝術市場帶給某些此類藝術作品的“回報”,又成為藝術家自我說服與肯定的“資本”。這些表面看起來的合理性和部分的市場“認可”則給中國當代藝術的反思和重構帶來了不易察覺的危機,它以一種溫和而順應惰性的方式麻痹著我們對藝術的敏銳感和責任感。
我們該如何審視和運用我們的傳統符號?它們過去曾經承載了什么?在當下的語境中又有怎樣的重構可能?
首先,藝術家需要虛心地向古人學習,正確地認讀這些傳統符號,并且“透過這些符號,重新認識和把握傳統的文化和藝術精神。而這種精神正是我們確立自我身份、贏得話語權、構建自己的藝術生態和語言體系的根本動力和不竭源泉。相反,一些藝術家和批評家對于傳統的無知以及在作品中對傳統因素的濫用和投機行為正使我們有遠離和歪曲傳統,甚至建立一種‘偽傳統’的危險。”其次,作為一位有著社會承擔和文化承擔的中國當代藝術家,應該充分認識到傳統符號在凝聚和提升當代國人精神、彌合一個多世紀以來的文化斷層、促進社會的全面和諧發展過程中體現出的重要作用和意義。不能為新而新,為怪而怪,要把傳統符號蘊含的特定文化和精神內涵與當下的人文和精神狀態進行合理、有效的契合,讓人們由此切實感受到藝術家試圖傳達出的關于傳統與當代、藝術與人文的真誠思考。也唯有此,才能真正逐步明晰和確立中國當代藝術的突圍之路,實現自我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