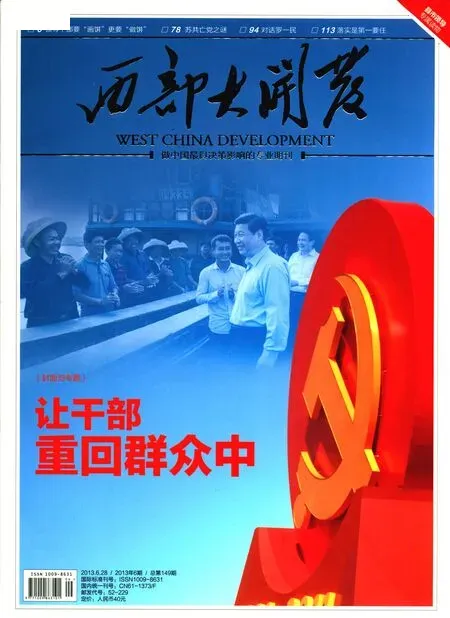城鄉統籌四大觀念誤區
□ 文/劉業進
(作者系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副教授)

農民為中國實施趕超戰略付出了沉重的代價,然而新的制度設計仍在原有的城鄉二元體制軌道上持續。一個時期以來,各地就城鄉統籌發展、城市化、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議題進行了廣泛的探索,我們發現其中存在一些思想觀念的混亂,不揭示這些思想上的混亂及背后錯誤的學理依據,就有可能把政策引向錯誤的方向。
計劃思維誤區
城鄉二元分割是計劃經濟的產物。然而我們發現,為了消除二元分割,有些地方政府反倒借助計劃經濟的思維和手段來解決問題。
隨著城市化進程的推進,在18億畝耕地保護紅線的硬約束下,以“占補平衡”為操作性依據,暴力拆遷在各地時有發生。從經濟社會發展的角度,我們并不反對城市化,但城市化數量指標只能是事后觀察的數值,不應是政府積極追求的結果。其次,政府并不能扮演“超級理性”的角色。亞當·斯密在《道德情操論》曾這樣警示政府中掌權的人:在政府中掌權的人,容易自以為非常聰明,他似乎認為他能像用手擺布一副棋盤中的各個棋子那樣非常容易地擺布偌大一個社會中的各個成員,他并沒有考慮到,在人類社會這個大棋盤上每個棋子都有自己的行動原則。
主導拆遷的地方政府和被拆遷的無數房屋產權持有者都在斯密的“棋盤”之中,每一個棋子都有自己的目標。而以某種集體“目標”作為政策目標,用強制性手段實施,則可能走向政策初衷的反面。一些官員和經濟學家撇開這個事實,大談土地使用效率的提高和城市化率,這種錯誤思維模式把城市化誤解為工程技術問題,雖然大規模的計劃經濟早已從人們的記憶中淡去,可計劃經濟的思維方式仍時不時地重返一些經濟學家和地方官員的頭腦。他們缺乏對私人財產權利的尊重,不顧無數分散的農民個人及其家庭的行動原則,僭越政府職能,反而削弱了政府的公信力,引發社會不穩定。改變這種局面需要地方政府能從那些戴著商業面具的計劃經濟思維方式中走出來。
結果導向和民生論迷信
以民生和發展的名義提出政府包攬生老病死各項事務,這種觀點不是建立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職能的理性分析和對政府行為合理期待的基礎上,我們把這種觀點稱為“結果導向與民生論迷信”。典型的表述如:“無論是中央政府,還是地方政府,在為百姓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提供服務保障方面是義不容辭的”。這種政策建議的誤導性在于,以其有限的作用和有限的正確性掩蓋了真正重要的問題。
修正錯誤有兩種方式,一種是以錯誤掩蓋錯誤,這就是民生論,用錯拿的錢建設民生,以突出民生關切來為超常宏觀稅負提供合法性支持。政府強化再分配的本質是:用權力機構的信息和決策替代無超常宏觀稅負條件下市場分散化報酬系統以及慈善和非營利組織調整后的收入分布,這既是信息基礎的替代其實也是決策模式的替代。歸根到底是集中理性決策替代更大數量的分散的理性決策。
在經濟體系中,價格是一個競爭過程發現的結果。對于作為發現過程的結果,直接的行政干預乃是對這個發現過程的傷害。一個直接后果是擾亂相對價格體系,給出錯誤的資源配置信號;二是導致進一步干預正常產生價格信號的競爭過程,直至對合法產權作出限制乃至侵害。
與強化政府再分配的直接民生論不同,我們提出一種基于社會合作體系的迂回民生論。在盡可能少的公共權力干預的市場過程中,無數勞動契約談判和企業家創新行為決定了收入分布,這是一個伴隨著生產過程的同時性過程。這一過程也伴隨著政府稅收,但是稅收是服務于市場過程的,基本沒有再分配工具性作用。
是“強化市場型政府”還是“強化政府型市場”是兩種根本不同的視角。
“農村糟糕、城市文明”的觀念誤區
近代百年中國的“現代”轉向,制造了一種反鄉村的意識形態,即現代文明是與城市聯系在一起,而“鄉村是黑暗的,是文明的地獄”。其實在建設城鄉統籌中,應認識到農村有其獨特文化價值。已經現代化了的現代國家美、德、日等國,鄉村仍作為一種文化樣態被呵護,鄉村生活寄托著許多人的美好生活方式。鄉村有其獨特的文化價值。
事實上,城鄉一體化既有農村人口向城市轉移,也有農村中小城鎮發展壯大,新城鎮的涌現,也有可能出現人口從城市向農村的轉移,所譖“逆城市化”現象。逆城市化有三大誘因,一是農村土地增值;二是逃離城市高成本和抗拒各種初顯端倪的城市病;三是以現行戶籍制度為標志的城鄉二元治理制度不接納新進城農民工。
近年來,隨著中國東部經濟的發展及新農村建設步伐的加快,農村土地越來越值錢,農民身份獲得的利益越來越多,有的農村戶口甚至牽扯到上百萬元人民幣的收益。甚至還出現了曲折的“非轉農”案例。浙江省桐鄉市曾在一年間出現52例跨省“非轉農”。
不過,并非所有“逆城市化”現象背后都是巨大的利益誘惑。在東部,相當一批人選擇離開大城市,與無法支付高額的生活成本有關。進城者長期在收入低標準、生活低質量、保障低水平的社會底層徘徊,被日益邊緣化。“再加上高額的房價與不斷上漲的物價,即使政策完全放開,多數進城人員也難以實現落戶生根的意愿。”不管“逆城市化”原因何在,人們的行動表達了約束條件下的優化行動。
“逆城市化”現象給我們的啟示是,用動態的眼光理解城鄉統籌和城鄉一體化,既考慮農民向城市轉移,也考慮把市民向農村轉移,還考慮農村自下而上自我城市化的道路。人們所追求的是雙向流動的城鄉格局,是生長的城市化、城鎮化。
“土地換社保”、“土地換戶籍”誤區
市場經濟轉型過程是一個確權過程。但最近幾年伴隨快速的城市化進程,一種破壞產權的勢頭越演越烈。幾乎所有的強制拆遷都在美好藍圖的名義下合法進行。土地換戶籍、土地換社保就是最近涌現出來的具體操作方案。
發生在重慶的“土地換戶籍”改革本質上是在做市域范圍內的農業用地“占補平衡”,在城市近郊占用農地,在遠郊將宅基地進行復耕整理,保持農業用地總量不變,被一些學者稱為“偉大的變革”、“其意義不亞于當年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
重慶的“土地換戶籍”到底是制度創新還是舊體制復歸?“土地換戶籍”論表面談制度改進,實質上談的是經濟效率、經濟增長,并進一步將物質利益增長設定為人類存在的目的。
“土地換戶籍”論者在自己劃定的資源配置范式內,有其自治的效率標準和評價依據,但一旦跳出原有資源配置范式,把獨斷的機制設計置于無數分散的個體自身并根據相對價格體系變動和環境變化作出響應時,所謂令人驚訝的“偉大”技術細節也就不過如此,畢竟它不過是對一個自發演化進程的拙劣模仿。我們可以模仿技術,甚至可以模仿制度,但模仿一個系統的演化進程,是我們無能為力的。迄今為止,在組織經濟事務上,大范圍的模仿都以失敗告終。這種錯誤的嘗試乃是主事者未能意識到“個體發生一系統發生”的中斷的結果。
是以公民權利增長維持經濟增長,還是以計劃經濟方式推進城市化,促進城鄉經濟增長?是以GDP看待發展,還是以自由看待發展?這是根本不同的道路選擇。對“土地換社保”、“農村宅基地合并集中居住”、城市用地“公共利益”取得等試驗而言,苴“創新”背后乃是產權侵蝕和產權殘缺,是以合法名義進行的不正當財富轉移。
城鄉統籌背后存在的問題表面是收入上的城鄉差別和地區差別,背后深層的問題是消除城鄉身份歧視和土地產權差別。
——《篳路藍縷:計劃經濟在中國》評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