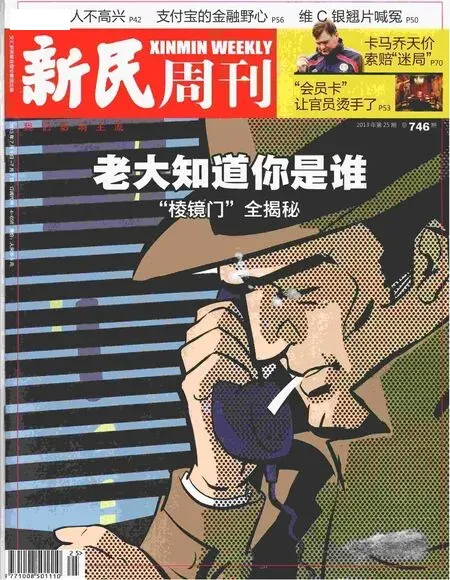窗外兩棵“樹”
沈嘉祿
我家窗外能看到兩棵“樹”,一棵是東方明珠,一棵是原南市發電廠的煙囪,現在是當代藝術博物館的“旗桿”。
十年前搬到這里的時候,為一眼就能看到北窗外的東方明珠而欣喜。南窗外的那根煙囪距離更近些,它聳立在單調的民居夾縫中,經常趁人不注意時,吐出一朵龐大的灰色煙團,在煙囪上方徘徊片刻,然后在江風推動下,雍容華貴地朝城市腹地漂移。
如今在上海,在某些場合公開表示喜歡東方明珠大約是一件可恥的事,相當于一不小心暴露自己ED或早更的難言之隱。批評這個建筑物的種種不是,甚至用人的某個器官來惡喻,倒很容易引來在座者的附和,更是飯桌上活躍氣氛的胡椒粉。這幾乎是一場沒有任何風險的話語游戲,甚至不需要藝術經驗與理論準備,只需撿拾一堆惡搞式的網絡詞匯就貌似極具幽默感了。往更深的層面上說,東方明珠差不多成了宣泄某種不滿情緒的最佳對象。它有頂天立地的體量,占據了顯赫的位置,屢屢被當作新聞圖片的背景,中外游客到訪上海后的第一站就在那里,它具備了在網絡時代成為語言暴力圍攻對象的基本條件。
說實話,我也不喜歡它,放棄過數次登高望遠的機會。但是家住浦東的時候,廚房北窗正好看得到它的上半部。我是看著它一點點升高的,有一天下班回家,發現那根據說好幾噸重的天線已經安裝完畢,大有舉重若輕之感。那天晚上我喝了一小杯酒,一種見證歷史的自豪感油然而生。不久我家搬離浦東,告別浦東的最后一眼,我的視線是在東方明珠上斬斷的。
十多年前,在外灘名存實亡的情人墻上,隔岸觀望浦東,東方明珠的確有點突兀或怪誕,但罵歸罵,人們還是以它為背景拍照留念,外省人尤其、年輕人尤其。后來陸家嘴的高樓越來越密集,它不再木秀于林,不再獨木難支,所謂的霸氣也收斂了許多。或者說,簇擁的摩天大樓解構了它的空間,當然你也可以說,它們幫東方明珠分擔了更為尖刻的質疑。歷史也給了它走秀機會,比如那次APEC會議,瀑布般的焰火從球體上傾瀉,兩岸狂歡,世界矚目,它的存在價值再一次得到證明。
是的,讀者朋友一定聯想到巴黎的埃菲爾鐵塔,還有盧浮宮前的玻璃金字塔,它們好像負有原罪,打落地那天起就一直被狗血。外國人在藝術這檔事上吐起槽來,絕對是六親不認、黑虎掏心。后來,他們發現批評既然不能改變事實,就只能面對它。東方明珠也命中注定是一箭垛,有一外地朋友對我放狂言:“如果我是上海市長,上任后第一件事就是炸掉它。”五年后他攜夫人再次來到上海,我陪他們游外灘。華燈初放,熏風襲人,他們以東方明珠為背景拗造型,橫拍豎拍,大秀恩愛。為照顧他的面子,我只當他沒說過那句話。
東方明珠建成快二十年了吧,假如明天要炸掉,上海人會怎么想?我說不準,往日的既成事實已成歷史存在,歷史存在就是政治。我還知道圓明園路的原文匯報大樓炸掉后,連老外都覺得可惜,它年紀雖輕,但也是歷史啊,也是外灘源的一部分。
人在艱難困苦中成熟得快,在信息浪潮中也可以成熟得很快。南市發電廠的那根大煙囪就沒有因為世博會而炸掉,光榮退休,應運重生,臨時做成氣溫表,后來在上海雙年展前設想過浪漫絢麗的轉身,但民眾已將豐富感情維系在它身上,愛惜并珍惜它的笨拙形象,有時報告氣溫的燈光沒亮,群眾會打電話到市政府。于是考慮到民眾感情,就以這個形象固定下來。我家里備有氣溫計,但太太更樂意用望遠鏡讀出它的報數。
這幾年,霧霾經常拜訪申城,東方明珠與大煙囪首當其沖淹沒在一片混沌中。而我更留意這般風景:東方明珠的下半身還依稀可辨,最上面的那個小球卻久久不愿露面,好像它也懂得了什么叫含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