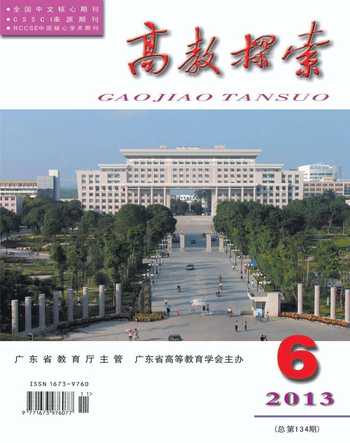悖離與異化:工具理性視域下高校虛擬管理模式的價值反思
任小燕
摘要:工具理性作為現代工業革命以來科學技術高速發展和急遽變革下產生的人類社會現代性的重要表征,在高校虛擬管理模式中體現出一定的公平、信任和效率。但與此同時,無可避免地導致了高校管理中人際關系的脫域、機械思維的主導、情感道德的缺場、管理權力的隱性轉移、管理責任的虛化、信任危機的顯現等一系列問題。
關鍵詞:工具理性;高校管理;虛擬管理模式
高校虛擬管理模式,是指高校管理者在工具理性視域下,由管理者、計算機、通信設備、互聯網等組成的“人—機”互動系統,通過綜合運用各種網絡平臺、電子程序等現代化遠程管理方式進行高校綜合管理的方式。高校虛擬管理模式通過智能化、網絡化管理,超越了傳統管理模式難以規避的時空局限,因而具有便捷、高效等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傳統的實體管理模式而成為當下高校的主導性管理模式。
一、現狀與問題:工具理性在高校管理中的實踐隱憂
馬克斯·韋伯曾將合理性分為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作為現代性的一個重要特征,工具理性以現代技術為工具和手段,一味追求實踐行動中的功利性和效益性,而無視價值、道德、情感等非功利性因素,是一種典型的工具崇拜和技術崇拜。工具理性是現代工業革命以來科學技術高速發展和急遽變革下產生的人類社會現代性的重要表征。隨著工具理性的急速膨脹,人類理性由原初的解放性工具,異變成為統治整個人類乃至自然的霸權性工具,人類轉而由理性工具的創造者蛻變為理性工具的受役者。“私人空間被技術現實所侵占和削弱”,整個社會衍變為一種機械的模仿,即“個人同他的社會、進而同整個社會所達到的直接的一致化”。[1]
工具理性在高校虛擬管理模式中體現出一定的工具性公平、工具性信任、工具性效率和經濟合理性。與此同時,在高校虛擬管理模式中遭遇到極端推崇和過度使用,得以急速擴張,極度膨脹。雖然多年來學術界對其不乏微詞,且批判有加,并呼吁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的融合互補,然而工具理性卻依舊鬼使神差般地在高校管理的實踐層面長驅直入、勢如破竹,突破了工具理性作為一種外在管理手段的應然,進而反客為主,演變為對高校管理的內在理念、人文精神乃至價值理性的一種肆意侵略和無情侵蝕,從而無可避免地導致了高校管理中人際關系的脫域、機械思維的主導、情感道德的缺場、管理權力的隱性轉移、管理責任的虛化、信任危機的顯現等一系列難以規避、無可小覷的現實問題與未來隱憂。
工具理性視域下的高校虛擬管理模式存在以下弊端:虛擬管理系統在高校所有管理領域的極端推廣和無限制使用,使人的真實個性遭遇挑戰乃至抹煞,網絡虛擬群性①逐漸被規定;工具理性的特質被極度放大,高校管理以完全客觀、極度精準、量化管理為追逐目標;管理程序的被動使用和無條件服從,人的思維遭遇被規定和被固化,自由創造力遭受冷遇,難以發揮應有的作用;技術權威得以無限度地凸顯和放大,管理權力遭遇隱性轉移,管理責任受到無形弱化,情感道德嚴重缺失。
高校作為培養高等人才和孕育文化的重要場域,其教育、培養、管理、考核的對象是“人”,關涉師生的教育教學、科學研究、教育實踐、學科發展、機構建設、學生活動、教工生活、人事黨務等,涉及到教研場所、教學課堂、實踐基地、辦公場所等活動場域。洞見人性、觀照人性,多元模式,本是高校管理特質的應有之義,而排斥人性、拒絕情感、規避道德,這成為當下極度膨脹的工具理性與高校管理實踐難以規避的現實悖論。
二、原初與淪變:作為現代性重要表征的工具理性的異化
關于對現代技術及其導致的工具理性的價值與信仰的淪變,早在一戰期間,斯賓格勒在曾被當時學界斥責為“歷史的占卜術”的《西方的沒落》中,對在現代技術主導與控制下的未來文明做了可謂是一種巫術般的預言和魔咒般的描繪,對科學技術發展的致命危害做了憂慮萬分、痛徹心扉,甚至驚世駭俗的批判。斯賓格勒以歷史形態學的方法將人類歷史看成從出生到死亡的生命周期。“機器做工作,并強迫人同它合作。整個文化活動達到了這樣的程度,連大地都在它的下面顫抖。”[2]當人類的心智進入理性主義時代,抽象的概念取代了生動的生命世界,科學技術開始成為統治人類的新暴君。而當傳統生活被單調的機械勞作所取代,人類原本詩意的生活狀態,亦被痛快淋漓地拋棄在來時的路上。
斯賓格勒將機器描述為“越來越沒有人情味,越來越禁欲、神秘、深不可測”甚至是“魔鬼”,并由于其“把神圣的因果關系交給人,由人憑借一種先知先覺的全能使其……不可抗拒地運轉”,因此意味著“對上帝的離棄”[3],而這些對機器特質的描述同樣是對科學技術的真實寫照。從某種意義上說,科學技術的工具理性更是對人類信仰與價值存在的否定與拋棄。
馬爾庫塞在《單向度的人》的“控制的新形式”一章中指出,技術是實現現代社會控制的方式,作為“國家機器的技術結構與效率”,兼具生產性和破壞性。當代社會中,技術的控制體現了社會集團與社會利益的理性,而一切與此產生的矛盾均成為不合理,一切與此進行的對抗均成為不可能。“私人空間被技術現實所侵占和削弱”,整個社會衍變為一種機械的模仿,即“個人同他的社會、進而同整個社會所達到的直接的一致化”。[4]
梁漱溟在探討中國傳統文化中價值理性主導、工具理性缺位的同時,提出有必要合理地培育工具理性,但明確反對以消解價值理性為代價,反對一味推崇工具理性的唯科學主義傾向。二十世紀初盛極一時的“科玄論戰”,科學派主張科學萬能,高揚工具理性,認為價值理性無用,主張消解價值理性。而玄學派主張價值理性與工具理性的統一,反對消解價值理性。雖然玄學派對科學派的極端主張進行了極力聲討,但在學習西方、推崇科學、追求現代化的時代風暴下,多少顯得蒼白無力。現代新儒家也認為,過度夸大工具理性,將會消解價值理性,會如西方一般產生“單向度的人”,從而造成人類社會的意義迷失和人性異化。
三、悖離與異化:工具理性視域下高校虛擬管理模式的人性悖論
1.人際關系的脫域
傳統的時空統一的交流方式被現代性的時空分離所替代,從而在一定程度上誘導了人的惰性特質,進而必然導致人際關系的“脫域”現象。所謂“脫域”,是指“社會關系從彼此互動的地域性關聯中,從通過對不確定的時間的無限穿越而被重構的關聯中‘脫離出來”。[5]高校管理者僅需在相對封閉的時空下、通過機械的人機互動,便可完成那些在傳統管理模式下必須通過時空開放式的人際溝通才能進行的工作。人際互動的缺失和人際關系的脫域,其導致的必然結果是,人的真實個性的湮滅,人的虛擬群性的被規定,人將只會在客觀、既定的虛擬系統下進行交流。
高校管理者企圖憑借高校虛擬管理系統以機械的人機互動代替傳統的人際互動,試圖以對真實個性的毀滅和對虛擬群性的規定為代價,進而實現高效的績效管理。殊不知,虛擬管理系統的開發者和使用者依然是“人”自身。“人”的存在,就意味著個性的多樣性、方式的多元性、理解的差異性、人際互動的必要性。每個人都具有生動的個性和獨特的個體特征,都有表達個性的需求和必要,而作為培養高層次人才的高校,更應在管理上凸顯人性化、個性化。傳統的人際互動關系,永遠無法被機械化的人機互動所取代。靈動的個性表達和自由的人際互動,必然需要彰顯。
2.機械思維的主導
高校管理者在預先設定好的電子程序的控制下,機械地進行著按部就班、環環相扣的工作程序,而不能與這個預設的機械程序有絲毫不同或隨機變化,否則便無法進行下一步的管理操作。每個管理者都仿佛都是這一龐雜的機械程序中的一個必然的預設環節,毫無自由、變化與創造可言,管理模式機械化、單一化,高校管理的有效性和多元化難以彰顯。
虛擬管理系統開發和普及,在給管理帶來一定程度的科學化和規范化的同時,卻導致了管理者對虛擬管理系統的極端依賴,以及使用者機械思維的生成與強化。對管理者而言,凡事必依賴虛擬管理系統來實施管理,凡事必經過虛擬管理系統來界定認證,甚至唯虛擬管理系統馬首是瞻,實施管理非虛擬管理系統不可,離開了虛擬管理系統,管理事務必將陷于無序和癱瘓無疑。然而,虛擬管理系統的程序設計必然存在時空差異,這使得預設與現實不一致成為必然。如果現實情況不在預設之內,或者出現系統故障,許多管理與操作將難以執行和維持。對虛擬管理系統的使用者而言,長期對虛擬管理系統的機械程序的適應與運用,必然產生固化的機械思維,對管理程序的無條件服從和一味順應,使得原初的自由性不斷缺失、創造力逐步退化、人本性加速消解,進而將原本應該具有豐富的創造性和多元化的高校管理模式演變為既定的、固定的、僵死的、機械的工具性行為。
3.情感道德的缺場
人機對話代替了人際對話,人機交流代替了人際交流,虛擬空間替代了真實空間。在工具理性的控制下,本該“在場”的情感卻遺憾的“缺場”。可以說,工具理性自產生之日起,就是作為情感與道德的對立面而存在的。完全客觀、絕對冷靜、極度精準,這些排斥情感的要素,便是工具理性與生俱來的特質。而人作為工具理性的服務對象,情感與道德的缺場,其本身就是工具理性自身的邏輯尷尬。
高校的各類虛擬電子管理系統涉及到師生的教學、科研、人事、黨務、財務、資產、教工生活、學生活動等多種事項,服務主體關涉到教師、學生和管理者自身,服務地域涉及到教研場所、辦公場所、課堂、實踐基地等等。在各職能部門極力追求辦公自動化、辦公高效化的前提下,工具理性的客觀與精準的特質被極度放大,甚至對教學質量、科研水平、活動能力、人事評定這些本該有著極大的人性考察和情感體驗成分的考量對象,都力圖通過客觀與理性的電子工具來計算和衡量。這就仿佛一個有血有肉有著鮮活生命和豐富情感的人,被冰冷的現代理性工具分解為各種物質成分和化學要素去分析和考量其價值一樣,論斤秤兩,令人費解和發指。在這一分解過程中,充滿著工具理性的虛擬管理系統毫無疑問地成了無情宰割教研生命的劊子手。既然對生命無情宰割,便毫無疑問是道德缺失者。在工具理性考量下的“物質數量”里,究竟有多少“質”;在衡量的“化學成分”中,又究竟有多少“用”。而作為被剝離了“血肉”的生命現象里至關重要的情感與道德,卻無疑是被迫“靈魂出竅”。
4.管理權力的隱性轉移
正如斯賓格勒在《西方的沒落》中對現代工業文明下的機器的描述那樣,單純的科學技術手段是“把神圣的因果關系交給人”,這意味著“對上帝的離棄” 。[6]在工具理性視域下,虛擬技術使用者又將自己委身于技術,且進一步將“因果關系”交給了技術本身和技術掌控者。技術知識對于使用者而言,意味著客觀性、確定性、信任性、服從性,這些原則同樣適用于高校虛擬管理系統。在這些原則的統攝下,管理者企圖通過虛擬管理系統來實現現代化的高效管理,傳統意義上的現實管理者(人)將管理事務交給虛擬管理者(虛擬管理系統,即技術)全權處理。虛擬管理者因此便具有毋庸置疑、無可辯駁的客觀性、精準性、正確性,高校的各項管理事務和信息數據,必須經過虛擬管理者的審核、認定和處理,方可生效。這一管理過程的實質,便是將人的管理權乃至決策權移交給虛擬管理者(技術)。這是作為現代化工具理性的重要表征,從某種意義上說,這種唯技術主義的工具理性更是對人類自身價值存在的否定與悖離。
5.信任危機的顯現
傳統的信任方式是在共同在場的“當面卷入”式的互動中發生的,“基本信任的維系是通過諸如目光凝視、身體姿勢及手勢,以及正經談話等習慣性方式得以完成的。”[7]而在現代工具理性話語體系中的高校虛擬管理模式,其信任機制的主要特征是虛擬管理模式下的管理者與使用者對于虛擬管理系統這一抽象體系的無條件信任和無條件執行。然而,這一脫域機制下的、理念性的工具信任,在管理實際中往往顯得有些纖弱,甚至令人質疑。這種纖弱和質疑,源于對虛擬系統開發者的程序設定的技術拷問,源于對虛擬系統管理者所制定的客觀指標的有效度的質疑,源于對虛擬系統使用者在運用虛擬模式時的指標理解的有限性,以及技術掌握的有限性。當傳統的“當面卷入”式的互動方式漸趨消弭,當人的交流更多地通過抽象體系下進行機械性互動時,這種抽象體系下的高校虛擬管理模式,帶來的卻是難以規避的信任危機。
四、轉向與限度:工具理性視域下高校虛擬管理模式的生存空間
高校虛擬管理模式無疑遭遇了這樣的尷尬:在高校虛擬管理模式中,人的關系被電子數據所表征,人的思維被規定在電子系統的機械表達能力之內。正如弗洛姆所說,人變成了一架沒有思想、沒有情感的機器,人作為生產機器的一個齒輪,成為物而不再為人。層出不窮的新管理工具的開發與運用,是否就真正得到了預期效果?工具設計的合理性如何?多種工具之間的兼容性如何?程序設定的開放性如何?不得不說,不同職能部門各自為政,其開發的虛擬管理工具之間,以及同一管理工具在不同事件處理中,都缺乏應有的兼容性與開放性,由此導致許多不必要的重復勞動,以及本該簡單卻人為復雜化的環節。
“技術仿佛是一種潛力競賽,不斷增長是它固有的特性;這種增長一點也不根植于現實的必然性,即‘經驗的必然性中……其基本任務就是擴大技術潛能范圍……以這種方式來考察的最復雜的科學化了的技術看起來就像是為藝術而藝術。”[8]而當人的全部生活都成為技術所支配和操控的綜合體之時,當人們開始為了技術而技術之時,人便失去了其特有的社會性和能動性,人性也被撕為零散的碎片,只好被動地發揮其機械性的功能。[9]
更不必說,許多情況下,管理工具往往隨著管理者的更替而同步更替,隨意性和人為性極大,新老工具之間亦缺乏應有的穩定性、繼承性和發展性。從表面上看,高校管理工具百花齊放盛世繁華,實則卻成了滿足某些人沽名釣譽、追逐利益的名利角逐場,而高校師生和管理事務,無疑成了這種名利角逐的共舞者和犧牲品。
當然,這不等于否認先進的科學技術給工作帶來的便捷。但是一味地追求科學技術帶來的工具性便捷,而將“人”及其情感、創造、人際互動等種種本該“在場”的要素統統排斥在管理場域之外,從而忽視高校管理之根本所在,無異于得魚忘筌、舍本逐末,終將淪為工具理性所必然導致的技術崇拜。畢竟,工具理性視域下的高校虛擬管理模式,只能是高校管理的輔助工具,不會也不可能成為優化高校管理職能的治本良方。因此,工具理性在高校管理中,其生存空間應當是設定的和有限度的。毫無節制的使用和過分拓展,不僅無益于高校管理,反而會誘發諸多難以規避的現實問題和未來隱憂。提高高校管理水平和工作效率的根本與關鍵,還應當聚焦于“人”,以實現高校管理理念的轉變和由此生發的高效管理機制的深度改革。
注釋:
①虛擬群性,在本文中是與真實個性相對立的表達,特指人在虛擬環境下所遭遇的強制性的行為規范和思維規定,進而無可避免地形成的一種被動意義的去個性化和同質性。
參考文獻:
[1][4][美]赫伯特·馬爾庫塞.單向度的人:發達工業社會意識形態研究[M].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8.9.
[2][3][6][德]奧斯瓦爾德·斯賓格勒.西方的沒落[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6.467.
[5][7][英]安東尼·吉登斯.現代性的后果[M].南京:譯林出版社,2000.19,87.
[8][蘇]格·姆·達夫里楊.技術 文化 人[M].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169.
[9]吳文新.科技與人性——科技文明的人學沉思[M].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3.38.
(責任編輯于小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