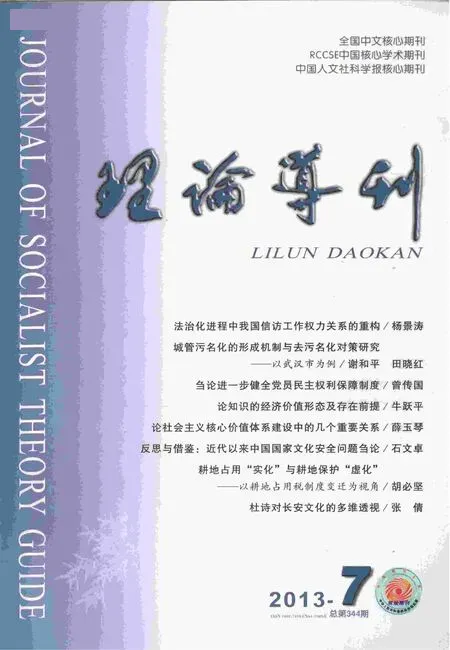立法辯論的價(jià)值維度
李店標(biāo)
摘 要:作為議會(huì)審議法案的一項(xiàng)關(guān)鍵機(jī)制,立法辯論所具有的多元價(jià)值已為人們所認(rèn)可。自由與秩序的統(tǒng)一、公平與效率的平衡、民主與集中的結(jié)合、多數(shù)與少數(shù)的協(xié)調(diào)是立法辯論的形式價(jià)值。提高立法質(zhì)量、實(shí)現(xiàn)利益整合、制約行政權(quán)力和保障法律實(shí)施是立法辯論所追求的目的價(jià)值。而設(shè)置議事障礙、理性不足、為政黨所左右和議員缺席等現(xiàn)象導(dǎo)致了立法辯論價(jià)值呈現(xiàn)衰退的跡象。
關(guān)鍵詞:立法;立法辯論;議會(huì);形式價(jià)值;目的價(jià)值
中圖分類號(hào):D920.4 文獻(xiàn)標(biāo)志碼:A 文章編號(hào):1002-7408(2013)07-0105-03
一般而言,立法辯論是指在議會(huì)審議法案的過程中,依據(jù)辯論規(guī)則的規(guī)定,觀點(diǎn)對(duì)立的議員之間針對(duì)法案內(nèi)容所進(jìn)行的言辭爭(zhēng)辯、論證和反駁。起源于英國(guó)議會(huì)的立法辯論制度之所以成為世界各國(guó)議會(huì)所借鑒和模仿的對(duì)象,主要因?yàn)榱⒎ㄞq論所具有的多元價(jià)值已為人們所認(rèn)可。綜觀國(guó)外立法辯論的理論、規(guī)范和實(shí)踐,我們發(fā)現(xiàn),立法辯論的價(jià)值體現(xiàn)在形式和目的兩個(gè)層面,而且立法辯論的價(jià)值目前也呈現(xiàn)出衰退的跡象。盡管作為制度形態(tài)的立法辯論在我國(guó)還沒有建立起來,但理論界已經(jīng)意識(shí)到建立中國(guó)特色的立法辯論制度是大勢(shì)所趨。因此,考察立法辯論的價(jià)值維度對(duì)我國(guó)立法辯論制度的建構(gòu)具有重要的借鑒和啟迪意義。
一、立法辯論的形式價(jià)值
立法辯論的形式價(jià)值,是指立法辯論的制度設(shè)計(jì)和實(shí)踐操作在表象上所體現(xiàn)出來的一系列優(yōu)良品質(zhì),這些品質(zhì)既具有獨(dú)立意義又具有工具意義。具體而言,立法辯論的形式價(jià)值主要包括以下幾方面:
1.自由與秩序的統(tǒng)一。辯論自由是議員所享有的一項(xiàng)特權(quán),也是議員經(jīng)過長(zhǎng)期斗爭(zhēng)而確立的一項(xiàng)議會(huì)議事原則。議會(huì)“既是國(guó)民訴苦的委員會(huì),又是他們表達(dá)意見的大會(huì)。它是這樣一個(gè)舞臺(tái),在這舞臺(tái)上不僅國(guó)民的一般意見,而且每一部分國(guó)民的意見,以及盡可能做到國(guó)民中每個(gè)杰出個(gè)人的意見,都能充分表達(dá)出來并要求討論”。[1]議員辯論自由在各國(guó)議會(huì)的議事規(guī)則,甚至是一些國(guó)家的憲法(如美國(guó)憲法)中都有明文規(guī)定,其直接目的在于解除議員辯論發(fā)言時(shí)的思想顧慮。在立法過程中,辯論自由意味著議員針對(duì)正在審議中的法案內(nèi)容以及其他議員的觀點(diǎn)可以自由發(fā)表意見,以確保法案辯論的充分性和真理的及時(shí)發(fā)現(xiàn)。必須指出的是,辯論自由是以言論免責(zé)作為保障的,并應(yīng)排除權(quán)力的壟斷。因?yàn)楝F(xiàn)代立法程序意味一種溝通、對(duì)話和妥協(xié)機(jī)制,如果允許權(quán)力的獨(dú)斷專行,立法的民主性將不復(fù)存在。然而,出于會(huì)議秩序的考慮,辯論自由又是受到限制的,如辯論發(fā)言必須經(jīng)主席許可、不可隨意插話、發(fā)言次數(shù)和時(shí)間的固定化、發(fā)言應(yīng)切題和避免重復(fù)、使用文明語言等。限制辯論自由對(duì)于議會(huì)制民主而言并不是沖突而是必要,因?yàn)榻^對(duì)的自由在人類社會(huì)并不存在。在立法辯論中,自由與秩序是對(duì)立統(tǒng)一的關(guān)系,如果沒有秩序作為立法辯論的價(jià)值導(dǎo)向,議員之間的激烈言辭對(duì)峙勢(shì)必會(huì)導(dǎo)致議會(huì)的混亂不堪。因此,議長(zhǎng)(或主席)這一角色在立法辯論中不可或缺,其負(fù)有保障辯論自由和維護(hù)辯論秩序的義務(wù),并通過執(zhí)行議事辯論規(guī)則和慣例來追求二者的有機(jī)統(tǒng)一。
2.公平與效率的平衡。立法辯論的程序設(shè)置在諸多方面都體現(xiàn)了議員之間的公平性。首先,在發(fā)言資格的取得上,盡管分為辯論前的預(yù)先登記和辯論中的隨時(shí)請(qǐng)求兩種方式,但無論采用何種方式只要獲得議長(zhǎng)準(zhǔn)許,議員都可自由發(fā)言。其次,在發(fā)言次數(shù)的限制上,各國(guó)辯論規(guī)則對(duì)議員的發(fā)言次數(shù)都有明確規(guī)定,所有議員都必須予以遵循,而不能有所例外。再次,在發(fā)言時(shí)間的限制上,所有議員必須在規(guī)定時(shí)間內(nèi)發(fā)言,超過時(shí)間范圍將被強(qiáng)制終止發(fā)言。最后,在辯論后的表決上,無論采用何種表決方式,議員都是一人一票并且每一票的效力都是相等的。同時(shí),立法辯論也是追求效率的,如緊急法案辯論、優(yōu)先法案辯論等就是大多數(shù)議會(huì)為縮短或簡(jiǎn)化辯論進(jìn)程使法案加速通過的措施;再如呼聲表決、舉手表決等決策機(jī)制也是為了提高立法辯論的效率而設(shè)定的。當(dāng)然,各國(guó)議會(huì)立法辯論眾多規(guī)則的設(shè)計(jì)并不僅僅是追求公平抑或效率某一種價(jià)值,而是力求實(shí)現(xiàn)兩種價(jià)值之間的平衡,如發(fā)言次數(shù)和時(shí)間的規(guī)定。據(jù)世界議會(huì)聯(lián)盟的統(tǒng)計(jì):在發(fā)言次數(shù)上,英國(guó)、印度等國(guó)為一次,荷蘭、挪威等國(guó)為兩次,哥斯達(dá)黎加為三次甚至四次;在發(fā)言時(shí)間上,美國(guó)、德國(guó)、法國(guó)等為五分鐘,丹麥、西班牙等為十分鐘,埃及、科威特等為十五分鐘,加拿大、新西蘭等為二十分鐘,比利時(shí)、菲律賓等為三十分鐘。[2]
3.民主與集中的結(jié)合。辯論作為議會(huì)民主立法的一項(xiàng)關(guān)鍵機(jī)制,就是為各種意見、愿望和利益的自由表達(dá)提供活動(dòng)空間,真正使議會(huì)成為聽取民聲、匯集民智和表達(dá)民意的舞臺(tái)。“議會(huì)的作用就是表明各種需要,成為反映人民要求的機(jī)關(guān)和有關(guān)大小公共事務(wù)的所有意見進(jìn)行爭(zhēng)論的場(chǎng)所。不同理由和意見的表達(dá),出現(xiàn)爭(zhēng)論、辯論是正常的,這種談?wù)摚瑳Q不可等同于空談;相反,它對(duì)于各種相互沖突的利益相互制約、相互作用、相互協(xié)調(diào),對(duì)于在利益均衡的基礎(chǔ)上制定政策,是必不可少的。”[3]盡管民主是立法辯論所追求的主要形式價(jià)值,但卻容易造成立法程序進(jìn)展緩慢、成本巨大、決策時(shí)機(jī)延誤,甚至做不了決策等問題。因此,實(shí)現(xiàn)民主與集中的結(jié)合對(duì)于立法辯論效果的取得意義重大。盡管立法辯論中民主與集中的結(jié)合并不能保證所有的立法決策都正確,但其至少能夠保障決策過程不會(huì)違背民意。立法辯論并不僅僅是追求單一的辯論過程,也許這一過程對(duì)議員自身所產(chǎn)生的影響較大,但做出什么樣的決策結(jié)果對(duì)于民眾似乎更具有現(xiàn)實(shí)意義。因此,諸多國(guó)家的議會(huì)都將辯論后的表決作為一項(xiàng)重要內(nèi)容納入辯論規(guī)則之中,以強(qiáng)調(diào)辯論在形式上保證民主和集中的結(jié)合。總之,立法辯論是過程民主性和結(jié)論集中性的結(jié)合,通過民主來完成立法決策信息的輸入,通過集中來完成立法決策信息的輸出,使立法既接近于民眾又接近于真理。
4.多數(shù)與少數(shù)的協(xié)調(diào)。現(xiàn)代民主議會(huì)的立法過程大都貫徹了服從多數(shù)和尊重少數(shù)的理念,力求實(shí)現(xiàn)多數(shù)與少數(shù)的協(xié)調(diào),因?yàn)椤白h會(huì)程序的基礎(chǔ)性原則就是按照多數(shù)人的意見行事,并保障少數(shù)人的發(fā)言權(quán)”。[4]由于立法辯論是多數(shù)與少數(shù)之間的溝通過程、說服過程,也是相互妥協(xié)的過程,因此無論最終法案通過與否,決策過程和結(jié)果都能兼顧多數(shù)與少數(shù)的利益。可以說,多數(shù)與少數(shù)的協(xié)調(diào)鮮明地體現(xiàn)了立法辯論的形式價(jià)值。Walter Oleszek針對(duì)美國(guó)國(guó)會(huì)的立法辯論指出:“在形式意義上,立法辯論可以讓立法者和公眾確信國(guó)會(huì)做出的決策是以民主的方式進(jìn)行的,而且充分尊重了多數(shù)人和少數(shù)人的意見。”[5]雖然立法辯論意味著必然要有一方與決策結(jié)果相靠近,但這種結(jié)果卻是建立在多數(shù)與少數(shù)之間利益博弈和均衡的基礎(chǔ)之上。一旦按照多數(shù)決原則進(jìn)行了決策,少數(shù)都應(yīng)當(dāng)無條件地服從多數(shù)的裁決結(jié)果,但同時(shí)少數(shù)的發(fā)言權(quán)利依然會(huì)被尊重,少數(shù)也依然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見。當(dāng)然,在立法辯論中最能體現(xiàn)多數(shù)與少數(shù)相協(xié)調(diào)價(jià)值的要數(shù)簡(jiǎn)單多數(shù)規(guī)則的使用,“在有可能選擇的規(guī)則中,只有簡(jiǎn)單多數(shù)規(guī)則有這種特殊的好處:它本身既能防止少數(shù)代表整體采取行動(dòng),也能防止少數(shù)阻礙整體采取行動(dòng)。”[6]
二、立法辯論的目的價(jià)值
立法辯論的目的價(jià)值,是指立法辯論在制度設(shè)計(jì)和實(shí)踐操作過程中所要追求的實(shí)際效果,其具有多元性和位階性。提高立法質(zhì)量是立法辯論的首要目的價(jià)值,實(shí)現(xiàn)利益整合、制約行政權(quán)力和保障法律實(shí)施也是立法辯論所追求的重要目的價(jià)值。
1.提高立法質(zhì)量。立法質(zhì)量的高低一般需要通過法律的實(shí)施效果予以驗(yàn)證,但立法程序機(jī)制對(duì)于立法質(zhì)量的影響不可被忽視。辯論作為立法審議的一項(xiàng)程序機(jī)制,其至少可以在以下三個(gè)層面提高立法質(zhì)量:第一,立法辯論踐行著民主立法。Gerald F. Gaus認(rèn)為,辯論可以避免非理性的立法,辯論也經(jīng)常被描述為民主。[7]在立法利益多元化的現(xiàn)代社會(huì),通過立法辯論這一民主程序可以為議員充分表達(dá)民意和展開公平博弈提供較大空間,不僅能使各種意見和建議能夠反映表達(dá)出來,而且通過不同觀點(diǎn)之間的辯論才能擺明利弊。第二,立法辯論踐行著科學(xué)立法。“首先,不同主張的立法代表之間立法辯論的優(yōu)勢(shì)在于可以彌補(bǔ)單邊主體對(duì)于客觀事物認(rèn)知的不足,還可以避免單邊主體在立法內(nèi)容上的極端規(guī)定;其次,立法辯論可以避免相對(duì)主義者‘在無法達(dá)成內(nèi)容上的一致時(shí),過早地放棄了溝通的對(duì)話;再次,立法辯論還是防止立法者在立法技術(shù)唯理性上走得太遠(yuǎn)的重要機(jī)制。”[8]第三,立法辯論利于遏制立法腐敗。立法辯論不僅堂堂正正地承認(rèn)了利益集團(tuán)的存在,而且為立法利益的公開化和程序化爭(zhēng)奪提供了舞臺(tái)。如果立法程序化和規(guī)范化程度較低,必然會(huì)為立法腐敗滋生提供溫床,而真正開展實(shí)質(zhì)意義上立法辯論,就能破除“立法程序后臺(tái)化”運(yùn)作,有效避免諸如“郭京毅式立法腐敗”現(xiàn)象的發(fā)生。
2.實(shí)現(xiàn)利益整合。由于西方國(guó)家議員的身份具有特殊性,決定了其在立法辯論過程中所代表的利益群體和參與辯論目的具有多元性。議員在立法辯論過程中既要保障自身的利益,也要維護(hù)所屬政黨和選民的利益,甚至是社會(huì)的利益,而這些利益的表達(dá)、分配和權(quán)衡都可以通過立法辯論予以實(shí)現(xiàn)。第一,立法辯論能保障議員自身的利益。如美國(guó)國(guó)會(huì)的立法辯論可以被議員用于向選民、其他機(jī)構(gòu)、游說者、競(jìng)選者、甚至國(guó)會(huì)其他議員發(fā)出信號(hào),表明其是有效和負(fù)責(zé)的立法者。這對(duì)他們的連任將起到很大作用。[9]第二,立法辯論為選民監(jiān)督議員提供了途徑。“如果沒有辯論(指其發(fā)言階段),選民、公眾觀察議員,大概只能靠查閱議員的投票記錄了解他們。……有了辯論,議員就能靈活、具體闡述其對(duì)各事項(xiàng)、對(duì)各方面的看法。借助傳媒對(duì)議會(huì)辯論的報(bào)道,選民、公眾迅速了解議員對(duì)各個(gè)事項(xiàng)的詳盡想法,他們對(duì)議員的議政表現(xiàn)、議政能力從而形成恰如其分的判斷。”[10]639第三,立法辯論可以強(qiáng)化民眾對(duì)政府、政黨和社會(huì)的認(rèn)同。現(xiàn)代議會(huì)立法辯論的公開性運(yùn)作,使得民眾能夠認(rèn)識(shí)到他們?cè)诹⒎ㄟ^程中實(shí)現(xiàn)了平等代表和利益表達(dá),從而強(qiáng)化了對(duì)政府體制和政黨制度的認(rèn)同。同時(shí),立法辯論也能強(qiáng)化民眾對(duì)社會(huì)的認(rèn)同,“雖然法案的提出和辯論沿著政黨路線進(jìn)行是合理的,但議會(huì)決策程序的設(shè)計(jì)不僅僅是用以表明哪方更強(qiáng),而是以整個(gè)社會(huì)的觀點(diǎn)來看待當(dāng)前的某些議題。”[11]
3.制約行政權(quán)力。從立法辯論演變的歷史來看,最早產(chǎn)生于英國(guó)議會(huì)的立法辯論就是以對(duì)王權(quán)的制約為首要目的的,而在當(dāng)今權(quán)力分立的國(guó)家,立法辯論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對(duì)行政權(quán)力進(jìn)行制約。“辯論在政治社會(huì)被廣泛認(rèn)可,享有議會(huì)豁免權(quán)的議員有權(quán)利也有義務(wù)表達(dá)出他們的不受政府歡迎的想法。”[12]43行政權(quán)的膨脹和擴(kuò)張已經(jīng)成為不可否認(rèn)的現(xiàn)象,其所帶來的副作用也是顯而易見的。如在美國(guó),行政機(jī)關(guān)所享有的立法否決權(quán)就使得國(guó)會(huì)立法辯論的價(jià)值大大降低。但必須承認(rèn),議會(huì)立法辯論對(duì)行政權(quán)的制約還是能夠起到一定作用的。“盡管英國(guó)政治界對(duì)辯論改變政府政策的功能評(píng)價(jià)不高,但通過立法辯論迫使政府修正其法案的事例每年都在大量出現(xiàn)。從枝節(jié)性修正、政策性修正,直到整個(gè)一項(xiàng)法案被否決,都是經(jīng)過辯論而實(shí)現(xiàn)的。”[10]638當(dāng)然,立法辯論也有利于政府了解民眾需求,從而為正當(dāng)行使行政權(quán)提供有益幫助。“議會(huì)辯論原則上應(yīng)定位于政府與公民之間的觀點(diǎn)溝通,但實(shí)際上并非總是如此,盡管政府部長(zhǎng)和反對(duì)派都極力向人們告知其觀點(diǎn)的正當(dāng)性。然而允許辯論中政府與反對(duì)派不同觀點(diǎn)的存在與表達(dá),甚至是政府內(nèi)部不同觀點(diǎn)的辯論是同樣重要的,因?yàn)樗麄兘沂玖嗣癖妼?duì)政府執(zhí)政的不同價(jià)值觀。”[12]32
4.保障法律實(shí)施。一方面,立法辯論能夠?qū)袷胤óa(chǎn)生積極影響,即立法辯論可發(fā)揮公民法制教育的功能。現(xiàn)代議會(huì)的立法辯論大都可以通過電視、網(wǎng)絡(luò)、報(bào)刊雜志等途徑為公民提供大量的立法信息,這不僅可以使公民及時(shí)了解法律的內(nèi)容,而且更容易使公民對(duì)法律形成共識(shí)和增加認(rèn)同,如此自然有利于其主動(dòng)遵守法律。另一方面,立法辯論可以為司法和執(zhí)法中的法律解釋提供途徑。在遇到疑難法律問題時(shí),目的解釋是司法和執(zhí)法者在實(shí)施法律過程中主要運(yùn)用的一種方法,而立法辯論記錄可以為他們了解立法目的和公正處理案件提供參考,并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法律解釋的隨意性。以美國(guó)最高法院為例,其審理案件所參考的立法歷史資料主要有委員會(huì)報(bào)告、國(guó)會(huì)立法辯論記錄、委員會(huì)聽證記錄和原始法案文本等,而在1980年至1998年間其所參照的立法辯論記錄就占了立法歷史文件總量的22%。[13]
三、立法辯論的價(jià)值衰退
在當(dāng)代社會(huì),議會(huì)制民主面臨著巨大考驗(yàn),不僅因?yàn)樽h會(huì)自身在組織結(jié)構(gòu)、議員的知識(shí)結(jié)構(gòu)和心理優(yōu)勢(shì)等方面漸趨衰落,而且公眾對(duì)議會(huì)也產(chǎn)生了信任危機(jī)。與此相關(guān)聯(lián),議會(huì)的立法辯論價(jià)值也呈現(xiàn)出衰退的跡象,設(shè)置議事障礙、理性不足、為政黨所左右和議員缺席都是典型表現(xiàn)。
1.設(shè)置議事障礙。設(shè)置議事障礙是立法辯論過程中議員最常用的策略,主要是以發(fā)表冗長(zhǎng)演說的形式來阻撓法案的通過。如在1933年,美國(guó)民主黨參議員為了反對(duì)“將私刑拷打黑人的案件歸邦聯(lián)法院審判”法案的通過,接連發(fā)言5天,從而創(chuàng)造了一項(xiàng)議會(huì)辯論發(fā)言最長(zhǎng)的世界記錄。議員的冗長(zhǎng)發(fā)言主要是出于黨派偏見或狹隘的目的,目前已演變成一種辯論戰(zhàn)術(shù),只要出現(xiàn)有爭(zhēng)議的議案,參議員都會(huì)進(jìn)行冗長(zhǎng)發(fā)言,以迫使多數(shù)黨做出讓步或調(diào)整立場(chǎng)。以美國(guó)為例,近幾年在參議院辯論中冗長(zhǎng)發(fā)言每年多達(dá)幾十次,僅1999年至2000年一年期間,因冗長(zhǎng)發(fā)言中斷辯論并提交表決就有近50次,而且進(jìn)行冗長(zhǎng)發(fā)言或威脅進(jìn)行冗長(zhǎng)發(fā)言的議員數(shù)量呈上升趨勢(shì)。[14]319各國(guó)議會(huì)一般通過避開或中止辯論并交付表決、提出集中條款辯論并交付表決、提出限制辯論時(shí)間動(dòng)議等形式應(yīng)對(duì)冗長(zhǎng)演說,但實(shí)際效果并不理想。原因在于,冗長(zhǎng)發(fā)言雖為個(gè)別議員所為,但其代表了議會(huì)中一定派別的觀點(diǎn),往往也代表了某些選民的觀點(diǎn)。“在大多數(shù)西方立法機(jī)構(gòu)中,設(shè)置議事障礙的機(jī)會(huì)較之過去受到了更多的限制,但機(jī)會(huì)還是有的,只有在政黨統(tǒng)治控制一切(而且通常不存在什么表決投票)的議院里,議事障礙才是一種根本不存在的概念。”[15]
2.理性不足。伯恩斯認(rèn)為,要使立法得到國(guó)會(huì)的充分辯論,議員應(yīng)具有聰明才智和各種知識(shí),能夠理性地辯論且能夠接受別人的建議。[14]318-319為保障理性辯論,各國(guó)議事辯論規(guī)則都有關(guān)于發(fā)言內(nèi)容的規(guī)定,如應(yīng)避免使用侮辱性、攻擊性和冒犯性語言,不得隨意打斷他人發(fā)言,應(yīng)避免脫離主題和重復(fù)爭(zhēng)辯等。但實(shí)際情況是,議員在辯論過程中不理性的言論屢見不鮮,議員大打出手的現(xiàn)象也時(shí)有發(fā)生(如美國(guó)、韓國(guó)、烏克蘭等),這不僅顯現(xiàn)了立法辯論的理性不足,同時(shí)也嚴(yán)重?fù)p害了議會(huì)的權(quán)威。具體而言,立法辯論的理性不足主要表現(xiàn)在:第一,濫用發(fā)言權(quán)。“雖然只有議員可參加議會(huì)辯論,但議員的辯論并非完全是理性的。因?yàn)槊總€(gè)人都可以將任何主張問題化,每個(gè)人在辯論中都可以提出任何主張,每個(gè)人都可以表達(dá)他的態(tài)度、愿望和要求;在辯論內(nèi)外,任何形式的脅迫都不能阻止發(fā)言者行使自己的權(quán)利。”[16]第二,勝負(fù)取代了溝通。立法辯論的目標(biāo)本應(yīng)在于通過溝通來完善法案,真正實(shí)現(xiàn)法案的民主審議,但議員在辯論中傾聽和接受觀念正在發(fā)生改變。“因?yàn)樗麄兊哪繕?biāo)不是彼此之間達(dá)成一致,而是為了贏得辯論,也就是說服觀眾他的立場(chǎng)是最正確的。”[17]第三,形式化傾向明顯。正如沃爾德倫所言,立法機(jī)關(guān)是一個(gè)多元性的機(jī)構(gòu),議員來自于異質(zhì)性的、文化多元的社會(huì)中各個(gè)團(tuán)體。在立法辯論中除了彼此用以交流的相對(duì)僵化且形式化的語言之外,在議員之中,根本不存在對(duì)文化和社會(huì)理解的共享。[18]
3.為政黨所左右。國(guó)外的政黨體制也會(huì)對(duì)立法辯論產(chǎn)生重要影響,因?yàn)樽h員大多都有其所屬黨派,立法辯論為政黨所左右也是在所難免和難以克服的事情。立法辯論為政黨所左右的表現(xiàn)和原因主要包括:第一,議員一般要通過遵循其所屬黨派的路線來維護(hù)自身的利益,因而在立法辯論中往往不愿或難以表達(dá)自己的真實(shí)想法。這使得立法辯論所平衡的只能是政黨之間的利益,而忽視了民眾和社會(huì)的利益需求。在政黨利益的左右下,“辯論只會(huì)導(dǎo)致本集團(tuán)的立場(chǎng)變得越來越極端,就像個(gè)人根據(jù)其偏好選擇與志同道合的人在談話一樣。”[19]第二,各國(guó)議事辯論規(guī)則的不健全也為政黨左右立法辯論提供了可乘之機(jī)。政黨領(lǐng)袖不僅可以優(yōu)先發(fā)言和總結(jié)發(fā)言,而且能夠確定議員的發(fā)言名單和劃分黨內(nèi)議員的發(fā)言時(shí)間,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立法辯論成為了黨派之間爭(zhēng)奪利益的手段,而忽視了立法辯論原本應(yīng)追求的價(jià)值。第三,執(zhí)政黨對(duì)立法辯論的影響最為嚴(yán)重,甚至?xí)a(chǎn)生徹底的破壞性。帕倫蒂指出,在美國(guó)2006年的第100屆國(guó)會(huì)期間,由于立法和行政都為共和黨所掌控,使得眾議院的許多法案都是在秘密情況下提出的,沒有聽證會(huì),辯論也流于形式,民主黨人在整個(gè)立法過程中幾乎被屏蔽,共和黨人則收縮自如地執(zhí)行著自己的意志。[20]
4.議員缺席。出席議會(huì)是議員應(yīng)負(fù)有的一項(xiàng)義務(wù),這是其對(duì)議會(huì)、選民和自身負(fù)責(zé)的主要表現(xiàn)。但當(dāng)今許多國(guó)家的議會(huì)在立法時(shí)會(huì)有眾多議員缺席會(huì)議,導(dǎo)致辯論無法充分展開,甚至使辯論流于形式。不可否認(rèn),議員有眾多事務(wù)需要處理,但其對(duì)于立法這項(xiàng)本職工作的如此處理方式卻令人擔(dān)憂。當(dāng)然,這與立法辯論在制度設(shè)計(jì)上本身存在瑕疵有直接關(guān)聯(lián)。如在加拿大眾議院,議長(zhǎng)從不鼓勵(lì)議員暗示其他議員的缺席;在美國(guó)參眾兩院,缺席的議員可以和另一個(gè)與自己意見相左的缺席者事先約好都不參加投票。羅斯金認(rèn)為,“議員缺席立法會(huì)議或許表示議員正忙于其他重要的事務(wù),也可以認(rèn)為僅僅是因?yàn)閼卸琛?偟膩碚f,這表明議員不再將立法視為主要職責(zé)。他們通過缺席來承認(rèn)自己并不重要,至少不像最初設(shè)想的那樣。有什么辦法來解決這個(gè)問題嗎?唯一的辦法就是削弱政黨紀(jì)律,改變按政黨意志投票的方式,這樣誰都無法預(yù)測(cè)投票的結(jié)果,激動(dòng)人心的演說和緊張的氣氛就會(huì)回到議會(huì)辯論中,議員們就會(huì)有興趣和動(dòng)力出席討論。這樣一來,法案的通過過程就會(huì)更加混亂,難以預(yù)測(cè)。[21]
參考文獻(xiàn):
[1][英]密爾.代議制政府[M].汪瑄,譯.北京:商務(wù)印書館,1984:80.
[2]Inter-Parliament Union. Parliament of World[M].New York: Facts on File, Inc.,1986:430.
[3]趙成根.民主與公共決策研究[M].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0:284.
[4]Philip Laundy. Parliaments in the Modern World[M]. London: Ashgate Publishing, 1989:95.
[5]Oleszek, Walter J. Congressional Procedures and the Policy Process (6th ed )[M]. Washington, D.C.: Congressional Quarterly Press, 2004:167~168.
[6][美]科恩.論民主[M].聶崇信,譯.北京:商務(wù)印書館,1988:73.
[7]Gerald F. Gaus. Justificatory Liberalisn[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228.
[8]葛先園.主體間型立法的概念及其意義[J].法律科學(xué)(西北政法大學(xué)學(xué)報(bào)),2011,(4).
[9]Michael A. Genovese and Lori Cox Han. Encyclopediaof American Government andCivics[M]. New York: Facts On File, Inc.,2009:381.
[10]蔣勁松.議會(huì)之母[M].北京:中國(guó)民主法制出版社,1998.
[11]Jeremy Waldron. The Law[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Chapman & Hall, Inc.,2005:14.
[12]Pasi Ihalainen. Agents of the People[M]. Leiden:Brill,2010.
[13]Michael H. Koby. The Supreme Courts Declining Reliance on Legislative History[J]. Harvard Journal on Legislation. 1999,(36).
[14][美]伯恩斯.民治政府美國(guó)政府與政治(第二十版)[M].吳愛明,譯.北京:中國(guó)人民大學(xué)出版社,2007.
[15][英]米勒,波格丹諾.布萊克維爾政治學(xué)百科全書[M].鄧正來,譯.北京:中國(guó)政法大學(xué)出版社,1992:517.
[16]Aleksander Peczenik. On Law and Reason[M]. New York: Springer,2008:156.
[17]Stephen Macedo. Deliberative Politics : Essays on Democracy and Disagreement[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1999:62.
[18][美]沃爾德倫.法律與分[M].王柱國(guó),譯.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124.
[19]John S. Dryzek.eliberative Global Politics[M]. Cam bridge: Polity Press,2006:51.
[20][美]帕倫蒂.少數(shù)人的民主(第8版)[M].張萌,譯.北京: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09:255.
[21][美]羅斯金.政治科學(xué)(第九版)[M].林震,譯.北京:中國(guó)人民大學(xué)出版社,2009:306.
[責(zé)任編輯:張亞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