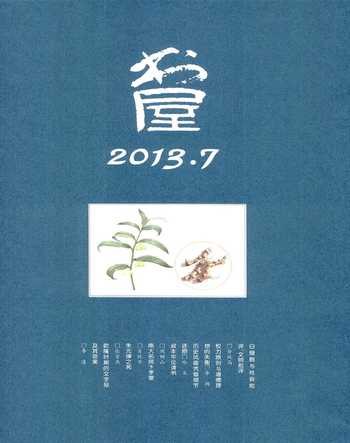讀王船山的三闕詞
苗祺輝
船山先生曾謂李、杜“內極才情,外周物理”,其詩,如“未央、建章,千門萬戶,玲瓏軒豁,無所窒礙,此謂大家”。如果我們把先生的詞也比成一個大的建筑物,那么,“庭院深深深幾許”?答案也只好這樣說:“楊柳堆煙,簾幕無重數。”先生學富五車,無論在哲學、史學還是在文學方面的修養,在他所處的時代里,實處于一個不易企及的高峰!先生著作頗多,僅以余力填詞,前后達四五十年之久。所作詞亦多有不協律處,且有些所用典故太多,讀起來佶屈聱牙,但仔細品品,還是寓意深遠,激楚蒼涼的。
船山先生“生于屈子之鄉,而遘閔戢志,有過于屈者”。他為了反抗清朝,亦曾發動過武裝起義,并遭慘敗,此后,國勢頹靡,更不可為,他不得不退居荒山,然其孤忠之心不易,一直關注國事,心憂天下。伴隨著時間的消逝,他感覺到復國的希望越來越渺茫,當他不得不發出“潭龍齁睡太癡頑,欲續衰年已懶”之感嘆時,對以武力推翻清朝統治已不再抱有希望。故于其詞中,宣其“幽蚃之情”,我們不妨看看船山先生的三首詞。
其一,《踏莎行·與李治尹夜話致身錄事有感而作》:“幾許興亡,憑誰料理,血痕一縷留青史?從來白刃殺英雄,懨懨兒女叢中死。 霜氣飛空,星光墮水,閑宵半吐傷心字。他年莫問草堂荒,蕭蕭落葉隨風起。”
此詞標題中之李治尹,按彭靖先生所撰之《王船山詞編年箋注》之箋注為:李治尹,名向明,衡陽人,文學報瓊之子。
《致身錄》按彭靖先生之箋注:當為船山之兄石崖遺稿。觀書名,當為記休閑后所歷之作。《七十自定稿》之七律《寄題先兄祠屋》句“《致身錄》在憑誰續?爐冷香消亦等閑”可證。
此詞之上闋以大歷史的視覺去寫中國歷史,并發出了內心的孤吼:“從來白刃殺英雄,懨懨兒女叢中死”,他寧愿為白刃所戮,亦不愿死于兒女叢中,直就文天祥《過零丁洋》句“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點染而成,不過詞意更為深婉而已。細想之,此詞上闕亦表達了船山先生對于亡國教訓的總結與內心的無奈,而非對一人一姓的覆滅的悲悼。我們如果在讀此詞的同時,讀一讀《明史·后妃傳》、《明史·呂維祺列傳》等史料,則可知有明一代,特別是其中葉以后,皇帝之荒淫、外戚之弄權與宦官之作惡,較之唐代并無二致。于此可見先生在此所寄寓的興亡之恨,卻是很深廣的。下闕則寫自己復明無望隱居于湘西草堂之一個夜晚與李治尹談論《致身錄》的悲痛之情。“半吐傷心字”,“他年莫問草堂荒,蕭蕭落葉隨風起”,則給人無限的悲涼感,感情激越,心緒蒼茫。
其二,《昭君怨·本意》:“千古英雄一淚,只在琵琶聲里。冷笑看功臣,畫麒麟。 嬌面胡風吹皺,拚與紅顏消受。赤鳳不知愁,漢宮秋。”
麒麟:漢殿閣名,亦作麟閣、麒閣。《漢書·蘇武傳》:“甘露三年,單于始入朝,上思股肱之美,乃畫其人于麒麟閣,法其形貌,署其官爵姓名。”謂其“皆有功德,知名當世,是以表而揚之,凡十一人”。
赤鳳:鳥名,鶉也,見《禽經》。《搜神記》:“漢代十月十五日,以豚酒入靈女廟,擊筑奏曲,聯臂踏地為節,歌‘赤鳳來,巫俗也。”庾信《道士步虛詞樂府》:“赤鳳來銜璧,青鳥入獻書。”李商隱《可嘆》:“梁家宅里秦官入,趙后樓中赤鳳來。”趙后,趙飛燕也。
知道了上面兩個典故,此詞表面上的意思便不難理解了。而竊以為,這首詞在船山先生的詞中屬上乘之作,他是借詠王昭君以紓己之紆郁之情。船山詞,正如葉恭綽氏所云:“言皆有物,與并時披風抹露者迥殊。知此方足以言詞旨。”彭靖先生于《王船山詞編年箋注》中箋注此詞則云:“玩詞意,當為明室降清之臣,如洪承疇等人而發。但不能確指寫作年份。”船山先生此詞,亦可謂“離婉于直”。婉陳,故不失詞旨;直達,故字里行間英風勃發。一面是嬌面、紅顏、琵琶聲、漢宮秋,一面是英雄、冷笑。真真是亦婉亦直,亦柔緩亦豪邁。而上下兩闕之歇拍,用漢麒麟閣事與漢伶玄《趙飛燕外傳》事,出語輕俏而用意深遠,而如此豐富、深刻的內容卻借詠王昭君而熔鑄在這樣一個短調里,確為一不朽之作。
其三《滿江紅·直述》:“淚冷金人,渭城遠、酸風痛哭。君莫笑,癡狂不醒,口如布谷。墮地分明成艮兌,通身渾是乾坤肉。耿雙眸、黑白不模糊,分棋局。 千鐘粟,誰家粟?黃金屋,誰家屋?任錦心繡口,難忘題目。為問鶴歸華表后,何人更唱還鄉曲。把甲辰堯紀到如今,從頭讀。”
“淚冷金人”句:李賀有《金銅仙人辭漢歌》,序云:“魏明帝青龍元年八月,詔宮官牽牛車西取漢孝武捧露盤仙人,欲立置前殿。宮官既拆盤,仙人臨載乃潸然淚下。”
布谷:鳥名。每谷雨后始鳴,夏至后乃止。
艮兌:二卦名。《易·說卦》:“艮三索而得男,故謂之少男。艮為山。”又曰:“兌為澤,為少女。”
鶴歸華表:《搜神記》載,遼東城門外華表上,一日飛來一白鶴,忽作人語,曰:“有鳥有鳥丁令威,去家千年今始歸。城郭如故人民非,何不學仙冢累累。”
此詞題曰“直述”,康和聲據以為“乃為二心之臣,全忘故國者發”。審詞意,殆可信。此詞上闕寫亡國之痛,并擴大其內涵,并表明自己的心跡——“耿雙眸、黑白不模糊,分棋局”,所謂黑白,是非清濁也。棋局者,政局也。“口如布谷”,殆謂及時而鳴,及時而止也。“墮地分明成艮兌,通身渾是乾坤肉”,當謂做人應頂天立地。此詞下闕開頭便說“千鐘粟,誰家粟?黃金屋,誰家屋?任錦心繡口,難忘題目”,則更加直白——縱有千鐘之粟,可貯金屋之女,亦須問其來自“誰家”,任憑自己有優美文思、富麗詞藻,亦須視人、視題目而為,不能信口雌黃,任意諛頌。“為問鶴歸華表后,何人更唱還鄉曲”則云人生短暫,何必違心!變節仕宦新朝者,即便衣錦還鄉,但在鶴歸華表后,亦不過累累荒冢。人生不過百年,應該珍惜名節,免貽后世之羞!此詞歇拍“把甲辰堯紀到如今,從頭讀”,蓋我國歷史以甲子紀年,始于帝堯甲辰元年,言不可忘也。讀船山先生的這首詞,亦使我想起他《鳳凰臺上憶吹簫·憶舊》中的一句——“堪嘆生生死死,今生事、莫遣心違”,此大抵為船山先生一生的真實寫照。在明末清初詞壇盛行“淫詞”、“鄙詞”、“游詞”,士大夫普遍以詞為小道的背景下,先生以詞悼國恨家亡,不僅擴大了詞的內涵,還提高了詞體地位,將詞體提高到和詩一樣可以“言志”的高度。
世人皆以為,船山一生秉儒家忠君愛國之貞操,立救國濟世之宏愿,對明王朝有著濃厚的孤忠之情,“自先世為明臣,存亡與共”乃其心理基礎。而竊以為,船山投入反清復明斗爭,并非單純為“戀明情結”所驅動,如果考量當時清王朝推行民族壓迫政策而對廣大漢民眾所造成的苦難(即船山先生《黃書》中所謂之“生民以來未有之禍”),那么就可知先生還具有擔憂蒼生苦難的人文關懷的精神。在先生的心頭,一直像蛛網一樣交織著各種矛盾。正如他在《九昭》里所說:“雖他日哀歌亦無救于滅亡,則愛身全道,固非心所安也。”
總之,船山詞絕非無病呻吟之語,而是用至誠至信、至性至情的哀思凝結成的。我亦想說,生命是一種真實,好的文學作品,其實是發自內心的真實的語言,只有真實地愛了、恨了、寫了、追求了,才是人生與藝術最大的收獲。船山詞的最大價值正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