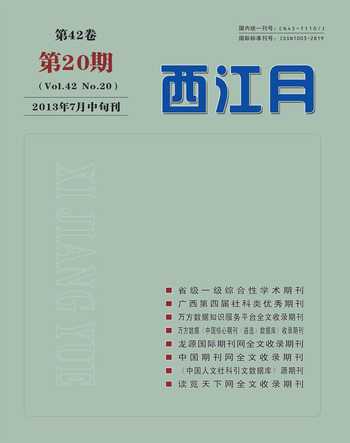簡析精神分析對文學的影響
于慧萍
【摘要】精神分析理論是在弗洛伊德本能理論的基礎上,歷經百年滄桑發展起來的理論。無論在西方還是在中國它的影響都極其深遠,它由心理學領域不斷向其它領域滲透影響,如哲學、宗教、文學等。在文學領域,精神分析主要從兩個方面產生影響:一是對文學創作的影響;二是對文學批評的影響。
【關鍵詞】精神分析;文學創作;文學批評
“精神分析”一詞對于現代人來說一點都不陌生,它是由奧地利醫生兼心理學家弗洛伊德開創的、研究人格的理論和心理治療的一種臨床醫學方法。但是這門學問不斷向哲學、政治、宗教、文學、倫理學、社會學等諸多領域滲透,并產生了重要影響。僅從文學這一領域來講,它給文學這一領域所帶來的廣泛和深刻變化,是現代任何一種文藝理論或思潮都無法超越的。藝術家拿它來指導創作,開掘人的心靈世界;理論家和批評家拿它解釋分析各種文學藝術文本,發掘作品潛在的意義。
一、精神分析在西方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自開創以來對歐美的作家給予了方法性的指導,他的“俄狄浦斯情結”、“死亡本能”、“生存本能”、“白日夢”等觀點,以反傳統的視角,對西方文學創作和文學批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一)對文學創作的影響
精神分析之所以對西方文學產生深遠影響主要原因是精神分析傾向分析人的無意識動機,而文學本身就以寫人的性格和心理為主,兩者有共同的關注對象——人的心靈。精神分析學的出現讓作家前所未有的關注人物本身、感覺、精神狀態,他們在寫作技巧上突出表現為意識流寫法,追求人們頭腦里潛在的思緒和意識,以及將紛亂復雜、恍惚迷離的內心世界原原本本的展現在讀者眼前,這就導致了意識流小說的流行。意識流作家依照弗洛伊德學說,關注人的整個心理結構,揭示人潛意識當中的本能。如被視為意識流小說里程碑的喬伊斯的《尤利西斯》,打破傳統,通過潛意識記憶的回顧,把人物整個內心世界裸露在讀者面前。另外一位受弗洛伊德學說影響較深的意識流小說家勞倫斯,在《兒子與情人》中細致描寫了保羅處在母愛和性愛之間的矛盾心理,展示了弗洛伊德“本我”的欲望渴望與“超我”意識控制的掙扎。
除此之外,精神分析對20世紀西方的傳記文學也產生了不可忽視的影響。由于精神分析家在記錄病人案史時,常會進行傳記式的研究,而文學傳記家往往解剖分析傳主的精神生活,兩者有其共通之處,傳記文學中浸透了精神分析的技巧和觀念。弗洛伊德寫《達·芬奇》就把精神分析應用到傳記中,打破傳統的傳記敘事模式,對傳主的童年經驗、夢、性欲、精神病態等無意識和深層人格進行研究。探索出一種新的傳記形式,之后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這種傳記形式形成一種風尚。
(二)對文學批評的影響
精神分析法除了被運用到文學創作中,還在文學批評中出現了傾向。首先從弗洛伊德自身開始,為了展示人類的無意識心理,他經常舉作家及其作品中人物的例子來論述人的無意識動機,如他提出的著名的“俄狄浦斯情結”,就是借希臘悲劇《俄狄浦斯王》中“殺父娶母”的情節分析論證了潛意識中的“戀母情結”。他還對莎士比亞的悲劇《哈姆雷特》進行了與眾不同的分析研究,他認為哈姆雷特之所以對他的叔父遲遲不肯下手,是因為他自身存在的“戀母情結”在作怪,他對母親的占有欲望如同叔父一樣,于是對仇人的恨轉化為對自己的譴責,鏟除仇敵,等于奪己性命,所以他只能猶豫不決。
雖然當初對于弗洛伊德的觀點看法褒貶不一,但如今,精神分析用于文學批評已經司空見慣。它對傳統文學批評進行了填補,在傳統批評研究作品的歷史環境、社會背景等外向方面的基礎上,揭示隱含在作品表層意義下的“無意識”的內容。
二、精神分析在中國
精神分析理論在中國的傳播,自20世紀新文化運動就開始了,其傳播途徑主要是以歐洲語言為直接以及日本作為間接傳播渠道。其對中國作家的文學創作及其文本批評也產生了重要影響。
(一)對文學創作的影響
弗洛伊德在《夢的解析》中說:“夢是一種(被壓抑的)欲望的(經過偽裝的)滿足”,夢是愿望的達成,而這愿望是一個受壓抑的愿望,雖然文學與現實有關系,但并不是現實,是對現實的幻想,因此夢與文學一樣都是被壓抑的愿望的滿足。所以文學被認為是情感欲望的表達自然有其正確的一面,魯迅深受其影響,他對日本作家廚川白村《苦悶的象征》極其欣賞,而廚川白村是發揮了弗洛伊德的“壓抑說”,把文學當做苦悶的象征,跟夢一樣,都是受壓抑的愿望的滿足。魯迅自己曾在《故事新編·序言》當中談到他創作《補天》時說:“首先,是很認真的,雖然也不過取了弗羅特說,來解釋創造——人和文學的——起源”[1]。由于精神分析理論將性本能解釋成人類意識以及所有實際活動的原動力,性愛在文學中的表現不再像過去艷情小說那樣隱匿,以創造社的郁達夫、郭沫若等為代表作家,他們極其擅長寫變態的性愛,如郁達夫在《沉淪》中寫“他”的窺視癖;《茫茫夜》的于質夫與吳遲生搞同性戀。除此之外,精神分析思想在中國還形成作家創作的風格,如施蟄存、張愛玲等人,他們專事精神分析小說,變態、夢幻、潛意識、表現超乎尋常倫理的性愛關系。
(二)對文學批評的影響
精神分析在中國的狂潮不僅表現在文學創作領域,也表現在文學批評中。出現了從事精神分析理論對中國文學進行解讀批評的研究專家,如郭沫若、聞一多等。僅陳思和主編的《精神分析狂潮——弗洛伊德在中國》一書就列出郭沫若、聞一多、魯迅、周作人、潘光旦、施蟄存等24人的33篇的文章。
作為運用精神分析進行文學批評的代表,郭沫若早在20世紀20年代,就開始用弗洛伊德學說批評研究中國古代文學中的《楚辭》、《詩經》、《西廂記》等作品。郭沫若用弗洛伊德學說解讀古代文學,對文學批評起到了創新作用。他從《離騷》、《湘夫人》中讀出屈原的性心理,從《胡笳十八拍》讀出蔡文姬患有歇斯底里癥狀。他還在1921年發表的《<西廂記>藝術上的批判與作者的性格》一文中,說“《西廂記》里‘休將眼角留情處,只這腳跟兒將心事傳,此外在《西廂記》中敘述到腳上來,鞋上來的地方有好幾處,對女性的腳好像有很大的趣味。所以我推測王實甫這人必定是受盡種種鉗束與誘惑,逼成了性變態者”,[2]并且他舉纏足一事證明“就男子而言,每以腳之大小而定愛憎,愛憎不在乎人而在乎腳。這明明是種‘拜腳狂”[3]
以精神分析理論研究中國文學的學者還有聞一多,潘光旦等人,聞一多善于將精神分析理論與文化人類學結合,從文化形態上考察文學藝術文本,將其結論與性愛、生殖聯系起來。他將《詩經》的時代概括為:殺和淫。這剛好與弗洛伊德的“死亡本能”和“生存本能”對應起來。潘光旦善于從社會學的角度對中國歷史文學作精神分析的考察研究,例如他寫的第一部系統的研究同性戀的著作《中國文獻中的同性戀舉例》。同性戀在弗洛伊德學說里被稱作“自戀求同作用”所導致的心理現象。
無論是在西方還是在中國,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在地域上影響廣泛;無論是在過去還是在未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在時間上影響久遠;無論是在科學領域還是在文學殿堂,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在意義上影響重大。雖然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在很多方面存在缺陷,如夸大無意識的理論以及泛性論,但他對文學創作、批評領域的開拓、啟發、開創性的影響是無法抹殺的,因此我們應該正確的看待其積極影響與消極意義。
【參考文獻】
[1]周怡,王建周.精神分析理論與魯迅的創作[M].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
[2][3]陳思和.精神分析狂潮——弗洛伊德在中國[M].江西高校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