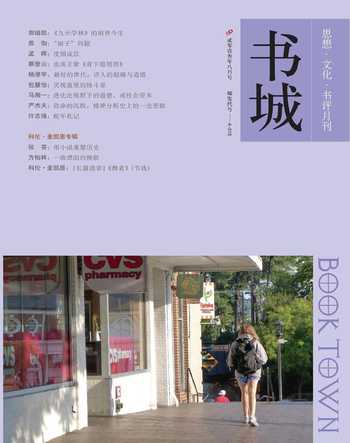靈視盤里的格斗家
包慧怡
伊麗莎白一世與詹姆士一世時代的英國頗似鬼屋一棟:對黑暗中世紀的迷思早已化身一縷尖叫隱入墻紙,文藝復興似殘燈一盞搖搖欲滅滴下繽紛燭淚,推開那扇圓窗向外眺望,或者凝視墻上油畫框中航海家陰郁的眼睛,似乎可以看到啟蒙之光忽閃在前方夜色中。桌上堆著莎士比亞第一對開本(已經落了少許灰),版畫本《浮士德博士》(帶有馬洛的親筆簽名),以及成山的地圖、角規、星盤、六分儀、重力錘。這些儀器的收藏家和設計者,伊麗莎白宮中的御用魔法師,人稱狄博士的約翰·狄(John Dee),首先是光學大師、數學家、棱鏡工匠、水晶球藝人,然后是占星師、通靈人、卡巴拉學者、煉金術士;其軼作包括《論燃燒鏡》、《整體的鏡子,或為英國托缽僧羅杰·培根辯護:這位偉大的哲學家取得的成就并非借魔鬼之手,如無知的民眾所認為的那樣,而是渾然天成》,遺作有《象形單字》(1564)、《為比林斯雷的歐幾里得譯本所作的序》(1570)、《論七大行星的神秘統御》(1583)等—在狄的年代,魔法與科學不過是一枚硬幣的兩面,同屬于一項對象遍及宇宙的解密工程,而世界及其中萬物就是一場盛大的光學表演—或曰神顯。
詩集《王道士的孤獨之心俱樂部》無法不讓人想起狄博士的群鏡—狄的鏡子又稱靈視盤,凝神其中便可與天使或精怪交流,詢天問地,以答案改造現實,譬如狄就是這樣為伊麗莎白一世選定了登基吉日(1559年1月15日),并為女王的大航海時代繪制秘密航圖。王敖的詩歌亦能改造現實,一種精密的、微醺的、致幻的、心理和語言可能性層面上的新現實。那漸入的尖新的快感如空中之華般易逝而絕對不可把握,注意力稍稍懈怠就可能錯過,但我幾乎不曾識得一種更確鑿、更經得住反復蹈踏的現實,也不曾在閱讀的短暫與高強的緊繃后體會過一種更美妙的松弛—“最大的利益”,加斯東·巴什拉說:“乃是空幻的利益。”實際上,王敖并非蘭波或者前期的葉芝那一類型的幻視詩人,我相信他并非特意與后兩者純熟玩于掌心的古典詩體和韻律劃清界限,只不過他的靈視活動找到了更自然、更接近其本質肌理的節拍器,一如美酒淌入獨一無二的酒瓶。這樣的詩可被反復消耗卻無法被減損,其結構近似于一棵向著天空不斷伸展分杈的花樹;正是一種類似的動量—狂歡之欲與究秘之欲(或曰向圣之欲)的雜糅—誘使古代希伯來人發明了用以祭祀的枝形高燭臺,光是《但以理書》中的匆匆一瞥就足以令我們心旌搖曳。比如這一首《絕句》:
最后離開的贏了,他們找到的地獄
香緲幽邃的一枝,仍在猜想,仍在節律之濱
微轉。他們傳遞的浮花,為什么不朽
像海之鏡上,浪蕊的熒光,讓我們在岸邊奔跑
邊相信,太平犬也來自一顆星。
又比如這首《王道士與水晶人》(摘選),我將它理解為一套有機榫合的“絕句”:
1.
在花粉點顫的世界里,你找不到水晶人敲斷的火焰,他的鼻子橙黃雙手劃槳,仿佛河邊的宇航員
他坐在一匹小馬的方向盤身后,踩著更清脆的蹄音
跟絲絲泄露的煤氣一起,來到我的雪夜,來到我冰湖般的床前
當我在半昏迷的家里,羨慕著某一瞬的幽光
2.
為他逝去的那個時刻,有刺猬在翻滾中稱王
頻頻點頭,左右刺破,當花粉的圣壇崩解,現出沙漏的絞架
……
那世界里的偶然叫命運的輪軸廠,昨天的命運仿佛停電的賭船
只有黑暗的骰子聲,與穿透蝶翅的雨點,在交頭接耳
3.
……
我和水晶人之間,無法商談的悖謬成直角的戰場,散發月坑中起伏的徒然
春風吹過砍落的馬耳,帶著一種葡萄香,散入不需要秘密的天空
再見。沒有回家的我,轉身就是縱深的卷須與排浪,卻沒有柯勒律治之花
該如何看待這些幽黯而閃爍的幻境,既然它們誕生于音節與詞義之間的罅縫,在各就各位后又誘發了更多的罅縫和深淵?它們是一組幻境終端機,一如令小愛麗絲無比挫敗卻流連忘返的仙境與鏡中世界嗎?拿最簡短的第一首《絕句》來說,我們看到的是一個但丁設計著擊鼓傳花的新規則嗎?是巴比倫人把星辰崇拜的絕癥傳染給了馮夢龍?是路易斯安那州的颶風減速為小龍卷嗎?我可以不間斷地數下去,直至把這短短的五行編作一本幻境百科,因為《絕句》本質上是一種留白的、誘人書寫的、臨界爆炸的寫作,就像日全食周圍飄逸的日珥。王敖寫下了許多這一類型的短詩,它們的行進方式近似一場基因突變的分形運動,每根手指的尖端分別生出掌紋各異卻遙相呼應的手掌,又好似捷克動畫導演揚·史云梅耶的黏土動畫。
機械、軍火、金屬、礦物、地質、鳥類學、爵士樂……他詩中博物志式的視野再次讓我們想起了狄博士。約翰·狄式形而上學的基礎其實是以數學為主要方法論的赫爾墨斯秘教(即使披戴基督教的面紗),也就是說,幾何學服務于制鏡工藝(有時是水晶球技術),進而幫助他捕捉天使的蹤影和靈啟;反之也一樣,通靈中天使的暗示或首肯堅定和完善著狄的科學知識體系。與其說狄博士致力于整飭玄學與數學這兩極所代表的思維方式,莫如說它們在他的心智習慣中從來就密不可分,共同構成了他一生追求的背景:“如果你對反射光學很熟練,”狄寫道,“你就能夠將任何星球的光束比自然界更強烈地反射過來,”這里,“任何星球”和“比自然界更強烈”是值得深玩的措辭。狄的聲名在隨即到來的理性時代中遭到了貶抑,人們稱他為巫師、招魂者、假先知,或者中性一點的,“瑪古斯”(大魔法師),忘記了他的首要實踐方法和背后的實證精神,一如他們對待一輩又一輩的煉金術師。對詩人王敖而言,不存在這種年代誤植的危險,在看似局限的文字格斗場上,他以一種與狄類似的消弭界限的精神(或許兩人的星盤上都有一顆強力的海王星),翻新著隱喻與字面之間的摩擦系數,將我們帶往比狄的大航海計劃更遠的地方:
半月峽灣的落日,與奔跑著把人群趕向黑夜的裸警,是不是睡眠抄襲死亡的一次曝光
還是多枝的天空下,持燈的鳶尾花背著螳螂,調笑這拿鐮刀的
—《絕句》
又如:
無數新生的圓
我路過,觀察之后,爬上房頂,繼續往前走,太陽落山
空氣中閃著冷光,我突然用四只手轉動自己,上升到靜止中
—《圓》
如我們在以上兩首短詩中所見,《王道士的孤獨之心俱樂部》中有不少作品可被看作關于生存體驗乃至詩藝本身的寓言,只是,與《玫瑰傳奇》、《聲譽之宮》、《金盾》這類經典中世紀寓言詩不同,他的寓意通常無跡可循,且極少暴露作者自身。《絕句》中,持燈的若是鳶尾,它在調笑誰?握鐮刀的若是螳螂,躲藏又何為?還是說,這場諧趣卻步步驚心的格斗,傷害的只是和雙方一樣多枝的天空嗎?此處的修辭簡直讓人想起盎格魯-撒克遜人或者古斯堪的納維亞人在其史詩中慣用的“迂回隱喻”(kenning)—中世紀維京人稱戰士為“戰斗的蘋果樹”或“持利器的槭樹”,火焰是“椴樹的毀滅者”,黃金是“海上的火焰”,大海則是“鯨魚之路”,如此循環往復—然而王敖的隱喻絕無程式和代碼可言,一切都是詞面在流動和碰撞中炸出的異次元空間。《圓》中的“我”終于尋回了聞名于《會飲》的那種失落的至福,攜新近回歸的另一半自己,上升到月亮以上的世界共柏拉圖談笑嗎?闡釋在詩歌脈脈不語的張力面前總會顯得松松垮垮,再豐富也將歸于貧乏,因為詩,一如瓦萊里所言,“乃是聲音與意義之間被延長的猶豫”(Le poème, cette hésitation prolongée entre le son et le sens)。就這一點而言,《圓》可被看作一首尤為純粹的論詩歌及其生成過程的“元詩”。
與我們在前期葉芝身上看到的那種因全然沉浸并棲身于紛紜的意象而導致的人性的缺席不同—誠然,詩歌中過分冷靜和剔透、完成度極高的美往往伴隨著一定程度上詩人的退隱,而擁有一種超驗的、無我的、入梵的表象,因為“現實”的血氣會敗壞這類靈視詩歌的純度,在王敖這里也不例外(主要指短詩,在部分長詩里他另有別樣的野心,此文不表)—與葉芝那種主動放棄一部分個性而成為一件樂器,任本民族新近從古卷中發掘出來的神話和史詩傳統通過自己的身體發出淙淙泠泠的樂音,或是自愿成為塔羅牌大阿卡納系統中的“最高祭司”,任天啟神、精靈乃至凡人(葉芝曾通過記錄其妻喬琪·海德-莉絲在入神狀態中的“口諭”來從事所謂的“自動寫作”)通過詩人的唇舌來傳遞信息的那種“無我”不同,王敖看似不動聲色的詩句中其實飽含著高度個人化的感情,即使經過了大量的抽離節制和修辭轉換,仍可窺見那些隱在暗處、蓄勢待發的疾風暴雨。這個特點在他那些書寫或者看似書寫愛情的詩中表現得尤為特出,比如以下這三首《絕句》:
那個俊俏的爬樹的,已經換上
長裙的你,總是你,在我醒來時,逗弄著
我飽經風霜的小孩心理,我的眼神
像我體內慌慌的力量,流竄在你的指尖,說著愛神啊
(2009)
醉的船只,載我們上床,醉拳之后
怎能不相愛,就像核桃啊,躺在櫻桃的身邊
要靜靜相對,又想要交歡—
帶我們回去吧,手臂上枕著臉龐,透澈的眼睛仿佛
落淚的水蒼玉;有人要從樹上落下;還有人在枝頭紅著胸前
(2003)
很遺憾,我正在失去
記憶,我梳頭,失去記憶,我閉上眼睛
這朵花正在衰老,我深呼吸,仍記不住,這笑聲
我側身躺下,帽子忘了摘,我想到一個新名字,比玫瑰都要美
(2001)
耳朵,這是使得工作中的王道士區分于狄博士的那種卓絕的感官,即使兩人都是耐心的望鏡者—后者的光學之鏡與前者的詞語之鏡。我之所以偏愛以上這三首詩是因為我完全迷醉于其中內在的、不依傍任何韻學傳統的、幾乎逼近了神秘的節奏;他的逗號不是蝌蚪卻是冰激凌上的脆果仁,帶來最直接的生理快感,使得斷句這一行為幾乎有了情色意味。王敖的詩韻向讀者要求的是張開的內耳、屏住的呼吸。植物學家、詩人Chloroplast曾說:“文字的平衡不是靜止,而是如拔河角力,”另一位詩人費魯文將之闡發如下:“二人角力,一蹲一踞,繩雖不動,但力在繩上,飛鳥欲落而不能。弓開滿月、引而不發,箭雖不動,但鋒芒所向,無不悚然。此均靜定而具萬般動象動靜合一之境……飽滿、充實,無限之可能性,自在其中,高深淵妙,莫過于此。”我想,王敖最好的那些詩,確能擔當得起這兩段話所指向的詩歌境界。
這是極高的境界,我們的莊子熟悉這境界,當萬般動靜合一都落眼于語言之無限可能性—可能性,恰恰是今日之漢語詩歌寫作亟需拓深、能贈予每一位作者與讀者的最基本也最寶貴的價值。和所有對自己的手藝絕對嚴肅并致力于將它逐步固定下來的詩人一樣,王敖的寫法有其局限性,不過,即使是這局限也時常表現為攝人的專注,以蹈空的舞姿(輕逸是它的表象),旋成射往無限之箭。約翰·狄博士在布滿灰塵的實驗室里不舍晝夜地設計水晶球,為自己生于一個“自然界似乎就要泄露自己秘密的時代而萬分激動”,令王道士激動的,我想,該是某種截然不同的預感,當他坐在風雪中,等待“落入空海的鏡球……去謎團里建國”(《菩薩之歌》)。昔日雅各在雅博渡口與神摔跤而幸存,從此更名為“以色列”,而王敖以“自我天啟”式的想象力與之頻頻過招的,乃是至高的虛空本身。在這一意義上,恰如布萊克之于英國素體詩傳統,王敖或可被稱為中國新詩史上第一位全然的靈視型詩人,正是:
誰在生命的中途,賜予我們新生,讓失望而落的
神話大全與絕句的花序,重回枝頭
中年的搖籃,蕩漾著睡前雙蛇的玩具,致酒水含毒
遙呼空中無名的,無傷的夜,是空柯自折一曲,讓翡翠煎黃了金翅
—《子夜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