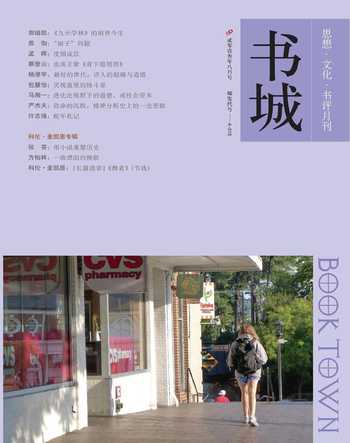書城萊頓
書玉
騎自行車的小城
到達萊頓是五月初。從伯明翰飛往阿姆斯特丹的飛機上俯瞰,比起英國鄉間起伏的丘壑,荷蘭的田野真是平坦,那是荷蘭人填海造田從大自然手中討出來的結果。再近些,就看到一片片整齊而色彩繽紛的彩色地毯。過了很久才恍悟那是大片的郁金香農莊。五月的郁金香是荷蘭特有的風光。
大學城萊頓在荷蘭最大的兩個城市阿姆斯特丹和鹿特丹之間。從阿姆斯特丹坐火車只要十五分鐘。城市真的不算大:從最北邊的中央車站橫穿老城中心到我位于城市南端的臨時公寓,走路也只要半個小時。據說人口只有十萬多一點,其中五分之一是萊頓大學的學生、教授或者我這樣來自世界各地的訪問學者。

小城的魅力以它別具一格的自行車向我展開。從中央車站的游客中心取了公寓鑰匙,我走向車站廣場。三三兩兩的年輕人,放松地享受著五月的陽光;一個賣熱狗和烤腸的食品車;街邊的店里走出的一對戀人拿著令人眼饞的冰淇淋;不遠處矗立著一個荷蘭的象征大風車,一副小地方的溫馨和親切。沒有汽車來往鳴叫,卻看到旁邊停車場里鋪天蓋地上下幾層的自行車,氣勢蔚為壯觀。顯然,因為地勢平坦,街道比較狹窄,加上城市本身不太大,這里是以自行車為主要交通工具。去住處的一路上看到的都是匆忙而快樂的騎自行車的人,輕捷地穿過密集的后巷和縱橫交織的河道。明媚的五月天里,他們看上去都那么健美、年輕。即使年紀大的人,因為騎車都顯得富有活力。車子跟人一樣,高大結實,大多是用了很久的老車破車,看不到在北美用來做運動競技的那些名牌車,但自然就有一種笑傲世俗的瀟灑和實在:世界上還有像自行車這么好的交通工具嗎?又環保,又鍛煉身體,而且不用花時間精力跟別人比虛榮心。它令我想起了大學歲月,校園里那些破舊卻永遠年輕的自行車。可畢業后,我們那么輕易甚至迫不及待地丟棄了它們,去追逐似乎速度更快的汽車和別的東西……
這個一直騎自行車的小城自信而富足,充滿著書生氣。
萊頓的書店
小城的另一個魅力就是它的書。我從沒有見過哪個城市能有這么密集的書店。
從我臨時的住所,位于萊頓南城的Hogewoerd144號到我臨時上班的辦公室,位于城西萊頓大學旁邊的亞洲研究國際交流中心(IIAS),只有約十分鐘路程,可是除了第一次上班的那個早上,我以后都要花少則半小時、多到兩個小時的時間在路上。因為路上的誘惑太多,有太多的東西可看:在縱橫交錯的運河上看形態各異的橋,在古城中心看殘留下來的文藝復興時期建筑的市政大廳的壯觀設計,在此起彼伏的教堂鐘聲里,看沿河高大民居的墻上用異國語言寫的詩句,還有那些穿插在大街小巷里的古董店和書店。
記得到達萊頓的第二天,我從辦公室出來,在回家的路上決定在市中心的那家V&D百貨商店買急需的床單和浴巾。從Breestraat街的主門進去,一進門竟是書籍和文具部分,而且鋪開一大片,幾乎是一家小書店的規模。這一不尋常的安排陳設讓我對萊頓刮目相看。如今世界上還有幾家大的百貨店進門處不是化妝品就是首飾?
Breestraat街是萊頓城最繁華的兩條商業街之一,而除了輝煌宏偉的市政大廳坐落其上,它還以“書店街”出名。僅在我上下班經過的這后半條街上,就有三家賣新書的書店。最有檔次的是正對著市政大廳的Van Stockum 書店。這個書店坐落在有著高屋頂的十七世紀建筑中,高大敞亮,室內裝潢卻很現代。進門迎面的高墻上就是英國詩人濟慈的詩—《死亡》(On Death):
Can death be sleep when life is but a dream,
and scenes of bliss pass as a Phantom by,
The transient pleasures as a vision seem
And yet we think the greatest pains to die
……
浪漫主義詩人這憂郁華美又有些輕靈超脫的詩句一下子就把從喧鬧的大街上走進來的人拉到一種靜寂與反思的心境。讀讀書吧,讓忙碌的腳步有一刻停歇。
書店里主要的書都是荷蘭文,跟一般書店一樣按主題分類。中間長桌上推介的是暢銷或最新出版的。荷蘭語是個小語種,當代荷蘭作家也不多,但是書店里荷蘭語出版的書、鋪天蓋地。多數是翻譯過來的,世界各地的書最新的書在這里似乎都能找到。以小小的荷蘭人口計算一下書的市場,可以想象荷蘭人讀書的勤奮和對世界的好奇。荷蘭人幾乎都會說一口流利的英語,問起原因,他們很謙遜地說因為我們是小語種,就要學習其他語言。但實際上,這種出版各種語言的書籍的傳統是有歷史淵源的,十八世紀歐洲最重要的政論報紙“萊頓公報”(Gazette de Leyde)就是用法文出版的。
書店樓下還有專賣大學課本的部分,為萊頓大學直接提供合作服務。
出來沿街走過幾家店鋪就是另一家書店Boekhandel De Kler 。它看上去似乎更通俗些,因為一進門有很大的雜志和暢銷小說部分。可是稍往里走,才發現內中胸壑。不僅各個題目的書頗有選擇,而且有相當數量的英語和法語書籍。這個書店其實也有一百四十多年的歷史,最早是 De Kler 家族擁有,故得名。在荷蘭有五家分店,各家選書都有自己的特色。萊頓這家分店目前似乎在重點推介驚怵小說Thriller,好像在尋找通俗市場。果然,與其中的店員聊了一會,發現他們也在感慨做實體書店越來越難。
在兩家書店之間,還有一個專賣兒童書籍的書店。沒有進去,但看著門面招牌的五顏六色和櫥窗里的喜人陳設,可以想象孩子路過時會如何動心。后來發現萊頓全城大概有四五家專門賣兒童少年書籍的書店,即使像一般的書店,也都無一例外專門設有兒童閱讀角落,裝飾得花花綠綠舒適溫馨。讓孩子直想坐下來,跟爸媽一樣看書。
Breestraat街過了橋就叫Hogewoerd,也就是我住的那條街。沿街的房子與河邊那些高頂的帶花園的公寓比算不上好區,都是三層的出租公寓。密密集集,每隔幾步一個大門。門外的名號牌上有著十來個住戶的名字。住的大多是學生、游客或訪問學者。街上面也有很多各式各樣的店鋪。咖啡館,室內裝潢用品店,自行車店,二手貨古董店和西餅店。大部分商店門臉與北美或中國的比起來都太小了,有的如果不注意會以為是民居的一部分而走過。它們靜靜地趴在這些建筑的一樓,不喧嘩不奪目,融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這條街上的“五月花書店”(Mayflower bookstore),在萊頓也算小有名氣,因為專賣英文書。一個五十平方米開外的大房間,右手是新書,左手是二手書。左邊靠窗部分,背靠背放著兩架鋼琴,而稍后的一角是攤滿書的一張長桌。幾乎就是一個家庭圖書館的感覺。偶爾有一兩個人進來,四周看一看,與熱情的女店主打個招呼,讓她幫著訂一本書,走了。小店又恢復了寧靜。
在實體書店日衰的今天,在人們越來越浮躁只想刷屏的今天,到了萊頓,徜徉在各種各樣的書店里,即使多數書我讀不懂,也滿心喜悅。有種奢侈,有種感動。

免費書店“萊頓書閣樓”
對那些喜歡讀書但又不想買書或怕背著太沉重只想隨手撿幾本書在客居時看看的旅行者和背包客來說,萊頓還有一個秘密的好地方,那就是可以享受免費書籍的大書庫“萊頓書閣樓”(Book Attic Leiden),在城東一條美麗優雅的街上。中午時分,從剛剛泛綠的樹叢后面可以看到年代久遠的Marekerk教堂圓拱頂。近處整齊的院落里一簇簇的盆花在盛開。“書閣樓”的大門緊閉,上面寫著一個什么慈濟會的名字。經過路人指點,我才看到旁邊像是車庫的院落才是通往閣樓的大門。
“書閣樓”在一家堆滿雜貨和棄置的雕塑作品的大倉庫間。通往“書閣樓”的樓梯陡陡的,暗暗的,但一走上去就豁然開朗。足有二三百平方尺的大空間里是一架架一堆堆的書。這里的書都是由個人或各種機構圖書館書店捐出的,也包括出版社多余的書或者樣書。因此是各種語言、各種類型的書籍大雜燴。除了荷蘭文,以英文、法文和西班牙文最多。書籍也大多是舊的,甚至有些年代。不過是免費的,每個人都可以任選七本帶走。也歡迎把不用的書再留在這里,讓后來的人受益。
聽說這個書籍回收中轉站的主意是一群萊頓的志愿者想出來的,兩年多前付諸實施。每周服務三次,周二晚上七點到九點,周四、周五下午一點到五點。我去的那天在這里工作的五六個人都是各種年齡的志愿者。他們在不同的角落里拆包登記,給書上架,或幫來訪者找書。聽我說想了解荷蘭作家,一位叫彼得的老先生熱心地向我推介荷蘭暢銷女作家Cissy Van Marxveldt (1989-1948) 。Cissy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寫作,擁有大批年輕女性讀者,以她的系列小說Joop ter Heulz最為著名。這個系列從Joop作為高中女生到戀愛結婚,生兒育女,里面穿插很多書信日記,塑造了一個有主見、不斷成長的二十世紀荷蘭新女性。我不好意思拂老人的好意,告訴他這好像太歷史了。因為一個星期下來,發現在萊頓時間好像可以很慢,而且過去與現在也不見得有那么大差別。老人還幫我找到幾盤專門為說中文的人學荷蘭語的磁帶,介紹我認識另一位志愿者瑪塞拉。瑪塞拉是智利人,來荷蘭也有二十年了。現在在萊頓大學讀碩士,每天抽出兩三個小時來這里幫忙。當發現我跟她一樣,是滿世界跑的世界公民,她圓圓的臉上閃著激動和熱情,留下電話,約我再見面。又指著墻上的一個告示,說周日這里還有一個讀書會,完了之后大家會換個地方去喝酒。
萊頓的朝圣者博物館
除了新書店和免費書店,萊頓可能也是擁有最多古董店和古董書拍賣商的地方。你想,大學里有那么多藏書豐富的老教授和收藏家們,再加上悠久的歷史,東西南北來歷復雜的居民,這里的古董和珍奇書籍自然豐富。
萊頓賣古董書的老字號拍賣行叫Burgersdijk & Niermans。坐落在萊頓最古老的街區,靠近圣彼得大教堂的Pieter Skwartier那一帶。那周圍有保存最好的古老建筑和很多高檔古董店。走近這間看上去不起眼的三層建筑,最明顯的標記就是寫著拉丁語的黑鐵招牌“所羅門的圣殿”(Templum Salomonis)。這個店名和建筑都是來自十四世紀有名的法學家和書籍收藏家Philips Van Leyden(1328-1382),這里是他的住宅,因他的私人圖書館而得名。幾個世紀以來這個房子幾易其主,但都跟書有聯系,不是印刷工就是書商。B&N公司的兩個創始人Pieter Burgersdijk 和George Niermans本來也都是大出版集團Brill的雇員。一八九四年兩個人接手Brill原來的拍賣和古董書收藏部分,并在現在這個地址上開始了他們的生意。
店鋪分前后兩個部分:前面是書店,主要是賣一些珍本書、古典系列和學術書。后面就是辦公室。公司每年舉行兩次拍賣活動,五月的這次剛剛結束。雇員們正緊張地把拍賣出去的書打包郵寄。
B&N自己也出版一些小眾型圖書,尤其是有關荷蘭和萊頓的文化歷史。有十八世紀三個最有名的書商的旅行日記,有關于萊頓城的建筑歷史,還有一本再版多次的英文歷史書《老城新人:美國朝圣者在萊頓》(J. Kardux & E. van der Bilt – Newcomers in an old city. The American Pilgrims in Leiden, 1609-1620)。這本書幫我意外地了解了萊頓與新大陸的聯系,還把我引向萊頓另一個有名的地方,朝圣者博物館 (Leiden American Pilgrim Museum)。
博物館實在很不起眼,就在市公共圖書館和藝術中心的斜對面,我卻轉了兩圈,問了三撥人才找到。在一個低矮的十三世紀的老房子里,朝圣者博物館的館長也是導游Bangs博士一邊帶我和另一對參觀者看不大的兩個房間,一邊講解朝圣者的歷史。
原來,當年歐洲十六世紀宗教改革后,從天主教分離出來的新教在英國成為國教,也叫圣公會(Anglicanism)。圣公會內部的一些教徒反對僵化固定的教會儀式和嚴格的等級規定,認為除了《圣經》是最可靠的上帝之詞外,個人有權選擇與神溝通的方式。他們后來被稱為分離教派(Separatist),也就是Puritans。分離教派在英國受到打擊和排擠,很多教徒被罰款甚至入獄。于是一批教徒在William Brester和John Robinson帶領下離開英國,尋找可以給他們宗教信仰自由的地方。他們來到荷蘭,在阿姆斯特丹和萊頓安頓下來。更多的人陸續投奔這里,最多的時候達到五百余人。他們聚居在一起,在這里生活了十幾年。這就是后來被稱為“朝圣者之父”(Pilgrim father)的那批人。
這個博物館展示的就是十七世紀一個比較有地位的傳教士家庭的大致情形。住處分成內外兩個部分,里面靠著壁爐為中心,是家人活動吃飯的地方,而外面的一半空間就是用來紡布的。Bangs博士對這里的一切很熟悉,對我們無知的提問也很耐心。他一口英語說得實在太完美,一問才發現其實他是美國人,芝加哥大學畢業后來萊頓大學讀博士。后來就留下來,因為他的研究興趣是十六七世紀的萊頓藝術史,因此創辦了這個博物館。但他的主業其實是收集歷史檔案資料,研究和寫書。他最近的一本書就是關于朝圣者在萊頓的歷史,書名叫《陌生客和朝圣者》(Strangers and Pilgrims)。據他解釋,當初英國的教徒之所以能在萊頓安身,是因為當時荷蘭對宗教信仰相對寬容,而萊頓繁榮的工商業也使這些人找到了可以做的事。萊頓大學成為他們傳播思想的平臺。當時Breaster在萊頓大學教英文,Robinson在大學注冊攻讀博士學位,并參加當時的宗教辯論。他們還印刷小冊子,傳播他們的宗教思想。這些人在萊頓生活一段時間后,后來又再度起航,登上“五月花”號輪船,于一六二○年到達北美洲,在東部麻省的Plymouth 落下腳,這就是新英格蘭最早的歐洲移民。 Plymouth Colony和感恩節一樣,奠定了新英格蘭的傳統,是今日美國精神的基石。但也有一些朝圣者客死萊頓。比如Robinson,于一六二五年去世,他的墓碑就在萊頓城中的圣彼得教堂。
離開博物館時,我發現了Bangs博士臉上的一絲落寞。又是一個寫書人,一個在文字中尋找家園的人。他看上去也有六十歲了。當初他來萊頓并留下來,是因為什么?他在客居萊頓的那些朝圣者身上,看到他自己的影子了嗎?
萊頓的出版傳統
萊頓對書的情有獨鐘是有歷史淵源的,萊頓的出版印刷也有其獨特的傳統。
中世紀,與法國、英國和西班牙都有各種各樣聯系的荷蘭是羅馬天主教和歐洲君王權貴割據相爭的對象。荷蘭幾個世紀在封建割據中試圖獨立的狀態,可以從處于新舊Rhine河交界之間形成的小丘上的圓形堡壘Burcht Van Leiden 看出一端。這里已經成為萊頓從一二○三年到一四二○年再到一五七四年幾次被圍但終究生存下來的象征。
自十五世紀末開始,萊頓的印刷業和紡織業開始馳名歐洲,尤其是粗棉毛布和羽紗,成了萊頓的名牌產品。Burcht旁邊的市圖書館的老房子就是當年接待來往商人的客棧(Inn and Coach house),現在如果你去逛當地的周末集市,會看到很多攤販上賣的還是大幅的布匹。
小鎮在十六、十七世紀開始繁榮,繁榮的原因之一就是一五七五年萊頓大學的建立。據說,歐洲“八年戰爭”期間,萊頓人站在反戈的荷蘭貴族一邊,抵抗當時的西班牙統治者。一五七四年五月到十月間,小城整整被圍困了近六個月,有一半人失去生命。后來運用河道才運進物資供給,市民得到拯救。這一情形在當時的畫家Otto Van Veen 的畫作《萊頓的解圍》(Relief of Leiden, 1574)中得到栩栩如生的表現。如今每年的十月三日,都是萊頓的“勝利日”,是要舉城相慶的。今日荷蘭王室的祖先,當時的“護國公” 威廉一世為感謝萊頓人,讓萊頓人在減稅和建一所大學之間選擇一項,作為獎賞。有眼光的萊頓人選擇了后者,也因此成就了小鎮此后幾百年的名聲。
當時萊頓最有名的工商業除了紡織還有印刷。荷蘭在十六到十八世紀的歐洲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運動中,以對宗教和信仰的寬容及言論自由的態度聞名。而萊頓大學的成立,吸引招徠了歐洲各地的學者、宗教分離主義者和持異見者,成為一個論壇和思想傳播集散地。新教的理論家以大學為基地,熱衷于編寫大量的神學著作,各種民族語言的《圣經》也相繼出版,萊頓因此也成為歐洲印刷和出版的一個中心。
這一階段萊頓歷史上出現了幾位很有名的書匠,最有名的是Christophe Plantin(1520-1589)。這個出生在法國卻在比利時安特衛普成就了自己的事業的印刷工既是一個手藝非凡的書匠,也是一個見識淵博的出版家。一五八三年,他在安特衛普的生意被西班牙人攪亂,而萊頓這個新建的大學城又急需一個好的印刷工,他就遷居萊頓建立了自己的印刷所。Plantin的到來使萊頓的印刷出版上了一個新層次。他出的希伯來、拉丁和荷蘭文的《圣經》因校對準確、印刷精美成了后世的典范。Plantin還出版了大量的希臘羅馬經典、法文和拉丁文圖書。同時期另一個書匠叫Lodewijk Elzevir(1540-1617),他曾在安特衛普跟Plantin學藝,后定居萊頓,是Elzevir印書館(House of Elzevir)的創始人。這個印書館以十八世紀出版了被教會視為異端的伽利略學說而為后人銘記。
可以看出,萊頓的印刷人出版商在歐洲文藝復興和近代科學知識傳播上的巨大貢獻。他們本人不止是術業有專攻的技工,而且都有遠見卓識,敢于為思想知識行動。
買賣圖書的書商們與萊頓大學的關系也十分密切。十七世紀當地很多書商都是一邊賣書,一邊出書。世界上最重要的學術出版社Brill的創始人就出自一個有名的書商Luchtmans 家族。Brill 于一六八三年創辦,借助萊頓大學里眾多教授和學者的力量,當時以出版各種語言的《圣經》、東方語言、神學和種族學書籍為強項。三百年來,這個古典語言和人文學書籍的傳統一直得到延續,并在法律和社科方面也有發展。一方面,出版很多大學教授的學術研究,另一方面,其中大量的書籍被用作大學教材,成為一個國際性的大學術出版商。不過Brill二戰期間因與納粹合作提供多種語言的軍事手冊和課本而使公司聲譽一度受到影響。上個世紀八十年代資金緊縮,Brill關閉了倫敦和科隆的辦公室。九十年代后又有所發展。至今,在萊頓和波士頓有兩間辦公室,每年出版有一百余種學術雜志、六百余種學術著作和參考書。其中的萊頓漢學書系(Sinica Leidensia) 上個世紀三十年代開始,由最著名的漢學家組織編寫,叢書收錄有專著、文集和翻譯作品,以古典漢學和權威作者而著稱。近年來,也開始積極組一些當代研究的書稿。去年我還應邀為他們審讀過一部書稿。
萊頓的城市精神
前幾天在網上看國內的一個鳳凰網讀書會欄目,在清華教書的加拿大人貝淡寧(Daniel Bell)正為他與人合寫的一本新書《城市的精神》對話汪暉。在討論什么是城市精神和愛城主義(civicism),貝的一句話讓我很有感觸。他說,獨特的城市精神才能讓人產生歸屬感。
到萊頓已經不知不覺快兩個星期了。我對小城的大街小巷、名勝古跡也差不多走熟了。在這個到處都是學生、學者和書店的地方,我有一種久違的賓至如歸的感覺。
天氣好的時候,沿著小城外圍的Singel河從城南到城北繞城一周,可以看兩岸草地上的綠柳紅花,看運河船里喝酒作樂的人,看寫在墻上的詩,來自世界上各種各樣的文字。陰天下雨,就可以待在書店、圖書館,或者去朝圣者博物館隔壁那家古董店,在一堆堆故紙里,挖掘十七世紀的荷蘭版畫(engraving)和各種各樣的地圖。窗臺上擺的青白瓷罐很眼熟。原來這就是著名的Delftware,盛行于十七世紀和十八世紀的荷蘭特產,最初正是模仿中國青白瓷器,是當時在歐洲流行的“中國風”的一部分。
如果用一個字或一個意象來形容萊頓的精神,我想就是書吧。這里的人是讀書人、寫書人和出書人。連這里的墻上也寫滿了字。“寫在墻上的詩”是萊頓城的一個文化項目,從一九九二年開始已經有逾百首來自世界各種語言的詩被精心描畫在大街小巷上的各式建筑的墻壁上,包括美國詩人威廉姆斯(William Carlos Williams,1883-1956)的這首詩:
Love is like water or the air
My townspeople
It cleanses, and dissipates evil gases.
It is like poetry too
And for the same reasons.
愛像水,像空氣,
城里人,
它清潔,消除邪惡之氣。
它也像詩,
因為同一個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