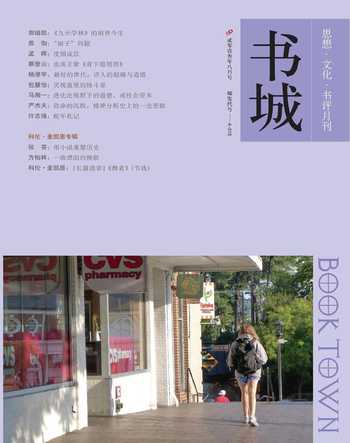克萊斯特譯介的中繼站
盧盛舟
在《O侯爵夫人》(上海譯文出版社,2010)出版之前,市面上德國古典作家克萊斯特的作品譯集只存《克萊斯特作品精選》(楊武能等譯,2007),通過網(wǎng)絡倒是可以下載到上海譯文出版社一九八五年版的《克萊斯特小說戲劇選》(商章孫等譯)。其實,這兩本譯著的選篇完全一致,或限于篇幅,它們在小說部分未錄克氏的《洛迦諾的女丐》(1810)和《圣凱茜麗或音樂的魔力》(1810),戲劇部分未載《施洛芬施泰因一家》(1803)、《彭忒西勒亞》(1807)、《海爾布隆的小凱蒂》(1810年)等重要劇作。袁志英先生翻譯的《O侯爵夫人》收錄了克萊斯特所創(chuàng)作的全部八篇中篇小說,彌補了前書的部分遺憾。
海因里希·封·克萊斯特在德國文學史上的名聲和地位堪比歌德、席勒。在同時盛行的啟蒙主義和魏瑪古典派美學觀的視野里,克萊斯特算得上是一位邪典作家。他生前幾近無名,三十四歲在柏林萬湖飲彈自殺,身后被接受史收編成經典大師。袁志英先生在譯后記中不僅對克氏“危機人”式的生平作了介紹,對所譯中篇小說也作了內容上的導讀。這份克制的導讀避免了一九八五年版的譯本序里打著彼時時代烙印、從而顯得過于武斷的解讀模式。克萊斯特的中篇小說向以曲折的長句和幽隱的意蘊著稱。德國文學研究界曾出過一本頗受歡迎的入門讀物,叫《文學研究的立場—克萊斯特〈智利地震〉的八種模態(tài)分析》,它試用各派文學理論,對克萊斯特的一部中篇小說探幽發(fā)微。僅觀書名,我們就能察覺到克氏作品意義內涵的豐富,雖然這定題足以嚇退大多數(shù)疑心于形式的讀者。
袁志英先生還談了“五四”以降我國文學界對克萊斯特的接受過程,暗示了這位德國古典作家在國內遭受的冷遇。對此,我試補充一例:二○○五年恰逢席勒雙百忌辰,德國政府把該年定為“席勒年”,人民文學出版社也隆重推出了六卷版的《席勒文集》。二○一一年,同樣是官方文化中的“克萊斯特年”,國內文學出版界卻未見微瀾。不過話說回來,“我們如何介入古典作家”不光是個出版議題、閱讀議題,同時也是一個寫作議題,乃至一個生活議題。再補充一例發(fā)現(xiàn):村上春樹在《海邊的卡夫卡》里借筆下人物之口談論舒伯特D大調奏鳴曲時云:“羅伯特·舒曼誠然是舒伯特鋼琴樂難得的知音,然而即便他也稱其如天路一般漫長。”其實,舒曼刊載于萊比錫《音樂新雜志》的原文是“這天路般漫長的交響曲如同讓·保爾一部厚厚的四卷小說”。村上的取舍或許表明,對今人而言,讓·保爾(同樣是德國古典作家!)之名應該不如“天路般漫長”這一修辭來得討喜吧。
細心的卡夫卡讀者是不會對克萊斯特這個名字感到陌生的。卡夫卡在書信和日記中曾數(shù)次提到過克萊斯特,他的處女長篇《失蹤者》開頭使用的敘述卡爾·羅斯曼丟失行李的長句似在向克萊斯特致敬。卡夫卡向菲莉斯坦承過他和克萊斯特在心理上乃至文學上的親緣關系(1913年9月2日),分享過他對《科爾哈斯》一作的敬畏之情(1913年2月9日)—“昨晚我沒給你寫信,因為讀《米歇爾·科爾哈斯》讀到很晚。(你不知道他嗎?如果不知道,就不要讀他的作品,我以后給你讀)”需知,一九一三年的頭三個月,他給情人是每日一信。卡夫卡因讀克氏破例,聯(lián)想到康德讀盧梭的類似掌故,讀者應會忍俊不禁。若嫌上述引文煽情不夠,倒還有一例更符“文案美學”:出版人威利·漢斯在一篇憶文中聲稱(見《布拉格午報》,1933年8月7日),受病痛折磨的卡夫卡在去世前寫信向克勞普施托克醫(yī)生抱怨:“我再也無法朗讀克萊斯特的小說了。”只是這封信早已佚失,出版人之言的真實性亦不可考。
除了一生創(chuàng)作的八篇中篇小說外,克萊斯特的戲劇、書信和雜文都有很高的文學價值。在德國,僅其全集的歷史批判版本(校刊版)就有若干。克萊斯特全集的中譯不可驟得,但終有羽化之時;而另一方面,鑒于克萊斯特在國內知音寥寥的局面,進階讀者或研究者要是故作疾首狀,那這種態(tài)度和無知一樣,都是不足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