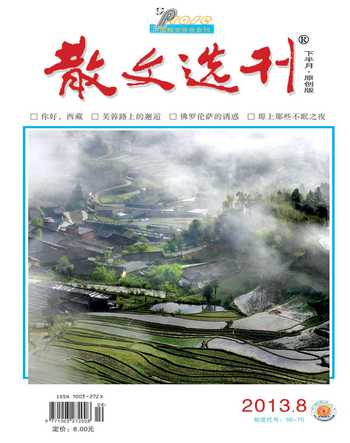光陰故事
白衣書生
每逢停電,我在家大抵是坐不住的。前不久的一天,我早晨下班歸來,一下車就見整條街都在停電,一些商店外自備的柴油發電機突突突的直是轟鳴。于是我家都沒回,直接招了一輛車,去了富樂山下芙蓉漢城的江畔喝茶曬太陽。
從芙蓉橋頭沿著江堤一路走過去,茶樓倒是連續而密集,可我卻沒有停下,直走到那段路的中段一家叫做“光陰故事”的茶社面前方止。它的名字好像還有“咖啡語茶”這類顯是時尚的幾個字,但我到底沒有記住。只是覺得深懷了對那些光陰里的故事莫名感慨,就像心里忽然被某樣東西抓住了,便自然去到它面前那約莫十幾個平米的園子里的某桌落座。至于旁邊室內布設的典致,除了初到時隨意地朝大扇的玻璃窗內掃過一眼,然后就是后來進去上洗手間時才見得真切。
這店是個老字號,在那兒已經存在了七八年。不過,以前我不止一次地去過它旁邊的“一畝田”稀飯莊,也去過另側的“漢城一品”茶樓,卻從沒去過這家。即便多少次路過,隨意地張望上一眼——哦,光陰故事,好!便走過了。想是當初緣分未到,故而才一直只是它的路人。
我去時,只有一個服務員坐在門口的那張茶桌邊,安靜地不知在絮弄些什么女人的小物件。那是一個20出頭的年輕女子,白皙而平靜的梨形臉上,加之一對瞇兮小眼的襯托,長發輕垂,更顯迷離。我不知她是否在想曾經某段人生中的一件原本看似平淡零碎卻對她又風起云涌的事,也不知道她是否早已習慣于這么在時間的緘默流淌中幻想未來,只是不自覺地就與茶社的底色融為一體,徑直透出一股恬淡不驚的氣息,在那看不見的空氣中濃郁地彌漫。一副細柔的身肢,裹在玫紅而緊身的近膝的毛線裙里,加之黑底白點打底褲下的一雙筷子般的小腿,往那兒不經心地一坐,就成了一株不無靈秀的點綴。足以讓人想起暗夜中的一盞焰苗飄忽的燭火,或是音樂小酒吧不起眼的角落里的一枝小朵的玫瑰。不過,她終究算不得漂亮,也沒有青春年華所應有的那些難以按捺的活潑。故而,我并沒有對她有過多的注意,也不曾多說一句話。大抵,也就那么平淡無奇地瞄上一眼,如同初到時習慣性掃視茶社外的布設一般漫不經心。
坐下,喝茶,打盹。初春的陽光已然泛起燦爛的模樣,從一側的天空照下來,落在身上溫暖十足。伸手拉近旁邊另張鋪了布墊的清漆藤椅,脫掉鞋把腿放上去平伸著,我就這么愜意而安閑地小憩,寧靜而并無來客。疲累和著混沌,便自然地將所有的知覺拖入一個深遠而恍惚的世界。時光的漫涌,就開始變得與己無關了。
約莫一個小時過去,我清晰地醒來。陽光依舊暖著,路上仍然是稀拉的行人。身體里原本有著的沉重與倦意,不知何時就被那看不見的江水給淘去了許多,只剩得一些不明就里的淺痕,像是久經風雨浸蝕后的晦澀,一塊生命深處躺著的墓碑。無從琢磨,也無法脫離。
于是,我就撇開那些沉重,開始打量起周遭來。順帶看看會有些什么樣的人來去,又會有些什么樣的事情。說是觀察,欣賞,都似乎說得過去。甚至有時,我還發現內心有種頗為興趣地捕撈與獵奇在暗自流淌。那些平常得再平常不過了的自己或是別人的行走,神態,言說,恰在此時莫名地煥發起昂揚的生機。似乎每個平日里看起來毫不起眼的細節,都有可能帶給我一些少有的觸摸,諸多的猜測,以及鋪天蓋地而來的分析。我忘了自己是誰,只是一味地沉浸在解剖青蛙,看別人解剖青蛙,或是青蛙的自我解剖中。于此,我的興致盎然,在那些川流不息的掃描與瞬時的彼此掃描中,便變得合情合理了起來。要知道,眼睛與內心一旦達成某種共識,要想攜手并肩精誠合作的話,那么自然就能將某粒空氣中隱而未現的飛塵,放大成一個內容豐富的宇宙。所以,我不敢擔保,那個原先坐在茶社外而后又進到玻璃窗內的雅座里坐著打毛線的女服務員,其眼光是否已經磨煉成為深懷警惕的間諜。
因了一個名字,就去一處茶社喝茶。即便是一個人去,也無所謂。但去是去了,卻終坐不久。一般兩小時左右就走。想是那心內的寂靜與身外的流涌,莫名其妙所達成的某種契合,終是需要去打散與肢解掉的,不然就難以回到人間煙火。沒有了煙火味兒,那么生活難免就會受到重創,從而發生斷裂與脫節,讓人最終形神俱毀。我能看見這些未來,自然就會有意識地去規避。就像看一場電影,雖激動人心感慨流涕,但終有完結落幕的那一刻。而那一刻,就是清醒突兀地呈現。
這就如同,靜久了我就坐不住,就得起身往外走,去另外的環境與心境中溜達一程。算是調劑,也算是重回了生活。就像家里停電的事,也就兩三天工夫,待得電業工人把那條街上舊的線路給換完了,壁墻里的血管中又會奔流起不息的歡愉。讓人在無盡流浪的光陰中,忘卻諸多原本清新的故事。
責任編輯:趙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