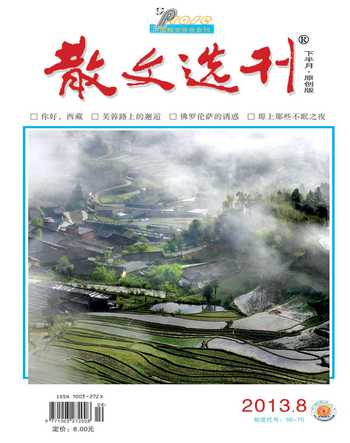我安身立命的幾次考試(外一篇)
盧年初
說安身立命,似乎言重了,那時大學畢業,不用勞神勞力,一紙分配至少能夠解決個溫飽;幾十年過去,一路走來,細風和雨,平淡無奇,也叫阿彌陀佛。然而,離開了學堂,依舊有幾次考試,動人心魄,對我的人生進行了不折不扣地砥礪。
剛開始在師范教書,教的是語文基礎知識,分期分部分教。頭遭相遇的便是語音,也就是普通話。在省城大學里學過,可沒放心上,未使上力,用家鄉話交流也聽得懂,用不著字正腔圓一本正經,委婉動聽似乎是女生的專利,而我們便是怪腔怪調。于是學的只是浮光掠影。而今邁步從頭越,亡羊補牢,為時未晚。跟著錄音機,一字一句念精準;對著鏡子,舌位口形練到位。好在那時的中師生清純,對老師莫名地崇敬,也沒有多少挑刺的,將就著蒙出那種韻味來,便能涉險過關。然而不久,全省的中師老師,要進行普通話的統一考試,力求人人達標。語文科的老師享受著羨慕,我的內心卻起伏跌宕,要求高些不說,若是連其他科老師也考不贏,那就貽笑大方。事實擺在這兒,同行中有幾個基本功要強,畢竟只是筆試,死記硬背即可,要通過這次考試掙一回面子。萬無一失的辦法,便是背字典,凡是弄不清的、有可能出差錯的字全部標出來,特別是邊音和鼻音,卷舌音和平舌音,這是我們容易混淆的“地方病”,要從根子上診治,這樣反復加深印象,直到親近無誤。兩個月以后,考試如期舉行,考完挺滿意,自覺能領先一籌。成績許久才出來,大家的分數似乎差不多,根本沒顯出什么波瀾。原來是我太慎重,初出茅廬的人,對事的輕重往往缺乏掂量。
但是通過這次考試,我的底氣驟然飆升,像進行了拉網式的排查,自認為異常點不多了。何時何地講普通話,不再畏手畏腳,不再自慚形穢,在這行走不遠的小城,以后這便成為了我的一項技能。一個人的技能是你區別于他人的地方,也是你安身立命的本錢。每每遇到一些公眾表達的活動,人家總是覺得非你莫屬,你在這一瞬間燦爛綻放。再以后,我走上領導崗位,作報告用的也是普通話,臺下人等肅然起敬,鴉雀無聲。
1995年春的考試,至少表面上看,于個人發展更有意義。這還得從先年說起。我在教書崗位上干了十多年,工作熟稔之后便生出些閑心,寫了些小文,在全國報刊發表。有朋友推薦去市日報社,干了一陣子,自覺個性與這職業有些距離,便又縮了回來。可一顆動蕩的心縮不回來了,想飛,想看看書本外的世界。這時候,又來了一個機會,學校校長通知我到區里參加一次考試。我有點莫名其妙。校長說,是個綜合部門差寫材料的,想招人;并補充說,他已給通知的人講了,我可能不會去,連市報社都未去的。我怕失去這個機會,連忙說只是去比拼一下,看周邊到底有多少人寫文章比我強。那時許多轉行的人,事情沒眉目時,生怕壞了愛崗敬業的形象。
那次考試是在區委黨校進行的。參考的人大概有五六十,座位自選,一進去我便坐在前排居中的位置,表示旁若無人,不在乎成為大家的焦點。考試就是一篇作文,題目是“生命的價值”。我給學生進行過若干次作文輔導呢,知道怎么去唬住閱卷的老師,開頭便引用一個名言,表示學識廣博,出手不凡。我引用的是笛卡爾的:我思,故我在。至今想來,這句話與后文多大的內在聯系,不得而知。寫到中途,弄出來大致有了底,便伸了伸腰,喝了一口茶,望望后面的一群人,許多人在絞盡腦汁冥思苦想中,額際上汗涔涔的;還有的抽著煙,干脆放棄了。我更自信了些,卻又有些不好意思,許多是學理科的,難怪干澀不暢,這是場不對等的考試。寫完后,還剩下20分鐘,并沒有什么檢查了,卻沒急于交卷,好像是種不地道,如同養精蓄銳的人和拉肚子的人賽跑,落下不算本事,還有點殘酷。
結果出來很快,果然考了個第一。調令卻延緩了一陣,據說中間還有些復雜和蹊蹺。要調部門的領導寬我們的心,不需要多想,不需要找人,等通知便是。就這樣不費吹灰之力,一篇文章解決了調動,而且調到在別人看來是個前途無量的地方。也就是這樣,我開始了機關文字的漫長生涯。許多人不愿干這事,許多人同情干這事的人,辛苦,又沒有權力。但是我懷著一顆感恩的心,沒有寫作,便沒有我的改變;沒有領導的識才,也不會有我的成長。時間更久遠以后,才知公文寫作是做行政工作最好的磨煉,它是工作的鼓動,工作的策劃,工作的催促,它不僅止于機械地動筆,更多的是創意和調度,行文便是為政。事實證明,我后面駕馭工作的順暢,都是源自于這種隱形的訓練。記得那一次考試的稿子存放在辦公室,有一次搞搬家式大掃除時發現了,我們無端的汗顏,有點做賊心虛地作了垃圾處理。和我一同進單位的還有幾個人,后面的發展都較為順利,偶爾憶起那次考試,感慨萬端,仍是掩不住自豪,考著進來的,多么光明正大的門徑!
去年的一次考試是在沒有料想中進行的。五年一次的換屆,許多老同志要退出班子,將老的同志要接上來。我大概屬于后者。前面走了若干程序,我入了圍,但種種跡象表明,結局難以光明。到了幾進尾聲時,突然要進行面試。我揣摩了一下,是否還有轉機?然而只是一閃念,不,沒有了,只是一個程序,也許是誰心血來潮,很多工作做的目的不是為的結果,而是為的說服眾人。于是,我的心里反倒多了份怨意。
考官們大都是些年輕人,大都熟悉,可你一想招呼,他們還擺出一副不認識的架勢,好像會黏糊開后門似的。這叫公事公辦。我們都是些五十左右的人了,上也好,下也好,在這樣的基層,也就那么遠了,經受這么一陣勢,一擺眼,油然生出某種委屈感。我抽到的題目,大概是政府的某個副職不在家,作為同級的你,代替處理某個事件,該如何應對。這有點像公選了,有點像考驗一些年輕者。我們是根據業績推薦上來的,可能任的又是一些閑職,未免小題大做。依我的理解,應該對考察中獲取的情況,進行一點質詢,以便作出正確的結論才是。我的回答有氣無力。
考完之后有些懊惱,不是為考試的發揮問題,而是自己的態度。那些看透世界的人,總是疏于進取,很少意外之喜;那些自以為是的人,總是在既定的答案中陷落。考試更多的是自己對自己。節制,淡定,寬容,是永不落幕的考試。就比方人家的這次面試吧,也許感性一些好,隨意一些好,可評判的標準,又難以操持了。人的年紀一大,就缺乏了被人考核的耐心,而只喜歡指點別人。修煉沒有止境,是因為人生不同的時段,有著不同的雕琢,這與我后來料中的結局無關。
診所
我生病了一般不上醫院。那里花費的時間長,而且喜歡廣泛鋪陳,甚至小題大做,一個部位的問題,會叫許多部位受教育。我喜歡上診所。診所具有親和力,入題也直截了當,有點像而今的家長請家教的范兒,自我,感性。我對自己的身體狀況一向心灰意冷,總是懶于訴說病史和忌諱,而診所以及它的主人,總視你如故交,當你的活檔案,這種心照不宣,似乎帶來的不僅是簡便,而是與人為善。
我這么多年上診所又固定于一家。診所也就是個解決小問題的地方,圖的是熟門熟路,一扎進去,也就再沒有改弦易轍的意思。但診所的醫生卻更換了幾次,我就像個接力棒在他們間傳遞著。附近像我這樣的人還有很多,心甘情愿地讓脈搏抓在他們手里。一個診所是一個區域不能忽視的地方。人是睜著一只眼閉著一只眼活著的,睜著的眼是為那些歡樂滿懷的日子,閉著的眼是為那些愁云密布的日子。別看那只眼是閉著的,其意是少見為妙,一旦有了痛癢,他們找得到去排解的路。
最先接觸的醫生是個單身女人。她的醫術其實并不適合我,是以婦產科見長的。有一次我家屬聊起一個在大醫院上班的同學,她還跟過她的班,這增加了一點關聯。她是那種波瀾不驚的人,長相平淡,為人隨和,容易相處。而我的病也是平淡,一是易感冒,二是腸胃淘神,稍有醫術,也能將就應付。我的腸胃很年輕時就出了問題,胃出血,這樣口服藥物有諸多限制,為了保重,我的做法更左,幾乎有了什么情況,一律用點滴接待。她的視力些微有點近,卻竭力掩蓋,一次性入針的成功率也還高,我也便不戳穿。她用藥很重控制,說用多了不好,容易形成抗藥性。她舉她自己的例子。她的腸胃也糟,卻很少吃藥,只是注意飲食,多熬粥吃,胃病在于養,在于補。我笑道,要都這么著,診所會蕭條。她也笑道,這也好嘛。
有一次給我治病,她可慌了神,一個拉肚子,用了三天藥,沒有轉機。她也不回避,當著我的面,給她哥打電話。她有些自豪,她哥在廣州開得有診所,醫術甚高,賺錢也不賴。她哥在電話里給了一個藥方,果然見效。再次見面,我夸獎了幾句,她的臉分外紅潤,一個有靠山的人,尤其在其露招顯靈之后,那種快樂是多么的敦實啊。
她結過婚的,沒得幾年,不知什么原因離了。她害怕時光的流逝,越老找對象越掉價。我覺得她像得了一個病,再婚的病。前前后后約見過很多,有公務員,有醫生和老師,也有做小老板的,都沒有認真處多久。有一陣子,她告訴我,這回是正兒八經的了,是個年紀略大點的小領導,身體好,薪水也還不錯。偶爾往她那兒路過,還真看到一個嚴肅拘謹的面孔,他們一起小鍋小灶了。但是過了一段,我再去門診,那早成了往事。她還不斷怨我,這么好的朋友了,一個對象也沒介紹過。我只能苦笑,接觸面窄,眼中無貨呢!況且,她有所不知,那全面撒網的策略,在小區產生了不小的反響,都說醫生嘛,總把這方面的事看得很淡。她難得找到屬于她的良藥了。
她后來去了廣州,我以為是給她哥當幫手。不是的,她哥回來接手她的診所。我的惋惜轉變成喜出望外,如同丟了小芝麻,撿了大西瓜。她說把我的情況托付給她哥了。我不明白自己是個包袱還是什么奢侈品。我對她由衷感激。
新的醫生輪廓中可以看到他妹妹的影子,做派卻迥然不同。他斷病是說一不二,不用質疑;用藥如韓信點兵,多多益善。如果不是有以前的先入為主,即那次隔空打穴般的治診,我甚至懷疑他不過是虛張聲勢,以牟利為目的。他很會渲染氣氛,經常宣講在大口岸救治的一些個案,那種眉飛色舞,神乎其神,常會令你為一點小病來就診而大呼慚愧,太委屈他了,殺雞焉用牛刀。
大氣的醫生從來不操持小事。他的愛人白白凈凈的,一張菩薩臉,注射輕描淡寫,柔中帶剛,很受患者贊譽。后來,他的兒子也跟著歷練,做些跑腿打雜的事,據說也是讀過衛校的。這兩個人看他的臉色行事,時不時卻要臭臭他。他喜歡海闊天空,由醫及彼,認為世上的一切都懂得多,尤其扯到政治經濟一些重大領域的事兒,也是如數家珍地擺眼。其他的人聽了心里明鏡似的,卻不道破。只有她娘兒倆敲打說:這水平,這覺悟,可以上北京去了。
在他治診期間,我有了點小職務,些許享受了些格外關照。門面并不寬,卻在屋后隔出個簾子,剛好放得下一張床。每次來吊水,他總會叫我這兒躺下,似乎與外面排排坐的人屬于兩個不同的世界,他說給我用的藥好些,我不反對,領情卻難,藥費也多些嘛。他的忽悠叫人熨帖,比方治感冒吧,把你的癥狀一問,會立馬說:打兩針立竿見影,包管不影響你的工作。過了兩天,效果不顯,他又說:你得注意休息呀,身體是工作的本錢,不然這回的病拖久了。再過兩天,還未絕跡,他便說:干脆在家躺兩天,看單位的工作怎么轉動,不在現場才能弄清哪些人不看你的冷。瞧瞧,他在教我如何做管理,可我是來醫病的呢。
診所的生意比以前紅火許多,社區給頒了一些先進的牌子,人們便想起他的妹妹,問在外闖蕩得怎樣。他說好呀,什么都有了。不知是誰勸他也該過些日子了,該買輛小車,出診也方便。他一直不買,他說,如果真有要上門的,必有車來接。他從不忘記自己是個有層次的醫生。然而有段時間觀念改變了,碰到開車子過去就診的,總要詢問、觸摸一會,看和哪種人買一個檔次的好,而不是重的什么牌子。這大概是三年前的事。車子一買,兩口子便離開了,我這才知道他們過去都是有單位的,而今鄉鎮衛生院又返聘了,便要回去保那個飯碗,他需要往來奔波。他把診所交給了兒子。他很精明,常常抽空來坐一坐,讓人感覺不到他離開,還在坐鎮,還像一件博物館的珍品,依舊神秘地盛開。
我的疾患又由他兒子拿捏了。年輕人的技藝自然有所稚嫩,只是我舍不掉這診所的緣分,舍不掉在他們的親緣中流淌。反正依樣畫符,也無大礙。偶爾年輕人也有茫然失措時,我便寬慰道,該如何如何,好像我成了名醫生。來吊水的人還是有一些,只是熱鬧少了,用假寐打發難耐的時光。來陪診的人等得膩了,會到對面的游戲室打上幾把。也不知是否合規合法,反正時關時開,游戲捉上了迷藏,像病毒在體內的出沒。而左邊是個打字室,挺有名氣的,許多單位忙不過來的,常會把東西拿過來。
我把自己藏得很深,不愿意碰到一些熟人,治病不是件丑事,也不見得榮光。那打字咚咚咚的聲音,從來沒這么清晰過,如同打針;而那些靈光閃耀的字,如同一滴滴肩負重大使命的藥水。
責任編輯:蔣建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