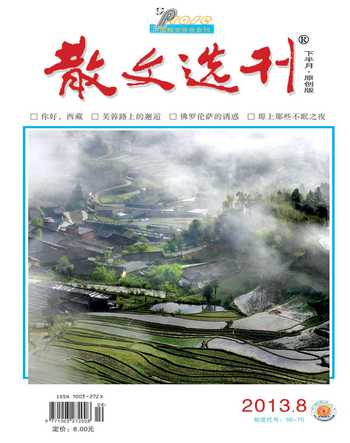病中雜思
因為患輕度靜脈曲張癥,前不久,我住進了上海某醫院,準備動手術治療。雖說,前后只不過五天時間,躺在醫院卻有了諸多念想——
要學會適應。這次住院,是我平生第一次。自然,動手術、掛鹽水也是第一次。第一次住院,我既感到新奇,亦頗感意外。是的,當我辦好入院手續,進入病房時,發現三人一間的病房內,竟無電視機;掀開棉被稍作抖動,棉絮塵便在透進窗戶的陽光下,像“霧霾”又恰似“沙塵暴”般地舞動起來,令我疾首蹙額。接下來的時間,便是無休止的常規檢查,以及拍胸片、做血管造影,等等。一切比我想象中的要煩瑣、復雜,一切讓初來乍到的我因為缺乏心理準備而驟然煩躁起來。“既來之,則安之。看病、養病,需要時間,需要耐心”,隔壁床來自上海崇明的老伯,似乎看出了我內心的不安,笑吟吟地開導我。“我們是來治病的,又不是來享受的。比起家里,肯定有不如意的地方,我與你一起暫且將就著住幾天吧!”妻子又開始“嘮叨”。我一邊打開窗戶,一邊回味老伯和妻子的話,覺得也有些許道理。畢竟,醫院不是療養院,更非娛樂園,既然自己到醫院是來治病的,那么,還有什么比治病更重要的呢?為了治好病,還有什么不可以放下的呢?適應環境,配合治療,本該是患者的職責。否則,一味苛求醫院、醫生而放縱自己,又怎么促進醫患關系的進一步好轉呢?如此一想,我便得以釋然。從此,對于飛舞的灰塵,視而不見;對于半夜的吵鬧聲,聽而不聞;對于醫院提供的飯菜,也不再抱怨;且不再往街上跑,而更愿意靜靜地躺在病床上,或讀書,或聊天,或聽從醫師、護士的召喚。
不要太在乎自己。進入病房不久,主刀醫師就來詢診。仗著一點“特殊關系”,我提出能否第二天就安排手術,可這位主刀醫師直言不諱道:“哪有這么快,人家比你早來還候著呢。輪到你,最早是后天下午吧!”主刀醫師的話,離我原本“當天手術,第二天出院”的預期相差甚遠。于是,我始蔫頭耷腦。此時,靠門口病床的那位剛從寶鋼退休的大哥開腔了:“其實啊,有關系沒關系真的不是很重要。一旦住了院,要說有關系,都有關系;要說沒關系,都沒有關系。”這位大哥的話,雖沒有明說,但意思卻很明白:只要住了院,一切得按規矩行事;只要住了院,醫師對每一個病人都要負責。而其要告訴我的潛臺詞,則分明是“不要太在乎自己”。慢慢的,我想通了,悟徹了。在醫院,我就是一病人,其他什么都不是。既然是病人,就得聽醫師、護士安排。女兒說的話,更是一針見血:“爸,這里又不是小縣城,反正沒有人認識你,你不要太在意自己,該穿病服還是穿病服,頭發亦不必每天洗吹。”女兒的話,果然起了作用。我放下了,變從容了,也輕松了。有一天,趁手術還未進行,我穿著病服,也未作任何打扮,從醫院的角角落落緩緩地走了一遍。確乎沒有碰到任何一個熟人,我看看別人,別人也瞧瞧我,但如同我并不理會別人一樣,別人也只是眨巴一下眼很快就將目光轉移到別人身上去了。唉,我真的不該太在乎自己,要架子干什么。其實,即便是名人也不必糾結于自我,而況我乎。朱德庸說過:“大部分人的名只能流傳三代:你兒子會記得——啊,我爸爸;你的孫子稍微記一下——哦,我爺爺;等到再下一代——誰啊?給他看下照片,放到旁邊馬上就忘了。這就是一個人的名。”說得多耐人尋味。
最能聽到淳樸的真話。記得劉芳菲說過:“小時候我媽和我說的一句話讓我至今難忘:‘醫生這個職業的好處就是:來見你的人,說的都是實話。”是啊,當今社會,假話多、真話少,能夠聽到真話,實屬萬幸。醫院,作為社會一角,或許,就是真話的奇葩園了。不啻是醫師能夠聽到病人的真話,病人之間亦能聽到淳樸的真話,真情的忠告。盡管只是五天短暫的相聚,但是同室三人之間儼然成了病友,大家可謂無事不談,無話不說。記得剛入病房之時,一面帶著行李,一面又要外出吃飯(沒訂飯)。妻子正躊躇于對行李是帶走還是留下之時,隔壁床的病友妻子直率地說:“這么重的行李,不必隨身帶了,我們會給你們看管好的,你們放心去好了。”聽罷,竟感動得我們無語凝噎。而半天待下來后,三人的話題似乎更為寬泛,大家從孩子、房子、票子等家事,一直談到國事、天下事。期間,各個不偽飾,不虛妄,不做作,更沒有官話、套話。可不是?那位從崇明來的大伯,雖長期憂患于嚴重的靜脈曲張癥,但說到如今先進的治療手段,以及農村的醫療保險,他笑得合不攏嘴。而那位從寶鋼退休的大哥,既為自己曾在設計單位的高工資、高獎金而欣喜,也替單位與寶鋼合并后減了收入而嘆息;既慶幸于自己十多年前購入的兩間新房價格已然翻番,亦嘆息于當今大上海房價的居高不下。雖說,病友間反映的只是個人的喜怒哀樂,但表露的卻是一種真性情:感謝亦希望政府為民惠民,因為中國夢首先就是人民群眾的全面小康夢。
幸福就是一種心情。有人懷疑,住在醫院還能感悟幸福?是的,同室的我們三位病友,家境都還可以。于是,似乎更有本錢來談幸福。我曾經寫過文章,對于幸福的理解是:在吃、穿、住基本保障的前提下,幸福就是一種心情。那位大哥,說起兒子兒媳叫其賣了空置的房子,多去外地旅游,享受快樂的退休生活時,他覺得自己正享受幸福;那位大伯,動好手術的當晚,女婿竟坐了一個晚上陪護他,第二天他贊不絕口,滿臉的幸福。我似乎也沉醉在這般幸福之中。雖說,只是極小的一次手術,但妻子特地請年休假陪我,家人不時的電話問候,女兒和準女婿的多次探望,單位領導、同事和朋友的慰問,莫不令我感到慰藉。親情、友情,讓我剎地感覺她像一位中醫,用敏感而溫熱的指尖感觸著我的脈搏和心跳,甚至內心;有時,感覺她又像一位魔術師,輕輕拂去人世的凡塵,讓云霧散去,引來陽光雨露……而最讓我感動的,則是病房的護理員們了。這些護理員阿姨年齡都在45歲以上,平日里,她們一個人要負責三間病房九個病人的二級護理,且必須做到24小時隨叫隨到。之后,我了解到她們每天只能睡四五個小時左右,每年也只能休息幾天,且月工資只有兩千多一點。問之:“累嗎?這點工資怎么補貼家用呀?”答曰:“身累心不累,工資雖然低了點,但孩子工作了,沒有多大負擔。特別看到你們病人康復后一個個出院,我們高興著呢!”一番動人的話語,飽蘸著阿姨們對“幸福就是一種心情”的獨到的理解與感悟。難怪,我住院的五天里,總能見到她們為病人服務時老是漾著一臉的笑容。“這個特殊崗位,其他人想進來還進不來呢!”她們珍惜自己的崗位,她們美麗著,更幸福著。
做任何事情都是要付出代價的。不管你信不信,這是一條規律。聽醫師說,患靜脈曲張癥,是一種職業病,多發生在農村地區,以及教師、醫生、舞蹈演員、營業員身上。大熱天大汗淋漓時的冷水浴,長期的站立或久坐,經常的咳嗽,等等,都是患病的誘因。想起自己從小寄養在農村,洗冷水浴是家常便飯;返回城里利用寒暑假打工,經常干挑水、抬石等重活,兼以做糧食助征、軋棉花、打箱(機械廠翻砂車間一種取澆鑄件的活兒)時受到灰塵和特別氣味的刺激,令自己常常咳嗽不止;以后又做教師和公務員,以及利用業余時間長期伏案寫作,似乎要遠離靜脈曲張實在很難。盡管做事情是要付出代價的,但回想起來, 覺得終究是利大于弊、得大于失。曾經的特殊經歷,畢竟是一種無可替代的人生閱歷;500多萬字的作品,畢竟是自己智慧和心血的結晶。以輕度的靜脈曲張換取上述結果,我值,我賺了。而況,知道了病因,以后學會與病患周旋妥協,并盡可能提防它避開它,自可以將病患帶來的損害降到最低點。然而,尤須告誡自己和別人的是,《2010國民體質監測公報》提醒我們——“再不健身,我們都老了。”報告稱,工作中的體力活動大幅度減少,再加上攝入的能量提高,工作繁忙等因素,導致成年人的身體素質每況愈下,未老先衰。學會與病魔斗爭得講藝術,“打鐵尚須自身硬”,只有自己把身體鍛煉好了,搞強壯了,病魔才無從下手,我們也才有可能征服它。
每一天都帶來新的希望。始料未及的是,做靜脈曲張手術,竟要全身麻醉。我知道全身麻醉會有一定的風險,但我不懼。麻醉前,我格外的鎮靜。麻醉三個小時醒來后,我對自己開玩笑說:“沒事,我還活著,只要活著,就有希望。”這種“希望”心理,碰逢每天晨曦初露時更讓我膨脹發酵。不是嗎?我躺在靠窗的病床上,每天早晨的第一縷陽光,透過窗外的高樓大廈,溫煦地映入我的睡眼。它似勤勉的信使,正向我們傳遞希望的信息:“又是新的一天,一切皆在康復之中。”真得感謝醫術精湛的醫師們,手術過后的第二天,我們就能下床,過三四天就能出院,差不多一個月就能痊愈了。于是,油然想及:人生無常,誰都會碰到這樣那樣的磨難和挫折。有磨難有挫折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在磨難中消沉,在挫折中躺下。誰能把磨難和挫折當做財富、視作機遇,與之搏擊,并戰勝它,駕馭它,誰就能擁有希望、擁有明天、擁有未來——因為每一次的磨難,都孕育著堅韌的品質、機敏的智慧;每一次的挫折,都埋下了檢視、反思與超越的伏筆。是的,抓住每一天,過好每一天,就是希望所在。誠如白巖松所言:“生命中有一個很奇妙的邏輯,如果你真的過好了每一天,明天就會不錯。”有一次,當我躺在病床上注視著鹽水一滴一滴往下走時,我想起了“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之言,深感時間飛馳。于是,暗下決心,出院后,我得將損失的時間奪回來。平日忙于事務,難得靜下心來去思考點什么,居然這次小手術的機會,成全了我對一些人生問題的思考。
朱自清先生曾經感慨:“過去的日子如輕煙,被微風吹散了,如薄霧,被初陽蒸融了;我留著些什么痕跡呢?我何曾留著像游絲樣的痕跡呢?”在這個世上,我總覺得自己該留下一些痕跡,哪怕是輕煙薄霧和游絲,這大抵便是我動筆寫就這篇《病中雜思》的緣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