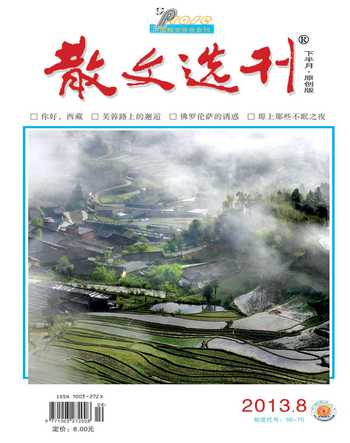酸楚的叮囑
賀小林
隨著年歲的增長,有關死亡的消息聽得越來越多。
在老家生活時,我家門前是一條村莊的主干道,村上每有老人死去,都會用門板抬著經過我家門前放到宗祠里去,在祠堂開完追悼會后,又會經過我家門前把壽木扛到山上埋葬。那時,母親就會在門口點燃一把稻草,再在稻草上堆放一層厚厚的糠,說是這樣會讓燃起的黑煙阻止鬼魂的進入。來到城市生活后,面對死亡更多的是在車禍現場。我原先居住的地方前面是一個十字路口,每年都會有四五個人因車禍在此喪生。死者親屬悲痛欲絕的場面看多了,心也脆弱了許多,總感覺到生命是這般的脆弱,脆弱得不堪一擊。這些所見所聞讓我對生老病死的概念有了更深的理解,生是我們在這個世界經歷的過程,死是每個人必然的歸宿。如此想來,對于生我們要活得坦然,而對于死亡要理解這是人生的必然。只是我以為活著就要好好地活著,這樣死去才會不留遺憾。比如,我們無法挽留身邊的親人永遠跟我們生活一起,他們必然都會一一離我們而去。我們也不會一直與自己的兒孫相處,這種擬定的離別定然無奈。檢點人生的時光本就短暫,和諧地活著是對于生命最好的交代。蠅頭小利不能誘惑我們偏離贍養父母的軌道,煩人小事更不能成為我們不和諧的理由。
這段時間,我一直心情抑郁,是因為關于死亡的思考多了,是因為離去的親人和朋友多了。站在蒼茫的大地上,我顯得十分孤單,感觸是透骨的凄涼。我的一生守寡,愛盡苦難的老姑孤獨地抵達人生的終點,我的一輩子都沒有回過娘家的祖母靜靜地躺在床上無疾而終,我的一個要好的朋友因情感受挫而服毒自殺,我的一個曾經的同事在新婚不久,在剛剛為人父時被病魔吞噬生命,我的一個兒時伙伴在去打工的路途命喪車輪,我的一個學生在極度自卑的陰影中用繩索結束了生命,我的一個遠方親戚在烈日下發暈跌落30余米高的腳手架,我老家的一個長輩因腦溢血突發正在等待死亡的來臨,我朋友剛出生的小孩子因早產還處在危險期……
顯然,我是開心不起來的,但我依然堅強,堅強地聆聽每個痛苦的聲音,堅強地面對這一次又一次的不幸,堅強地經歷人生的每一個困苦的過程。時光不會停止。還有很多跟我有關的人會一一離去。我能哭泣嗎?面對這既定的事實,哭泣只能是極其無助的表現。我不悲傷又能怎樣?這撕心裂肺、不再相聚的分離相對于親情洋溢的我們而言是無可更改的軌跡。
前段時間,我回到老家,母親拉家常似的跟我說起了村里的一些人和事。隔壁的張大娘死了,死因是她不滿她的兩個兒子兒媳之間無休止的爭吵,喝了一瓶農藥死在后山上,一個放牛的老漢聞到惡臭才發現,找到時尸體已高度腐爛。村口的劉大爺在梅雨時節被雷電擊中,一個人死在了陰暗破舊的老屋里,死時他手里還握著一把火鉗子……
我有些傷感,著實也不愿聽,而母親又自顧自地講開了,講得很平靜很緩和,像無風的湖面沒有波紋,像屋檐滴落的雨水始終是一個聲音。屋前李大嬸的兒子在一次搭乘別人的摩托時被甩下了車,后腦被路旁一根尖銳的茶樹枝穿過,還沒到醫院就沒救了。李大嬸的兒子因還沒有成年,屬于斷命鬼,是不能安葬的,尸體被推到火葬場燒了,骨灰倒在了縣城的禾水河里。居住在后山腳下的龍小慶被人殺死在家里,鮮血流出了門檻,派出所的人員調查了好久也沒有抓到兇手。聽說是龍小慶在家里搞別人的老婆,被別人用屠刀劈死的,刀落在屁股上,把屁股劈成了兩半。說完這些,父親又補充了一句,告訴我隔壁村的老舅昨天死了,他去悼念過了,送了50元祭禮,順路又去看望了居住在同一個村已是癌癥晚期的我的堂伯父,也給了50元錢作為慰問。父親說這些時也很平和,不帶任何的感情色彩,儼然在背誦一些枯燥的阿拉伯數字,從他臉上尋找不出任何的喜怒哀樂。
我發現人至暮年后的父母更喜歡跟我說起死亡的話題,喜歡嘮叨著身邊一些故去的人的名字和他們的事情。他們會時常叮囑我要為他們畫好遺像,買好壽木,制好壽衣壽鞋。他們經常說人過60就不是自己主宰生命了,而是上天主宰著自己。他們會驚奇于身上的每一個病痛,會恐懼于每一條有關死亡消息的報道。飯量減了,他們會懷疑是有病魔纏身,骨骼疼了,他們會不厭其煩地尋找原因。
父母的這些行為舉止讓我很是心疼。這是給予我生命的父母對于死亡的理解,這是撫養我成人的爹娘極其無助的掙扎,這是用牙縫里節儉出的錢供我讀完大學的雙親對于生的留戀……我是無法挽留父母的,我知道父母終有一天會離我而去,離我的兒子而去,離他們所有的親人而去,像枯葉一般飄零而去,像流水一樣一去不回,像一縷青煙搖曳在藍天直至不見蹤影。
父母交代的這些事,我很不愿去做,是出自內心深處的不愿。而我又不能不去做,我怕父母難過傷心,我也看不得父母難過傷心。我還必須很積極,我知道不然父母會誤解我的拖拉,這樣就會讓父母滋生許多無端的指責;我著實又不愿父母不開心,希望他們一直開開心心地走完人生道路上剩余的部分。
我不是父母的長子,我還有兩個哥哥,一個妹妹,對于同一個父母而言,他們都是父母的牽掛,他們同樣也是最牽掛父母的人。對于辦理父母百年終老以后的事,我自然不能自作主張。與兩個哥哥商量時,父母就在一旁,似乎是在恭候他們的兒女為他們安排后事。父母都很平靜,偶爾還會插些話,以發表自己的意見。比如他們會告訴我們壽木要現做的,油漆在用時再刷,這樣才新,遺像還是用瓷板烤制,這樣耐用又耐看,遺像上要把所有兒孫的名字都刻上去,母親還特意點到了我剛剛出生的一對雙胞胎兒女的名字。她說,遺像一般都是在六十歲繪制,如今已是六十有三了,本來早就要制作,就是在等待我兒女的降生,這也是她一直催著我結婚生子的原因所在。如今,兒孫都齊了,他們也沒有過多的憾事,等著終老的心也很坦然……
父母說這些時,我們都很難過,難過得淚流滿面,似乎是在聆聽雙親的臨終遺言,似乎臨近的就是一場生離死別。
責任編輯:趙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