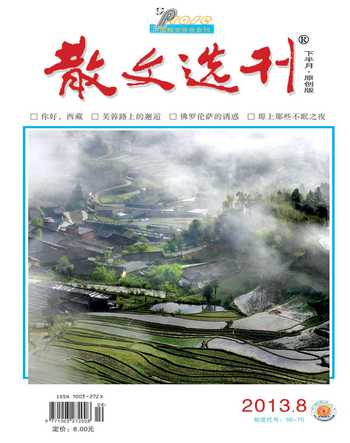兵娘
吉方君
一
高中畢業后,我不顧家人反對,放棄在公社黨委辦公室的工作機會,投軍入伍去了“天涯海角”。
我是家中的三代獨子。按當時公社的規定,獨子,尤其是像我這樣的三代獨子,是決然不能報名參軍的。因為在公社領導身邊當差,“有話好說”,加之父親找武裝部長說情,加之我身體倍棒,體檢輕松過關,才成了那屆入伍青年中的一個特例,圓了男兒當兵夢。
到連隊后,我才知道自己并不是沒有思念和牽掛。當時,家里有三位親人:祖父、祖母和父親。生母在我還躺在襁褓中嗷嗷待哺的時候,就跟父親離了婚,我是在祖父、祖母和父親的懷抱里度過的童年。我最思念的親人當然是祖母,是她給了我人世間最崇高的母愛。可是祖母患有嚴重的支氣管哮喘,年邁體弱,身體極差。雖然如此,她還撐著病弱的身體操持家務。當時父親和祖父都是生產隊的“主勞力”,甭說白天請假,甚至還要夜里出工。因為只有多掙“工分”,才有“口糧”,不至餓飯。我父親曾兩天兩夜,一人割了全鄉最大的一塊田——八斗丘,并且連割兩季,因此被評為勞動模范,出席全縣群英會。這個家,多么需要一個身強力壯的家庭主婦啊!
似乎是冥冥之中的前世之約,我入伍次年,經二叔母介紹,我的母親——當然是繼母,悄然來到父親身邊。這年她45歲,正值人生盛年。
父親在信中介紹了母親的情況。她叫王艷蘭,本縣劉河鎮黃坪村王院人,有過兩次失敗的婚姻,父母雙亡,沒有兄弟姐妹,無兒無女。二叔母后來告訴我說,母親初來時,我祖母正臥在床上痛苦地呻吟——老人已經病危。常言道,一人得病,全家不安。當時家里的氣氛確是有些凝重和凄涼。二叔母很是擔心母親害怕和嫌棄,轉身離去。因為當時,她完全可以選擇另外一戶。那戶人家是干部,生活條件我家沒法比。
但是,母親義無反顧地選擇了留下。
母親是操持家務的一把好手。上山砍柴,下地種菜,捕魚撈蝦,洗衣做飯,還時不時地幫村里去世的人洗臉擦身穿衣戴帽料理后事,讓村人刮目相看。“兵娘”的名字,很快在全村叫響。
祖母逝世的第二年,我回家探親,第一次見到父親在信中反復提到、被村人稱為“兵娘”的母親。
二
參軍后的第五個年頭,我退伍還鄉,接過父親曾經執過的教鞭,成了村小學的“孩子王”。
村小學建在一座小山坡上,離家不遠。站在學校門前的山坡上,可以看到望南坡下老蔡院裊裊升起的炊煙。
那一年,我23歲,在部隊,我是連里的軍訓尖子,是基地小有名氣的“秀才”。
退伍這年,遠在黃石的生母想把我弄到她身邊工作。繼父是抗美援朝老兵,退伍后到大冶鋼廠當工人。得知生母想法,熱心的繼父自告奮勇,去找他在公安局和人武部擔任要職的老戰友幫忙,接二連三給我所在部隊寄來了接收信函。生母來信說,接收手續都辦好了,我一退伍,便可去市局當刑警。生母雖然沒有跟我一起生活,卻對我的秉性了如指掌。那時,我確是對當“和平兵”有些厭意。而去市局當刑警,真槍實彈,抓捕罪犯,實在太有誘惑力了。于是這年底,在老兵們都惴惴不安害怕退伍的當口,我竟主動向連里打起了退伍報告。這樣一來,我出任司令部宣傳干事的事泡湯了,“去市局當刑警”化為泡影,最后,我竟然成了一介“教書匠”。巨大的心理落差,讓我陷入迷茫。
初到學校,我脾氣十分火爆,曾當著全校教師的面拍桌子罵校長,臭脾氣傳遍全鄉,就連當時的文教站長都知道我是“大王”。那年頭,農村基礎教育是“分級辦學、分級管理”,村辦小學是民辦教師挑大梁。他們承擔著與公辦教師相同甚至更為繁重的教學任務,但工資待遇不及公辦教師的五分之一,而且隨時可能被村干部以種種借口辭退。為了保“飯碗”,民辦教師們都盼著“轉正”,即轉為公辦教師。“轉正”要經過文化考試。因為涉及“飯碗”,考試極其嚴格,而且三五年才有一次。雖然家在本村,但全體教師都在學校“住教”,一到夜晚,老師們都關門閉戶,挑燈夜戰復習功課,以備幾年一次的“轉正考試”。
而我,全然不把復習備考放在心上,因為我壓根兒就沒打算“轉正”。到校很長一段時間,我不在校“住教”。每天下午放學后,我要么回家在竹林里打沙袋子,要么拿著漁網去水庫捕魚,把個校長氣得七竅生煙,幾次找文教站長要撂挑子。他對站長說:“這個退伍兵太不像話,我說也說不過,打也打不贏,這個校長我實在沒法干了!”不久,這個校長真的調走了。
學校來了新校長。
新校長是本村人,也是全鄉第一個“考試轉正”的民辦教師。他“轉正”以后調到縣城中心小學當校長,被樹為全省教育系統的勞動模范。他后來告訴我說,他主動請纓回本村小學當校長,就是為了“收拾”我的,他說他都做好了挨打的準備。
新校長到校不久,對新教師也就是我搞了一次“業務考試”,理由是“凡進必考”,其實是要給我一個難看。校長揚著一份試卷說:“這是小學畢業班的期末數學試卷,你做一下。”我是縣一中的高中生,雖然在校偏科,數學不是很好,但小學數學豈能攔得了我?我輕蔑一笑,沒說什么,提筆應試。但是當我展開試卷以后,才知自己的知識貧乏到了什么程度。考試結果,我只得了14分!
面對考試成績,我突然覺得自己一無是處。在部隊,我參加高考都不止這個成績,怎么才過幾年就荒廢成了這樣?就我現在這種水平,也好意思牛皮哄哄頂校長,也好意思在課堂上指手畫腳訓學生?
這天下午放學后,我沒像往常一樣回家,而是在學校宿舍里坐著發呆。
當橘紅的夕陽將要沉入望南坡的時候,宿舍的門“吱呀”一聲開了。我抬頭一看,是校長。校長說:“你母親送被子來了。”
我一時不知說什么好,站起身,愣愣地看著母親為我掛蚊帳,墊棉絮,鋪被單。
校長走后,母親小聲說:“校長說了,只要安下心來,好好復習,你肯定考得好。再說住教是學校制度,一人不拗眾……”
我默默地點了點頭。
這是一床印有大紅牡丹圖案的被單,我在那間四面透風的宿舍里睡了10年。
三
“轉正”后的第四年,我被調到了縣教委,妻兒也隨之進城。而已步入暮年的母親,依然與父親生活在我的出生地,仍然保持著他們往日的生活節奏,早出晚歸,披星戴月,勤扒苦做。
早在小女出世時,已經破舊的紅被單讓母親換下,從此沒有再用。但我后來發現這床打有補丁的被單,鋪在母親床上。我“轉正”后,特意囑咐妻子為母親買了兩床新被單。
有年我和妻子回家趕母親的生日,恰巧幾位朋友也去了。大家走進母親的房間,噓寒問暖。談笑聲中,我無意間看到母親床上仍然鋪著我曾用過的那床被單。被面上,又新增了不少補丁。
客人走后,我責備母親說:“家里不是還有新被單嗎?這么破舊的東西還鋪在床上,讓人看了多不好!”
站在一旁的父親聽我這樣說,有些生氣:“我看你是忘了本了!老話說新三年,舊三年,縫縫補補又三年。這床被單你在學校睡得,現在我們睡就丟你的人了?”
母親卻說:“伢兒說得對!這床被單確實太破,好人好客,實在丟人,以后不用了!”又說,“我做鞋底正缺布料,這床被單正好派上用場!”
后來我每次回家,父母床上果然沒有再鋪這床被單。我想,那床被單肯定是讓母親做鞋用了。
8年前的那個秋天,我經歷了“從政”后的首次挫折,“拍桌子罵校長”的場面再次上演。機關非學校,人際關系復雜,原本稱兄道弟的人趁機離間,落井下石,讓我一時倍感凄涼。
就在這當口,國慶節后的第六天,從老家傳來母親中風的消息。一時間,我的屈辱化為泡影,心里只有四個字:“救治母親!”我急速趕回家中,發現母親躺在床上不省人事。父親拄著棍子,坐在床前直抹眼淚。
危急時刻,我突然有了母親曾經有過的鎮定,迅速叫來了村里的醫生和鄰村的郎中進行會診,很快診斷出了母親的中風系“腦梗死”所致,當即采取中西結合的辦法,西醫輸液和中醫針灸同時進行。經過兩個多月的中西治療,昏迷半個多月的母親竟然神奇生還,康復如初。
那段日子里,“救治母親”給了我前所未有的力量。為母親求醫問藥、病床看護、換洗尿布,替父親分擔憂傷,幫妻子忙里忙外,讓我找到了自己的價值。
經歷了那場劫難,一家人把母親看得更重了。她是“兩世人”。能活著,就是奇跡;能與父親相依為命,就是幸福。
前年六月,父親去世。料理好父親后事,我想把母親接到縣城,她沒有同意。
四
大年初二,母親起床后暈倒,手被摔破的電視機劃傷。在此情況下,我和妻子不由分說,硬是將她從鄉下接到縣城。我本想在她的有生之年,好好孝敬她,卻沒想到老人僅在城里住了40天,就去世了。
母親逝世后,我和妻子清理老人遺物,發現先前買給她的新衣服、新被子和新鞋等物,都原封未動地放在箱子里。在箱子的底層,我們找到了那床打滿補丁的被單。
這正是母親當年鋪在我學校宿舍里的大紅牡丹被單。這床被單,綴滿了母親的一針一線。大小不一、顏色各異的補丁,補了一層又一層,占去了大半個被面。正是這床綴滿補丁的被單,曾經撫平了我的青春叛逆,鼓勵著我年復一年挑燈夜讀,見證了我的命運轉機……
我天國里的兵娘啊!
責任編輯:趙波
美術插圖:段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