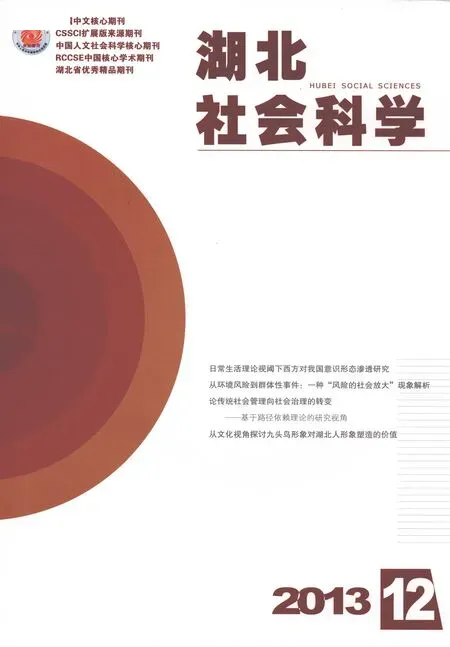淺議主體間性理論視域中思想政治教育過程的重構
史宏波,侯士兵
(上海交通大學學生工作指導委員會,上海 200240)
▲思想政治工作研究
淺議主體間性理論視域中思想政治教育過程的重構
史宏波,侯士兵
(上海交通大學學生工作指導委員會,上海 200240)
思想政治教育主體間性把交往作為自己的生成機制,并將交往引入思想政治教育過程,有利于從本質上更全面、更真實地理解思想政治教育過程及其特性。主體間性要求思想政治教育過程必須是一種“主體—客體—主體”交往實踐過程。在思想政治教育過程中,受教育者既是占有教育內容的主體,具有主體性;又是與教育者交往的主體,具有主體間性。
主體性;主體間性;思想政治教育過程;重構
以主體間性理論審視思想政治教育過程,必然要求在思想政治教育過程中賦予教育者與受教育者雙主體的地位,要克服傳統觀念中以教育者為中心,視受教育者為純粹客體所帶來的各種問題和局限,使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在思想政治教育的交往過程中形成主體間關系,并由此衍生出主體間的相互規定、相互生成。
一、思想政治教育主體間性的內涵
“主體間性理論的繁榮主要肇始于胡塞爾倡導的現象學運動,后繼的哲學解釋學的興起和社會交往理論的廣泛傳播,使對他者、交往共同體的理解成為哲學重要的課題,主體間性問題由此成為現代西方哲學的顯學。”[1]主體間性理論既是現代西方主體性哲學面對人類特定歷史境遇,深刻反思單向性的主客關系的工具合理性取向及其消極影響的必然結果,也是當時解決種種社會尖銳沖突的理論訴求。關于“主體間性”的界定和理解,不同的哲學流派從不同層面和維度進行過研究,對我們理解思想政治教育主體間性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胡塞爾的主體間性理論為了解決主體之間構造世界的交互性,涉及了主體之間對于客體的關系問題。他認為“他人”的存在通過移情和共界作為“大家的世界來構造”[2](p900),因此,“我”和“他人”就有了可以共同知覺的“對象”和“客觀性”。胡塞爾力圖通過建構主體間性走出“唯我論”的困境,但問題在于他無視人類賴以生存的客觀世界和實踐活動,把主體間性僅僅局限于人的認識和精神世界,在本質上還是先驗主義和唯我論的。伽達默爾本體論的哲學解釋學體系,批判了現象學的先驗唯心論,認為主體間應通過對話達成主體雙方的“視閾融合”,非常強調主體間的溝通和理解,推進了人們對主體間性理論的進一步理解。馬丁·布伯力圖超越傳統認識論哲學中的主體性原則,構建一種“我—你”關系的主體間對話模式,破除對話中“我”的單一主體地位,肯定主體間關系的實在性和先在性。布伯以主體間關系本身來直接構筑主體間關系模式,“是對主體間性理論的重大發展,也標志著當代西方主體間性理論開始走向成熟”。[1]但是,布伯的這種關系模式存在著明顯的缺陷,即在肯定“我—你”主體間關系的同時,完全無視“我—他”主—客體關系的存在。隨著主體間性理論探討的不斷深入,雅斯貝爾斯首先將交往引入了主體間性理論,認為“如果存在的交往成為現實的話,人就能通過教育既理解他人和歷史,也理解自己和現實,就不會成為別人意志的工具。”[3](p2-3)然而,他卻不懂得交往只能是實踐中的交往,離開實踐,何談交往。以“交往行為理論”著稱的哈貝馬斯將主體間性問題作為一個突出的社會歷史問題進行了頗為深入的研究,力圖從歷史和現實的角度解決主體交往的意義和合理交往的可能性條件。他指出,理性在現代社會中一個最大的病變形態就是走上了工具化道路,要克服人類社會目前面臨的種種危機,就要以“交往理性”代替“工具理性”,認為“交往行為的目標是導向某種認同。認同歸于相互理解、共享知識、彼此信任、兩相符合的主觀際相互依存。”[4](p3)其實質是理性由以“主體”為中心轉變為以“主體間性”為中心。哈貝馬斯試圖通過商談倫理學賦予不同主體在交往中同樣平等的地位,但卻因為忽視人的現實生產實踐和交往實踐而成為一種空談。
綜上所述,近代西方哲學因其先天的缺陷并不能從根本上建立合理的主體間性。我們的任務在于以發展著的馬克主義為指導,取其科學合理的內核為我所用。主體間性的理論價值首先在于科學區分主主關系與主客關系的不同性質,對主體性進行更為全面的理解。其次在于這一理論提供了解決對象化活動弊端的全新視角和思維方式。受主客二分思維方式的深刻影響,人們不自覺地會將思想政治教育實踐作為一種對象化活動,用主客體理論進行指導,把受教育者作為欲加改造的對象,強調思想政治教育是教育者對受教育者施加可控性影響的對象化活動,教育者與受教育者的關系是一種主體與客體的對象性關系。以對象化活動處理教育者與被教育者之間的關系,結果在實踐中把教育者與受教育者原本“人與人”(主—主)的關系當作“人與物”(主—客)的關系處理,受教育者成了被訓練、塑造、利用的客體,降低甚或遮蔽了受教育者作為主體的地位和價值。要消除對象化活動的這種弊端,就要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徹底厘清教育者與受教育者的關系,進而探索改變思想政治教育目前困境的良策。
筆者認為,思想政治教育主體間性主要是指建立在交往實踐基礎之上的、以教育內容為共同客體,教育者與受教育者在思想政治教育過程中相互生成的交互主體性。思想政治教育主體間性絕無厚此薄彼的特性,它反對一方主體性的發揮是以另一方作為客體為代價的,它內在地規定教育者與受教育者之間應是“主體—主體”與“主體—客體”雙重關系統一構成的以共同客體(教育內容)為中介的“主體—客體—主體”關系的有機統一。因而可見,“主體間性實際上是人的主體性在主體間的延伸,它在本質上仍然是一種全面、真實的主體性。提出思想政治教育主體間性思想,并不是簡單地對思想政治教育主體性的更新替代,而是一種傳統教育觀念的變革,是對思想政治教育主體性的揚棄。”[5]
二、思想政治教育主體間性的生成機制
思想政治教育主體間性是在教育者與受教育者的交往中得以體現的,交往是主體間性的生成機制,離開了交往,就無法理解主體間性,所有的實踐活動都無從啟動和展開。主體間性的思想政治教育,必然要把交往引入思想政治教育的全過程,并以其作為思想政治教育過程展開的起點。
思想政治教育作為一種特殊的實踐活動,教育過程總是與實踐觀密切相連。長期以來,受對象化實踐觀的影響,人們對思想政治教育的認識大多都停留在“對象化活動”上。對象化活動的長處在于處理人與自然、人與物的關系,而不是處理人與人的關系。對象化活動反映的是一種單向的“占有”關系,是單一的主體對客體的單向占有。因此,在對象化活動中生成的主體性是單向的,是帶有明顯占有性質的個人主體性,具有強烈的不平等性。在思想政治教育過程中,受教育者(即客體)是教育者(主體)認識和施加可控性影響,并予以訓練、改造的對象,這既是對象化實踐觀的一個明顯缺陷,也是思想政治教育廣受詬病的一個重要原因。即便是后來有人為了克服傳統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二分的弊端提出了“雙主體論”、“主導主體說”,雖然對優化思想政治教育過程提出了有益的探索,但從根本上說,這些討論依然沒有走出傳統理論的泥淖,沒有從理論上予以受教育者應有的主體地位。無論其如何推演,教育者主體性的發揮依然是以受教育者作為客體為代價的。可見,“對象化活動”的實踐觀支配下的主體性思想政治教育既無力突破主體的封閉性,也不可能找到實現主體間性思想政治教育的邏輯起點。
主體間性既離不開交往又通過交往來實現。交往具有鮮明的社會屬性,它反映的不是主體—客體關系,交往的任一方都是主體,他們是平等、共生的關系,在精神和物質上彼此規定、共生,創造、塑造著彼此間的關系,最終實現共同生長。交往作為人類不可缺少的實踐活動,具有特殊復雜的關系結構,其既包含人與人關系的“主—主”關系結構,又包含人與自然、人與物的“主—客”關系結構。但它又不是“主—主”和“主—客”的簡單連接,而且以交往雙方共同占有的客體物為共同客體的“主—客—主”關系的有機結合和內在統一。“任何單一主體對客體的改造,即‘主體—客體’關系,都不過是‘主體—客體—主體’結構的一個片斷和環節;主體在作用客體的同時就載負并實現著‘主體—主體’交往關系,并受其牽引和制約”。[6](p57)表現在思想政治教育過程中,就是有別于既往“教育者(主體)—受教育者(客體)”單一關系結構的“教育者(主體)—教育內容(客體)—受教育者(主體)”交互關系結構,從根本上改變了受教育者的從屬地位。
對象化的思想政治教育,把教育過程中本該是“主與主”之間的關系,當作“主與客”的關系來處理,從而扭曲、錯亂了教育過程中受教育者的地位,使受教育者總是成為教育者施加可控性影響并予以塑造、改造的對象,而湮滅了受教育者本應有的主體地位。從“對象化活動”到“交往”的轉變,其意義在于還思想政治教育過程中教育者與受教育者雙方關系的本來面目,使教育過程成為教育者與受教育者之間、受教育者與受教育者之間交往、共生的過程。在此過程中摒棄不平等的教育者與受教育者之間的主客關系而走向彼此共生的主體間關系,生成主體間性。也只有主體間的生成、發展才能使在交往中教育者和受教育者都成為真正的主體。因此,思想政治教育主體間性對主體性的揚棄,進而以“主體—客體—主體”的關系重構“主體—客體”關系,不只是教育者與受教育者之間關系和地位的變革,更主要的是,它使思想政治教育過程真正成為教育者與受教育者心靈交融的過程,成為彼此規定、互相生長的過程。
三、受教育者在思想政治教育過程中的主體性和主體間性
依據思想政治教育主體間性的理解,思想政治教育過程的三個核心要素構成了“主體—客體—主體”關系結構。此結構中,受教育者作為主體的地位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與教育內容構成“主—客”關系,成為占有教育內容的主體;二是與教育者構成“主—主”關系,成為與教育者具有平等地位的主體。但受教育者作為兩種關系中的主體,有著根本不同的性質,需要我們予以說明,前者體現的是受教育者的主體性,后者體現的受教育者的主體間性。
(一)受教育者在思想政治教育過程中的主體性。
主體性(Subjectivity)是主體在對象性活動中,運用自身本質力量,能動地作用于客體的特性,是人的自覺能動性。很顯然,在教育內容面前,受教育者是理所當然的主體,教育內容是受教育者認識、占有和消化的對象,即客體。教育者在思想政治教育過程中始終起主導作用,引導受教育者樹立與社會發展需要相適應的思想道德素質。但思想道德素質的形成不可能也不應該靠教育者生硬地“灌注”,必須依靠受教育者的自我生成、自我生長、自主建構,因為任何外界影響因素都必須通過人的內因起作用,人的思想品德是在客觀外界條件的影響下與主觀內部因素相互作用的積極活動中,主體接受外界的各種刺激影響,通過主體自身的作用,逐漸形成和發展的。此時,受教育者的主體性主要表現為對教育內容認識、占有和消化的自主性、能動性和創造性。
第一,自主性。自主性是受教育者成為主體的前提。在思想政治教育過程中,教育者是一定社會要求的表達者,是思想政治教育活動的組織者,在教育過程中起主導作用;而受教育者是有著主觀能動性的發展著的人,他們在教育過程中不是機械、僵化地接受教育影響,而是在教育影響下不斷自主地進行著自我教育、自我建構。受教育者不再是教育者占有、支配的對象,而是一個個能夠自我教育、自我建構的個體。當然,受教育者的自主離不開教育者的引導,離開了教育者的教育引導,就談不上思想政治教育過程,受教育者思想政治素質的發展就是自發的甚至是盲目的。
第二,能動性。思想政治教育過程是教育者與受教育者雙方彼此規定、相互生長的有目的的實踐過程,無論離開了哪一方,教育過程都不可能成為完整的過程。而且,教育者主導作用的發揮是以受教育者主體能動性為基礎和前提的。沒有受教育者發揮主觀能動性予以配合和接受,無論教育者主體性如何強勢,其施加的教育影響都不可能產生效果,有時還會產生負面效果,阻礙思想政治教育過程的展開。在對思想政治教育過程進行研究和建構時,強調教育者的主導作用,對于保證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和方向,顯然是必要的。然而,忽視或者無視受教育者的主體能動性,卻是得不償失的,會對思想政治教育產生極為消極的影響。因此,在思想政治教育過程中必須充分注意受教育者主體能動性的調動和發揮。
第三,創造性。創造性是人的能動性的突出表現,是人對現實的超越。培養受教育者良好的行為習慣是思想政治教育過程的歸宿。思想品德形成中的外化就是指受教育者把已經內化了的思想觀點、價值觀念、道德準則自主地轉化為自己的思想道德行為表現和行為習慣的過程。認識、情感、意志的培養最終都要落實到行為習慣上來。受教育者的創造是對自己的不斷更新和超越,即他們在自己思想品德的生成、生長和建構過程中,發揮主觀能動性,對自己已有的認知和行為習慣的不斷更新和超越,以符合自己和社會的雙重需求。
(二)受教育者在思想政治教育過程中的主體間性。
受教育者作為思想政治教育過程中教育內容的占有者、支配者,與教育內容構成一種主客關系,受教育者是主體,教育內容是客體,二者在對象化活動中分別處于占有、支配和被占有、被支配的地位。但受教育者與教育者在思想政治教育過程中應在交往實踐的基礎上形成一種平等的交往關系,這種交往是自我主體與對象主體間的交往,反映的是主體與主體間的彼此理解、相互生長的關系。受教育者的主體間性主要表現在:
第一,交互性。“社會——不管其形式如何——是什么呢?是人們交互活動的產物”,[7](p532)這說明社會是互動著的社會主體的關系性存在。任何人類實踐都離不開交往,思想政治教育作為一種特殊的實踐,當然也離不開交往。在思想政治教育過程中,無論是交往的形式,還是交往的內容,交互性都是主體間性的一個重要特點。形式上,交往雙方持續不斷地轉變著施受狀態;內容上,交往雙方的理想信念、思想觀念、價值追求、道德品格、行為習慣等等,都在交往中時刻傳遞。這種全方位的交往,使得交往雙方在彼此規定、相互影響中不斷重構、成長自己。在此意義上,教育者引導教育內容的選擇、加工,受教育者通過和教育者共同深化、升華教育內容,從而完成教育內容的內化、外化,達到教育目的。
第二,平等性。交往的過程不在于復制、重復確定不變的知識或信息,而在于通過教育者與受教育者雙方不同的知識經驗以激蕩出更好的、更有益的思想和觀念。但在思想政治教育實踐中,常常出現這樣的狀況:教育者“居高臨下”,受教育者“望而生畏”,教育方式是簡單、粗暴的“填鴨式”、“我說你聽”,受教育者鮮有機會表達自己的思想、觀念。殊不知,在教育過程中,教育者與受教育者都是具有主體性的人,具有平等的人格,任何企圖壓制、控制對方的行為都是不合理的。真正的主體間性應體現為交往中的平等的主體間關系。在這種關系中,一方應把對方看作是人格與自己完全平等的主體,而不是企圖控制、壓制、支配的客體。在交往中,通過交流、溝通,達到“雙向理解”、彼此融合。因此,主體間性要求雙方應有均等的交往機會,且雙方都應是自由、平等地參與到思想政治教育過程中。
第三,寬容性。寬容是主體間性的內在要求。只有在寬容的氛圍、環境和心態下,主體間的溝通、交流才能言無不盡,彼此之間的思想才能在融洽的環境中得到碰撞和提升。在思想政治教育過程中,要取得良好的教育效果,務必使教育者與受教育者達成共識,而共識是人們在沒有內外壓力和制約下的理想情景中進行溝通達成的。在寬容的交往氛圍中,每個成員都有自由發表意見、表達自己見解的機會與權利,也最容易得到別人的支持和幫助。教育者在民主寬松的環境下實施思想政治教育,比較容易獲得信心,而受教育者也易于接受教育者所施加的影響。
第四,受制性。思想政治教育過程中,教育內容是教育者與受教育者交往的前提,同時制約二者的交往。受教育者的主體性無論如何發揮,都必須反映社會發展的客觀要求,不能偏離社會發展的軌道。思想政治教育活動作為一種社會實踐活動,具有鮮明的意識形態特征,教育內容反映了一定階級、政黨、社會群體的要求,必然從根本上制約著教育者與受教育者的交往關系。教育者與受教育者即便是平等的交往,但依然受制于教育內容。因此,交往本身要受到教育內容的影響。沒有脫離內容的交往,也就沒有不受限制的交往。
第五,超越性。隨著思想政治教育活動的持續進行,受教育者主體性得到充分全面的發展后,受教育者的受教過程就會逐漸擺脫教育者所施加的影響,表現為受教育者對教育者的超越,即主體對主體的超越,而這毫無疑問正是我們教育目的實現的標志。
[1]高鴻.現代西方哲學主體間性理論及其困境[J].教育與研究,2006,(12).
[2][德]胡塞爾.胡塞爾選集[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7.
[3][德]雅斯貝爾斯.什么是教育[M].鄒進,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1.
[4][德]哈貝馬斯.交往與社會進化[M].張博樹,譯.重慶:重慶出版社,1993.
[5]張耀燦.思想政治教育主體間性涵義初探[J].學校黨建與思想教育,2006,(12).
[6]任平.走向交往實踐的唯物主義[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7]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責任編輯張豫
G641
A
1003-8477(2013)12-0194-04
史宏波(1978—),男,上海交通大學學生工作指導委員會,講師;武漢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博士研究生。侯士兵(1975—),男,上海交通大學學生工作指導委員會副處長,講師。
2012年度上海市學校德育理論研究課題“交叉學科視野下思想政治教育理論創新研究”(2012B001)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