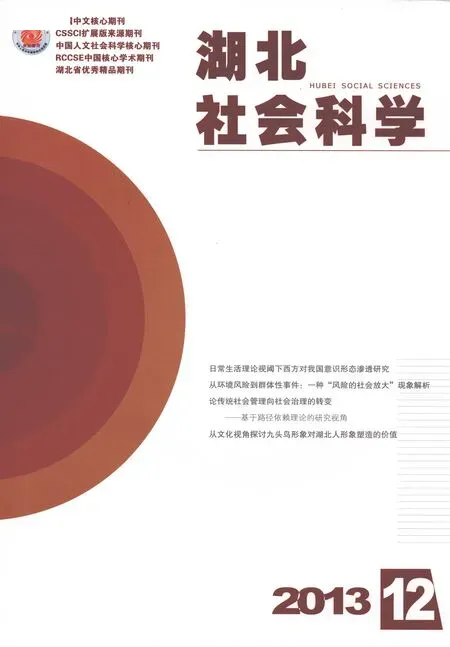胡塞爾論形式公理系統(tǒng)的完全性
李義民
(九江學院思政部,江西九江 332005)
胡塞爾論形式公理系統(tǒng)的完全性
李義民
(九江學院思政部,江西九江 332005)
在放棄了《算術哲學》中的心理學方案后,胡塞爾在哥廷根的兩個講座中提出了一個新方案解決數(shù)學基礎問題。該方案通過形式公理系統(tǒng)證明了想象數(shù)的有效性和實數(shù)系統(tǒng)形式上的一致性。其中,胡塞爾論述了一種“確定的簇”來說明算術系統(tǒng)的完全性,并對希爾伯特的完全性公理進行了批判。
算術哲學;胡塞爾;簇;完全性;公理化
在現(xiàn)象學方法論探索中,胡塞爾所關切的核心主題是數(shù)學與邏輯,這種研究被胡塞爾稱為“哲學-數(shù)學的(philosophico-mathematical)研究”。二戰(zhàn)之后,胡塞爾研究已經(jīng)迅速成長為一門專學,美中不足的是,對復雜艱深的現(xiàn)象學方法論的興趣使研究者們常常遺漏了胡塞爾所瞄準的科學問題。當代學者們發(fā)現(xiàn),胡塞爾在1901年之前的數(shù)學基礎研究也具有重要價值。
1901年冬,胡塞爾受邀在哥廷根數(shù)學學會做了兩個重要講座,相關文獻被稱為《兩個講座》(Doppelvortrag,下文用簡稱DV代替)。①《兩個講座》最早作為附件收錄在胡塞爾全集第12卷《算術哲學》中。K·舒曼和E·舒曼在盧汶檔案館重新編訂《兩個講座》時發(fā)現(xiàn)了更多的手稿,相關內容發(fā)表于2001年《胡塞爾研究》(17,pp87-123)。2003年英譯本《算術哲學》收錄并整合了這兩部分內容。本文將探討胡塞爾在這兩個講座中提出的簇(Mannigfaltigkeit)②胡塞爾在三種意義上使用了Mannigfaltigkeit這個詞,一是字面意義“多”,二是數(shù)學中的“流形”或“簇”,三是他的哲學規(guī)定,即由若干公理所確定的形式性對象,這些對象構成一個集合。這個詞的英語翻譯相對簡單,但也存在困難。英語中有set、multiplicity、manifold等譯法,不過,該問題的主要研究者現(xiàn)在都譯為manifold。這個詞的恰當漢譯較難,在《邏輯研究》中倪梁康先生的翻譯是流形、雜多,李幼蒸先生在《觀念I》和《形式邏輯和先驗邏輯》中譯為復多體、多樣性。鑒于兩位前輩的翻譯互不一致以及該詞在胡塞爾哲學中的重要性,這里試作探究,以就教方家。在使用字面意義時,胡塞爾語境中的Mannigfaltigkeit顯然是多而不雜的,所以取“多樣性”更合適。涉及數(shù)學意義時用流形、簇已是通譯(晏成書先生翻譯羅素《數(shù)理哲學導論》中的manifold用的就是簇),但流形字面上沒有表達胡塞爾的哲學意義,即特定的對象域,復多體也不適合這個含義。Mannigfaltigkeit在字面上或有“重”、“復”之意,但“復多(體)”在漢語中是不好理解的。用簇似乎更契合胡塞爾的“對象域”,也兼顧了數(shù)學意義,缺點是沒有直接表達“多”。所以,可以提議用簇和多樣性來翻譯胡塞爾文本中的Mannigfaltigkeit。簇論(Mannigfaltigkeitslehre)是胡塞爾從1890年代初開始到1920年代末長期思考的問題,在《危機》中也有論及。盡管在《觀念I》和《形式邏輯和先驗邏輯》等作品中,胡塞爾對簇論有更多論述和更清晰的表述,但他的主要思想在《兩個講座》中已經(jīng)形成,此后沒有重大改變。在1900年的《邏輯研究》第一卷中胡塞爾用“純粹的簇論”批判邏輯心理主義。通過簇論,胡塞爾論述了一種萊布尼茨意義上的普遍數(shù)學,證明了數(shù)學基礎問題,相應地也揭示了一種超越形式邏輯的純邏輯;或者說,簇論提供了一種形式本體論和世界一般(word-in-general)的形式結構。在《形式邏輯和先驗邏輯》中,胡塞爾進一步希望通過簇論揭示邏輯的終極意義。的完全性問題。關于胡塞爾的數(shù)學哲學研究,國外大致有兩種方法。一種是“內在的(internal)”,即根據(jù)胡塞爾本人的思想和“語言”來閱讀胡塞爾;另一種是“分析的(analytical)”,就是用分析哲學的眼光和語言來解釋和建構胡塞爾的本意。本文擬采用分析的方法。
1.“基礎概念”與胡塞爾早期的哲學立場。“基礎”一詞可以非常簡潔地刻劃胡塞爾終生工作的基本特征。胡塞爾哲學總是試圖不斷地追問問題背后的根據(jù),或意義背后更一般的意義根源。這種帶有方法論性質的反思方式無疑出自布倫塔諾,但并非與數(shù)學基礎研究毫無關聯(lián),即究竟是什么東西構成了數(shù)學的可靠基礎?所以在《算術哲學》(Philosophie der Arithmetik,下文用PA代替)中胡塞爾明確指出,他的算術哲學不僅僅是“計算的形而上學(Metaphysik des Kalküls)”。在PA中,胡塞爾對“基礎的(Elementar或Fundamental)”與“基本的(Grund-,英譯為basic)”在使用上作了區(qū)分。這種區(qū)分在德語、英語和漢語中似乎都不是實質性的,而在胡塞爾的PA文本中則是原則性的。區(qū)分之后,“基礎概念(Elementarbegriffe或Fundamentalbegriffe)”一詞就體現(xiàn)了胡塞爾與眾多基礎研究者,尤其是與弗雷格的根本分歧。
胡塞爾的時代是“嚴格化”之風勁吹的時代。這種嚴格化要求,數(shù)學必須首先對基本概念作明確規(guī)定,然后從概念到其他概念、從概念到命題、從命題到另一個命題和從理論到另一個理論,都不允許存在邏輯空隙,更不允許存在矛盾。1780年代,Dedekind和Peano建立的算術理論中,有1(或0)、后繼、數(shù)這三個概念沒有被定義。弗雷格認為這是不嚴格的,他在稍早的《算術基礎》中則定義了所有的概念。但胡塞爾認為:“(人們)過于熱衷于被設定的嚴格性,試圖也定義一些,因為它們的基礎性質既不可能也不需要定義的概念。”[1](p96)在胡塞爾看來,只有復合概念可以通過分析而被定義為其基本要素。
對弗雷格而言,算術命題不是先天綜合判斷,算術是純分析的。弗雷格之所以如此自信是因為他利用了萊布尼茨的“相同置換”定義。這個定義是:“能用一事物代替另一事物而不改變真,這樣的事物是相同的。”[2](p76)在《算術基礎》中,為了定義數(shù),弗雷格認為萊布尼茨的“相同(identity)”可以改換成“相等(equality)”;然后弗雷格舉了一個比較直觀的例子,即如何可以用直線a的平行線b的方向去定義直線a的方向。根據(jù)“相等置換”弗雷格有:
a∥b?(a的方向=b的方向)?a的方向是“與a平行”這個概念的外延。
類似就有:適合概念F的數(shù)是“與概念F等數(shù)的”這個概念的外延。[2](pp76-80)
此外,弗雷格還通過等價概念給出了等數(shù)概念的定義。經(jīng)過一番論證,弗雷格的結論表明,基數(shù)是所有等價類的類。
在PA中,胡塞爾認為弗雷格用“相等”代替萊布尼茨的“相同”是不合適的,相等置換不能保真。同時,“相同置換”是沒有根據(jù)的。如果追問“在某些或所有真判斷中一個內容置換另一個內容的基礎是什么”,唯一適當?shù)幕卮鹗撬鼈兊膬热菹嗤!懊總€相同的性質可以確立真值相同的判斷,但真值相同的判斷并不確立相同的性質”。[1](p97)弗雷格之后的語言哲學研究表明,“相同置換”并不是普遍的,這與胡塞爾的批評不謀而合。
其實,胡塞爾與弗雷格并非完全沒有共同語言,他們都反對數(shù)是事物的物理屬性,都認為數(shù)的客觀性在于它是觀念性的東西。對弗雷格而言,數(shù)是觀念世界中的“對象”,數(shù)學的真與心理體驗無關。胡塞爾不贊同把數(shù)理解為純邏輯概念,認為這完全背離了數(shù)的直覺意義,即事物的數(shù)(Anzahl,基數(shù))是一個“多少(How many)”的概念。胡塞爾接受了布倫塔諾關于物理現(xiàn)象與心理現(xiàn)象的嚴格區(qū)分,如果數(shù)不是可被表象的物理現(xiàn)象,那么就只能在心理學中分析其客觀性的根據(jù)。
胡塞爾認為算術的基礎概念是不能被規(guī)定的,這其實是宣告純數(shù)學的數(shù)學基礎證明是行不通的。胡塞爾的道路是,在描述心理學中反思基礎概念的性質和符號方法的一般邏輯意義,在此基礎上為數(shù)學奠基。
2.《算術哲學》中的難題。不過,就“以算術為數(shù)學奠基”而言,1890年前的胡塞爾與其他基礎研究者是完全一致的。具體而言,當時學者要做的工作是建立嚴格的算術理論來論述一個一致的實數(shù)系統(tǒng)。這種研究都具有“還原論”性質,胡塞爾的不同僅在于他是在心理學中進行這種還原。但是在PA中,胡塞爾遇到了一個無法克服的問題。1890年,胡塞爾在給施通普夫的信中說:“在考慮教職論文中仍然指導我的觀點——基數(shù)概念構成一般算術的基礎——很快被證明是錯的(對基數(shù)的分析已經(jīng)使我清楚了這一點)。無論用什么巧妙的方法,無論什么非本真的表象,都不能從基數(shù)概念中得出負數(shù)、有理數(shù)、無理數(shù)和各種復數(shù)。對序數(shù)概念、量的概念等同樣如此。”(Hua XXI,p245)
“不能從基數(shù)概念中得出負數(shù)、有理數(shù)、無理數(shù)和各種復數(shù)”,其實就是不能把實數(shù)還原為基數(shù)。我們知道,在PA中,基數(shù)是一種出自集合聯(lián)合(Kollektive Verbingdung)的形式概念或范疇。基數(shù)既非物理事實(它在經(jīng)驗領域無對應物),也非心理事實(從而是主觀表象),而是一種綜合行為把任何可能的、若干個對象單元統(tǒng)一而成的純形式的“多”。胡塞爾認為他在PA中對基數(shù)概念的處理是成功的,但按照這種心理學的概念分析,他無法構造出如-1、%、√2等這樣的數(shù)。這些數(shù)在意識中沒有預先被給予的對象,是反直觀的,所以沒有真實(reale)意義。在DV中,胡塞爾把基數(shù)之外的分數(shù)、負數(shù)、無理數(shù)等統(tǒng)稱為想象數(shù)(das?imagin?re)。
在數(shù)學史上,人們始終無法理解想象數(shù)是什么。想象數(shù)問題是當時基礎研究者的共同難題,它包括想象數(shù)的本體論性質和它們在算術計算中的合法性兩個方面。這個問題對邏輯主義而言,利用邏輯-數(shù)學的定義相對不難,但其背后的哲學根據(jù)卻大有問題。例如,胡塞爾在DV中批判了戴德金的還原論。戴德金認為,數(shù)的建構是一個自由創(chuàng)造的過程,前提是在自然數(shù)的穩(wěn)步擴充中,新數(shù)通過創(chuàng)新的定義引入,新數(shù)的計算法則盡可能服從舊的法則并在整個數(shù)域中不引起矛盾。胡塞爾認為,自然數(shù)域是封閉的,它的對象是由其概念而被嚴格給定的,不能通過定義而任意擴充。胡塞爾認識到,如基數(shù)、負數(shù)、有理數(shù)、無理數(shù)等,它們的意義相互矛盾,是不可“通約”的,把實數(shù)還原到自然數(shù)是不可能的。
我們知道,自然數(shù)有一種奇特的“繁殖能力”。在自然數(shù)域內,自然數(shù)的加法、乘法等運算可以無限進行并有確定的結果,但相應的逆運算卻是有限的。如a-b=c,如果a<b,則c在自然數(shù)域之外。如果要使各種逆運算是完全的,就必須造出新數(shù),所以想象數(shù)都出自算術的逆運算。然而,想象數(shù)雖然出自自然數(shù),但卻不能通過自然數(shù)而獲得清晰的說明,比如歸約為自然數(shù)。自然數(shù)的這種神秘性質使數(shù)學家們深感震驚和困惑。
盡管否定了各種基礎主義方案,但胡塞爾沒有放棄基礎主義的信念。胡塞爾還是相信想象數(shù)與自然數(shù)有某種實質性關聯(lián)。如果這種關聯(lián)不是意義上的,從而可以否定戴德金的創(chuàng)新定義方案和自己的現(xiàn)象學方案,那么另一可能的關聯(lián)就是算術運算本身。,是開方運算把x和-a關聯(lián)起來。胡塞爾意識到,運算形式作為形式之物是普遍的,算術是一種特殊的邏輯學。這樣胡塞爾就找到了一個新的探索方向,但探索的過程是異常艱辛的。直到1901年受希爾伯特公理化方法的影響,胡塞爾才提出了一個新方案:在形式公理系統(tǒng)中論證想象數(shù)的合法性,從而保證它們既不屬于自然數(shù)但又可以是自然數(shù)的各種逆運算的確定結果。這樣,數(shù)學基礎問題就在于論證,在什么條件下,運用想象數(shù)的運算是有效的。這就是DV中討論的核心問題。
3.簇論。算術運算的邏輯性質使得胡塞爾求助于形式演繹系統(tǒng),這被認為是靠近了弗雷格的邏輯主義:數(shù)學的可靠性在于邏輯。但二者的共識幾乎僅此而已。胡塞爾始終不認同弗雷格對基數(shù)(從而可能的對想象數(shù))的邏輯定義,認為想象數(shù)是不存在的、無意義(指稱)的。他說:“讓我們考慮整數(shù),正數(shù)和負數(shù)的公理系統(tǒng)。當然有一個意義。因為平方是被定義的,–a和=也是。但在整數(shù)中不存所以我不能提出這個問題:一個確定的量x滿足x2=a。這是哪個量?”[3](p438-439)
弗雷格對這種觀點作了激烈的批判,在他看來,對象對科學而言是本質性的東西,人們無法想象某種科學在研究不存在之物,如數(shù)學研究的是沒有指稱的。[4](p123)顯然,弗雷格只是斷定了的存在,他并不能回答究竟是什么,因為他的邏輯主義是失敗的。胡塞爾認為,想象數(shù)問題出自算術的形式化,是數(shù)學從數(shù)量科學到抽象形式理論轉換的產物,人們不理解想象數(shù)是因為人們對算術運算作為形式演算這種方式缺乏理解。
通過形式演繹系統(tǒng)反思想象數(shù),這使胡塞爾發(fā)現(xiàn)了萊布尼茨所設想的普遍數(shù)學的重要價值。胡塞爾認為普遍數(shù)學是最高層次的數(shù)學,一種理論學(Theorienlehre),獨立于所有具體的知識領域。
實現(xiàn)這種科學的方法是一般化,就是“用形式的表述代替對象的有確定內容的表述”。例如,人們在代數(shù)中用a、b等字母代替自然數(shù)就是這種方法。不僅算術、幾何,而且其他各種知識領域都可以這樣處理。這樣,一個具體理論的知識內容全部被抽取,只剩下與原命題相對應的形式命題。每個具體命題都對應一個形式命題,每個形式命題也有相應的具體命題,一個具體理論相應地就轉化為形式的命題系統(tǒng)。其中,一些數(shù)量有限、相互獨立且不矛盾的命題是基本命題(即公理),其他的命題則是公理的邏輯后承。在這種形式理論中,它的對象域由公理通過演繹而限定在特定范圍內,也就是說不是任意的。“我們稱這樣被規(guī)定的對象域為一個確定的、僅在形式上被規(guī)定的簇。”簇中的對象是各種形式性的對象、關系等觀念物,如命題形式、命題關系等。所以,一個形式理論可以把握一類來自不同經(jīng)驗領域的科學理論,因為它們有相同的形式理論,而被形式化的理論就是這類理論的一個特例。相應地,胡塞爾可以明確規(guī)定“純粹邏輯”概念,它與亞里士多德的命題邏輯的區(qū)別在于,純粹邏輯不再處理經(jīng)驗的實體。
如果對某種形式理論再進行抽象,就構成普遍數(shù)學。這是一門關于演繹理論的科學,也就是關于各種簇的理論(Mannigfaltigkeitslehre)。在這個階段,可以把各種形式理論進行系統(tǒng)的分類,并把一個形式理論與一類不同形式的理論系統(tǒng)地關聯(lián)起來,從中可以引出一些重要結論。例如,公理化的歐式幾何是一個三維歐式簇,是一類系統(tǒng)相關的不同曲率簇的一個特例。這里胡塞爾要探討的是不同理論的結構關系,也就是理論的數(shù)學結構。通過這種結構,可以構造出其他可能的演繹系統(tǒng)。比如,胡塞爾認為,在純形式領域可以用不同方式改變形式系統(tǒng)。如取代3維歐式幾何簇,可以選擇4維甚至n維,建立n維的所有幾何簇,它們仍然可稱為是歐式幾何,因為除了維度外,公理形式?jīng)]有任何本質上的改變。這樣人們就找到了可以建構無限多個可能學科的形式的方法。[5](p170)由此Centrone認為,胡塞爾先于希爾伯特認識到:人們應當把證明本身視為一種數(shù)學建構和一個數(shù)學研究的對象。[6](p157)
所以,與當時弗雷格和希爾伯特的演繹系統(tǒng)不同,胡塞爾的簇論還研究為演繹系統(tǒng)奠基的形式結構。具體而言,就是研究不同簇中的概念、命題和論證形式之間的對應關系。雙方更進一步的差別是,簇論不僅僅是數(shù)學方法論性質的,而且具有本體論性質。在《邏輯研究》第一卷《純粹邏輯學導引》中,胡塞爾就是根據(jù)這種研究觀念性對象和觀念性事態(tài)的簇論,提出了“形式本體論”的概念,即簇的形式結構是各種科學的先天結構。在此意義上,各種知識領域之所以統(tǒng)稱為科學,就在于它們擁有同樣的結構形式。
與此相應,胡塞爾論述了一種普遍算術(arithmetica universalis)理論。以自然數(shù)為例,基本概念如“自然數(shù)”等由公理規(guī)定,而個別的自然數(shù)由“自然數(shù)”概念嚴格界定。如果把自然數(shù)系統(tǒng)公理化,那么在該系統(tǒng)中,不僅有其特有的公理、運算形式和運算法則,而且也有與整數(shù)、無理數(shù)等所共同的公理、運算法則和共同的算法(algorithm),這些共同的部分構成普遍算術。Hartimo認為,胡塞爾沒有清晰說明各種不同算術具體的結構關系,[7](p296)在此意義上,胡塞爾的普遍算術理論是不成熟的。所以可以發(fā)現(xiàn),在談論普遍數(shù)學時,胡塞爾總是舉幾何學的例子。
通過簇論,胡塞爾就為證明數(shù)學基礎問題搭好了腳手架。從普遍算術的觀點看,即便各種不同的數(shù)在意義上不可“通約”,但它們有共同的演繹形式。也就是說,從自然數(shù)到實數(shù)等,它們有統(tǒng)一的形式結構和法則,從而保證全部算術是相容的。只要想象數(shù)可被定義并在形式系統(tǒng)中保持一致,它們就不僅在數(shù)學中是有用的,而且可以作為純形式之物而獲得某種存在性。這與胡塞爾在PA中認為基數(shù)是純形式的,具有一致性。
4.新方案。在《形式邏輯和先驗邏輯》中,胡塞爾對自己的新方案作了清晰的總結:“我最初用確定的簇這個概念是為了一個不同的目的,即為了澄清使用想象數(shù)的概念運算過程的邏輯意義……我的問題是:在什么條件下,在形式上被規(guī)定的演繹系統(tǒng)(一個形式上被規(guī)定的簇)中,可以使用由系統(tǒng)所定義的想象數(shù)概念進行自由的運算?在什么時候,這種關于運算的演繹所產生的沒有想象數(shù)的命題實際上是正確的,也就是說,是規(guī)定它的公理形式的正確后承?擴充一個簇(一個被完好規(guī)定的演繹系統(tǒng))到一個新的簇,把舊的簇包含其內作為一個部分,這在多大程度上是可能的?答案是:如果系統(tǒng)是確定的,那么運用想象數(shù)概念進行運算就永遠不導致矛盾。”(Hua XVII,§31.p85)
新方案的要害是“確定的(definit)①胡塞爾在DV、《觀念I》、《形式邏輯和先驗邏輯》等著作中都是用“確定的definit”、“確定性Definitheit”,而不是希爾伯特用的“完全的vollstandig”、“完全性Vollstandigkeit”。簇”,即一個完全的公理系統(tǒng)。胡塞爾對它的規(guī)定是:“如果基于一個公理系統(tǒng)的每個可理解的命題,根據(jù)公理可被理解為或真或假,那么界定一個域的這個公理系統(tǒng)可稱為是確定的。或者說,如果只有兩種情況是可能的,或者命題出自公理,或者與它們矛盾。”這就表明,根據(jù)公理和矛盾律,在簇中沒有任何不確定的東西,而且任何句子的真與假都由公理決定。按現(xiàn)代邏輯的說法就是,在公理系統(tǒng)A中,出自A的任何一個命題,或者是A的一個后承,或者與A矛盾,即它的否定在A的后承中。我們知道,這是演繹完全性的標準含義。簡單地說,胡塞爾的新方案是:如果擴充公理系統(tǒng)A0得到新公理系統(tǒng)A1,A1是一致的且A0是確定的,那么A1的任何一個完全用A0的語言表達的后承,即沒有想象數(shù)的命題,是真的。
我們知道,在算術中從任何一個初始系統(tǒng)A0到A1的擴充都是增加了某種想象數(shù),如從自然數(shù)到整數(shù)增加了0和負整數(shù),從自然數(shù)到有理數(shù)則還增加了分數(shù),等等。這種擴充對公理集A0而言就是增加了數(shù)量有限的若干公理A+,從而保證算術中某種逆運算可以完全進行。胡塞爾認為:“A1=A0+A+且A0?A1,而兩個系統(tǒng)的邏輯后承F有:FA1=FA+A+且FA0?FA1”[1](p439-440)
增加了公理就意味著在推理過程中增加新的前提,這必然影響邏輯結論。胡塞爾的要求是,A1的任一后承p,如果完全是用A0的語言表達,則p也要能從A0推導出來。這是可以成立的。因為A1是一致的且p在A1中成立,即p必定不與A1的任何后承矛盾,又因為FA0?FA1且A0是完全的,所以p在A0中必然成立。
總之,胡塞爾的結論是:一條運用想象數(shù)的道路是可允許的,(1)如果想象數(shù)能夠在一個一致的、被擴充的演繹系統(tǒng)中被定義;(2)如果初始域被形式化后有這個性質,其下的每個命題的性質根據(jù)該域的公理或真或假。[3](p428)這樣,胡塞爾就證明了想象數(shù)在形式上的合法性,也就是整個實數(shù)系統(tǒng)的一致性和可靠性。
上述證明要面對的一個問題是,憑什么可以斷定一個初始演繹系統(tǒng)A0是確定的?這也是希爾伯特當時提出的問題。如果A0不是確定的,上述論證就完全失敗了。對此問題,胡塞爾非常自信地反問道,“每個僅包含正整數(shù)的命題根據(jù)正整數(shù)的公理或真或假,難道我沒有證明自己可以這么說嗎?”(Hua XII,p445)胡塞爾的看法是,如果只考慮加法運算和相等、不等兩種關系,自然數(shù)公理系統(tǒng)的完全性是可能的。因為,對于a+b,必有?a?b?c(a+b=c)為真,在不等于c時恒假。不僅如此,胡塞爾還認為算術的完全性是自明的,因為自然數(shù)、有理數(shù)、實數(shù)等等,如果被公理系統(tǒng)所規(guī)定,都可以根據(jù)公理證明,每個出自公理所確立的概念所構成的命題或真或假。
值得注意的是,胡塞爾的結論與哥德爾基于Peano公理所證明的不完全性定理是互為抵觸的,所以國外的一些學者試圖對這個矛盾進行反思。據(jù)王浩先生介紹,哥德爾晚年對胡塞爾的公理化思想很感興趣,但遺憾的是沒有見到哥德爾的相關論述。[5](p161)
5.兩種完全性。關于演繹系統(tǒng)的完全性,胡塞爾沒有照搬希爾伯特并與希爾伯特有重要區(qū)別。希爾伯特認為,如果任意給定的一些公理及其全部后承是一致的,那么它們是真的,并且公理所定義的東西存在。但弗雷格認為,是數(shù)學理論的真決定它的一致性,而不是相反。顯然,很多邏輯上一致的命題實際上是錯的。[1](p445-451)胡塞爾傾向于弗雷格的立場,即數(shù)學真理的真是不容質疑的,數(shù)學中真的東西不可能相互矛盾,真決定一致性。對簇而言,公理是真的,所以與希爾伯特不同,不需要證明公理系統(tǒng)的一致性。只要公理系統(tǒng)是完全的,出自公理的后承就是真的。在《觀念I》中胡塞爾仍然強調:“這個(確定的)簇的特征是,在給定的例子中,導自有關領域之本質的有限的概念和命題,以純分析的必然性的方式完全地和無歧義地規(guī)定了該領域中所有可能構造物的全體,這樣,出于本質的必然性,該領域中沒有任何東西是不確定的……就一個數(shù)學的確定的簇而言,‘真的’與‘公理的形式邏輯后承’是等價的,‘假的’與‘公理的形式邏輯的反后承’等價。”(Hua III,§72.pp135-136)
這樣,胡塞爾的形式演繹是從真到真的保真過程,從初始系統(tǒng)A0到新系統(tǒng)A1的擴充也是保真的。相反,希爾伯特的立場則頗顯奇怪,從一致性中怎么冒出了“真”?
為建立實數(shù)的公理系統(tǒng),希爾伯特在1899年的講座“論數(shù)的概念”中第一次提出“完全性公理”。希爾伯特認為,“增加任何東西的集合到實數(shù)系統(tǒng),使得在合并的集合中先前的公理被滿足,這是不可能的;簡單地說,也就是實數(shù)的對象系統(tǒng)不能以先前的公理保持有效的方式被擴充。”[8](p183)針對這種看法,胡塞爾區(qū)分了“相對確定性”和“絕對確定性”。“一個公理系統(tǒng)是相對確定的,如果它的存在域不接受更多的公理,但在擴充的域中,同樣的公理和新公理有效。”[4](p426)
胡塞爾認為,每個確定的數(shù)學公理系統(tǒng)在其域內是不能擴充的,但在其域外可以有一致的擴充。例如,在自然數(shù)域內自然數(shù)不可擴充,但如果把自然數(shù)定義為整數(shù),則在自然數(shù)外可以有一致的擴充;相應地,它的公理系統(tǒng)也是如此。所以,實數(shù)系統(tǒng)可以有一致的擴充并保持其原有公理的有效性。在此意義上,“絕對確定性明顯地意味著相對確定性”。相應地,“完全性永遠不是一個公理”,而是“一個確定的公理系統(tǒng)或簇的定理”。因為任何公理系統(tǒng)由于其純分析性質,本質上都是絕對確定的(完全的),所以,可以用“一個類似于完全性公理的封閉公理”,使研究對象固定在某個特定對象域。“如果每個根據(jù)公理系統(tǒng)而有意義的命題局限于公理系統(tǒng)的域中被規(guī)定,這個公理系統(tǒng)是相對確定的。如果每個根據(jù)公理系統(tǒng)而有意義的命題是普遍被規(guī)定的,這個公理系統(tǒng)是絕對確定的。所以,絕對確定的=完全的,在希爾伯特的意義上。”[1](p440)胡塞爾認為,希爾伯特的這種完全性是本質的完全性,一種“不真實的(unechte)完全性”。在胡塞爾看來,本質的完全性,它的意義是隱而不彰的,所以他對此論述不多。顯然,對胡塞爾而言,數(shù)學是一個可以前后一致地發(fā)展的開放系統(tǒng),希爾伯特的完全性概念是很難理解的。
在胡塞爾的時代,各種元邏輯的概念還沒有形成,所以胡塞爾所規(guī)定的概念與現(xiàn)代邏輯既相通又不同。一個簇在系統(tǒng)內的確定性與系統(tǒng)外的可擴充性,使確定性與完全性這兩個概念的關系相當復雜。大致說來,胡塞爾的確定性概念主要是指現(xiàn)代邏輯的句法完全性,而希爾伯特的完全性,現(xiàn)代邏輯認為是指范疇性(categoricity)。①“范疇性”是現(xiàn)代英美邏輯的一個常用概念,該概念由美國學者Veblen于1903年首先使用。Veblen認為,在一個公理系統(tǒng)中,如果任何可能命題的有效性完全由若干公理決定,并且增加任何公理都被認為是多余的,這種系統(tǒng)就是“范疇的(categorical)”。具體而言,范疇性概念刻畫了公理系統(tǒng)內所有模型(models)的同構性質。所以,胡塞爾的確定性與希爾伯特的完全性是不同的。有趣的是,胡塞爾認為自己所說的確定性就是希爾伯特的完全性,希爾伯特也是如此。兩人都沒有發(fā)現(xiàn)這兩個概念的差別。對此,Majer感嘆道,在數(shù)學邏輯的初創(chuàng)期,即使是希爾伯特這樣的數(shù)學天才,要清晰把握這些元邏輯的概念是何其艱難
最后,我們簡單談談胡塞爾在數(shù)學哲學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以引起國內學界的關注和重視。在19世紀末,胡塞爾不僅獨創(chuàng)了一種數(shù)學哲學,而且還通過論文、講座和與當時一流學者的通信為現(xiàn)代邏輯的發(fā)展提供了思想資源,并對今天的數(shù)學哲學研究仍然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遺憾的是,胡塞爾的數(shù)學哲學在西方學界曾長期被遺忘,直到上個世紀90年代,主要在英美學界興起了對胡塞爾數(shù)學哲學的研究,目前已經(jīng)初具規(guī)模。不少學者給予胡塞爾很高的評價,如Majer認為,胡塞爾現(xiàn)象學方法的算術基礎研究可以成為基礎研究三大流派外的一種流派。Centrone等人認為,胡塞爾的數(shù)學哲學“在深度和原創(chuàng)性上與同時代的康托爾、戴德金、弗雷格、羅素和希爾伯特處于同一水平”。
[1]Husserl,E.Philosophie der Arithmetik,Lothar Eley(Ed.) [M].The Hague:Martinus Nijhoff,1973.
[2]Frege,G.Die Grundlagen der Arithmetik.Eine logischmathematische Unter-suchung über den Begriff der Zahl. K?bner,Breslau,1884.
[3]Husserl,E.(2003)Philosophy of arithmetic,psychological and logical investigations with supplementary texts from 1887–1901.Willard.D(ed).Kluwer,Dordrecht,2003.
[4]Frege,G.Posthumous Writings.ed.H.Hermes,F.Kambartel and F.Kaulbach,trans.P.Long and R.White.Oxford: Basil Blackwell,1979.
[5]Hill,C.and Haddock,G.Husserl or Frege?Meaning,Objectivity,andMathematics.ChicagoandLaSalla:Open Court,2000.
[6]Centrone,S.Logic and Philosophy of Mathematics in the Early Husserl.Dordrecht:Springer,2010.
[7]Hartimo,M.H.Towards completeness:Husserl on theories of manifolds 1890–1901.Synthese156,2007.
[8]Hilbert,D.überdenZahlbegriff.Jahresberichtder Deutschen Mathematiker-Vereinigung8,1900.
[9]Majer,U.Husserl and Hilbert on Completeness:A Neglected Chapter in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Foundations of Mathematics,Synthese,Vol.110,1997.
責任編輯高思新
B516.52;B815
A
1003-8477(2013)12-0114-05
李義民(1970—),男,江西九江學院思政部講師,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哲學系2011級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