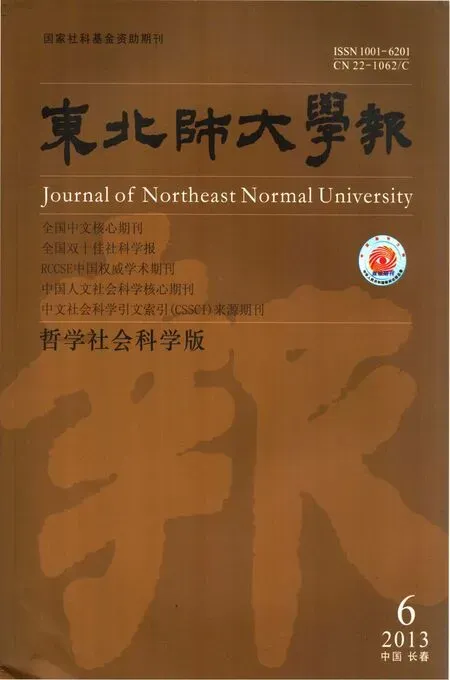論西方慈善文化中的理性精神
潘 乾,尹奎杰
(1.東北師范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部,吉林 長春 130024;2.長春師范大學 政法學院,吉林 長春 130032;3.東北師范大學 政法學院,吉林 長春 130117)
慈善是人類最古老的思想和行為之一,任何文化、任何宗教都包含有扶貧濟困、樂善好施的價值,無論是儒家以“仁愛”為核心的我國慈善文化,還是以“博愛”為核心的西方慈善文化,都是對“愛”這一共同的人類價值的詮釋。慈善是人類在同自然與社會的斗爭中互幫互濟、撫慰靈魂、提升境界的需要,是對甚至超出自己同類命運的關心。慈善是人類的伴生物,與人類文明的發展階段密切相關。自宗教改革和科技革命以來,西方對慈善文化中的理性精神這一價值觀念進行了重新凝結和定位,理性精神對于現代慈善具有積極意義和深遠影響。
一、西方慈善文化中的理性和理性精神
人類對理性的認識及理性精神的張揚不是從來就有的,而是經歷了歷史的生成與演變。在涉及理性的學術探討中,經常出現理性主義這一概念。一般而言,理性主義是關于理性價值的思想體系,而理性精神只是其中的精神實質與合理內核的體現,只有在精神實質的視角,二者才具有相同的含義。本文即從此意義上對西方慈善文化中的理性精神進行闡釋。
從詞源上看,西方人對理性的探索可追溯到古希臘時期的“邏各斯(logos)”和“努斯(nous)”這兩個詞。在哲學認識論上,理性一般是指人類所獨有的進行概念、判斷、推理等思維方式與思維活動的能力,同時又指人區別于動物具有調節自身行為、控制欲望與規范道德行為的一種價值判斷和精神力量。亞里士多德提出了“人是理性的動物”這一著名命題,認為:“人的功能,絕不僅是生命,因為甚至植物也有生命。我們所求解的,乃是人所特有的功能。……人的特殊功能即人的行為根據理性原理而具有的理性生活。”[1]亞里士多德認為人的理性能力表現為人特有的超越感性事物之上的進行判斷和推理的能力,以及控制自身欲望并使其向善的規范能力。
古希臘文明作為西方文明的源頭,也是理性精神張揚的源頭。希臘人所創造的群星璀璨的文化,是以理性為軸心,依此研究自然、社會與人生,并為西方科學與哲學的發展奠定了基礎。理性作為具有內在目的性的世界本體,而人的特殊性又在于通過自身的理性能力去揭示和認識世界的理性本質。理性一詞構成西方文化的核心,具有一脈相承的精神內涵:古希臘羅馬文化崇尚理性與科學,重視實證與量化,善于邏輯與分析,在西方文化中占有突出地位;文藝復興使人們的思想活躍,敢于自由探尋真理,以“個人本位”、“克服自然”為核心的價值觀念得到了張揚。因此,理性精神是在“理性”基礎上發展而來的,經過古希臘文明的孕育,是人類與自然不斷斗爭的產物,是社會化大生產和市場經濟發展的產物,特指一種精神文化和價值體系[2]。
經過時代的發展,理性精神體現在:不受傳統與權威束縛,勇于批判與探索、大膽創新與求實務新的精神;追求真理與崇尚科學;尊重人的價值與尊嚴,為人類自由和解放而奮斗的精神;頌揚民主并反對專制,充滿理想、現實與樂觀主義的精神等[3]36。雖然在理性精神的發展過程中,反理性的斗爭一直沒有停止過,但理性精神卻一直主導著西方文化的思維邏輯與存在方式。
現代理性精神推崇強烈的自主與自覺的價值觀,富有獨立思考與批判精神。它重視個人的正當利益,同時也賦予他人利益的重要性,只有尊重他人合法權益,才能保障自身的合法權益。這種價值觀重視社會公德,以及個人與社會之間的關系。因此韋伯認為,這種精神成為推動生產力快速發展的強大動力。理性精神是人的主體意識的覺醒,昭示著人類精神的解放,是整個社會得以形成和發展的支柱。理性化程度越高,現代化程度才會越高。西方慈善文化中無不滲透著澄明的理性精神,理性精神是人類的寶貴精神財富,在西方慈善文化中從不同維度呈現:
(一)理性精神的目的維度
歷史的發展證明,基督教是西方慈善文化的主要淵源,“博愛”、“富人原罪”等宗教教義構成了最原始的慈善源動力,博愛是基督教教義的核心,基督教以博愛為根基孕育并促生了現代西方慈善文化的內蘊。美國貝勒大學社會科學教授羅德尼·斯達克認為,基督教是唯一推崇理性的宗教[4]。正是這種對理性的信仰,最終熔鑄成資本主義的慈善理性,并成為整個西方社會的共同價值信仰和追求。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認為,“理性化作為一種同傳統觀念、傳統思維方式相對立的生活態度、價值觀念和思維方式,乃是貫穿于現代社會發展過程的一條主線。”[3]36而基督教中的“罪富文化”,對富人進行威懾,在譴責世俗財富和富人的物質欲的基礎之上,認為富人生來就是“有罪之人”,上帝對其“震怒”,只有將自己的全部財富捐贈給窮人,才能得以進入“天堂”。這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是一種“目的的理性”。
(二)理性精神的方法維度
“在我們生活其間的社會中,我們之所以能夠成功地對我們自己做出調適,而且我們的行動也之所以有良好的機會實現我們所指向的目標,不僅是因為我們的同胞受著已知的目的的支配,或者受著手段與目的之間已知的關系的支配,而且是因為他們也受著這樣一些規則的約束……”[5]。西方慈善文化觀認為:個人對正義、和平與集體福祉負有不可推諉的責任。人人平等,人皆互濟,“你愿意人家怎樣對待你們,你們也要怎樣對待他人”。慈善并不僅僅只是富人的事情,更是大眾的事情,“人人皆可慈善”。西方慈善通過這樣一種方法來對市民的慈善行為進行引導,從而形成一種社會慣性,進而成為慈善行為。
(三)理性精神的價值或利益維度
在西方社會和政府對慈善行為人的“理性人假設”這一理論中,慈善家作為一個“理性人”,必然會降低慈善成本,實現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因此,西方社會和政府在對待慈善家的慈善行為時,不管其是基于道德層面還是為了追求自身利益(包括名譽和物質利益),不管其是基于對弱者的同情還是為了減少自身的“原罪”,都視其為“理性”之人,對其進行名譽獎勵,使其獲得聲望,并通過減稅等措施來鼓勵社會公眾參與到慈善事業當中,保障慈善事業發展的持續性。
二、西方慈善文化與理性精神的內在關系
西方文化是在希臘理性文化與希伯來宗教文化的長期交合中共同促進形成的,而基督教又與其有著直接的文化傳承關系。文藝復興所要復興的希臘羅馬文化是由基督教會保存下來的。恩格斯說“中世紀是從粗野的原始狀態發展而來的,它把古代文明、古代哲學、政治和法律一掃而光,以便一切從頭做起。它從沒落的古代世界承受下來的唯一事物就是基督教和一些殘破不全而且失掉文明的城市”[6]。當古代羅馬帝國覆滅時,許多古代文明都隨之消亡了,只有基督教一如既往的流傳不息,也只有基督教唯一保存、繼承和發展了希臘羅馬的文明價值,認為其中的理性精神與人性思維與基督教教義具有一致性。從而,基督教將古希臘的文明結晶與宗教信仰結合,在理性與信仰的交合中,信仰成為理性的出發點和目的,理性成為信仰的手段和途徑。
(一)慈善文化與理性精神并存不悖
慈善是理性精神的轉化和拯救,慈善文化是在轉化和拯救的精神主導下形成的。可以說,今天西方的慈善文化是在基督教“愛的福音”下而孕育、傳播和發展的,因為世人認為最具有吸引力的福音見證是關心人、博愛窮人、弱者以及受苦的人[7]。基督教的慈善思想推崇良善、公正、同情與友愛,要求信徒尊奉超性美德“信德、望德與愛德”(faith,hope and charity)。其中,信是核心,體現對上帝的超功利的愛;愛是基礎,是發自內心的圣潔情誼,是與認知無關的天啟的內在律令。愛的影響遍及一切,在人們的心靈深處扎根,影響著西方人的慈善思想與行為方式。以至在今天的西方社會中,愛不僅是倫理價值的體現,它還超越其他社會價值,成為一切價值的源泉。在人世間一切倫理問題無法得到求解時,愛即成為聯系宗教生活與世俗生活的紐帶,成為消解對立之矛盾的最終途徑。
同時,基督宗教的慈善思想又是屬于希臘理性精神的。奧古斯丁肯定理性的力量,認為如果沒有理性的靈魂,我們甚至不能信仰,同時又認為,沒有神的引導,個人就缺乏理解終極真理的能力,也無法獲得道德上的再生[8]50-51。在奧古斯丁看來,慈善并非一般意義的給予和捐贈,而是對愛上帝的一種表達。柏拉圖將人類的理性和智慧道德化,強調理性是德性之本,亞里士多德也強調按照理性生活的人是神愛的對象。在理念—邏各斯學說、關于神、目的論、三位一體說、時間學說的論證、關于理想社會的學說以及喻意解經法等一系列理論問題上,基督教教義都接受了希臘哲學思想的重要影響,與之相互結合在一起[8]40-46。基督教教義運用希臘哲學的語言和范疇,強調仁慈、行善和憐憫,用理性解釋神諭和上帝的存在。因此希臘哲學能夠給予基督教慈善觀以合理解釋。由于融進了希臘哲學思想,現代的西方慈善觀以理性精神強大了自身,也在一定程度上培養了理性精神。
具有現代科學思想的西方人已經不再相信死而復活、末日審判等傳統教義,不再相信某種超自然的神靈啟示,他們把對基督的皈依視為人類道德意義上的楷模,把對上帝的敬仰視為現實困境的情感撫慰和戰勝一切的巨大精神動力。在現代西方社會中,科學代表著人的理性,上帝則代表著人的良知,二者在漫長的歷史過程中發生過激烈的沖突和抵牾,現在終于達成了互補與默契[9]。慈善文化已經融入與滲透到西方人的現實社會生活中。
(二)西方慈善文化根植于最原始的理性精神
在人類千百年的歷史中,宗教對人們社會生活有著深刻而特殊的影響。盡管各大宗教的教義不同,但都在關心人類的前途和命運。在今天,基督教仍是宗教關懷的主力軍。宗教關懷表現為一種對人的精神層面的安慰與關照,包括對人在不可抗拒的自然力量和社會的盲目力量面前對人生的本質與命運的正視,是對人類淪落于大災大難之中的拯救,傳達人的精神依托感和生存的信念與勇氣,體現出一種對本原性及終極性問題的思考,昭示著人類對靈性的超越。
基督教的慈善文化并非無源之水,相反,它是在西方理性主義的母腹中逐漸孕育成熟的。在古希臘,探求“邏各斯”的理性精神彰顯出求知、善辨、愛智、究理的特性。智者思想家將理性應用到人及人類社會的理性探索,將傳統價值觀置于理性的批判之下;蘇格拉底認為理性是解決人類生活中最重要問題——善與惡問題的唯一指南,并勸導人們去關注靈魂的善,以擁有幸福的生活;柏拉圖認為按照理性原則和智慧可重塑個人道德,才能實現整體幸福與社會和諧。他說:“我們的立法不是為了城邦任何一個階級的特殊幸福,而是為了造成全國作為一個整體的幸福。”[10]斯多亞主義認為,理性使人并承認個人的尊嚴,人應當根據理性原則來安排生活,自我克制、提高道德修養、擺脫痛苦和煩惱,以達到最高的善和幸福。
正是這些思想的影響和融入,使基督宗教思想保留了希臘哲學的理性光輝,為西方慈善事業提供了重要的思想來源。希臘理性精神表現的平衡人的心理、消除人的煩惱和慰藉人的心靈的社會關懷傾向,逐漸被基督宗教思想汲取。因此,人欲達到自身德性的善及獲取幸福,要把順乎理性作為真正的道德生活;要把智慧、勇敢、節制和正義作為最根本的美德,人要有信念掌握自己的命運,要過一種有尊嚴、有意義和有價值的生活。這些正是宗教的社會關懷的理性體現。
(三)具有宗教關懷的慈善文化彰顯了理性精神的人文價值
早期的西方慈善思想深受基督宗教影響,天國的神圣福音給人以精神鼓舞,滿足了人們歸屬的迫切需要。基督教教義否定人與自然和諧的人文精神,但卻保留了希臘哲學的理性光輝[11]98。基督教將“道”(邏各斯)轉換成為上帝賴以創世的根據,以及上帝用以拯救人類的耶穌基督,道與上帝同在,道是上帝。道成為肉身(人),住在我們中間,充滿著恩典和真理(《約翰福音》1:14)。基督宗教作為傳播“愛的福音”的宗教,宣揚一種嶄新的民主與道德,提倡謙讓、逆來順受;不以個人出身、財富、教育和才能論及個人價值;給深受厄運、面臨死亡恐懼的人許以永恒的生命,以進入天國領受天父的慰藉,對生與死的現實問題讓人們有了精神依托[8]43。
不僅如此,作為救世主耶穌基督對人類苦難的救贖和對整個人類的愛深深引起了處于貧窮的社會底層的被壓迫人民的共鳴。早在中世紀的社會救濟中,教會即發揮了慈善救濟的社會服務職能,在實踐中見證著“愛的福音”的宗教社會關懷。基督教會為那些貧窮和殘疾人提供社會服務,接納奴隸、罪犯、道德上的罪人,以及被遺棄的人,向一切處于苦難中的人伸出援助之手,以提供心靈上的慰藉。這種宗教關懷倡導人們的社會行為必須遵循上帝的意志,甚至就是上帝有關仁慈和行善的主張,而不是以人為中心的人的意愿和主張。慈善行為通過教會來組織和實施,是上帝意志的具體體現。世俗社會中,個人與組織的慈善活動與行為,就是履行對上帝的虔敬。宗教關懷形成了一種載體及動力,推動著社會從野蠻走向文明,不懈地探尋人類的幸福,以駛向理性的港灣,是一種對理性精神的追求。
三、西方慈善文化中理性精神的積極影響
黑格爾曾言:“每一有限物都包含著自我否定的內在傾向,力圖超出自身,轉化為他物,在不斷的轉化中趨向于無限。”[12]奧古斯丁同樣指出:“不是為了拋棄信仰,而是通過理性之光去理解,這種理性之光,你是憑借信仰,已經是牢牢地把握住了的”。理解是為了信仰,只有信仰了才是可以理解的,或者說,理解是手段和途徑,信仰才是出發點和目的。沒有古希臘的理性精神,就沒有現代西方社會思想與文化的巨大進步,也無從找尋西方慈善文化的價值取向。現代西方慈善文化在宗教意識與理性精神方面不斷進行著自我肯定與自我否定,追求著超越本身所蘊含的更為深邃的和超自然的東西。矛盾不但具有個性,也具有共性,理性精神不但對西方慈善事業有著深遠的影響,對我國慈善事業的發展也有著重要的積極意義。
(一)理性精神指引著西方慈善文化的發展方向
古希臘文化認為,上帝創造的宇宙是有秩序、有法則的,人唯有依靠理性才能遵循這些法則,而遵循自然法則的理性生活就是善的和符合道德的[11]95。西方文化中這種關注世界的本原問題,承認理性能力的至上性,讓美德服從于知識,讓感情依附于理智,最終形成了以理念論為標志的理性主義傳統,正是對這種理性的信仰,貫穿了整個西方社會,形成了傳統意義上的理性精神,并主導了現代西方慈善的發展方向。
(二)理性精神促進了西方社會各種利益的良性互動,保證了社會的有序發展
新教倫理及資本主義精神,培育了西方人崇尚個人主義及政治與文化的多元,親屬感情淡薄、精打細算與強烈競爭,并主張“小政府、大社會”等觀念,奠定了西方文化鼓勵捐贈的傳統和以個人主義為本位的文化價值觀。這種個人主義強調個人的獨立性、創造性和自由發展,不受或少受政府與社會的限制。美國的富人不愿通過納稅將自己的財富交由政府支配,因為政府是低效率的,而擁有權力又會導致權力的濫用。因此他們更愿意自己或交由基金會來管理財富,以發揮最大功能實現公共利益,履行社會責任,并體現社會公平及正義和改善人類生活。在西方,慈善活動經過新教改革和資本主義革命,已經融入到西方國家的社會建制中,成為西方社會平衡各方勢力、促進社會和諧發展的重要力量。
(三)西方慈善文化中蘊含的理性精神對我國慈善事業發展具有積極意義
雖然我國的文化背景、發展狀況與西方國家不同,但我們在建立現代慈善的過程中,亟需的不是改變或確立慈善文化的發展方向,而是要建立符合自身發展的慈善文化坐標,而我們缺少和需要解決的最大問題恰是理性,即作為現代化支柱的理性精神的相對缺乏。相對于西方的個人主義文化,我國的慈善格局是由與政府有著密切聯系的慈善機構主導的,政府是施行慈善的主渠道。然而,隨著社會的發展,國家的救助力量及于社會力量畢竟是有限的。慈善是每個人心中的良善美德,是發自人性的自然情感,是人們在大災大難或極端事件之時的奉獻愛心的愿望。傳統慈善更多地也是停留在經驗的層次上,偏向感悟與直覺的思維與行為方式,具有明顯的感性特征。而現代慈善應當從道德層面提升到社會責任層面,尤其在社會愈發凸顯出某些不平等以及貧富差距的矛盾之時,這是任何自發的個人情感無以調節的。慈善應當以實現整個社會的公益為先,是可持續的,并且付諸于理性,而不是靠一時的激情。只有將傳統的自然的道德情感上升為慈善理性,才能在社會公益事業中更好地發揮作用。
[1]周輔成.西方倫理學名著選輯:上卷[M].北京:商務印書館,1987:298.
[2]吳增基.理性精神的呼喚[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32.
[3]豐子義.論現代化進程中的理性與非理性[J].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8(5).
[4][美]羅德尼·斯達克.理性的勝利:基督教與西方文明[M].管欣,譯.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1.
[5][英]哈耶克.法律、立法與自由:第一卷[M].鄧正來,等,譯.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9:17.
[6]馬克思恩格斯全集(7)[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400.
[7][德]卡爾·白舍客.基督宗教倫理學[M].靜也,常宏,等,譯.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0:51.
[8]李秋零.神光沐浴下的文化再生[M].北京:華夏出版社,1998.
[9]晏立農.圖說基督教文化[M].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9:206.
[10][古希臘]柏拉圖.理想國[M].郭斌和,張竹明,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59:279.
[11]孫蘭英.意義的失落與重建[M].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
[12]劉建軍.追問信仰[M].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