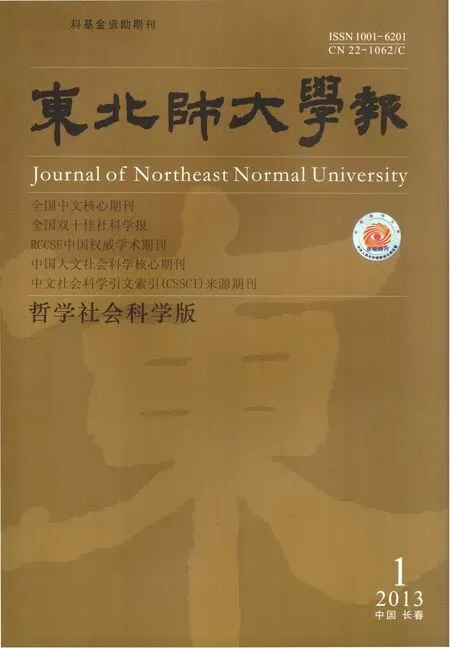葉適道器合一思想與其發展的文學觀
鄭 慧,張恩普
(東北師范大學 文學院,吉林 長春 130024)
南宋永嘉學派的主要代表人物葉適(1150-1223),曾獲得“集本朝文之大成者”的盛贊。發端于北宋,形成于南宋的永嘉學派是以薛季宣、陳傅良、葉適等為代表的事功之學。全祖望在《水心學案》按語中說:“乾、淳諸老既歿,學術之會,總為朱、陸二派,而水心龂龂其間,遂稱鼎足。”葉適堅持唯物主義的哲學思想,提出了以物為本的道器合一思想,堅持以發展的思想看待文學問題,以“尊古不陋今”的視角提出了文學理論的諸多觀點。比其稍年輕一些的詩人“永嘉四靈”就是在葉適的提攜、獎掖下,在南宋前半葉的詩壇留下了不同凡響的歷史足跡。同時,從葉適對“永嘉四靈”的態度表現中,也再次體現了葉適發展的文學觀。
一
葉適作為永嘉學派的集大成者,對當時盛行的理學家提出的某些唯心的論點有很多不同看法,他雖然沒有系統的哲學著作,但他晚年罷官退居故鄉水心村的16年(1208-1223)時間寫定的《習學記言序目》一書,記錄了他對哲學問題的一些看法。他提出了以物為本的道器合一思想。葉適認為,關于宇宙是什么,回答很簡單,就是“物也”。世界就是物質存在并充滿著物質的世界。他說:“夫形于天地之間者,物也;皆一而有不同者,物之情也;因其不同而聽之,不失其所以一者,物之理也;堅凝紛錯,逃遁譎伏,無不釋然而解,油然而遇者,由其理之不可亂也。”[1]699宇宙之中,天地之間,所有的一切現象,都是物的不同存在形式、表現形態,“物”乃是客觀世界存在的第一性的東西,物具有統一性,有“物之理”,即事物運動變化的規律,他認為所謂的“理”屬于客觀事物本身或所謂的“物”自身之“理”,是“不失其所以一者”,而物又有區別,統一的物質世界表現為各種不同的物質形態,客觀世界乃是形形色色的各有其特殊性,即“情”的物的存在總體,這就叫做“物之情”,不論其如何錯綜復雜,千變萬化,卻都有著“不是其所以一”的“物之理”,也就是物的“一而有不同”。在道與物的關系上,葉適認為道器合一,道在器數和事物之中,反對離開器物而談論所謂的“形而上”之道。葉適所說的“道”,主要是指事物變化的經驗法則和制造器物的技術原理。他說:“上古圣人之治天下,至矣。其道在于器數,其通變在于事物。”[1]697因而,理學認為的道與物統一在道的基礎上的觀點就是在物之外空言道,從而成為虛空的理論思想。葉適的觀點與之相反,他反對離開物空談道理,要指物所言,以物為本。因為“道”作為世界最高的統一性原理,與“物”之間形成了原理與實體的關系,因而葉適指出:“物之所在,道則在焉,物有止,道無止也,非知道者不能該物,非知物者不能至道;道雖廣大,理備事足,而終歸之于物,不使散流,此圣賢經世之業,非習為文詞者所能知也。”[2]702他針對理學的觀點,指出了“道”是要依存于物才能存在的,沒有不依存在物之上而獨立存在的道。
葉適以這一觀點為基礎,主張要“驗于事,考于器”,通過“考詳天下事物”來求得“道”和“理”。“考詳天下事物”以事物為前提,站在了理學以心性為前提的對立面,提出了“內外交相成”的唯物主義認識論。葉適的認識論,是道器合一思想在認識論上的表現。肯定道在物中,是認識的前提。葉適認為,人的認識首先來源于客觀世界,人通過耳目之官接觸外物從而獲得感覺、知覺,“夫欲折衷天下之義理,必盡考詳天下之事物而后不謬。”[1]614就是說,認識的來源和對象是客觀世界和具體事物,要認識天下萬物及其規律,就必須于物求知,要依據事物的真實面貌來反映事物,通過考察天下萬物才能得出正確的結論,不能憑自己的主觀臆斷來論證事物,也沒有離開萬物的先天固有的虛知、空知。然后通過思維器官的思考將外界的、從客觀世界所得來的認識進行加工而成為知識,即“自外入以成其內”與“自內出以成其外”的內外結合,“內外交相成”而取得知識。所謂的“內外交相成”就是葉適所提出的耳目與心官并用:前者所得為見聞之知,后者所得為義理、心性之知;前者相當于感性認識,后者相當于理性認識;前者自外入內,后者自內出外;二者交互作用,溝通心與物的聯系。葉適說:“耳目之官不思而為聰明,自外入以成其內也;思曰睿,自內出以成其外也。故聰入作哲,明入作謀,睿出作圣,貌言亦自內出而成于外。古人未有不內外交相成而至于圣賢,故堯、舜皆備諸德,而以聰明為首……蓋以心為官,出孔子之后,以性為善,自孟子始。”[2]207
葉適認為構成世界的基本物質是八物,氣又是構成八物的根源。他說:“夫天、地、水、火、雷、風、山、澤,此八物者,一氣之所役,陰陽之所分,其始為造,其卒為化,而圣人不知其所由來者也。因其相摩相蕩,鼓舞闔辟,設而兩之,而義理生焉,故曰卦”[1]696。從中我們可以了解,八物其實是“一氣之所役,陰陽之所分”,“其始為造”,并且不斷地“相摩相蕩,鼓舞闔辟,設而兩之”,這是說八物是由于陰陽二氣的互相摩蕩,有開有合而產生的,而八物最終又生化為氣,故“其卒為化”。“氣分陰陽”就是說,世界上一切的事物永遠都是一分為兩,永遠也不會有絕對單一的東西,葉適認為“凡物皆兩”,他說:“道原于一而成于兩。古之言道者必以兩。……交錯紛紜,若見若聞,是謂人文。”[1]732就是說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一切事物的形狀、性質都是由相互對立的兩個方面所組成的,這種“交錯紛紜”的狀況,就叫做“人文”。這種“一分為兩”,“所以通行于萬物之間,無所不可,而無以累之,傳于萬世而不可易”[1]732是普遍的,又是永恒的。因為“凡物皆兩也”,所以葉適認為:“天下不知其為兩也久矣,而各執其一以自遂。”[1]732這種片面的思想,片面的思維方法就是只見一面,不見對面,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這種思維方法的結果是“天道窮而人文亂也”。葉適在看到“凡物皆兩也”的同時,還指出了“一氣之所役,陰陽之所分”是導致運動的內部原因,萬物都是在不斷運動變化的,因而葉適說“萬物皆變”,無一例外。
二
葉適的道器合一思想對其發展的文學觀的形成具有十分重要的影響作用,是其發展文學觀的哲學基礎與理論淵源。葉適以發展的觀點看待世界,認為世界是永恒的運動與相對的靜止所構成,在這種哲學觀點的指導下,他形成了尊古又不陋今、強調發展的詩學觀點。前文引用的“夫形于天地之間者,物也”、“物之所在,道則在焉”來說明他的唯物主義傾向的兩句話,恰巧出自他的詩論。古詩到了周代能開始流行,是因為存在于物中的理是不可亂的。人們通過物之情,認識物之理,而對事物細致描繪充滿了物之情的詩歌,自然就成了可以解釋物之理的手段了。葉適總結了古代至當時的整個詩歌發展歷史,指出:“孟子言‘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后《春秋》作’。《春秋》作不作,不系《詩》存亡,此論非是。然孔子時人已不能作詩,其后別為逐臣憂憤之詞,其體變壞;蓋王道行而后王跡著,王政廢而后王跡熄,詩之廢興,非小故也。自是詩絕不繼數百年。漢中世文字興,人稍為歌詩,既失舊制,始以意為五七言,與古詩指趣音節異,而出于人心者實同。然后世儒者,以古詩為王道之盛,而漢魏以來乃文人浮靡之作也,棄而不論,諱而不講,至或禁使勿習;上既不能涵濡道德,發舒心術之所存,與古詩庶幾,下復不能抑揚文義,鋪寫物象之所有,為近詩繩準,塊然樸拙,而謂圣賢之教如是而止,此學者之大患也。”[2]700-701詩歌的體制由古至今發生了諸多變化,“舊制”一次次地被新的形式所替代,然而,古今之詩,雖“指趣音節”不同,“而出于人心者實同”。從這一點上來說,古今之詩應是具有同等價值意義的,不應當象理學家認為的“古詩為王道之盛”。因此葉適對于“自古樂府至本朝詩人,存其性情之正、哀樂之中者,上接古詩,差不甚異,可與學者共由”[2]701的做法十分贊同。
葉適能夠以發展的眼光看待詩歌的發展,就是對不同時期的各家各派的詩歌都能發現其中的價值,“后世詩,《文選》集詩通為一家,陶潛、杜甫、李白、韋應物、韓愈、歐陽修、王安石、蘇軾各自為家,唐詩通為一家,黃庭堅及江西詩通為一家。人或自謂知古詩,而不能知后世詩,或自謂知后世詩,而不能知古詩,及其皆知,而辭之所至皆不類,則皆非也。韓愈盛稱皋、夔、伊周、孔子之鳴,其卒歸之于詩,詩之道固大矣,雖以圣賢當之未為失,然遂謂‘魏晉以來無善鳴者,其聲清以浮,其節數以急,其辭淫以哀;其志弛以肆,其為言亂雜而無章’,則尊古而陋今太過。”[2]701這里對于只尊古詩而鄙今詩,和只學今詩而輕視古詩的做法都給予了批評,認為這樣做都是不全面的做法。宋人學詩,以學習白居易、姚賈、李商隱為開端,形成了江西詩派,但最后還是將目光投向晚唐,這一過程恰恰符合了葉適所提倡的唯物主義辯證法的發展觀,他認為萬物都是在不斷運動變化的,他說:“時常運而無息,萬物與人亦皆動而不止。”[1]156因此,詩歌風格也是在不斷發展演變的,古體詩、律體詩,江西詩派、晚唐體,這些都是詩歌發展的客觀表現。在律體詩“朽敗之余”,江西詩派起而彌補其“缺絕之后”,事物的永恒運動沒有窮盡,晚唐體又因糾正江西詩派而流行起來。新事物不斷地產生,代替舊事物的存在。葉適的運動發展觀很好地表現在了對詩歌理論的探討方面,因而他不拘泥于某一詩歌階段,在當時江西末流盛行時,提倡“永嘉四靈”的晚唐詩風以糾正江西的流弊,而在晚唐詩流行之際又能及時指出其存在的問題,追求更高的藝術境界。“四靈”反對理學詩派的“尊古”詩學觀,“情”被“理”所統轄,音樂美、形式美被枯燥的說理所代替,失去了詩歌的情韻美。他們與理學化詩風相抗爭,力圖突破詩歌的功利性,重新光大詩歌緣情、言情的特征。“四靈”以律體詩反對理學家提倡的古體詩,堅持“苦吟”精細的雕鏤詩歌。葉適的門人吳子良曾說:“水心之門,趙師秀紫芝、徐照道暉、徐璣致中、翁卷靈舒,工為唐詩,專以賈島、姚合、劉得仁為法,其徒尊為四靈。”[3]76從他的論述中我們可以知道他把四靈看作是葉適的門人,葉適支持四靈,有其哲學思想上的根源。他重世務,重功利,重外物的永嘉之學與程朱理學相對立,這就決定了他的詩學思想與如朱熹等正宗理學家是截然不同的。元人劉塤在《隱居通議》中提到:“永嘉有言:‘洛學起而文字壞。’”即認為理學家重道輕文的理論,妨礙了文學的發展。江西詩派后學多與理學家有聯系,有的本身就是理學家,他們以理學的誠心正意、窮理盡性為根本,加上黃庭堅的心性思想為宣傳理論,借助江西詩派以文為詩的形式,導致了詩道式微。因此,葉適對江西詩派提出的批評,也是對理學摧殘文學的否定,對恢復文學本真的審美價值的努力。明代學者徐學聚《兩浙名賢錄·趙師秀傳》中說:“自乾、淳以來,濂洛之學方行,諸儒類以窮經相尚,詩或言志,取足而止,固不暇如昔人體驗聲病律呂相宜也。潘檉出,始創為唐詩,而師秀與徐璣、翁卷、徐照繹尋遺緒,日鍛月煉,一字不茍下,由是唐體盛行。”[4]129這里同時也指出理學家“取足而止”忽視“聲病律呂”的文藝觀點,四靈興起唐體與學術思想界對理學的反撥聯系到了一起。葉適宣揚四靈的主張也同他哲學上與理學的爭論桴鼓相應。
三
葉適發展的文學觀也體現在對“永嘉四靈”的具體評價上。徐照、徐璣、翁卷、趙師秀四人,因其字號里都帶有一個“靈”字而被合稱為“永嘉四靈”。他們生活于12至13世紀的南宋永嘉地區,彼此旨趣相投,詩風相似,《四庫全書總目》中指出:“宋承五代之后,其詩數變,一變而西昆,再變而元佑,三變而江西。江西一派,由北宋以逮南宋,其行最久。久而弊生,于是永嘉一派以晚唐體矯之,而四靈出焉。”[5]217在針對江西詩派流弊而進行的詩風改革過程中,詩人們不斷探索,發現了晚唐詩歌的別樣味道,詩人楊萬里的《讀笠澤叢書》有:“晚唐異味同誰賞,近日詩人輕晚唐。”的詩句。四靈詩派也就是在這種條件下產生的。錢鐘書先生說:“一個學江西體的詩人先得反對晚唐詩;不過,假如他學膩了江西體而要另找門路,他也就很容易按照鐘擺運動的規律,趨向于晚唐詩人。”[6]因此,“永嘉四靈”反對江西、提倡晚唐不是突發奇想,而是有跡可循。
雖然,在眾多的以革新江西詩風為己任的詩人群體中,“永嘉四靈”只是不怎么起眼的一股小力量,但是,歷史卻給了他們一席之地,因為在光宗朝以后踏上詩壇的“永嘉四靈”,在以晚唐體糾正江西詩派的流弊的同時,也對晚唐詩作了深入的研究,對“晚唐體”有光大之功。葉適在《徐文淵墓志銘》中寫道:“初,唐詩廢久,君與其友徐照、翁卷、趙師秀議曰:‘昔人以浮聲切響單字只句計巧拙,蓋風騷之至精也。近世乃連篇累牘,汗漫而無禁,豈能名家哉!’四人之語遂極其工,而唐詩由此復行矣。”[1]490“永嘉四靈”在青年時期互相進行著文學的交流,從葉適的話中我們可以看出,在那個時期,江西詩派已墜入“連篇累牘,汗漫無禁”的末流之中,影響力所剩無幾,“永嘉四靈”繼承了中興詩人們以學晚唐來糾正江西詩風流弊的道路,深入發掘,許棐說“永嘉四靈”的詩為“玉之純、香之妙者”,正是針對江西的破律、拗律,“永嘉四靈”以“浮聲切響”的傳統,以音律和諧為詩之規范,不斷地通過鍛章琢句的努力,“語遂極其工,唐詩由此復行”。可見,“永嘉四靈”把對于晚唐詩的學習落到了實處,在倡導晚唐詩風的過程中十分用心,作出了極大的努力。
宋代詩歌經歷幾代人的探索開拓,形成獨立于唐詩的風格體制,是詩歌合理的邏輯發展的結果,其存在有自身的價值和理由,同時,發展過程中也產生了一些偏頗與缺失,于是才有了不同角度的探索與改革的途徑。葉適與“永嘉四靈”所選擇的道路從本質上動搖了宋詩形成的主流的傳統,向唐音回歸為宋詩的進一步發展開辟道路。在江西詩派的作品已經為人們所厭倦之后,四靈以自身詩作的清新秀麗給人們耳目一新的感覺。當時詩壇可謂“南宋詩流之不墨守江西派者,莫不濡染晚唐。”[7]然而,這種新鮮也不是永恒的,加上“永嘉四靈”詩作取境狹窄的缺陷,人們也對其感到單調乏味了。趙汝回《云泉詩序》曾指出:“世之病唐者,謂其短近,不過景物,無一言及理。”說明了“永嘉四靈”偏重寫景而很少關注人心靈的感受。葉適對于這種缺陷并非無動于衷,對此,他起初認為是扭轉江西詩風的無拘無束的特色,有鼓勵的意味,他曾說“然則所謂專固而狹陋者,殆未足以譏唐人也”[1]490,但葉適后來又對四靈的詩作表現一些不滿:“木叔不喜唐詩,謂其格卑而氣弱,近歲唐詩方盛行,聞者皆以為疑。夫爭妍斗巧,極外物之變態,唐人所長也;反求于內,不足以定其志之所止,唐人所短也。木叔之評,其可忽諸!”[1]221他對唐詩的一些不足已經有所認識,這一點在很大程度上可能受到了宋詩重視人格道德的內在之志風格的影響。這說明葉適對唐體的缺陷是十分清楚的,對唐詩和宋詩特質的把握相當精辟中肯。
總之,葉適道器合一思想是其文學發展觀的重要理論依據,他的發展的文學觀與當時的文學環境相結合,就自然會發現“永嘉四靈”的優長與不足,所以在南宋的文壇上才能因葉適的影響而留下“永嘉四靈”的一席之地,同時,在其談論“永嘉四靈”的話語間也使他的詩論與學術思想再次得到了統一。
[1]葉適.葉適集 [M].北京:中華書局,2010.
[2]葉適.習學記言序目[M].北京:中華書局,2009
[3]吳子良.林下偶談[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76.
[4]徐學聚.兩浙名賢錄[M].濟南:齊魯書社,1997.
[5]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M].北京:中華書局,2003.
[6]錢鐘書.宋詩選注[M].北京:三聯書店,2002:254.
[7]錢鐘書.談藝錄[M].北京:中華書局,1984: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