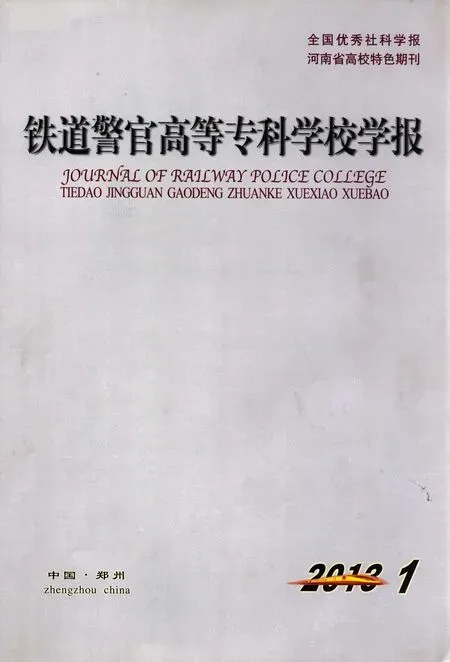新刑事訴訟法對偵查權的“限制”與“擴張”之剖析
海娜仁,李 青
(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北京100038;河南警察學院,河南鄭州450046)
我國《刑事訴訟法》制定于1979年,1996進行了第一次修改,本次修改是時隔16年之后的第二次修改。本次刑事訴訟法的修改,總結并吸收了改革開放30多年來的實踐經驗、改革成果和理論成果,是我國刑事訴訟制度的創新和突破。就偵查權而言,刑事訴訟法的修改對偵查的影響是全方位的,既有限制性條款,也有擴張性條款。適應新刑事訴訟法的新要求、進一步完善偵查工作是擺在偵查機關面前的新課題。
一、偵查權“限制”與“擴張”解讀
偵查是刑事訴訟的重要程序,在刑事訴訟中起著承上啟下的作用。由于我國特殊的刑事訴訟制度,相對于起訴和審判,偵查顯得尤為重要。偵查權歷來是理論界和實務界爭議最大的問題,其核心就是“限權”和“擴權”。
(一)偵查權
1.偵查權的概念。準確界定偵查權的概念是研究偵查權的基礎。美國法律哲學家埃得加·博登海默說過:“概念乃是解決法律問題所必需的和必不可少的工具,沒有限定嚴格的專門概念,我們便不能清楚地和理性的思考法律問題。”[1]
國內外學術界對偵查權的概念持有不同的觀點,未形成共識。本文中只列舉其中的幾個觀點,以作參考。在英美國家,人們通常把偵查權(Power of Investigation)與調查權(Investigatory Pover)互用,一般解釋為“授予政府機構的檢視和迫使透露與調查相關的事實的權力”[2]。我國臺灣學者認為:“偵查權屬于檢察官、司法警官及司法警察,乃為實施偵查上一切處分之權也。亦系公訴權作為之一種,受處分者應有服從之義務,故偵查機關刑事偵查權有絕對性,不以刑罰權存在為必要,即知有犯罪嫌疑者,應實施偵查。”[3]我國大陸學者多從權力的主體、目的、內容來界定偵查權,如有學者認為:“偵查權是依照法律對刑事案件進行專門調查工作,以收集證據、查明案件事實和查獲犯罪人,以及采取強制措施的權力。”[4]
司法實踐是以法律為導向的,關于“偵查權是什么”的問題,最好以法律規定作為參考。2012年新《刑事訴訟法》第106條第1款規定:“偵查是指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在辦理案件過程中,依照法律進行的專門調查工作和有關強制性措施。”根據刑事訴訟法的規定,除了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國家安全機關、監獄和軍隊保衛部門也有偵查權。因此,筆者認為,偵查權是指偵查機關依法享有的進行專門調查工作和采取有關強制性措施的權力。
2.偵查權的基本內容。偵查權的基本內容解決的就是偵查機關可以做什么的問題。國內學者普遍認為偵查權的內容就是偵查機關為了查明和證實犯罪、查獲犯罪嫌疑人而采取的一些專門調查和有關強制性措施的權力。一般意義上偵查權包括:傳喚權,訊問犯罪嫌疑人權,詢問證人、被害人權,勘驗、檢查、搜查權,扣押物證、書證權,鑒定權,通緝權,采取技術偵查措施權,采取強制措施權。有的學者認為,上述權力是屬于偵查行為權,偵查權不僅包括上述偵查行為權,還應包括偵查啟動權和偵查終結權[5]。
(二)偵查權的“限制”與“擴張”
權力是利與弊的統一體,一切權力都面臨著“限權”和“擴權”問題,偵查權也一樣。偵查權作為一種公權力,如果合理使用能夠有效地打擊犯罪、維護社會穩定,相反,若使用不當會侵害人權、破壞社會和諧。因此,如何做到“限權”和“擴權”的平衡是立法界和司法界共同面臨的問題。
1.偵查權的“擴張”及其意義。偵查權的擴張是指偵查機關所行使的偵查權力的增多或者是強化。偵查權是一種國家公權力,打擊犯罪是偵查的主要任務,偵查權大小應與打擊刑事犯罪需要相適應。當前我國正處在社會轉型時期,刑事犯罪形勢嚴峻、打擊難度較大。因此,從打擊犯罪的角度來看必須根據形勢的需要適當的“擴張”偵查權。只有有了法律的保障,偵查機關才能更好地打擊犯罪、維護社會治安。
2.偵查權的“限制”及其意義。偵查權的限制是指通過法律及其他手段對偵查權的行使進行約束和監督。英國歷史學家艾克頓認為:“權力傾向于腐敗,絕對的權力傾向于絕對的腐敗。”偵查權作為公共權力具有“天然”的擴張傾向,公共權力既是個人權利的保護神,又是個人權利的最大最危險的侵害者。近幾年來不斷出現的冤假錯案,不僅侵害了公民的權益,而且降低了司法公信力。偵查是起訴和審判的基礎,對冤假錯案的發生偵查機關具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因此,從偵查法治化和保障人權的角度來看必須對偵查權進行“限制”。監督不到位的權力是可怕的權力,對帶槍的權力行使者監督不到位就更加可怕[6]。
偵查權是一個歷史范疇,也是一個地理或者文化的范疇。偵查權的限制和擴張都不是絕對的,限制是擴張下的限制,擴張是限制下的擴張。正是在這種不斷的“限制”和“擴張”中權力行使才會更加合理。
二、新刑事訴訟法對偵查權的“限制”與“擴張”性規定
2012年刑事訴訟法的修改是我國多年司法改革的經驗總結及法治文明發展的重要標志。新刑事訴訟法對偵查程序的改革較多,對偵查權作了適當的“限制”和“擴張”,充分體現了刑事訴訟之打擊犯罪和保障人權的雙重價值。
(一)新刑事訴訟法對偵查權的“限制”性規定
新刑事訴訟法對偵查權的限制性規定主要概括為以下幾個方面。
1.偵查階段辯護律師權利的增加。本次刑事訴訟法的修改在1996年刑事訴訟法的基礎上進一步加強了控辯對抗。新刑事訴訟法中不僅規定偵查階段律師成為辯護人,而且賦予了較多的權利。主要有:一是,犯罪嫌疑人自被偵查機關第一次訊問或者采取強制措施之日起,有權委托律師作為其辯護人,律師辯護權從審查起訴階段提前至偵查階段;二是,賦予辯護律師在偵查階段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幫助、代理申訴、控告、申請變更強制措施、向偵查機關了解案情和提出意見等各項權利;三是,除第37條第3款規定的三種特殊案件的辯護律師在偵查階段會見犯罪嫌疑人要取得偵查機關同意外,其他案件的律師均可直接會見在押犯罪嫌疑人,會見時不被監聽。辯護律師還有與在押犯罪嫌疑人通信的權利。
新刑事訴訟法不僅規定犯罪嫌疑人在偵查階段可聘請辯護律師,而且賦予了辯護律師更多的權利。偵查階段辯護律師的介入為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權利提供了法律依據,解決了長久以來“辯護難、會見難”的問題。然而,偵查階段辯護律師的介入及會見權的擴大對偵查工作來說是一種挑戰,增加了偵查取證的難度。
2.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確立。“非法證據排除”的入法是新刑事訴訟法的一個亮點。針對偵查機關偵辦案件過程中存在的一些違規操作情況,為避免冤假錯案的發生,新刑事訴訟法明確規定對于通過非法手段收集的證據予以排除。主要包括:一是偵查機關嚴禁以非法手段收集證據;二是對偵查機關通過非法手段和非法程序所獲得的證據予以排除;三是人民檢察院對偵查機關收集證據的合法性進行調查核實和追究責任;四是法庭上在對收集證據的合法性有爭議時偵查人員應出庭說明情況。
新刑事訴訟法對非法證據排除問題作了較詳細的規定,為司法實踐中防止偵查機關非法取證、檢察機關和法院果斷排除非法證據提供了法律的保障,也是限制偵查權、規范偵查權的重要舉措。
3.對偵查訊問工作設置了諸多限制。口供歷來是刑事訴訟重要證據之一。犯罪嫌疑人口供的獲取是偵查工作的重要內容。犯罪嫌疑人都有趨利避害的心理,因怕受到刑罰的處罰,誰都不會輕易交代自己的罪行。在這種情形下,刑訊逼供成了獲取口供的常用手段。從近幾年發生的錯案來看,刑訊逼供是造成錯案的重要原因,它使偵查訊問的合法性受到了諸多質疑。新刑事訴訟法對偵查訊問設置了諸多限制性規定,以便規范訊問工作、保障人權。主要有:一是,新《刑訴法》第50條規定,不得強迫任何人證實自己有罪;二是,對在押犯罪嫌疑人的訊問一律在看守所進行;三是,偵查人員在訊問犯罪嫌疑人時可以對訊問過程錄音錄像,對可能判處無期徒刑、死刑的案件或其他重大案件的訊問,應全程錄音錄像。
當前,我國偵查實踐已有訊問同步錄音錄像制度,尤其在檢察機關自偵案件的偵查中訊問同步錄音錄像較普遍。新刑事訴訟法中對訊問影響最大的是“不得強迫任何人證實自己有罪”的規定。該規定有利于禁止刑訊逼供、保障人權,也加大了偵查訊問工作的難度。
(二)新刑事訴訟法對偵查權的“擴張”性規定
刑事訴訟法從1996年修改到本次修改時隔16年。16年間,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有了巨大的變化,刑事犯罪也出現了新情況、新形勢,現行刑事訴訟法中有些規定已經滿足不了打擊犯罪的現實需要。犯罪形勢是調整偵查權的基礎。針對我國刑事犯罪形勢嚴峻,犯罪種類、手段翻新,打擊難度大等情況,有必要對偵查權進行適度“擴張”。新刑事訴訟法對偵查權的“擴張”性規定有:
1.賦予了偵查機關技術偵查權。我國立法領域和學術界,對秘密偵查和技術偵查沒有嚴格的區分,常常把二者混合使用。技術偵查措施的概念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上的技術偵查措施指偵查活動中的一切具有技術內涵的調查事實、收集證據、查獲犯罪嫌疑人的方法,即技術性實施的偵查措施和一部分秘密偵查措施。狹義上的技術偵查措施指的是偵查機關運用技術裝備調查作案人和案件證據的一種秘密偵查措施。后者包括電子監聽、秘密錄像、秘密拍照、用機器設備排查、傳送個人情況數據以及用機器設備對比數據等手段[7]。有學者認為秘密偵查措施主要包括三類:技術類偵查措施(電子偵聽、電話竊聽、電子監控、秘密拍照或錄像、郵件檢查等),誘惑類偵查措施(如機會提供型引誘、虛示購買、控制交付等),派遣秘密調查人員類偵查措施(包括線人、特情、臥底偵查員等)[8]。
新《刑事訴訟法》第148條至第152條對偵查機關采用技術偵查措施問題作了較詳細的規定。主要內容有:一是,可以采取技術偵查措施的主體是公安機關和人民檢察院;二是,可以使用技術偵查措施的案件種類有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動犯罪、黑社會性質的組織犯罪、重大毒品犯罪、其他嚴重危害社會的犯罪案件,重大的貪污、賄賂犯罪案件,利用職權實施的嚴重侵犯公民人身權利的重大犯罪案件;三是,通過技術偵查措施獲得的材料只能用于偵查、起訴、審判,并且對技術偵查中得知的秘密加以保密;四是,偵查機關在特定情況下可以采取隱匿偵查措施和控制下交付措施;五是,通過技術偵查措施收集的材料在刑事訴訟中可以作為證據使用。
2.完善了證據種類。新刑事訴訟法在原有證據種類的基礎上增加了辨認筆錄、偵查實驗筆錄及電子數據三種證據。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的發展,刑事犯罪呈現出越來越隱蔽、智能化、科技化的趨勢,偵查中可獲取的傳統證據越來越少,電子數據等新型證據反而越來越多。新刑事訴訟法對證據種類的完善為偵查中收集一些新型證據提供了法律依據,有助于解決取證難、證明難的問題。
3.適度放寬了一些強制措施。新刑事訴訟法從我國當前打擊犯罪的實際需要出發,并在充分考慮保障人權的基礎上適當放寬了一些強制措施。一是,傳喚、拘傳時間延長。新《刑訴訟》第117條規定:“傳喚、拘傳持續的時間不得超過十二小時;案情特別重大、復雜,需要采取拘留、逮捕措施的,傳喚、拘傳持續的時間不得超過二十四小時。”新刑訴法把傳喚、拘傳的最長時間從十二小時延長至二十四小時,使偵查人員有更多的時間對犯罪嫌疑人進行訊問以及進行其他的調查取證活動,是對偵查權的適度擴張。二是,監視居住的有關規定。新《刑事訴訟法》對監視居住作出了比較詳細的規定,有利于監視居住的規范化。新刑事訴訟法第76條規定,在偵查期間可以通過電子監控、不定期檢查等方法對犯罪嫌疑人進行監督,并可以對其通信進行監控。這些規定在規范監視居住的同時也適當擴寬了監視居住中偵查機關的權力,有利于打擊犯罪。
三、偵查工作如何適應修改后的新刑事訴訟法
新刑事訴訟法將從2013年1月1日起實施。新刑事訴訟法在適度強化偵查權的同時,也為偵查工作提出了更多更高的要求。偵查人員應該正確認識刑事訴訟法修改的重要意義,并在偵查中認真落實新刑事訴訟的相關規定。
(一)正確認識刑事訴訟法的修改
法律的修改是指對已頒行的法律文件進行修訂、改變的一種立法活動[9]。一方面,法律作為具有強制性、權威性的行為規范,要充分發揮其對社會主體的規范、引導和調整作用,就必須具有一定穩定性;另一方面,法律的價值和生命在于對社會關系的有效調整,而社會關系是不斷變化著的,為了有效調整變化了的社會關系,需要對法律進行適度的修改。本次刑事訴訟法的修改是新時期保障人權和打擊犯罪訴求的體現。修改后的刑事訴訟法充分體現了打擊犯罪和保障人權的雙重價值訴求,不僅順應民意,也順應了司法需求。偵查人員應站在人權保障和偵查法治化的高度去領會刑事訴訟法修改的重要意義。
(二)革新偵查觀念
新刑事訴訟法對偵查程序作了較多的修改,無論是限制性條款還是擴張性條款,都是法律的進步,二者沒有截然的界限,限中有擴、擴中有限才是真實的。偵查人員應改變傳統觀念,樹立正確的偵查理念。具體有:一是強化偵查程序意識。實踐中出現的違法偵查行為大多由片面追求實體真實的觀念引起,因此,有必要在觀念上強化對偵查程序的正當性意義的認識,牢固樹立程序意識,在偵查中自覺遵守程序法規則。二是樹立偵查均衡意識。偵查過程涉及多種價值的選擇和均衡問題,對此,偵查人員有必要樹立一種均衡價值觀。“均衡價值觀不為秩序、公正、效率確立一種不變的價值等級,也不承認實體正義或程序正義,控制犯罪或保障人權哪一個方面絕對優越……而是注重基于具體條件和個案情況的不同,從符合更高層次利益的角度來確定各種利益的優劣”[10]。三是強化偵查證據意識。由于歷史傳統和法律文化的消極影響及證據制度的不完善,偵查工作中還殘留著“重口供、輕證據”的積習。在新刑事訴訟法完善證據種類的契機下偵查人員應進一步強化證據意識,提高獲取證據的能力。
(三)豐富和發展偵查措施
修改后的刑事訴訟法對偵查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時給予偵查機關采取技術偵查措施的權力。隨著社會的發展,刑事犯罪隱蔽性、智能性、多變性程度越來越高,單純依靠傳統的偵查手段已經難以滿足打擊犯罪的需要。新刑事訴訟法賦予了偵查機關采取技術偵查措施的權力,從而結束了近年來技術偵查措施的尷尬地位。然而,技術偵查措施的使用具有嚴格的法律限制,具有局限性。在嚴格按照法律的規定使用技術偵查措施和常用措施的基礎上,應進一步豐富偵查措施,根據個案特點交替使用各種偵查措施。例如,新刑事訴訟法把辨認筆錄和偵查實驗筆錄列入刑事證據,因此,今后偵查中應該適當增加辨認和偵查實驗等偵查措施的使用。
(四)提高偵查人員的素質和能力
偵查工作的最終實施者是偵查人員,偵查人員的素質和能力直接影響著偵查工作水平。偵查人員在正確認識新刑事訴訟法的重要意義的基礎上,從偵查工作的實際和刑事訴訟法的要求出發,需要不斷提高自身的素質和能力。偵查機關要加強偵查隊伍建設,強化崗位練兵和業務培訓,切實增強偵查人員在發現偵查線索,收集、固定、鑒別和使用證據,運用偵查策略、強制性偵查措施和高科技偵查手段等方面的能力。
新刑事訴訟法以國家立法的形式體現了近十幾年來我國司法改革的成果,對于建設公正高效權威的刑事司法制度具有重要而深遠的意義。然而,新刑事訴訟法效能的發揮要依靠各司法機關對新刑事訴訟法的充分領會和認真落實。美國學者富勒說:“官方行為和法律之間的一致性是具備法治品德的法律制度的構成要素之一,而且是構成法律的內在道德的全部要素之中最復雜的一環。”[11]
[1][美]埃德加·博登海默.法理學——法律哲學與法律方法[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63.
[2]毛立新.偵查法治研究[M].北京: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8.14.
[3]刁榮華.刑事訴訟釋論(上)[M].臺北:漢苑出版社,1978.295.
[4]楊春洗.刑事法學大辭書[M].南京:南京法學出版社,1999.645.
[5]王德光.偵查權原理——偵查前沿問題的理性分析[M].北京:中國檢察出版,2010.7.
[6]王德光.偵查權原理——偵查前沿問題的理性分析[M].北京:中國檢察出版社,2010.304.
[7]唐金穎.淺談技術偵查措施在職務犯罪中的適用和完善[J].活力,2009,(6):199.
[8]唐磊,趙愛華.論刑事司法中的秘密偵查措施[J].社會科學研究,2004,(1):69.
[9]李友根.論法律的修改[J].江蘇社會科學,1996,(2):39.
[10]宋英輝.刑事訴訟目的論[M].北京: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1995.206.
[11][美]富勒.法律的道德性[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