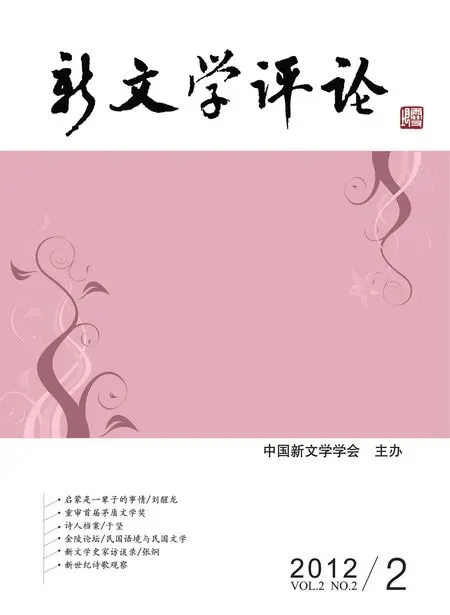武田泰淳與阿Q
——“自我”的分裂與浮游
◆ [日]王俊文作 張瑤譯
武田泰淳與阿Q
——“自我”的分裂與浮游
◆ [日]王俊文作 張瑤譯
前 言
對于在日中戰爭后更改志向從中國文學研究者變為專業作家的武田泰淳(1912—1976年)而言,魯迅是一個讓他畏懼的存在。在《L恐懼癥》(L恐怖癥《近代文學》1949.10)中,泰淳描述了敘述者“我”因魯迅“揭露出其非文學者”所遭遇的恐懼、即魯迅的威壓之感。而魯迅筆下的小說人物中,泰淳尤其關注的是阿Q。關于阿Q,泰淳說他是魯迅“因苦澀和熱淚而面容緊皺,無可奈何地讓其登場”的“弱者中的弱者、悲慘人類中最為悲慘的類型”①。泰淳秉持的創作方法是“一定要將自己置于最低層”②,因此他被阿Q所吸引是理所當然的。這一問題對于理解辨明泰淳的文學觀十分重要。
但是,言及泰淳對阿Q的理解以及“阿Q”對其創作所產生影響的研究幾乎不見。本稿在整理泰淳評論阿Q的文字的基礎上,通過分析其早期小說《機靈的野獸》(利口な野獣1948.3)③與《風媒花》(『風媒花』1952)④中所出現的“Q”,來考察泰淳文學中“自我”的存在方式。本稿將就泰淳如何受到魯迅影響,以及力圖塑造出異于過去私小說的“自我”⑤的泰淳是如何通過創造出“具有無數無限可能性的‘我’”⑥、從而確立起戰后派作家自我認同這兩個問題進行討論。考察泰淳文學中“阿Q”的影響,將給我們提供一種可能性去迫近混沌一片的泰淳文學世界的核心。
一、泰淳的阿Q論
在泰淳論及中國文學的作品之中,言及阿Q的作品有以下七篇。
⑦《對談 生命的歷史—宗教和文學— 阿Q正傳》(與宗正元的對談),(「対談·いのちの歴史―宗教と文學―·阿Q正伝」(宗正元との対談)),《真宗》,1970年1月、2月、3月。(Z未收,《自我中的地獄》(『私の中の地獄』),筑摩書房,1972年4月)
本節將根據這七篇作品來探討泰淳的魯迅觀以及阿Q觀。
泰淳首先指出透徹審視人與社會動態的魯迅的“老成不狂”(上文所列①《中國文學與人學》,以下僅標記序號,省略作品名)的冷眼。進而泰淳認為魯迅之所以讓阿Q這個角色登場是因為他本人“看到了”辛亥革命的失敗(⑤),泰淳把阿Q定位為“前現代性的中國生活的愚劣”(②)之象征。“弱者之中的弱者”(①)、“徹頭徹尾的愚者”(③)的阿Q被“革命”排除在外、“稀里糊涂地被槍決”(④⑦),而對于輕蔑無視阿Q的所謂“讀書人”,魯迅的批判十分激烈。對此泰淳提出如下意見。魯迅不會原諒那些“在變革之后的社會中取巧存活的”“機靈的人們”(⑥),因為“幸存的他們佯裝不知自己身上潛藏的阿Q性,只不過是蒙混過關罷了”(④)。與之相對,魯迅則把“剝離阿Q肉身上浸染的舊惡、以及從這種惡出發來變革自我的過程定為自身文學修行的道路”(②)。也即,魯迅對于不能正視自身“阿Q性”的知識人,難以抑制厭惡情緒。
除以上阿Q和偽革命者(知識分子和先前的統治者)的對比以外,泰淳還強調魯迅文學中阿Q與村民(看客們)之間的對比,并對描繪這一對比的魯迅“強烈的生的實感”(③⑦)予以關注。這一點可謂泰淳阿Q論的特點。例如,相較“阿Q與村民的對比”,泰淳的終身摯友、魯迅研究專家竹內好則更重視“利用愚弱的聰明人強者”之偽革命者與“因憧憬強勢而被封閉于弱勢中的奴隸的象征”之阿Q之間的對比⑦。
如上所述,泰淳一方面強調以知識分子為主的“偽革命者”身上的“阿Q性”,另一方面從阿Q與村民的對比這一獨特的視角出發,提出了浮游于村鎮的統治者和村民之間的嶄新的阿Q形象。
二、分裂——“Q”=作為“機靈的野獸”的“自我”=“蟲”/“狼”
(一)從私小說的“真誠”到戰后文學派的“自我分裂”
戰后,作為小說家躋身文壇的泰淳帶著戰后文學派作家這一強烈的自我定位,懷抱雄心壯志,力圖開拓出異于戰前“私小說”的新的文學。不過,雖然希望與“私小說”完全決裂,但是泰淳對于“私小說”的“真誠”與“不食人間煙火中的濃烈凡人氣味”仍然心懷敬愛,這一點正是泰淳的獨特之處⑧。對于“私小說”的這一矛盾態度決定了泰淳會執著于“書寫自我”。
泰淳反復強調,在上海所經歷的戰敗體驗是使自己(能)成為小說家的決定性契機。經歷戰敗,泰淳感受到“被世界所遺棄”、“日本人的事情只有日本人可以書寫”,從而成為作家,并認識到“就算是真正意義上既不強悍又不正確的人,也還有可寫的東西”。因此,泰淳把“書寫自我”當作依憑⑨,主張“作家的生活方式”就是“寫盡自我”⑩。
另一方面,泰淳通過強調以往私小說的“自我”與戰后文學派中的“自我”的分歧,用以確立“戰后派作家”的自我認知。例如,他認為日本私小說所嘗試的方法是,“作為人類一員的‘自我’有時候被認為是悲慘的,有時候被認為是可怕的存在,通過表現與告白‘自我’,從這一吐放惡臭的小雜貨店中,導引出全新的人論”,私小說的方法乃是“現代性自我的發現”、“個人主義的追求”。而與戰前私小說類型作品的最高峰、志賀直哉的《暗夜行路》僅關注“潔癖和誠實”不同,戰后文學派作家筆下的“自我”是“私小說的‘自我’所無法想像的,他們膨脹、變色,力圖脫離“私小說的‘自我’,因而呈現異樣復雜的生物樣態”。之所以會如此,乃是由于“‘自我’、‘日常’、‘真誠’與糾結扭曲的現實社會大漩渦之間不可能毫無關系。”換言之,對于因經歷戰爭和戰敗而將“無法相信人類”作為自身出發點的戰后派作家而言,“‘自我’決不是永恒不變的安定的存在”,而是“具有無數無限可能性的‘自我’”。
泰淳作為國家權力駐外機關的職員在國際都市上海迎接日本戰敗,是戰后派作家之中有著獨特經歷的一位。他之后回想道:戰敗所帶來的日本人地位的逆轉“映照出了第三第四個‘自我’”。他之所以創造出無數個“自我”,同時也是身份認同的確保與超越。“作家堅持自身統一性的努力,以及從這一自身中擺脫出來的努力。……正是這一過程讓他創造出他的‘自我’”。泰淳還主張,與社會學家不同,“就小說家而言,要背負自身無法解決的矛盾和對立才更為可靠。”
綜上所述,對于泰淳來說,“自我”是區隔于私小說作家的“自我”、并非巋然不動的表白和“自我陷落”的對象,而是蘊含著不斷變化可能性的存在。“‘我’并不單是一個獨立的人,而是被放置在復雜社會中的”“‘奇妙的生物’”。而作家便是通過和這樣的“我”相廝磨來體驗內部的分裂和外在的擴散,從而創造出自己的未來性。
(二)作為“機靈的野獸”的“Q”
泰淳描寫這一身份認同探索過程的作品是小說《“愛”的形式》。這篇作品是以泰淳從上海歸國后所經歷的“不可思議的四角戀愛”為藍本寫作而成的。對于小說的主題,佐佐木基一這樣指出:“通過描述男女間愛的形式漸漸變得曖昧、稀薄的過程,著眼點放在刻畫主人公一邊對自身進行分析,同時極大拓展內心、并且變得堅強”。可以說小說的主題是通過痛苦的戀愛體驗而進行的自我分析和自我確認。
泰淳在創作談中表示,基于真實體驗的這篇小說之所以能從緊密依附于體驗的私小說性的狀態之中解放出來,乃是由于提煉出了“危險的物質”和“機靈的野獸”這第二和第三個“我”的緣故。用小說的原話來說,所謂“危險的物質”是“由于動物性能量過弱而產生的惡”(250頁),“懶得做事,又對一切都謹慎小心”的“平時的自己”(242頁)。而所謂“機靈的野獸”是指酒醉的“我”。“機靈的野獸”中的“機靈”是指“酒醉后多少變得粗暴或人事不清這一點被認為好似野獸”,而且“在戀愛中不會受到傷害,也不會有什么損失”(247頁)的不純的戀愛態度;“野獸”是指“動物性能量過強產生的惡”(250頁),“厚顏無恥,什么事都干得出,毫無感覺”(237頁),有著“令人鄙夷的行動能力”(245頁)。
如前所述,發表在1948年3月號《新文化》上的短篇小說《機靈的野獸》,同年12月改名《我與“我”的對話》成為《“愛”的形式》的第三章。泰淳認為,小說的第三章最為重要。這一章由敘述者山下(原型為泰淳)的排便事件和四角戀關系中一環的木村(原型為堀田善衛)送來的絕交信所構成。值得注意的是,這篇小說中出現了“Q”這樣的記號,并且它在“我與‘我’的對話”中起到了核心的作用。
排便事件發生在“批評”同人們在有樂町為戰敗后從上海歸國的泰淳和堀田舉行歡迎會之時(1947年1~2月左右)。在歡迎會上泰淳突生便意,為“應急”他跑到黑暗的小巷里解決。可是之后當地的流氓闖入會場,命令泰淳“用雙手捧著排泄物,到數奇屋橋的溝里處理掉”。泰淳“順利地完成了此項工作”。
泰淳用Q這個記號來表示“糞/排便”。例如,主人公兼敘述者的山下這樣說明。“想要排便的不是我,而是‘我’。我是多么地厭惡糞這樣的詞語。諸如茅廁之類的語言,我一直決心終生都不會把這類丑惡的文字寫進我的文章中。我把它寫在這里是多么地不情愿!(我以后決定用Q來作為這個文字的羅馬字表記)”。(236頁)進而,小說中執拗地不斷描寫指尖那頑固而難以去除的Q(糞)的味道。山下逃出歡迎會的會場,帶著四角戀關系中的唯一女性町子進入了賣年糕小豆湯的小店,山下聞著抹茶的氣味,把手放在茶碗上時,突然想到了“Q”。他在洗手間“用自來水沖洗指尖,認真仔細地、不斷地洗。可是放在鼻子下時還是有味道。再洗,然后再聞,但仍然可以聞到味道”。最后他終于放棄,回到了座位上,“默默地注視著她的臉,一邊將手指尖滑進純白餐桌布上的漂亮的抹茶茶杯里面。慢慢地搓洗著手指尖,然后再換另一只手”。“我(指山下,下同——筆者注)把帶有抹茶濃郁香氣的手指尖靜靜地放到鼻子旁邊。這樣一來,那種古樸而沉靜的茶香就飄入了鼻孔。與此同時,剛才的氣味,也開始慢慢地、漸漸地變得強烈了起來。那種氣味還是固執地,如同現實本身一般,明明白白地,沒有離開我的手指尖”(241頁)。第二天,又“用香皂使勁清洗自己的雙手,終于聞不到昨日的氣味了。就這樣終于消除了那可惡的痕跡”(242頁)。
可見,作品執拗地描寫的“Q”,不僅單是表現糞的氣味的符號,而且從在小巷里排便、用雙手捧起自身排泄物這層意義來說,也是“厚顏無恥”“什么事都干得出,毫無感覺”的符號,即也是象征著“機靈的野獸”的“自我”的符號。
因此,“清洗手指=除去異味”這一行為非常具有象征意義,可以認為是一種試圖擺脫“自我”的行為。歡迎會的第二天,在木村送來的絕交信中,“Q”的氣味被當作是山下本身來描寫。在這封絕交信中,“Q”的“氣味”兩度登場。這兩處分別是,“你的手親熱地放在了町子的肩膀上——難道你忘了嗎——那是被你自己的污物污染過的手”(243頁,下劃線為原文所有,下同)。此外,“你仍然會同往常一樣毫無表情地讀這封信吧。而且,是用你昨天留有異味的那雙手打開,并把它握在手里。……我,對于你的那雙手,對于那雙手連接著的你的存在本身,感到無限的厭惡”(244~245頁)。也就是說,木村把殘留著“Q”氣味的山下的手與山下本人重疊在了一起。
讀過絕交信的山下對于木村“非常在意”的手說,“那手就是我自身這一事實是無法掙脫的”(245頁),消極地承認“機靈的野獸”這一“自我”的存在。此后,在這一章的最后一節有如下敘述:“我把自己看慣了的手提到離眼睛很近的地方。……微微地有些味道。……這不是昨天的氣味。……是我自身分泌的氣味。……是一種具有深邃的難以排除的意味的氣味。這種氣味讓我死心的同時又給我帶來安心的感覺。在不安的同時,又傳遞給我類似精力朝氣一樣的東西。給我了一種我和‘我’合二為一共同活下去所必需的奇妙力量”(245頁)。
可見,這段文字所描寫的是敘述者山下對由“Q”所象征的作為“機靈的野獸”的“自我”的全面并且積極的認可過程。
那么,想進一步推論的是,泰淳對于“Q”的這一用法——屬于多個“我”之一的“機靈的野獸”——與他的阿Q論或許存在關連。“我”的機靈的“無感覺”與阿Q的愚劣的“無感覺”雖然是有差異,但可以說兩者都是弱者為了生存下去而不得不采取的苦澀的策略。不僅如此,泰淳的自我分析是不是也有可能受到了“阿Q自身中存在的人的弱與丑”的觸發呢?雖說泰淳強調以知識人為主的“偽革命者”的“阿Q性”,但是欲冷靜地開刀解剖自身的個人主義時,阿Q也有可能提供了某種“啟發”。關于這個問題,在兩者表面上的相似點之外還需要進一步深入探討。為此筆者下面想從泰淳文學中的“蟲”的視角來進行分析。
(三)四分五裂的“自我”——“Q”、“蟲”、“狼”
泰淳在隨筆《追求自我》(1948.8)中,用獨特的比喻來表現作家所創造的“我”的本質。“作家被自己創造出來的多個‘自我’所包圍的樣子,與其說是享受天倫之樂的老人子孫滿堂的狀態,毋寧說更像是一位負傷者在看著從全身的傷口里爬出的蛆蟲的景象。恐怕作家從自己作品中的‘自我’所感受到的,是與負傷者相同的戰栗吧。”(參見前注10,115頁)換言之,對于泰淳來說,多個“自我”就像是從自己全身的傷口里爬出來的蛆蟲一樣的存在。
因此,泰淳文學中的“蟲”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例如,自傳性小說《異形人》(異形の者《展望》,1950.4,Z5)講述的是與泰淳相仿的二十歲前后的主人公糾結于社會主義者和少爺身份之間的故事,“簡直就像矛盾的標本那樣”,主人公的糾結被形容成一種“變形蟲的蠕動”。(60頁)此外,在1941年,也就是泰淳29歲那年,經歷了軍旅生活后歸國的泰淳對于打算奉獻出自己的青春乃至人生的中國文學研究,產生了深深的不安、焦躁以及無力之感,泰淳將那時的自己描繪為“蟲”。他說,“一想到都市的生活是由這么多無數的建筑物構成的,就感到個人如同蟲豸一般”,“覺得自己不就是已被驅逐而出的蟲子”,“在東京過著這樣的生活,粘附在中國文學之上的我們這些蟲豸,不是很寒磣嗎……可是,中國文學、中國的古典,甚至于中國本身都完全無視我們這些蟲豸,慢慢地遠去”。
戰敗后泰淳成為小說家、開始全力從事創作活動時(1948年),他在過去發奮寫就的處女作《司馬遷》的再版自序中,這樣寫道:現在的自己是“藏身于船板的裂縫之間、意識不到大海存在的‘舟蟲’”,作為出發點的這部作品讓現在“安住在船底孱弱燈光的”自己感到“非常不安,但同時讓我想起活著(的重要性—筆者注)”。即泰淳將希圖安逸于不經反省思考的著作生活的自己命名為“舟蟲”。此外,在總結自身面對中國的基本姿態的50年代初期,泰淳把失去作為“民族的觸手”這一外國文學研究者的初衷、持續墮落的卑怯的自己形容為“蛔蟲”。“他痛苦不堪,希望能夠變形為在胎內卷成一團的安全的蛔蟲,不聞也不問。”
泰淳將自己定位為“蟲族一員”,這不僅來自“寄居在社會的一條寄生蟲”的自我認識,而且也源自自身內部遭到蟲類侵蝕這一自我分裂的構想。
這種“蟲的哲學”——在人體內部“讓人刺癢難耐地繁殖”,“縱橫上下呲咬身體”,并且互相蠶食,“必定斗至只剩最后一只”的思想,在泰淳文學的最高峰、長篇小說《富士》(《海》1969.10~1971.6,Z10)中,顯現于主人公、精神病院青年實習生的夢里。主人公“我”,夢見自己遭受從耳中打入無數蟲子這一奇怪的刑罰,“很快,我的身體雖然表面上還保持‘我的形狀’,但體內也許已充滿了蟲子。我已完全變為‘蟲人’(276頁)。當“我”再一次做同樣的夢時,夢境與現實相混淆,呈現了一個“蟲的世界”——“甚至我周遭也已充滿了蟲子,全是蟲子,已經成了一個蟲子們相互呲咬直至剩下最后一條的世界”(339頁)。
此外,在泰淳的最后一部作品,即講述戰敗前上海生活的《上海之螢》(《海》1976.2~9,Z18)中,蟲在主人公的夢里變身為螢火蟲,“一邊支撐一邊蠶食”一位中國女性的尸體”(186頁)。
限于篇幅,在此雖然無法對泰淳的“蟲哲學”展開詳細的分析,但是筆者認為,泰淳文學中的“蟲”的思想,受到佛教很深遠的影響。泰淳在介紹源信《往生要集》的文章《〈往生要集〉的蟲》(1970.11)中寫道,“首先我覺得很好的是,源信所描寫的‘穢土’中的蟲的生存狀態”(Z18,380頁)。泰淳這樣稱贊源信的姿態:“對未到墜入地獄、還在人道就已存在的蟲之現象、蟲之苦惱,進行了極為客觀而冷靜的描述”(同前注,381頁)。可以說,這篇文章中所介紹的“蟲的生存狀態”與上文提到的《富士》和《上海的螢》中的描寫是一脈相承的。泰淳執著于“蟲之現象、蟲之苦惱”,與他所一貫主張的戰后派作家的精神——“自我分裂”的姿態——也不無關系。正因為如此,泰淳才將作家筆下的無數個“自我”形容為從作家全身傷口里爬出來的蛆蟲。也即,在“自我分裂”的意義上,可以認定“我”→“Q”→“蟲”,這一分裂機制的存在。
而泰淳受到影響的《阿Q正傳》當中也出現“蟲”。阿Q咒罵比自己弱小的人為“毛蟲”,如果對方比自己強大,就將自己貶低為“蟲豸”,借此脫逃。這種可謂阿Q“精神勝利法”象征的“蟲”到底給泰淳文學中的“蟲”帶來何種影響,在此還無法立即作出判斷。不過,在《阿Q正傳》的最后一幕中,想要“咀嚼”游街時被民眾包圍的阿Q的皮肉以及皮肉以外的東西,或是“咬他的靈魂”的狼的眼睛總是讓人聯想起泰淳文學中縱橫上下蠶食人體的“蟲”。連“救命”都沒來得及喊出來的阿Q,“覺得全身仿佛微塵似的迸散了”。有關這一對餓狼的眼睛,丸尾常喜認為這是“阿Q從圍觀處決的看客身上所看出的‘奴隸’的眼睛”,“這對眼睛訴說了被渙散地相隔絕、相互間毫無心靈溝通的人們,以及因此無法擺脫‘食人’宿命的人們的深深的孤獨。”如前文所述,泰淳的阿Q論的特征便是將著眼點放在魯迅文學中阿Q與村民(看客們)之間的對比上,泰淳斷定:“這一對比與魯迅文學的主要母題‘這是個吃人的世界’及‘人類是孤獨的存在’也相關連。”可以說,包括阿Q在內的群眾之絕望的孤立狀態、和有著食人狼般的眼睛的群眾的殘酷性,帶給泰淳激烈的沖擊。
實際上,泰淳也受到了魯迅作品中“狼”的深刻影響。例如,魯迅的短篇小說《孤獨者》(1925.10 收錄于魯迅的第二部小說集《彷徨》)通過描繪深夜曠野中受傷哀嚎的狼,讓與世界斷絕的主人公魏連殳的孤獨形象躍然紙上。泰淳為這一意象所吸引,在自己的短篇小說《無聲之男》(1954.7)中也描繪了“面對深夜的虛空嗥叫”的狼的形象。此外,在《阿Q正傳》中登場的“狼”是作為吞噬人類肉體和靈魂的某種力量的象征而出現,這一點與泰淳文學中一邊蠕動一邊蠶食人體的夢中之蟲有著相通之處。但是,正如丸尾常喜所指出的,《阿Q正傳》中的“狼”是互不理解卻互相攻擊的愚昧國民(“奴隸”)的象征,而泰淳的“蟲”則指的是一種自我解剖和自我分裂的象征,而這種自我解剖和自我分裂反映的是泰淳自專制政府的拘留所、戰場及戰敗經歷中所形成的、對于人與人之間的連帶所抱有的存在主義式質疑。也即,作為將自身微塵般分裂的文學意象,泰淳對源自佛教思想的“蟲哲學”以及《阿Q正傳》的“狼”進行再創造,從而將“我”內心中的無數個“我”用“Q”這個符號加以表記。而對于起名阿Q的理由,丸尾指出原因之一是因為聯想到與“精神勝利法”相關的辮子的形狀,魯迅才定下“Q”這個符號。與此相似,泰淳用“Q”這個符號來表示“糞、排便”,或許也與Q的形狀有關。既在“我”體內又被排泄出的骯臟丑惡的東西、既是“我”又不是“我”。可以說,泰淳使用“Q”和“我”之內的“蟲”這些符號,來表現錯綜復雜的“自我”。
三、浮游——社會·民眾/個人以及國境之間
(一)表里一體的“Q”/“阿桂”
在《阿Q正傳》的《第一章序》中,有一段對阿Q這一名字的考證。敘述者就名字的表記寫道:“阿Quei,阿桂還是阿貴呢”。意味深長的是,在總括其對中國基本姿態的長篇小說《風媒花》(Z4)中,泰淳在命名以郭沫若為原型的人物時,并未使用韋氏漢語羅馬字母標記法的K或是日語發音的羅馬字標記法K,而是以“Q”來表示。此外,將自稱為“Q”的好友的“身份不明的記者”、“與臺灣政府有關系”(112頁)的中國人起名為“桂”。
泰淳之所以將“郭沫若”標記為“Q”,與其對郭沫若的評價不無關系。郭偉指出“泰淳首先高度評價擁有充滿浪漫精神之詩性精神的郭沫若”,同時還引用了泰淳的這一評語:“中國的現狀正不斷將詩人、或歷史學家郭沫若改造成一位政治家”。可以說,泰淳所下的判斷與當時占主流的、從贊美革命的角度抬高郭沫若的評價傾向劃清了界線。關于《風媒花》中對郭沫若的評價,郭偉認為:“泰淳對郭沫若所抱有的忸怩之情,只能夠借助與郭沫若和其日本夫人所生的孩子們處于相同立場的混血兒三田村為媒介來表述”,并指出泰淳通過強調混血兒三田村,“力圖發現不受加害者與受害者這一單純二項對立束縛,超越民族、國家等人為界限的思想可能性”。郭偉認為應當關注將郭沫若相對化的混血兒三田村所代表的視點,筆者對這一見解也表示贊同。
在《風媒花》中,“Q”被介紹為“新中國文化的重鎮,政治領導者”(112頁)。而混血兒三田村將Q定位為“堅定的中國的文學者。他是明確的有代表性的中國人,新中國的杰出發言人”(157頁),并指出作為“日中混血兒”的Q氏的長男與其父存在著“根本性的差異”(157頁)。此外,三田村還批判Q氏與“中國文化研究會”(原型為竹內好等人主辦的“中國文學研究會”)的成員同樣,“受惠于古風純粹的國民性的幸福”,并強烈主張“不過他(指Q氏—筆者注)的孩子們正從失去這一幸福的位置出發”(157頁)。
也就是說,對于混血兒三田村而言,無論是中國人Q氏,還是日本人軍地和峯,他們都有著(或者說“受惠于”)堅定不移的身份認同,也正因為這一點他們成為被批判的對象。“混血”是泰淳文學中的一個重要主題,泰淳不僅僅將其視為單純的生物學現象,而是當作一種存在主義意義上的“方法”。在泰淳的“混血兒”概念中,還包括生活于異國的“喪失祖國者”。存在主義意義上的“混血”,既意味著立場的復雜性以及自我認同的糾結,同時借助內部的多元性,將弱者/強者和無力者/掌權者之間的對立相對化,給予弱者絕地反彈的力量,促使他們追求強韌的生活方式。也即,對泰淳而言,“混血”是人類為謀求生存而采取的一種“方法”。因此,泰淳站在“混血”的立場上,將持有堅定不移身份認同的Q相對化。
另一方面,自稱為“Q”好友的“桂”也可能與“阿Q”存在關連。因為如上所述,在《阿Q正傳》的《第一章序》中,“阿桂”作為“阿Q”的漢字表記之一被提及。“桂”與受“中國文化研究會”成員尊敬的“Q”不同,他是日中戰爭期間活躍在重慶的記者,并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之年來日,此后一直留在日本,被視作“身份不明的記者”(112頁)、“未與祖國直接相連”(113頁)、“沒有理想的男人”(218頁),一直被輕蔑。“僅有很強的自我保護本能”(113頁)的桂并未被賦予堅定的身份認同。對于致力通過描寫人物的并存狀態而從空間、整體上來認識世界的泰淳而言,“桂”與“Q”在身份認同這一問題上是表里關系,只有兩者并立才有意義。這一意義是指對身份認同多樣性的顯現、以及獲得超越堅固身份認同的全新身份認同的可能性。所以,在身份認同的浮游性這一點上,我們可以從“桂”和“Q”兩人身上讀出泰淳文學中“阿Q”的影子。
而其實原本《阿Q正傳》中的阿Q便是一個姓氏和籍貫皆不明的浮游式人物。他以短工的身份在未莊(村)和縣城間游蕩。因“進了幾回城”,“自然更自負,然而他又很鄙薄城里人”。阿Q對城里人在吃油煎大頭魚時還要加上切細的蔥絲感到“可笑”,但與此同時,又對未莊那些連城里的煎魚都沒見過的“可笑的鄉下人”感到不滿。在向趙家的女傭、年輕的寡婦吳媽求愛未果后阿Q丟掉了在未莊的生計,跑到城中成為盜賊的下手。而在未莊,阿Q又是在統治階級與村民(下層階級)之間浮游的人物。他自稱“和趙太爺原來是本家,細細的排起來他還比秀才長三輩呢”,“對于兩位‘文童’也有以為不值一笑的神情”,“所有未莊的居民,全不在他眼神里”。可見,阿Q是一位既可以說從屬于也可以說不從屬于村與城、統治階級與下層階級中任何一方的模棱兩可的存在。他浮游于未莊與縣城、統治階級與下層階級之間,被雙方所蔑視、所厭惡。
對于這樣的阿Q,飯塚朗指出其是“農忙時作為短工被記起,但是一到農閑時就被遺忘的男人”,未莊的人們雖然一度畏懼在城中成為盜賊下手的阿Q,但“大家后來發現,他終究不是什么值得害怕的強盜”。總而言之,阿Q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他的流浪性。
關注具有這種流浪性的阿Q的泰淳在《風媒花》中用“Q”來標記“明確的有代表性的中國人”郭沫若,把“未與祖國直接相連”的男人命名為“桂”,應當不是偶然。從根本上一直將郭沫若視作詩人的泰淳,既對中國革命“正不斷將郭沫若改造成一位政治家”感到遺憾,同時對力圖打破“阿Q式的現實”的中國革命抱以理解的態度。(《中國的小說與日本的小說》Z12)這一處于個人與國家、民族的狹縫中的糾葛正是通過并立“Q”和“桂”這兩個人物來表現的。而且,可以說通過表面似乎完全對立但實際上表里一體的“Q”和“桂”,舊中國矛盾的集合體阿Q這一形象被實體化了。也即,泰淳對阿Q的浮游性以及由此引發的悲劇性的關注,通過“Q”和“桂”這兩個人物形象的塑造體現出來。
泰淳通過對比“Q”與混血兒三田村,使“Q”的特征得以凸顯。而對于“桂”,則通過軍地等人的視點以及評價,將其戲化為一個不擇手段求生的人物。換言之,泰淳對“Q”與“桂”采取的都是相對化的態度。主人公峯的情人蜜枝的弟弟守在將“Q”和“桂”視作中國“文化人”的同時,認為如果真正熱愛中國的話不僅要去傾聽“文化人”的話語,“還要去熱愛浸透泥土氣息、粗野地呼吸的人們”(139頁)。可見泰淳是對中國的“文化人”持批判態度的。而另一方面,泰淳的筆致卻對趙樹理的長篇小說《李家莊的變遷》中受到“雙方蔑視、厭惡”但卻“渾身浸透著泥土氣息”的浮游式人物“小毛”給予了同情。下面,筆者將對“小毛”這一人物展開討論。
(二)“最卑劣的中國人”小毛——個人與社會、民眾的狹縫之間
《李家莊的變遷》發表于1945年,而其被翻譯成日文是在《風媒花》連載的前一年、也就是1951年10月。竹內好馬上給予這部作品很高評價,說它具有超越現代文學的新的可能性。小野忍對這部作品的說明則是:“以主人公鐵鎖從無知到覺醒的過程為軸,描繪了1920年代后半期至1945年抗日戰爭結束20年間李家莊的變遷……描繪了農村社會變革的全過程。”可見,在當時的日本文壇,這部作品的主題被理解為刻畫農民的覺醒以及反革命分子的失敗。
但是,在《風媒花》中,泰淳借以自己為原型的主人公峯之口,展開了獨特的《李家莊的變遷》論。峯評述道:“《李家莊的變遷》可真是一部可怕的小說。小說里出現了一個叫小毛的男人,他一邊對著村子里的頭兒點頭哈腰,轉過臉來又開始對村里的革命黨獻媚。……無論在什么時代,小毛都是無用之人。被雙方所輕蔑、厭惡,只能悲哀掙扎著生存,可以說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弱者。在讀到這個人物的丑態之時,我感同身受,一股冷戰。完全沒有事不關己的感覺(242~243頁)。”可見,泰淳并非對于革命陣營,而是對無論在哪個時代都被蔑視的“徹頭徹尾的弱者”小毛產生了共鳴。
而實際上,在《李家莊的變遷》這部小說中登場的“小毛”是姓名和職業都不明朗,似為統治階層爪牙般的人物,村民們將他視做敵對者,稱其為“狗尾巴”、“狗腿”、“怕死鬼”、“漢奸”。《風媒花》中的峯夢見自己變身成了這位被五花大綁押上批斗大會的“最悲慘最卑劣的中國人”(243頁)小毛。對于峯而言,小毛的丑態“完全沒有事不關己的感覺”,“自己從未為所作所為感到過后悔。因為到頭來,這就是真實的我,我的全身全靈。……生也好,死也好,我不能夠成為我以外的任何人”。(243頁)對于以竹內好為原型的軍地的批評(“峯安于于現狀,不思進取”),峯反駁道:“這不是開玩笑,小毛也有他認真的一面。只不過是由于他的認真是四分五裂的,所以并不如您那樣看上去引人敬畏。端容正坐、原地不動,這不正說的是你自己嗎(246頁)。”
竹內好在討論《李家莊的變遷》的文章《趙樹理文學之新》(《文學》1953.9,《竹內好全集》第3卷)中指出,趙樹理文學的異質性是在整體之中“包含著個體的問題以及自我實現的問題”(235頁),在這一作品中“個體與社會沒有任何矛盾”,“個即整體”(233、238頁)。但是,讓泰淳產生共鳴的小毛是一位被社會、整體排斥的浮游性存在。他不僅成不了統治者,也沒有可能成為革命家。此外,與相信個人和整體能夠統一的竹內好不同,泰淳雖然在理論上對毛澤東的《文藝講話》(1942.5)表示贊同,認為個體與社會、人民大眾相統一是未來的目標,但同時表示自己不知道“進入人民中去”的方法,主張自己始終“無法丟棄”“人類是最可疑的生物”這一戰后文學派的立場。
泰淳認為,小毛是“被雙方所輕蔑、厭惡,……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弱者”。佐佐木基一也曾指出,小毛其實便是阿Q。(《同時代作家的風貌·武田泰淳》講談社文藝文庫,1991.6,158頁)泰淳認為,新中國“確實發生了變革”,但是“仍然有小毛式的人物”,他對小毛這個人物產生了共感。采取“在精神最底層生存”這一策略的泰淳之所以會被小毛所吸引,是因為小毛“被雙方所輕蔑、厭惡”,是個人與社會、民眾之間不可調和與矛盾的體現者。持“人類是最可疑的生物”這一信念的泰淳,為了不被“非人類的幻影”(指理想主義—筆者注)遮蔽雙目,在“悲慘”而“卑劣”的小毛/阿Q身上看到了人類和人性的真實。
如上所述,在形似眾多“花粉”集合體的長篇小說《風媒花》中,“Q”、“桂”、“小毛”等帶著阿Q之影的人物都被作為“人之花粉”由屬于“蟲類”的泰淳“堅實地傳播”并加以分析。以弱者的絕對反彈為武器、把立志堅韌地生存的“混血”當作方法的泰淳,在自己的作品中讓這些阿Q群像登場,以表達自己對于與個人相對立的民族/國家、社會/民眾所抱有的疑問。與此同時,泰淳還利用多元化的構思,思考超越民族和國家這一人為界限的可能性,不斷探尋“自我”在這個混濁一片的世界上的存在方式。
結 語
以上圍繞“分裂”與“浮游”這兩個關鍵詞,對泰淳兩篇早期小說中“Q”的記號以及阿Q的影子進行了分析。這兩篇作品都是以“我”為主題的小說。《機靈的野獸》(1948年)為戀愛題材,以對“我”的自我分析為主題。而另一篇泰淳最早的長篇小說《風媒花》(1952年)既是一部力圖反映整個社會的“全體小說”,同時由于這部作品總結了泰淳自身對中國的基本姿態,因此是以“我”在世界中的定位為主要課題。在“作為日常生活者的‘我’的變化”以及“人類整體指向”這兩種意義上,兩篇小說都是在試圖超越過去私小說的立意之下完成的。
由此可見,在泰淳作品中就“自我”問題而出現“Q”這一記號以及阿Q的影子與“我”的生存狀態其實存在密切的關系,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在小說《機靈的野獸》中,“Q”作為媒介剖析出“機靈的野獸”這一自我分析的概念;而《風媒花》則巧妙地配置了“Q”、“桂”、小毛等從各個方面體現“阿Q譜系”的人物。即,“阿Q”是泰淳在進行自我分析時的一個重要媒介物。
泰淳將日本戰后派作家的精神定義為“將自己大卸八塊”。在這種不斷探求錯綜復雜的“自我”的泰淳文學中,“阿Q”承擔著“分裂”和“浮游”的問題,以各種各樣的形式介入作品。泰淳曾指出浮游于社會、民眾之外的“小毛也有他認真的一面,只不過其認真已是四分五裂”,而泰淳文學的浮游亦同樣為四分五裂的“認真”所支撐。這種“認真”,與泰淳深感敬意與親切的“私小說”中的“真誠”有著相通之處。作為一位批判繼承“私小說”的傳統并同時追求戰后文學派精神的作家,泰淳為了堅守這一四分五裂的“認真”,誠實地面對魯迅在《阿Q正傳》中所提出的各種課題,終其一生在日中兩國的夾縫之間不斷思索。
注釋:
①武田泰淳:《中國文學與人學》(「中國文學と人間學」),《望鄉》第5號1948年4月。增補版《武田泰淳全集》(筑摩書房1978~1982)第12卷、第102頁。本稿中泰淳作品的引用都依據該全集,以下將《全集》略記為Z,之后附上卷號和頁碼。此外,在注釋中“武田泰淳”省略為“泰淳”。
②泰淳:《我的創作經驗》(「私の創作體験」)中野重治、椎名麟三編《現代文學Ⅱ 創作方法與創作體驗》新評論出版社1954年8月。Z12,第386頁。
③據川西政明的調查,《機靈的野獸》起先發表在1948年3月號的《新文化》上,此后作為小說《“愛”的形式》(單行本《“愛”的形式》 1948年12月 八云書店 Z2)的第三章,改名為《我與“我”的對話》。見川西政明《武田泰淳傳》,講談社2005年版,第246頁。
④泰淳:《風媒花》,《群像》1952年1月~11月。收于Z4。
⑤泰淳:《瑣細的感想—關于戰后派作家的并立—》(「ささやかな感想—戦後作家の並立について—」),《文學界》,1952年12月。收于Z2。
⑥泰淳:《私小說與社會小說》(「私小説と社會小説」),《愛媛新聞》,1953年7月,Z12,第298頁。
⑦竹內好:《阿Q正傳》(「『阿Q正伝』」),《魯迅入門》,東洋書館,1953年6月。《竹內好全集》第2卷,第148頁。
⑧泰淳:《凡人氣味和不食人間煙火》(「人間臭と人間ばなれ」),《群像》,1947年1月。Z12。泰淳:《對“自我”的反省》(「『私』への反省」),《神戶新聞》,1961年8月21日。Z14。
⑨泰淳:《我的創作體驗》(「私の創作體験」),參見前注(2),第378頁。
⑩泰淳:《追求自我》(「私を求めて」),《文藝首都》,1948年8月。此外,他還寫道:“為了真正作為作家而存在,我必須書寫‘自我’、保持書寫“自我”的狀態、繼續不斷書寫“自我”,不能停下來”,“‘自我’,對作家而言,……就是宿命般的存在”等等。參見Z12,第114~115頁。
此外,竹內榮美子指出,泰淳小說所體現的“從〈‘我’是‘我’〉中抽身而出,認同多樣的‘自我’”這一特征,在其寫作《廬州風景》(1947年11月)的階段就“已經可以看出”。《清晨展開的風景—〈廬州風景〉》(「晨朝に広がる風景―『廬州風景』―」),《批評精神的形態中野重治/武田泰淳》,EDI,2005年3月,第206頁)
譯者簡介:張瑤,東京大學人文社會系研究科中國文學專業碩士生。
王俊文,福建泉州人。1995年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1999年畢業獲文學學士學位。同年升入本系比較文學與比較文化專業碩士班,2002年7月畢業獲文學碩士學位。同年10月赴日,2003年4月考入東京大學人文社會系研究科中國文學專業博士課程,2011年3月提交博士論文《武田泰淳與中國——以“阿Q”與“秋瑾”兩系譜為中心》,6月通過審查獲文學博士學位。現在早稻田大學、明治大學等任兼任講師。主要關心佐藤春夫、竹內好、武田泰淳、以及高橋和巳等日本的“中國文學者”與中國的關系。譯有《魯迅·革命·歷史——丸山升現代中國文學論集》(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