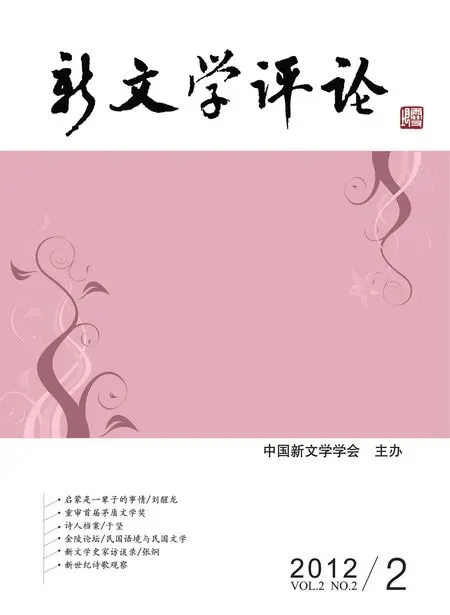關于文學史的研究和編寫問題
——張炯先生訪談錄
◆ 張 炯 李清霞
關于文學史的研究和編寫問題
——張炯先生訪談錄
◆ 張 炯 李清霞
問:張老師,您從上世紀50年代就參加中國文學史的編寫工作,對我國這方面工作至今的成績,您如何看?
答:是的,我在讀大學時就參加了北京大學中文系1955級同學集體編寫的《中國文學史》兩卷本和四卷本的工作,還參加了一段《中國小說史稿》的編寫。到上世紀70年代末和80年代又參加主持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的《中國當代文學史》的工作。90年代擔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暨少數民族文學研究所所長期間,又主持過由我和鄧紹基、樊駿共同主編的《中華文學通史》十卷本的工作,并將我主編的中國當代文學史三卷納入《中華文學通史》。新世紀我還主編出版了《新中國文學史》上下卷和《中華文學發展史》(上、中、下三卷)。在我的學術生涯中,于文學史編寫方面,我確實耗費了較多的時間。我覺得從上世紀初到現在,我國學者在中國文學史的編寫和研究方面都取得很大成績。這主要表現在幾個方面:
第一,各種類型的文學史編寫和出版,成果豐碩。
百年來,我國已編著和出版各種各樣的文學史著作1500多種。大家知道,從上世紀初林傳甲、黃人等學者的首批中國文學史著作問世,到新中國成立前,文學史著作比較有影響的還有王國維的《宋元戲曲史》、謝無量的《中國大文學史》、劉師培的《中古文學史》、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和《漢文學史綱要》、鄭振鐸的《插圖本中國文學史》、劉大杰的《中國文學發展史》(上卷)等。新中國成立后則有劉大杰的完整本《中國文學發展史》和林庚的《中國文學簡史》、王瑤的《中國新文學史稿》、張畢來的《中國現代文學史》、丁易的《中國現代文學史略》以及被教育部頒為大學文科教材的北大中文系1955級同學集體編寫的《中國文學史》四卷本和游國恩等編著的《中國文學史》、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編著的三卷本《中國文學史》。當時的中國文學通史一般都從先秦寫到清代。改革開放的新時期后到90年代初,則編寫和出版了大批包括通史、斷代史和各種文體史、地區史、民族史等各種類型的文學史著作。通史方面有前述的一百多位學者參加編寫的《中華文學通史》十卷,首次將我國各民族文學都納入,并貫通古今與臺港澳各地區,填補了我國文學史研究的諸多空白,作為完整的中國文學通史雖仍有不足之處,畢竟不失為世紀末的集大成之作。而尚未涉諸多少數民族文學、下限僅寫到晚清的通史著作,如林庚著《中國文學史》于歷史分期和藝術分析之富于個性特色;袁行霈主編的《中國文學史》四卷之重點突出,體現高校教材的要求;章培恒、駱玉明等的《中國文學史》三卷提倡人性的觀點,均各有特色,分別代表這期間文學通史編寫的新成就。文體史方面則有北京大學張少康等的《中國小說史稿》、楊義著《中國現代小說史》三卷、郭預衡的《中國散文史》三卷和姚春樹等主編的《20世紀中國雜文史》上下卷,都把有關研究向前推進。尚有陳美林的《中國章回小說史》、李昌集的《中國古代曲學史》、謝桃坊的《中國市民文學史》等出版。地域文學史的編寫也涌現出更多的著作,如不同學者主編的《上海文學史》、《湖南文學史》、《湖北文學史》、《云南文學史》(古代部分)和《臺灣文學史》、《香港文學史》等,均為認識和評價這些地區文學的發展,作出自己的學術貢獻。斷代文學史研究方面,由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余冠英、鄧紹基、劉世德主持的斷代史系列先后出版曹道衡等的《南北朝文學史》、喬象鐘等的《唐代文學史》和鄧紹基等的《元代文學史》外,還出版了褚斌杰、唐家健主編的《先秦文學史》、徐公持主編的《魏晉文學史》、孫望、常國武主編的《宋代文學史》。此外突出的還有趙明主編的《先秦兩漢大文學史》、趙逵夫主編的《中國先秦文學編年史》三卷和傅璇琮主編的《唐代文學編年史》三卷,以及方銘著《戰國文學史》、劉揚忠著《唐宋詞史》、嚴迪昌著《清詩史》、郭延禮著《中國近代文學史》、唐弢主編《中國現代文學史》等。其中編年史引證資料尤為豐富,開創了文學史編寫的新體例。而陳文新主編的貫串古今、多達18卷的《中國文學編年史》更是近年完成的浩大學術工程。20世紀文學史的整合研究也出版了黃修己、孔范今、張毓茂和嚴家炎分別主編的《中國二十世紀文學史》。新出版的王慶生、陳思和、特·賽音巴雅爾分別主編的《中國當代文學史》和洪子誠著《中國當代文學史》,雖詳略有別,或在文學史觀念、或在事實認定與框架結構方面均有新意。此外還出版了高占祥、李準主編的《新時期文學藝術成就總論》、張炯主編的《新中國文學五十年》和錢理群、溫儒敏、吳福輝著《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等,均體現了這期間現當代文學史研究的新成績。羅宗強著《魏晉南北朝文學思想史》和《隋唐五代文學思想史》、陳伯海主編《近四百年中國文學思潮史》、馬良春等編著《中國現代文學思潮史》、朱寨主編《中國當代文學思潮史》等則從宏觀的視角考察和梳理了各數百年我國文學思潮發展的歷程。民間民族文學方面,不僅有祁連休主編《中國民間文學史》和劉守華著《中國民間故事史》獲好評;各少數民族文學史的研究和編寫,迄今已出版了蒙古族、藏族、苗族、侗族、羌族、赫哲族、鄂倫春族、布依族、仫佬族、東鄉族、納西族、毛南族、京族等族別文學史,新出版的還有布朗族、基諾族、普米族、拉古祜族、達斡爾族、哈尼族、裕固族、土族和柯爾克孜族文學史或文學簡史。各民族文學關系的研究也有新的突破,中國社會科學院少數民族文學所承擔的這方面國家委托性項目已出版了劉亞虎的《中國民族文學關系史(南方卷)》,北方卷也已出版。此外還有李炳海著《民族融合與中國古代文學》、云峰著《蒙漢文學關系史》、馬學良等主編《中國少數民族文學比較研究》、傅光宇著《云南民族文學與東南亞》等也填補了相關的研究空白。海外華文文學在新時期也進入文學史家的研究領域。陳賢茂主編《海外華文文學史》修訂版(四卷)在對海外華文文學的特點和規律以及許多作家作品的深入論述方面均比初版有明顯超越。公仲主編的《世界華文文學概要》也參照豐富資料扼要論述了各地區華文文學的成就。周發祥、李岫主編的《中外文學交流史》和曹順慶著《中外比較文學史》(上古時期)、范伯群和朱棟霖主編《中外文學比較史(1898—1949)》更從比較文學的角度開拓了中國文學史研究的新的方面。郭延禮著《中國近代翻譯文學概論》是這方面難得的開拓性史著。文學接受史也出現了像陳文忠的《中國古典詩歌接受史研究》和馬以鑫的《中國現代文學接受史》等嘗試之作。趙敏俐、楊樹增的《20世紀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史》和張健的《清代詩學史》、黃修己的《中國新文學史編纂史》則為文學研究史拓開自己的領域。呂薇芬、張燕瑾主編的《20世紀中國文學研究》長達十卷,對將我國學者20世紀對歷代文學的研究作出總結性的考察,同樣屬于文學學術史研究方面的難得之作。可見,百年來我國文學史研究領域規模之宏大,著作成果之繁多。
第二,文學史專題研究方面的論著更產生眾多的新作。
近三十年來由于國家各級科學研究基金的支持,對歷代重要作家、作品、文學流派和文學現象的深入研究和空白的填補,出版了大量的新成果,逾上千種之多。如李忠明的《中國小說學通論》、趙山林的《中國戲劇學通論》做到史論結合,視野宏闊;沈澤宜譯注的《詩經新解》、姚小鷗的《〈詩經〉三頌與先秦禮樂文化》、黃靈庚的《〈離騷〉校詁》、曲德來的《屈原及其作品新探》、鄭杰文的《戰國策文新論》、葛曉音的《詩國高潮與盛唐文化》等著作,皆頗多新意;王瑤的《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現代化歷程》通過重要作家的剖析,見解深致,楊義等著《中國新文學圖志》則圖文并茂,胡明的《胡適學案》、董健的《田漢傳》、關紀新著《老舍評傳》、范際燕著《胡風論》等則在現代作家研究方面較為深入與全面;而張松如主編《中國詩歌史論叢書》9卷,袁良駿主編的《魯迅研究書系》11冊,劉中樹主編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書》10冊,嚴家炎主編的《二十世紀中國文學與區域文化叢書》十卷和謝冕、孟繁華主編的《百年中國文學總系》11冊,更屬這方面作者眾多、論證豐實、規模和影響較大的著作。這都說明,我國文學史的研究和編寫,百年來在不斷開拓和深入。學術視野越來越開闊,研究的方面和問題也越來越細致。
第三,文學史觀方面產生了重大的變革。
只要稍為比較今天的文學史著作與上世紀初的中國文學史著作,就可以看出百年間我國文學觀念和文學史研究觀念的巨大變化。特別是新中國建立后,由于馬克思主義的廣泛傳播,以辯證唯物史觀為基礎的新的文學理論和新的文學發展觀被越來越多的學者所接受,從而產生了文學史觀的深刻變革。文學雖然是審美意識形態,卻屬于受社會經濟基礎制約的上層建筑意識形態的一部分。它既是一定的社會生活的反映,也是不同時代人們精神世界的表現。它總扎根于一定的社會和歷史文化的土壤,并因社會歷史文化土壤的變化,文學的內容和形式也會產生相應的變化。文學作為人類的精神創造,既是主體與客體的統一,也是人類智慧對于社會生活的審美把握。它的歷史存在有起源、發展和變化的漫長過程。人們只有從意識反映存在又促進存在發展的相互辯證關系,從社會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意識形態相互作用的辯證關系,才能科學地解釋文學的歷史存在及其歷史發展,才能解釋歷史上不同作家作品和藝術流派、運動何以會產生不同的構成和內容與形式的差異。上述觀點被接受,不僅使我國的文學觀念產生巨大的變化,也使我國的文學史學產生劃時代的變化。文學史家們不限于記錄歷史上有何作家和作品,更著力于探討文學發展與社會發展的關系,從而使文學史學建立在穩固的人文社會科學的現代基礎上。盡管文學史不同于一定社會的經濟史、政治史、文化史,文學史家卻不能沒有經濟史、政治史、文化史方面的知識。甚至還要有文化人類學和社會心理學、普通語言學和古代漢語、現代漢語等方面的知識。文學史的任務遂被定位為客觀地描述文學發展的歷史過程,恰當地評價不同時代作家作品的歷史地位,探討文學發展的歷史規律。
第四,文學史研究資料的收集、發掘和編輯、出版方面也成績巨大。
近三十年,國家大力支持古籍整理、出版的工作。《先秦兩漢文》《全唐文》《全唐詩》《全宋詞》《全元文》《全清詞》等大型文集的整理、出版,以及像《中國近代文學研究資料叢書》、《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資料叢書》和《中國當代文學研究資料叢書》等上百種卷數、計以億字的書籍,還有各種作家文集、文體選集的編輯、出版等,都為文學史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方便條件。而考古發掘的新發現,如郭店竹簡、清華竹簡等的收集和整理,對先秦古籍真偽辨別就起了重要的作用。
我的閱讀視野當然非常有限,僅從上述所舉,即可看到經過本世紀數代學者的辛勤耕耘,我國學者不僅大多遵循唯物史觀為指導,建立了涵蓋中國文學通史、斷代史、文體史、思潮史、地域史和民族史的多層次多方位的研究體系,而且填補了古今文學發展研究的大量空白,開拓了許多新的領域,重新考定了許多重要的文學史實,更加深入、細致地研究了許多過去沒有研究過的作家和作品,使文學史研究奠定在相當扎實的科學基礎之上。因此,這方面的成就同樣為新世紀文學史研究的新拓進創造了良好的繼續前進的基礎。
問:文學的歷史分期問題一直是文學史著作必須予以妥善解決的問題,現今的各種中國文學史著作,在歷史分期上,并沒有統一的處理,請問你如何看待和處理文學史的歷史分期問題。
答:中國文學已有3500年有文字記載的歷史。它從萌芽狀態的前文學發展到今天與世界接軌的現代化文學,經歷了題材、主題、形式、風格的深刻而廣泛的演變。文學史研究工作者對它的發展階段曾從不同角度作過種種的考察,并進行了不同歷史分期的處理。現今大多中國文學史著作均按王朝更迭作為文學的分期。這固然不是沒有一定的根據。因為王朝更迭往往引起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的相應變革。但某些情況下的王朝更迭并不帶來這些方面的多少變化。所以,學者們也總嘗試從其他視角去進行分期,特別是從文學本身發展的特點來進行分期。在編寫《中華文學通史》十卷本的過程中,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和少數民族文學研究所參加工作的同志也曾提出這個問題,只是當時缺乏更深入的探討,沒有能夠提出新的有說服力的看法。只好仍然基本采用王朝分期的辦法。后來對這個問題我又做了些思考。在《中華文學發展史》中采用了另一種分期辦法。在中國文學的發展過程中,我以為有三個特點不同的階段,代表著中國文學發展的三次高潮。我把它劃為上世期(從先秦至唐五代)、中世期(從宋遼金至清代)、近世期(從鴉片戰爭至今)三個大時期。我是從文學本身的發展特點并兼顧社會政治、經濟、文化背景來加以劃分的。我國歷史發展中,不僅存在經濟基礎和政治等上層建筑意識形態的多次變革,在多民族共存的格局里,還有過多次的民族大遷移大融合,從而使中華民族的社會結構和文化結構都出現十分復雜的演化。因而考慮歷史的分期就不能不考慮上述特殊的狀況。我所以將我國文學史分為三個大的歷史時期,其根據是三個時期各有特點:
第一,上世期中國社會的結構形態是從原始社會、奴隸社會轉向封建社會前期,歷史跨度很大。雖歷三皇五帝直到漢唐,前后達兩千多年,可概稱為前封建時代。因為,自從黃帝、炎帝聯合打敗九黎族的蚩尤,產生首次大規模的民族混合。到秦漢統一中國,改貴族分封制為郡縣制,出現第二次民族大融合。又到魏晉南北朝和隋唐,發生第三次民族大融合。這就使社會結構顯現出相當駁雜的特點。堯舜時代存在“大同社會”,見于典籍。夏商兩代基本是奴隸制。至周代向封建制過渡。但周代仍然擁有大量奴隸,當時的商人有許多便是奴隸主。而居于華夏族周邊的西戎、北狄、東夷、南蠻等我國的其他民族,在周代還大多處于從原始社會到奴隸社會的發展階段,如前期沿海一帶的東夷還“披發文身”、東南一帶的越族則“斷發文身”。春秋戰國之后秦始皇一統中國,直到漢唐封建制確立,活躍于北方的匈奴、突厥、回紇和西南的吐蕃、南韶等民族地區,仍然盛行奴隸制,且因五胡亂華和五代十國的戰亂,中原的封建制也受到很大的破壞,產生過奴隸制不同程度的復辟。所以,上世期從整個中國的版圖來看,大多地方仍然處于奴隸制或奴隸制與封建制并存、混合的狀態。我們不妨稱之為前封建時代。這個時代的文化思潮從“公天下”的意識形態到“家天下”的意識形態產生首次巨變,從周公制禮作樂到禮崩樂壞、春秋之際百家蜂起,又一巨變,從秦漢統一中國,“書同文,行同倫”和漢武“獨尊儒術,罷黜百家”再次巨變,漢末佛教傳入,道教興起,黃巾作亂,歷三國、魏晉和五胡亂華,到南北朝,儒學被佛學和玄學沖擊,及至隋唐一統,儒學重興與儒、道、佛三教的沖突與和諧,更是一巨變。反映了前封建時代社會結構和民族歸屬、文化交融的駁雜與浪潮起伏。上世期許多民族還沒有文字,文學作品基本靠口傳,只有華夏族及在它基礎上發展壯大的漢族有象形字,從甲骨文、金文到寫于簡帛和紙上的篆字、隸書、楷書,由于書寫工具的簡陋和不易,從上古典籍起便言文分離。上世期中國文學是從不自覺的前文學發展到自覺的文學,從神話傳說、原始歌謠到后來的散文敘事和韻文詩章,其主要成就是詩歌和散文,它們構成中國文學發展的首次高潮。由于古代文字的發明取象形的路子,意在形中和形外,具有極其濃縮的象征性,加上書寫工具的限制,言文的分離便不可避免。隨著時代的推移,語言本身不斷豐富,被記錄的民歌雖更接近口語,如漢樂府和南朝的子夜吳歌,但與口語仍有差異。作為這階段文學成就主要標志的詩歌和散文,基本上都與口語有很大的差別。從《詩經》、楚辭、漢賦到駢文固然都不同于口語,唐代的古文運動更鞏固了散文領域的這種言文分離走向。而唐詩作為我國古典詩歌的輝煌高峰,雖有白居易對新樂府的提倡,然而言文分離的詩歌仍然占主流。這與文學的作者和受眾都主要是達官貴族和士人有很大的關系,也與這時期文學傳播手段不發達有關系。那時的文學傳播基本上是手抄,發明的印刷也是雕版刻字的印刷。
第二,中世期中國社會結構形態則進入后封建制,其特征是封建地主經濟占主導地位,現今中國版圖內的周邊民族的奴隸制因遼、金、西夏和蒙古族、滿族的強大并先后入主中原,很快都轉向封建制,家用奴隸即奴婢雖仍存在,畢竟已成為從屬于封建地主的奴隸殘余。宋、元、明、清四朝,商業和手工業有相當的發展,出現了更多十分繁榮的都市,產生有資本主義的萌芽,但整體而言,比較于封建地主經濟,商業和手工業仍處于從屬的地位,而且許多商人也多兼地主。許多重要的手工業更從屬于宮廷和官府。可以說這千年間中國的社會結構形態基本是封建地主所有制。其文化思潮主要是以宋明理學為圭杲的儒教封建思想。雖然后期西方人文主義思潮已開始傳入,而都市的繁華和市民階層的發展,則使文學傳播中的小說、戲劇崛起,與傳統詩文分庭抗禮,日益成為文學的主流,構成中國古代文學發展的第二個高潮。宋代的話本、元代的雜劇、明清兩代的小說和戲曲日益成為大眾審美的主要對象。中世期中國文學的主要成就是戲劇和小說,特點是言文趨于接近。這與城市的發展和市民社會的崛起有很大關系。文學的受眾從士大夫階層向市民階層的轉移都促使民間口語應用于受市民歡迎的文學體裁。《清平山堂話本》的出現與市井勾欄瓦舍說書人的生意鼎盛分不開,雜劇在宋末和元代興起,與草原游牧民族喜好說唱文學的傳統也有關,他們先后入主中原,帶來了本民族的說唱文學,而他們的漢語古文根底較差,他們便與市民一起成為文學的主要受眾,這都不能不使文學向口語靠攏。雜劇中的道白固然完全是口語,即令唱詞也相當白話化。元代的散曲比之宋詞也是大大口語化了。士大夫的傳統詩文雖然還用文言,但那種詩文已成強弩之末,難于再掀起高峰。明代的前后七子也罷,清代的桐城派古文運動也罷,都不能挽救它們的走向衰亡了。在明清兩代,小說成為文學的重要體裁,受到廣大受眾的熱烈歡迎。《三國志演義》、《水滸傳》、《西游記》、《金瓶梅》、《紅樓夢》等大批長篇小說的涌現,以及受到達官貴人和廣大士人、市民的普遍青睞,標志著我國文學向言文統一的方向大步邁進,掀起又一次新的文學高潮。而這時期活字印刷術的發明更大大促進了印刷業的發達和商業化,文學圖書的印刷發行成為一個重要的產業,出現了遍布全國的書籍銷售網,從而也使文學大大普及化。
第三,到了近世期,中國的社會結構形態便從封建社會淪為半封建半殖民地并轉向社會主義社會的初級階段。其特點是,在世界帝國主義列強的侵凌下,封建制被內部的民族資本主義萌芽和外來的資本主義浪潮所沖擊而走向淪落;從洋務運動到第一、二次世界大戰前后,資本主義在我國有相當的發展,而中國人民革命的勝利,導致新中國的建立,半封建半殖民地被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所取代。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以公有制為主體,仍容許資本主義經濟繼續存在和發展。其社會結構仍然相當復雜。整個來說,體現為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期。其社會文化思潮可以說產生劃時代的變革,傳統思潮中的封建性糟粕逐漸被揚棄,而源于西方的現代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為根基的人文思潮和社會主義思潮逐漸成為我國文化思潮的主流。世界范圍內出現的新的文學題材、主題、形式和風格的文學作品均被介紹到我國并使我國文學產生與世界接軌的轉變,文學的世界性與民族性的統一,成為這時期我國文學所追求的目標。期間,我國文學走向言文的完全統一。鴉片戰爭之后,外國思潮進入,首先產生了太平天國運動,太平天國的文書就是言文趨向統一的。太平天國被鎮壓,使這種趨勢受到挫折,但甲午戰敗后掀起的維新運動便伴隨梁啟超、黃遵憲、夏曾佑等發動的“文界革命”、“詩界革命”和“小說界革命”,也進一步推進了文學的言文統一。實際上19世紀我國的小說創作基本都是白話的,從《兒女英雄傳》到《七俠五義》,再到譴責小說中的代表作《官場現形記》、《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老殘游記》、《孽海花》等,莫不如此。至于五四之后的新文學的興起和完全代替了舊文學,在詩歌、小說、戲劇、散文各個領域白話全面取代了文言,使藝術表現手段走向綜合的長篇小說成為最主要的文學成就,使現代世界其他國家所擁有的各種文學體裁和樣式都被移植進來,文學的普及超過了歷史的任何時代。而隨著現代傳媒包括報刊、廣播、電影電視和電腦網絡的日益普及,文學作者和受眾的廣泛性隨著全民文化素質的不斷提高而不斷擴大。這更是20世紀我國文學的最鮮明的標志和最輝煌的成績,從而構成中國文學史上的第三次大高潮。
問:你說的我國文學的歷史分期確有相當的根據。你還編寫過《新中國文學史》,而在這個領域,從上世紀80年代到今天重寫文學史的浪潮中存在很多的爭論。你如何看待這些爭論?
答:是的,有過許多爭論。以我看,這些爭論涉及文學史學的若干基本理論問題,包括文學史研究的任務,文學史的真實性與傾向性問題,文學史評價中作家的政治身份與文學評價問題,文學作品評價的價值標準問題,普適性的文學價值與社會主義的核心價值觀問題等等。
我是這樣理解文學史研究的任務的。即文學史研究的基本對象是文學作品、作家和文學流派、文學運動的歷史存在狀況,以及文學發展的歷史規律,并力圖對不同時期的作家作品作出歷史性的評價。文學作品是文學研究的起點。當然,作品的存在與作家的存在分不開。并非所有的作品和作家都可以進入文學史。只有在文學發展的過程中具有新的重要歷史貢獻和歷史作用的作家和作品才可能進入文學史。文學史不同于政治史、經濟史或文化史,因為它們研究的對象和任務都不同。但這不等于說文學史與政治史、經濟史、文化史沒有關系,相反,它們之間有著密切的關系。我們當然不能以政治史、經濟史、文化史的研究來代替文學史的研究,但研究一定國家和一定時期的文學史,就必須了解相應國家和時期的政治史、經濟史、文化史方面的研究成果和知識。
文學史研究必然存在一個真實性與傾向性的關系問題。文學史當然必須追求真實。歷史上存在哪些真實存在過的文學作品和作家,它們產生于哪個年代以及其影響如何,作家的生平怎樣,作品的內容和形式怎樣,當時有沒有形成一定的流派和運動,這都必須有如實的記載材料,做假不得,隨意不得。而文學史家對歷史上的作家和作品的評價又必然有一定的傾向性。因為,文學史家總是有一定的政治立場和價值觀念、審美趣味、學術視野,這都影響到他對一定作家作品的思想藝術成就的評價。其中不免會存在一定的偏見。所以,對作家作品的比較穩定性的、能為大多數人公認的評價,往往需要多代評論家和文學史家的努力,才能逐步形成。歷史事實是客觀的,而對歷史事實的認知和評價,則是主觀的,總逃脫不了一定的傾向性。要做到客觀、公正、恰當的評價,文學史家就得有開闊的歷史視野和比較的眼光,就得盡量克服階級的、黨派的、小集團的偏狹性,就得站在歷史進步的立場和觀點上,并以包容各種不同藝術風格、流派的胸懷去看待作家和作品。
文學史評價中往往涉及作家身份與文學成就的評價問題。兩者在評價上當然有關系。但作為文學史,文學成就的評價是第一位的,身份評價是第二位的。毛主席是革命家兼詩人。在政治史中,他的革命家的身份自然很重要,詩歌創作的成就是次要的。而在文學史中則相反。同樣是革命家,毛主席的詩詞寫得比別的革命家好,就得給他高的評價。這方面,不能以人廢文。比如對胡適,在文學史中就不能因為他追隨過蔣介石而不肯定他的文學成就和貢獻。周作人曾當過漢奸,自然是他歷史上的政治污點,但文學史也不能因此就否定他的文學成就和貢獻。雖然污點也必須指出。過去,我們有的現代文學史著作,往往因人而廢文。對歷史上不革命或反革命的作家和作品,往往一筆抹煞。在重寫文學史中,對這樣的作家和他們的文學作品貢獻,給予一定的肯定評價,這是完全應該的。但也曾出現這樣一種傾向,即對像浩然這樣的作家和作品,卻又一概貶低或否定。這大概仍然是政治標準第一的觀念在作怪,而且那種政治標準第一也是缺乏分析的、不夠實事求是的。浩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過一定錯誤,但并不是“四人幫”的幫派分子。這是經過審查后做了組織結論的。何況他的創作并非沒有一定的藝術成就,為什么就一概抹煞呢?!其實,看得遠一些,歷史上有許多政治上并不進步、甚或反動的作家,文學史家也不曾一筆抹煞。比如阮大鋮在明代末年因投降滿清,很為漢人所不齒。但文學史卻沒有否定他所作的《燕子箋》劇作。近人于右任先生隨國民黨到了臺灣,他的政治立場曾反共。他的詩作仍然為我們所贊許。因為他的許多詩,確實寫得好。
文學作品的價值評價問題自然相當復雜。不同時代不同階級不同審美趣味的人們,對同一作品往往會產生不同的評價。因為他們的價值判斷的標準不同或有差異。因而在今天,我們就存在一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標準的問題。人們對文學怎樣評價,實際存在一個評價的價值體系,并不單純只有政治標準和藝術標準。雖然這兩個標準確實很重要。評價文學,當然首先要研究文學性的標準。即面對一個作品,首先要看它是否是文學,有沒有文學性。然后才看它的政治傾向如何?道德傾向如何?宗教觀念如何?等等。文學性就包括真善美,反映的生活真不真?思想的導向善不善?語言、結構、形象等形式的表現美不美?還有文學作品的整體風格是柔美、纖麗,還是陽剛、雄健等。你如果文學的審美觀念很狹隘,只喜歡某種風格而排斥其他風格的作品。那么,你在文學性的評價上就會陷入偏斜而難公正。作品的真實性是藝術的真實性,它源于生活的真實,卻又區別于生活的真實。文學藝術的創作容許采用夸張、象征、幻想等虛構的方法和手法,并不要求等同于生活的真實。因而,如果你用再現現實生活的現實主義去要求浪漫主義或現代主義的作品,自然就會南轅而北轍。文學史家總要有很大包容性的藝術品味,去看待不同藝術方法和手法所創作的不同風格的作品。而不能以一把尺度去衡量所有的作品。對不同作家作品的評價所以會分出高低,還有個比較的問題。鐘嶸《詩品》把古代的詩人分成幾等,就是比較出來的。至今,文學史著作對作家作品的介紹也都有詳有略,實際同樣把作家作品分成幾等,有的作家自己占一章,有的作家幾個人一章,有的作家則幾個人才占一節。這就是根據作家作品的文學性、文學貢獻的大小而比較出來的。在這種比較中,文學史家所用的尺度就不是單純的,而是包含多種視角多種層面的綜合價值評判體系。我們今天所提倡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則是一種衡量思想傾向的綜合評價體系。就新中國文學的評價而言,這種評價體系對文學史家是不可或缺的。它是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的,包含民族傳統的愛國精神和改革開放時代的開拓創新精神,以及公平正義、平等和諧的科學發展觀與社會主義的道德理念等。自然就文學的評價而言,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衡量的主要是作品的思想性,包括政治傾向性、道德榮辱觀等方面。對于古代文學的評價,人們在思想性層面更多從作品的人民性和進步性等方面來衡量。
問:當代文學評價中,你剛才談到浩然的評價問題。你覺得在新中國文學史編寫中究竟應該如何評價浩然才合適、才科學?
答:浩然無疑是在新中國文學的發展中占有比較重要地位的一個作家。他從上世紀50年代初期登上文壇,出版過《喜鵲登枝》等多部短篇小說集,60年代創作長篇小說《艷陽天》三部曲,文化大革命中又創作有中篇小說《西沙兒女》、《百花川》,到70年代末出版了他長期孕育和創作的《金光大道》四卷;80年代后他還創作有《山水情》《浮云》《老人與樹》和《蒼生》等中、長篇小說以及“自傳三部曲”。2005年12月中國文史出版社出版有《浩然全集》18卷,計1000萬字。可見,他的創作成果相當豐碩,屬于新中國創作最勤奮的作家之一。他一生的創作,基本上都是寫新中國農村變革的題材。對他的評價和爭論涉及如下幾個問題:浩然的身份和人品,浩然對新中國農村、包括對農業合作化運動描寫的真實性,特別是農村階級斗爭描寫的真實性,對浩然實踐革命現實主義和革命浪漫主義相結合及“三突出”創作原則應怎樣看?
關于浩然的身份和人品,主要涉及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現。當時出現所謂“一個作家、八個樣板戲”。“一個作家”就指浩然。意思是那時作家中只有他一個人沒有被揪斗,還能夠寫作。而且認為他投靠“四人幫”,受到江青的重用,還被內定為“文化部副部長”。有些評論家和文學史著作由此認定他的人品“壞”,是“四人幫”的“幫兇”。但文化大革命后,經過組織審查,結論是浩然并非幫派分子,只是犯有錯誤。實際上,文化大革命中還能寫作的作家并不止浩然一個。汪曾祺就改寫過樣板戲《沙家浜》,黎汝清就寫過《萬山紅遍》,當時還沒有成名的劉心武、諶容等都在文化大革命后期發表和出版過作品。魏巍的《東方》、孟偉哉的《昨天的戰爭》也基本創作于文化大革命期間。當然,他們沒有受到“四人幫”重視。浩然被江青帶去西沙,并非他投機鉆營的結果,而是“四人幫”運用組織名義下令要他去的。他沒有識破“四人幫”的反黨面目,是他的認識局限。但那時又有幾個人能識破呢?!浩然的錯誤屬于人民內部認識的錯誤。我們必須把他放在同時代的許多情況差不多的作家行列中去公平地評判他。而不能混淆敵我矛盾與人民內部矛盾,或根據道聽途說的并不確實的情況來評判,單獨苛求于他。
農業合作化運動是否真實、合理,對此,中國共產黨經過全黨四千多人的討論,最后以中共中央的名義頒布的《關于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已有明確的結論。即基本肯定1951—1956年合作化運動的成績。事實證明,那個時期從發展互助組到建立初級農業合作社和高級農業合作社,都促進了農村生產力的發展。胡繩在《中國共產黨七十年》一書指出,“當時的許多統計資料表明,合作社80%以上都增產增收,并且一般都是互助組優于單干、合作社又優于互助組,因此互助合作運動得到了廣大貧苦農民的歡迎,他們積極要求入社。”自然,農業合作化運動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發生的,卻又是符合廣大貧下中農利益和愿望的群眾性運動。富裕中農開頭觀望,富農則內心反對,但后來既因大勢所趨的政治壓力,也因社會心理學所闡明的從眾心理驅動,都先后加入了。1956年雖因毛澤東急于求成,發展得快了些,后來又做了整頓和鞏固。1957年還是獲得豐收。這是由老解放區農村互助組發展起來的運動,也是有組織有領導的席卷全國農村的運動。它促進生產力的發展就證明了它的合理性。它獲得廣大貧苦農民的擁護,就證明它的必然性。由于農業合作化運動,當時農村為我國工業化的資金投入做出了巨大的貢獻。這就是存在于當時中國大地的歷史真實。到了1958年,毛澤東急于走向“共產主義”,發動了“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化運動,這才造成農村生產力的破壞。因為生產關系超過了當時的生產力的發展水平,違背了客觀的經濟規律。人民公社化雖然也是歷史上發生的真實的運動,但它是左傾路線造成的災難。我們必須把它與前期的農業合作化運動區分開來,不能混為一談。浩然的文學作品,無論是前期的短篇小說,還是他的代表作《艷陽天》和《金光大道》描寫的都是前期的農業合作化,而非人民公社化。文化大革命中寫的《百花川》除外。浩然原來就是農民,參加革命工作后也參加過農業合作化運動,還長期與農村保持密切的聯系,擁有豐富的農村生活的體驗。他寫的基本上都是他所熟悉的人和事。所以,不能說他的描寫不真實。何況藝術源于生活又可以和可能高于生活,即使作家在革命理想的照耀下,對人物和情節有所理想化,那在文學的傳統寫作中也是允許的。
現在有些人贊成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也不反對現代主義和后現代主義,卻獨獨反對革命現實主義和革命浪漫主義相結合,這實在是很奇怪的。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的結合,是世界文學史上為許多偉大作家所采用所實踐過的。我國的古典長篇小說《三國演義》“七實三虛”,就體現了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的結合,否則就不會有諸葛亮“多智而近妖”的軍師形象,也不可能有關羽那樣“義薄千秋”的英雄典型。當年“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口號的提出,就把積極的浪漫主義作為自己有機的組成部分。世界社會主義文藝運動中的許多經典性的作品都是在遵循這樣的口號的背景下創作的。1958年毛主席受到當時群眾運動的鼓舞,更加強調浪漫主義的作用。周恩來總理后來解釋說,兩結合“以革命現實主義為基礎,以革命浪漫主義為先導”。我國著名作家梁斌說他所創作的《紅旗譜》中的朱老忠的形象,就是實踐革命現實主義和革命浪漫主義相結合,有意把朱老忠的形象“理想化”了的。老作家姚雪垠也闡述自己的名著《李自成》中所塑造的李自成的形象,也是有意實踐革命現實主義和革命浪漫主義相結合。應該說,無論是朱老忠的形象,還是李自成的形象,都塑造的十分豐滿、生動、真實,極有光彩也極為感人,富于藝術的魅力。藝術就是藝術,沒有人一定要把《三國演義》中的諸葛亮、關羽的藝術形象跟歷史上真實存在的諸葛亮、關羽混同起來。文學評論家和文學史家一定要有容納不同藝術色彩和創作流派的的胸懷,要分析和闡釋其不同的藝術特色。藝術作品的高下,關鍵在于是否提供了生動感人的藝術真實,而不在于創作方法。同是現實主義或浪漫主義的作品,也是有藝術高下的。它取決于作家的藝術才能和生活把握的廣度與深度。現代主義或后現代主義的作品也如此。拉丁美洲的魔幻現實主義,實際也是把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結合在一起的。所以,我以為,浩然采用革命現實主義和革命浪漫主義相結合的創作方法,不應受到責難。正如他后期采用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寫《蒼生》,不應受到特別責難一樣。
至于“三突出”的創作原則,是從文化大革命中對“樣板戲”的修改而總結出來的。見于當時文化部長于會詠寫的一篇文章。我以為,作為一種藝術經驗的總結,不無借鑒的意義。“四人幫”把它普遍化,要求所有的作品都去遵循,搞成藝術教條主義,這樣當然是錯誤的,應該被反對的。蔣子龍曾說過,那時他想寫個短篇小說,只有兩個人物,編輯卻要他遵循“三突出”原則,豈不可笑!但寫個大型劇本或長篇小說,寫的人物很多,而且確以英雄人物為主人公,那么,作家要借鑒“三突出”的經驗,就并非絕對不可以。因為一個大作品總有主要人物和次要人物,還有更次要的人物,作家不需要也不可能平均使用筆墨。當然,有的作品中主要人物也可能不止一個,如《水滸傳》就寫了許多英雄人物,各有各的故事情節。但就全書而論,最突出的筆墨還是用在宋江身上。我以為,作家創作可以有多種選擇,“三突出”也不失為一種選擇。浩然在《金光大道》中借鑒了“三突出”的原則,當然受到了當時思潮的影響,但關鍵還在于他筆下的人物是否寫得生動、真實、有血有肉,使讀者受到感動。“樣板戲”實際上也不是都做到“三突出”。《智取威虎山》中對楊子榮的突出是成功的。《紅燈記》里,李玉和、李鐵梅和江奶奶都很突出。《沙家浜》本以阿慶嫂為中心的戲,修改后要突出郭建光,實際上沒有做到,最突出最成功的的人物仍然是阿慶嫂。可見,“三突出”原則不是萬能的靈藥,不是什么作品都可以用。關鍵還得看作家的才能和生活基礎以及本來的創作意圖。上面提到的這幾個戲,文化大革命前的基礎就很好,經過不斷修改,精益求精,藝術上是更成熟了。所以今天仍然有許多觀眾喜歡。當代文學史的著作也不能因為江青曾插手就一概否定它。否則,又是“以人廢文”了。
社會主義時期的作品描寫階級斗爭的問題,不是浩然的作品所獨有的。《共產黨宣言》指出,自原始共產社會之后,“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斗爭的歷史”。“自由民和奴隸、貴族和平民、領主和農奴、行會師傅和幫工,一句話,壓迫者和被壓迫者,始終處于對立的地位,進行不斷的、有時隱蔽有時公開的斗爭……從封建社會的滅亡中產生出來的現代資產階級社會并沒有消滅階級對立。它只是用新的階級、新的壓迫條件、新的斗爭形式代替了舊的。”大家知道,階級斗爭的發現者并不是馬克思和恩格斯,而是法國的資產階級學者基佐。階級是由于人們在一定生產關系中所占的利益分配的地位而形成的。而階級斗爭不但表現為經濟斗爭、政治斗爭、軍事斗爭,還表現為思想文化的斗爭。那么,從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的時代,是否仍然存在階級斗爭呢?列寧曾指出,社會主義的過渡年代的特點是,既存在共產主義的成分,也存在資本主義的成分。我們今天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就屬于過渡的年代。新中國成立后,我國就向社會主義過渡。當時,國際上存在世界資產階級的反社會主義的包圍,國內原有的剝削階級,包括地主階級、資產階級和曾有一定剝削的富農,都有待改造。被推翻的民國政府到了臺灣后仍然叫囂和準備反攻大陸。當時國內外存在階級斗爭是客觀的事實。土地改革和朝鮮戰爭可以說是當時國內外階級斗爭的尖銳表現。在農業合作化的過程中,我國農村各階級因利益立場的差別而懷有不同的態度,對合作化的擁護、觀望和明里暗里的反對,就成為當時農村階級斗爭的一種表現。1956年,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宣布作為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矛盾已基本解決,已非社會的主要矛盾,而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與落后的生產力的矛盾已成為主要的矛盾。但會議沒有否定階級斗爭在一定范圍仍然存在。事實上也仍然存在。從1956年到1962年的波匈事件、國內右派事件和反右擴大化、蔣介石再次策劃反攻大陸以及國內一定范圍內出現地主、富農的“變天”思想與行為等,都說明一定范圍內仍然存在階級斗爭。面對上述現象的過于夸張的認識,導致毛澤東在1962年提出“階級斗爭一抓就靈”的“階級斗爭為綱”思想。這自然是左傾的不完全符合實際的錯誤觀點。但社會主義過渡時期階級斗爭一定范圍不同形式的長期存在,直到今天仍然是事實。只要社會存在貧富懸殊,存在階級分野,就不可能完全沒有階級斗爭。不承認這一點,就是否定歷史唯物主義的根本原理。社會主義的政權正確認識這時期階級斗爭存在的不同實際情況,通過發展生產力,縮小貧富差距,不斷調整和控制社會不同階級、階層的各種矛盾,達到將來工農差別、城鄉差別和腦力體力勞動差別都消失的社會主義高級階段,即共產主義社會,才能最終實現沒有階級對立和階級斗爭的社會。
如果上述觀點屬于實事求是的科學的話,那么,我們就比較能夠理解浩然這樣的作家為什么會在他們的作品中描寫上世紀50年代到60年代初的階級斗爭了。《艷陽天》和《金光大道》所寫的農村的階級斗爭和路線斗爭,是那個時期農村生活的現實存在,雖然,《艷陽天》受到“階級斗爭為綱”觀點的影響,有過于夸大階級斗爭之嫌,卻不能說它的描寫根本不真實。現在有人從西方人道主義的立場根本否定階級斗爭的學說,也從這樣的立場去否定浩然的創作,那就是另一碼事了。
上面說到,文化大革命中浩然有過左傾的認識錯誤,這在《百花川》的寫作中尤為明顯。但評價一個人和一個作家,我們都不能只看一時一事,而要看他的全人、全部表現、全部歷史。文化大革命期間還是北京市的作家,后來任過文化部副部長和中國文聯黨組書記的高占祥認為,“文藝是一個時代的記錄,是一個時代的足跡。浩然這樣寫階級斗爭、路線斗爭,正是盡到了一個作家的職責。試想,在那個年代,不寫階級斗爭,不寫路線斗爭,還能成為一個時代的作家嗎?浩然還能成為浩然嗎?浩然是一個品德高尚的人,他的人品、作品都是上品。”(見高占祥《〈浩然全集〉序》)我覺得,這是一個比較了解歷史情況,也比較理解浩然的作家和黨的領導干部,對浩然的負責任的評價,可以供我們文學史家參考。當然,文學評論家和文學史家也需要指出浩然的作品所存在的思想和藝術方面的局限與缺陷。我想對于浩然的評價所涉及的理論問題,實際上同樣適用于類似作家的評價。那個時代,柳青、周立波、李滿天、胡正、陳殘云、克非、王杏元等都寫過農村的題材。文學史家應該在同一平臺上把他們放在同一批評標準下去予以公正的評價。而不應對浩然一個尺度,對類似的其他作家又取另一尺度。
問:文學史研究和編寫中,文學與政治的關系是個非常重要的問題,你認為該如何處理才比較好?
答:在人類的意識形態中,最初期的文學是與政治等混同在一起的。原始社會的氏族部落的酋長,往往既是巫師,又是管理部落政治事務的頭人,在祭典或戰爭儀式中,在教育和娛樂的場合里,又能歌善舞,會講述神話與歷史傳說。這種狀況,在近代非洲某些黑人部落里仍然如此。由于社會分工的發展,文學才從混沌的前文學中分離出來。但歷史上,文學與政治一直存在密切的關系。孫中山說,政治是管理眾人之事。列寧說,政治是經濟集中的表現。毛澤東說,政治就是階級斗爭。他們從不同視角說的都有道理。在現實生活中,每個成年人都具有一定的政治立場、政治思想和政治感情,并往往決定他對于事物的愛憎。人們的政治立場往往是由其經濟利益所系的階級地位所決定的,但也有由他的政治思想信仰來決定。文學史上盡管也有不涉及政治的作品,如某些愛情詩、山水詩。但幾乎大多作家都會在作品中或明或隱地表現出自己的政治立場和政治傾向、政治感情。《詩經》中的“大雅”,多數作品是歌頌貴族的,而“國風”作為民歌,像《伐檀》、《黃鳥》、《碩鼠》等篇章則是抨擊和揭露、控訴貴族的,政治立場很鮮明。屈原的《離騷》既表現對楚王的失望和怨憤,又“哀民生之多艱兮,長太息以掩涕”,政治立場也相當鮮明。有的作家似乎退出當時的政治斗爭,歸隱于田園,像陶淵明那樣,保持政治的中立。其實,中立也是一種政治立場和態度。陶淵明不是沒有政治理想,《桃花源記》就寄托著他的政治理想。至于現代作家里,分為左翼與右翼,有“為政治而藝術”的,也有“為藝術而藝術”的,也是各有自己的政治立場和態度。就這一點來說,文學藝術確實脫離不了政治。同時,文學又確實能夠作用于政治,甚至如毛澤東所說,產生“偉大作用于政治”。《離騷》的忠君愛國和人民性的影響及于千古。田漢所作的《義勇軍進行曲》的歌詞,正因它產生了偉大的政治影響,才被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歌。文學與政治的關系還表現為另一面,即歷史上的政府、政治家對文學的發展也產生影響。三曹父子重視文學,與曹魏文學繁榮,產生“建安七子”,應不無關系。唐宋以科舉取士,重視文臣,對這兩代文學的輝煌,就有正面的作用。自晚清歷民國至今,政府、政治家對文學發展的影響,或促進文學的發展,或阻礙文學的發展,更是大家所熟知的。
文學史對文學與政治關系的描述,既應反映歷史的真實和探討文學與政治關系的規律,也要對作家作品的政治立場和政治傾向性作出評判。雖然,在文學史中政治畢竟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還是文學本身。但作家總有他的一定政治立場和態度,文學作品也總有一定的政治傾向性。文學與政治又確有多層的密切關系,對此給予一定程度的闡釋,不僅應該,也有利于加強文學史的科學性。
有的學者在所謂“文學歸位”說的影響下,厭惡與政治發生關系的文學,似乎文學一旦與政治發生關系,表現了一定的政治傾向性,那就不是好文學。甚至認為像丁玲、何其芳這樣的作家,沒有參加革命前,作品寫得很好,而參加革命后就不行了。我以為,這都是缺乏實事求是的分析精神的偏見。與政治有關的文學,首先要看是什么政治,是人民的、進步的政治,還是相反。其次,還要看到,固然存在與政治有關的不好的作品,包括因表達政治理念而產生概念化公式化的作品,但也存在寫得很成功的作品。恩格斯就曾指出,歐洲的許多偉大作家都是有傾向性的,包括古希臘的悲劇家埃斯庫羅斯、歐里比德斯和喜劇家阿里斯托芬。他明確說,席勒的《陰謀與愛情》是德國第一部有政治傾向的作品。我國歷史上,從屈原到魯迅,人們更可以指出許多偉大的杰出的作家的作品,都與表達當時進步的政治傾向相關。丁玲參加革命前所創作的《莎菲女士的日記》固然轟動一時,在揭露一個知識女性的病態的性愛心理方面有它深刻的一面,但作品反映現實生活的深度和廣度以及藝術描寫的生動、語言運用的純熟等方面,卻無法與她參加革命后所寫的《韋護》、《母親》、《太陽照在桑干河上》相比,她罹難復出后于新時期所重寫的長篇小說《在嚴寒的日子里》,雖然只是24章的未完稿,其人物刻畫之生動真實,筆力之蒼勁有力,更勝于《太陽照在桑干河上》,她后期所寫的許多散文都具有很高的藝術水準。何其芳早期的唯美主義的詩歌和《畫夢錄》固然因風格的獨特獲得好評。他參加革命后所寫的給少男少女們的《白天和夜晚的歌》則屬另一種題材和風格,當時在革命青年中產生有很好的影響。至于他后來詩作稀少,主要原因是他從事延安魯迅藝術學院文學系的教學工作,后來又被派到重慶從事文藝界的統戰工作和文學評論工作,還到晉察冀前線擔任朱總司令的秘書,新中國成立后他又被調到學術研究崗位,擔任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所長,無暇再寫詩。他作為作家的后期成就主要在學術和文學評論方面。而艾青參加革命后,他的詩歌創作就產生過不止一次的高潮,新時期復出后,他的《光的贊歌》等佳作,如井噴般涌出,這也說明作家參與政治,參加革命,就一定會導向文學創作的落坡的說法,是站不住腳的。
問:在研究和編寫文學史的過程中,特別是編寫《中華文學通史》的過程中,你對我國文學有什么新的認識?
答:概括起來,我的新認識就是,我國文學不僅是多民族的文學,也是非常多元多彩的文學,還是不斷開放的生生不已的文學。
魯迅先生當年把他的文學史著作標為《漢文學史綱要》,我想,他是認識到僅僅漢族的文學是概括不了中國文學的。應當看到,中國文學從古代起就是多民族的文學,今天更是多民族的文學。我國各民族分布于不同的地區,經過幾次大的民族遷移和融合,互相影響,顯長補短,從而使中華民族文學顯示出多民族多地區的特色,也顯示多元的特色,非常豐富多彩!比如,我們過去認為,中國文學的史詩似乎不發達。在古代,只有《詩經》中的《生民》和《公劉》兩篇勉強可稱“史詩”。而放眼多民族文學,則史詩美不勝收。藏族和蒙古族的《格薩爾(格斯爾)》、蒙古族的《江格爾》、柯爾克孜族的《瑪納斯》堪稱具有世界性影響的三大英雄史詩。《格薩爾》長達百萬行,迄今還活在藝人的口頭傳唱中,其長度遠遠超過希臘的荷馬史詩《伊利亞特》和《奧德賽》,也遠遠超過印度的《羅摩衍那》。光蒙古族就有大小史詩近200多種。蒙古族的《蒙古秘史》、維吾爾族的《福樂智慧》、藏族的《薩迦格言》和達賴喇嘛倉央嘉措的情歌,還有其他民族的許多作品,都大大豐富了中華民族文學的寶庫,閃耀著五色斑斕的光彩!魏晉后,北方和西方的鮮卑、羯、羌、匈奴等民族入主中原所產生的北朝民歌的蒼勁宏放,與南朝民歌的綺美柔麗,風格各異,相映成趣。西北各民族地區的草原大漠、高山峻嶺的雄奇風格與游牧民族的流動性,以及他們獨特的文化傳統、宗教信仰、生活方式,賦予他們的文學迥異于漢族的文學的內容與形式。而西南各地的眾多民族,生活在長江、珠江上游的青山秀水間,以農耕為主,文學的內容、形式與風格又另具別樣的風采。各民族中的許多作家還參與了漢文學的創作,為漢文學的發展作出重要的貢獻。屈原所屬的楚國,曾被漢族前身的中原的華夏族稱為“南蠻舌之邦”,雖處于華夏族文化的影響下,三楚風光民俗仍大異于中原。當時就屬于少數民族。而屈原創作的楚辭名篇《離騷》、《九歌》、《天問》等,都成為我國文學的千古絕唱。魯迅稱譽《離騷》比之《詩經》“則其言甚長,其思甚幻,其文甚麗,其旨甚明,憑心而論,不遵矩度……然其影響于后來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漢文學史綱要·第四篇》)可見屈原對漢文學的貢獻。后來,像金人元好問,遼人耶律楚材、回人薩都剌、滿人納蘭性德等等都有漢文的文集或詩詞集。現代以來,像滿族的老舍、蒙古族的李凖更被公認為漢語言的文學大師。今天,各民族作家大多都用雙語寫作,同樣為漢語文學的發展作出了貢獻。
文學的多元不僅表現在多民族上,還表現在思想內容的多元上。思想性是文學的靈魂,是文學發揮真善美作用所不可或缺的。我國古代的神話就是多元多譜系的。比如漠北草原的民族就有關于大樹和蒼狼的神話,中原的民族則有女媧造人、精衛填海、大禹治水的神話,南方民族卻有關于人從葫蘆中生出的神話和洪水來了、人躲進葫蘆中而得救的神話,還有關于盤瓠的神話。這些神話對人類起源和人與自然的關系,做了不同的想象和解釋。文學既是文化的重要部分,也是文化的重要載體和傳播媒介。文化的多元性自然會表現于文學中。在漢族文學中,儒家文化、道家文化和佛家文化都有很大影響。對蒙古族、藏族文學而言,佛家文化的影響尤其大。而對維吾爾族、回族文學,則伊斯蘭教的文化具有決定性的影響。薩滿教文化對東北諸民族和西南一些民族的文學也有重要影響。近代以來,基督教的影響也對我國許多作家和文學作品影響不小。西方人道主義和馬克思主義傳入我國,更為我國現代作家提供了新的思想之光,提供了新的人生觀、世界觀和價值觀。
正由于各民族文學的相互影響相互交融,再加上能夠吸納其他國家文學的優長,我國文學就長期處于開放的狀態,能夠新新不已,不斷推陳出新,不斷獲得創新的生命力。南朝劉勰在他所著的《文心雕龍》中就指出,“時運遷移,質文代變”。那還是千多年以前,他已經考察到文學因隨時代前進而不斷產生從內容到形式、風格的新變的規律。佛教的傳入,產生唐代演說佛經故事的《變文》,開了說唱結合的白話文學之先河。而北方民族固有的說唱文學,對后來宋元話本和金元雜劇的發展也有明顯的影響。近現代以來,我國文學從世界各國文學中吸納了許多新的觀念、新的取材視角、新的文學品類和體裁,從而使我國文學不但走向現代化,而且內容、形式和風格都大大豐富了。在這種創新中大多作家都能夠把民族傳統的繼承和對外民族、外國文學的借鑒結合起來,把民族特色與現代世界文學的大趨勢統一起來。
正因為我國文學的多民族性和豐富多彩、不斷創新,自然也表現為文學時空和地域版圖的不平衡性,從而也為文學史研究提供新的可資拓展的空間。
今天的全球化時代,馬克思、恩格斯當年在《共產黨宣言》中所指出的,由于商品、資本、人才、技術和文化的世界范圍的流動和交換,從而導致的“各民族的精神產品成了公共的財產。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為不可能,于是由許多種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學形成了一種世界的文學”這樣的時代業已到來。我們也必須以這樣更宏大的目光去考察我國文學與世界文學的關系,作為我們書寫中國文學史的必要的參照。
問:你對新歷史主義與書寫文學史的關系怎么看?
答:新歷史主義認為應當把歷史本體與歷史文本區別開來。一切歷史文本都是由當代人寫的,因此,歷史文本不可能完全再現歷史本體的狀況。這自然是對的。但歷史并非可以由后人隨意打扮的小姑娘。我們不能陷入歷史不可知論。在文學史的領域而言,由于文學史是以歷史存在的文學作品文本和創作這些文本的作家為基本的研究對象,而且可以參考相應時代的政治史、經濟史、文化史等其他研究成果,它的歷史真實性就可能比其他的歷史文本為高。當然,由于歷史上的戰亂和災害,許多文學文本已經消失,如現在我們對西夏的文學就罕有所知。在成吉思汗的軍隊滅亡西夏,焚掠一空后,西夏的文化遺存已寥寥無幾。這不能不是絕大的歷史遺憾!但我國歷代留存下來的文學文本與史籍畢竟很多,經過近代以來學者的不斷發掘和整理、出版,應當說為后人書寫文學史提供了越來越豐富、翔實的歷史資料。這是十分幸運的。正因如此,我們在編寫《中華文學通史》的過程中,才有可能努力拓展文學史的研究領域,填補中國文學史過去著作中的許多學術空白。我們不僅首次把全國56個民族的文學都納入文學史的視野,而且把臺灣、香港和澳門等地區的文學也納入我們的書寫中,還加強了對北朝文學的研究,將遼、金文學與宋代文學并列,對近代被忽視或重視不夠的俠義小說、鴛鴦蝴蝶派小說和現代主義文學、淪陷區文學等都做了新的補充和擴寫。
問:聽說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和少數民族文學研究所又在修訂《中華文學通史》,是這樣嗎?

2012.1.22—27春節期間于北京花家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