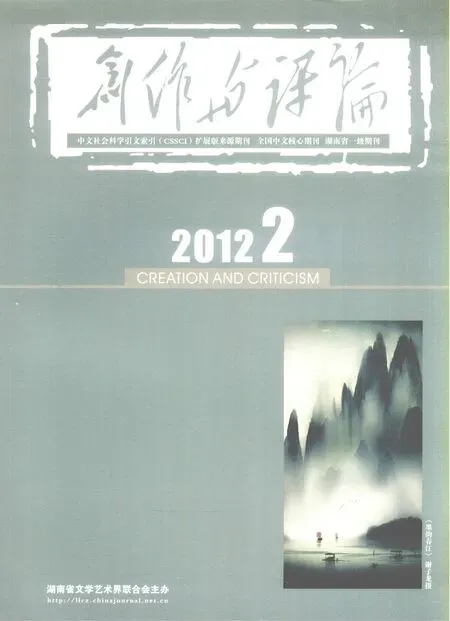消費文化語境下文化經典的改編*——以電影《白蛇傳說》為例
■ 閆寧
《白蛇傳》作為中國古代四大愛情傳說之一,經過自唐以來的歷代改編和時代的洗練,已成為深入人心的神話故事,被公認為中國民間文學的經典范本。其故事文本敘述有著中國文化意義上的價值觀,和獨屬中國神話色彩的魔法設定。這樣的建構使《白蛇傳》的故事文本非常適合影視劇的改編,于是電視劇《新白娘子傳奇》和電影《青蛇》紛紛出爐。《新白娘子傳奇》以純情為故事突破點,趙雅芝所飾演的白娘子以其溫婉賢淑的傳統氣質賺盡觀眾們的同情和眼淚;《青蛇》則以癡情的糾葛為入戲點,將陷入情欲中女性的妖氣媚骨淋漓盡致地展現出來,以后現代主義的迷離妖艷之美贏得觀眾的眼球。此兩者的白娘子形象深入人心,以至此后劉濤版的《白娘子傳奇》難以有所突破。在這樣的背景下,2011年9月底推出的電影《白蛇傳說》仍然取得了不菲的票房傳奇。《白蛇傳》被一拍再拍的前提下,電影《白蛇傳說》票房傳奇的背后是消費文化和經典改編的一次成功共謀,是在充分尊重市場消費法則的基礎上,將社會消費心理學成功運用于文本改編和影視制作中商業運營和文化創新的共贏。
一、明星效應運營下的角色添加
電影理論家雷蒙·迪爾尼亞認為明星直接或間接地“影響著社會的需要、動力和憂慮。他們是夢想的養料,使我們可以生活在內心最深處的幻想和迷戀中。明星們就像古代神話中的男女諸神一樣,一直被當作精神上的偶像來敬慕和崇拜。”他甚至認為“一個國家的社會史可以根據它的電影明星來寫。”①消費語境下的電影運營模式中,明星效應是不容忽視的票房刺激點。明星作為由觀眾制造出來的“被消費者”是電影構成的重要實體,一旦某個具有票房號召力的明星參加演出,就意味著導演得到了一個聚寶盆。利用明星效應來增加影片的賣點是電影產業普遍采用的一種營銷手段。但是,每位明星在消費群體中有特定的形象定位,影片的角色定位應和明星的這種大眾形象定位相合,否則明星定位和角色定位脫離的形式主義明星效應,會激起觀眾強烈的抵觸心理。對此兩者的依附關系,《白蛇傳奇》的制作團隊顯然是注意到了,并力圖將兩者完美的結合。
作為一部商業片,《白蛇傳說》的明星陣容可謂是傳說級別的了。針對各個層面觀眾群的口味,影片打造出復式多維的明星陣容:上有李連杰,中有各路鉆石配角,下有林峰、文章,可謂老少通吃、打擊面廣。但《白蛇傳說》的制作團隊并沒有把明星效應作為孤立的營銷策略,而是將其有機地整合入影片的故事改編中,力求明星定位和角色定位統一、角色添加和影片娛樂性統一,使本片跳出單一強調明星效應這種形式主義的宣傳所造成的“叫座不叫好”的魔咒。
統觀影片的明星陣營,為了凸顯娛樂性,笑星群體占據半壁江山。為此,編劇在尊重原著故事模型的基礎上添加了一條喜劇復線,即法海大徒弟“能忍”和“青蛇”——這對“傻小子”和“小蘿莉”的新鮮組合。能忍作為新創作的角色,其定位和扮演者文章的熒屏氣質是相契合的,有樹袋熊一樣的稚氣、木納、憨呆。青蛇伶俐“鬼丫頭”的熒屏形象也與扮演者蔡卓妍的明星定位相吻合。貼合演員定位的角色創造和改編使影片中能忍和青蛇的對手戲“笑果”突出。特別是文章飾演的能忍,呆頭呆腦卻頻頻爆出幽默臺詞,常讓觀眾樂不可支。如能忍被青蛇邀請“做朋友”的窘態、變身過程中的“萌”樣和青蛇古怪精靈的“淘”樣都通過臺詞表現的淋漓盡致、相得益彰。
另外,圍繞著這條喜劇復線,劇中又增加了許多包袱和亮點,幾乎為所有參演的明星都量身定做了相應的角色。在許仙到白府提親這一情景中,以楊千嬅、杜汶澤牽頭的各路笑星所組成的“親友團”發揮自身優長,極盡搞笑之能事。而“千面嬌娃”徐若瑄所扮演的雪妖,也發揮了其不老美顏的特征。又冷又白的雪妖,似乎給這位傳說級美人的不老之謎做了一個注解。在觀影的過程中,觀眾將這些影視形象和自己心目中的明星對號入位,在對明星身份定位的再確認中獲得一種認同的滿足感。角色添加和明星效應的組合,不僅保留了《白蛇傳》神話傳說的厚重感、傳奇性,也在細節上玩出了新花樣,屢屢讓觀眾體會到了新鮮、有趣,從形式到內容都大大地提升了影片的質感。
二、文化身份認同下的主角詮釋
在《白蛇傳》的故事原型被一改再改,一拍再拍的前提下,電影《白蛇傳奇》首先面臨的難題就是怎樣把一個觀眾耳熟能詳的神話故事改編得新穎而不空洞、現代而不雷人。讓人欣喜的是,本次的改編并沒有盲目地追求顛覆、創新。如果僅僅從核心故事和核心矛盾上來看,《白蛇傳說》的所有核心都和我們熟知的白蛇故事嚴絲合縫。改編的重點放在白娘子形象和愛情主題的現代闡釋上。影片對故事基本框架的保留,能夠讓觀眾體驗到故事流程的順暢性,沒有什么磕磕絆絆的不解之處。而對白娘子和愛情主題的現代演繹,則讓觀眾在情感訴求上尋找到一種時代文化認同和身份認同的滿足感。這種腳踏實地的心態、絕不好高騖遠的改編,不僅保留了傳統故事傳說的傳奇性,還增添了其現代元素,大幅度提升了影片的娛樂性和認同感。
“一千個觀眾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作為《白蛇傳》敘述的女主角,自故事產生開始,就不斷地隨著時代環境、社會價值理念的變化而變化。唐傳奇追異求新的性質和儒家“發乎情,止乎禮”的情愛觀,使最初的白娘子形象沒有跳出“妖”的界域,是一個靠色相誘惑男人并吸食精血的妖害,法海則作為正義的代表來收拾妖害,保一方之平安。明代以來,隨著市民階層的發展壯大,對人性正常欲望的肯定和對剝離物欲的純粹愛情的向往,使白娘子的形象漸漸褪去妖性而更多的展現出美好的人性。而五四以來,中國社會對個性解放、婚姻自主號角的吹奏,則讓白娘子最終完成了轉身,成為追求自由戀愛、捍衛美好情感的文化符號。從白娘子形象的演變我們可以看出,傳說不同于史實,其流傳具有時代的變異性,同一故事往往會在不同時代的口耳相傳中變幻出迥異不同的臉譜。
個性解放的號角已經吹了近一個世紀了,在“不怕出格,就怕沒個性”的現代社會里,人們必然會以極具時代性的角度來看待和理解這流傳了幾百年的愛情故事,并成為影響故事改編的重要元素。特別在當今消費語境下,“消費不僅要在結構的意義上被界定為交換體系和符號體系,同時還要在策略的意義上被界定為一種權力機制”②。大眾消費者在現代經濟中的權力意義被無限凸現,其價值取向成為文化產品生產、設計和銷售的“風向標”。③鑒于此,此次改編在白娘子形象的處理上就力圖在主角、主題詮釋上與當下社會的文化價值觀達成一致。在宣傳和營銷上,《白蛇傳說》自始至終都將80、90后人群作為產品的目標消費群體,聲稱影片所塑造的白娘子形象和要傳達的愛情理念,是對80、90后性格特點和價值理念的一種藝術化顯現。
《白蛇傳說》中的白素貞對愛情的態度具有80、90后人群的沖動傻氣和感性至上主義,不再是一個不食煙火或儒雅或妖嬈的女神姿態,而是會為愛做傻事,為愛不顧一切,為愛蠻不講理,有血有肉的女子。編劇放棄了“報恩說”,而是將白娘子和許仙的愛情演繹為“眼緣”的純感性主義。在這個充滿物欲誘惑和理性至上的現代社會里,我們多么希望在愛情的理想世界里撒著潑、打著滾地轟轟烈烈的愛一回啊!白素貞和小青在仙山向凡間眺望,看到許仙等一干人爬山,她被許仙堂堂外表和遠大志向吸引而傾慕于廝,于是一吻定情,二吻定江山。為了幫助許仙實現懸壺濟世的理想,白蛇甚至不惜耗損自己的生命精氣。由于耗損過大無法抵制雄黃酒的威力,她被法海打回了原型,在孤立無援的絕境中,卻又被自己傾盡所有愛著、護著的人深深扎了一法刀,生命奄奄一息。被打回原型的白蛇在法海等人的圍困中決絕的抗爭,卻突然挨了致命一刀,當她回身要反擊的時候,卻發現原來是許仙——那個自己為之抗爭到底的人。白蛇剎住致命一擊的招數,定定地望著驚慌失措的許仙,留下了眼淚——心中的山河為之頃刻坍塌,哀莫大于心死。黃圣依扮演的白蛇或許沒有趙雅芝版那般儒雅、識大體,不夠王祖賢版那般撩人、妖嬈,但她確實是用情最深最傻也最真的一條白蛇。在宣揚個性的今天,新白蛇追求愛情的生猛、捍衛愛情的彪悍足可在眾白蛇之中拔得頭籌了。
對于愛情的詮釋,編劇并未止步于此,新版許仙一改往昔的被動、愚昧、怯懦而轉變為堅定相信愛情、捍衛愛情的男子漢。當法海告訴許仙剛才的白蛇,就是他的娘子時,他再不是戰戰栗栗的害怕,而是堅定地說,真愛無人妖之歧——他冒險上金山寺為自己誤傷的素素偷仙草;許仙上金山寺不是法海欺騙或挾持的結果,而是為了救白素貞去偷取仙草。《白蛇傳說》里的愛情不再是白蛇報恩或白蛇單方付出的傳統故事而是一個雙方彼此深愛,愿意以生命捍衛對方的現代傳說。片末,夕陽下黃圣依扮演的白娘子抱著已經不認識自己的許仙流下眼淚,——“為什么要對你掉眼淚,你難道不明白是為了愛?”是的,這不是趙雅芝的白蛇傳說,也不是李碧華的青蛇傳說,這是一個關于愛情的傳說,那些陷入愛情的人也好、妖也好,同樣因為愛情,留下過或喜悅或悲傷的眼淚。對于我們僅此而已,無關對錯、無關倫理也無關理智。
三、價值多元化中的矛盾和解
自《白蛇傳》的故事誕生以來,白蛇和法海的斗爭一直成為故事演變流傳的主要矛盾。無論從最初,法海作為正義的代表,為保一方平安,施法鎮壓興風作浪的蛇妖;還是到最后,白蛇作為自由的象征,為捍衛愛情對法海的反抗。歷代版本對白娘子和法海的矛盾處理上,始終沒有跳出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要么白蛇扮黑臉法海扮白臉,要么法海扮黑臉白蛇扮白臉。這種二元對立的敘述結構是社會思維簡單化和價值取向單一化在故事敘述中的藝術化表達。在婚姻嚴格遵照“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社會里,這種二元對立的敘述模式也許能宣泄人們對包辦婚姻的不滿情緒。而現代社會是一個思想意識開放、價值觀念取向多元化的社會。個性是流行的標簽,情愛是順其自然的事,本無法海式的阻隔,也沒有誰有權利這么做。所以對作為佛教高僧的法海何以那么無理取鬧對白娘子和許仙死纏爛打,現代人在理智和情感上都很難理解和接受。改編如果依然以簡單的二元對立的敘述視角來處理白蛇和法海的主要矛盾,無論在藝術上還是觀眾接受上都難以取巧。
“在文學中,故事是作家的藝術創作物,而不是事實的真相,所以故事的敘述者(作者)可以憑個人的主觀愿望去安排人物的命運或故事的最終結局,……在一部文學作品中,‘故事’是可以由作者去任意描述得,同樣的一個事件,作者敘述得角度、方式(材料的取舍)、語氣(肯定或否定)的不同,將會使故事和人物的面貌產生決然不同的后果。”④文學人物甚至歷史人物的臉譜并不是一成不變的,作為藝術創造出來的人物,他們的內涵潛隱著再闡釋的巨大空間。事實上,當下越來越多為反面人物翻案的文學、影視作品不僅獲得了社會大眾的追捧,也獲得了經濟收益的成功。縱觀當下文化界,“翻案風”似乎構成大眾文化消費的熱潮。在此背景下改編《白蛇傳》,法海反面角色的重新定位將是消解二元對立敘述的重要突破點,何況出演法海的是李連杰。
當下文化消費行為特別是影視產品的消費中,對某位明星的迷戀和追慕是刺激大眾去影院觀影消費的重要因素。李連杰是中國影壇近二十年來“打遍天下無敵手”的“熒幕英雄”,英姿颯爽的風姿和干凈利落的功夫為其在眾多的影迷心中,樹立起感懷天下、俠骨柔情的大俠形象。李連杰出演法海是《白蛇傳說》的重要賣點,法海形象的改編如果與李連杰經營多年的熒屏形象相背離,眾多影迷絕然不會買賬,沒了購買的刺激,消費行為就無從發生。顯然這是影片投資人和制作團隊所不愿看到的,在時代價值取向的多元化和明星定位的雙重作用下,《白蛇傳說》為我們展現了一個全然不同的法海形象:他對世人有救民于水火的仁愛,對弟子有溫情倦倦的父愛,最后也有對妖孽感懷天下的慈悲。
在電影中白蛇和法海的矛盾不再是簡單的善惡之戰,雙方的動機都有善的、合理的因素。白蛇追求真愛,為愛癡狂,法海職業除妖,平安百姓,兩個人的行為都有其合情合理的一面。在多元價值觀共存的今天,存在即是合理的,我們無法責備為愛癡狂、蠻不講理的白蛇,更無法責備尊崇職業道德、伸張正義的法海。在情與理、法與情反反復復的糾葛中,我們看到的是白蛇的純、癡、執,看到的是法海的正、信、義,兩個人物不再是表示善惡的單一符號,而轉變為性格相依相離充滿矛盾的復合體。白蛇的癡情中帶有不可理喻的偏執,偏執中又展現傾盡一切的純情;法海的正義中帶有冷酷無情的決絕,決絕中又透露出悲天憫人的慈悲。所以,白蛇會奮不顧身的去救許仙,法海會關鍵時刻放白蛇一馬。這種相依相離性格因素的組合使白蛇和法海的形象內涵變得飽滿、厚重。因此,當影片在展現法海出于職業信仰,對素素不得不驅逐和痛下殺手的時候,我們看到的不再是雙方決一死戰,致對方于死地的兇狠,而是人妖交鋒,手段是狠的,心卻是軟的。人情味和現實意義的注入,使白蛇和法海最終的和解水到渠成。當法海在佛祖的啟迪下,感悟到眾生平等、慈悲為懷的佛理境地時,他扛起了雷峰塔成全了素素與許仙的最后一面。溫情的結尾為悲劇了幾百年的愛情悲情主義添上了一筆暖色。畢竟白娘子對愛情義無反顧的浪漫情懷構建了現代人超越現實的詩化夢境,雖然她做錯了事,涂炭了生靈,要為此付出慘痛的代價,我們依然希翼有一雙手伸出來滿足她的最后心愿——我們誰又能不犯錯呢?
注 釋
①劉廣宇:《影視理論綱要》,西南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137頁。
②[法]鮑德里亞:《符號政治經濟學批判》,夏瑩譯,南京大學出版2008年,第70頁。
③閆寧:《論民間文化在現代經濟中的軟實力》,《現代經濟探討》2010年第2期。
④梁巧娜:《性別意識與女性形象》,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3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