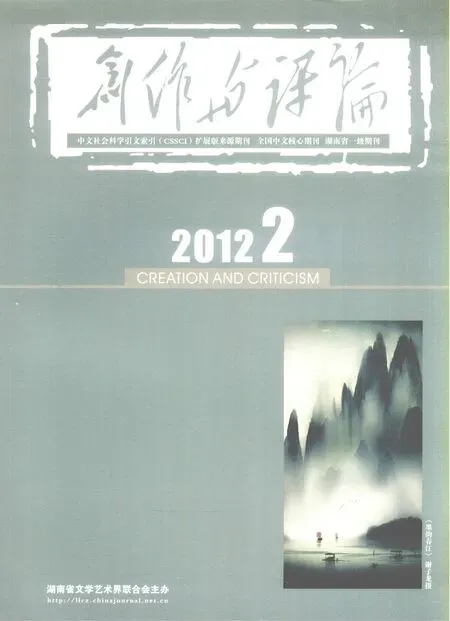歷史之痛與懺悔之思——評莫言的《蛙》
■ 周志雄
莫言在談到大江健三郎的創作時說:“寫作新小說時我只考慮兩個問題,一是如何面對所處的時代;二是如何創作唯有自己才能寫出來的文體和結構。”①這何嘗不是莫言自己創作的夫子自道。作為一個已經寫出了《紅高粱家族》、《豐乳肥臀》、《檀香刑》、《生死疲勞》等許多優秀作品的作家,莫言寫作《蛙》時有很高的起點,對于像莫言這樣“重復自己是可恥的抄襲”的成熟作家來說,寫作最大的困惑是如何面對已有作品的挑戰,在閱讀《蛙》時,我們會不自覺地追問,《蛙》在何種層面上構成了對莫言以往作品的超越?《蛙》如何處理莫言在談大江健三郎時提出的兩個問題?《蛙》的創作對當下的文學創作有什么樣的意義?
一
中國當代歷史是一個急速變革的歷史,歷史的機緣在不同的時代為人物的命運變化帶來了豐富的戲劇性,在歷史宏大的機制下,個人的身影是卑微而渺小的。小說敘事的魅力在于可以自由地穿行于虛構與歷史之間,以歷史性和想象性混雜的人物故事去重新整理和評價歷史,給讀者帶來閱讀的快樂,并獲得反思歷史的機會與展望未來的可能性。在命運的播弄和歷史的夾縫中,人性的卑微和屈辱在小說家的故事敘述中得到了生動的再現。與社會學家、經濟學家、統計學家、政治學家對歷史時代的描述不同,小說的歷史敘事既有豐富的生活細節,人性的可能性想象,也有超越于時代政治的悲憫情懷和人文關懷,甚至是哲學的思索和啟示。小說家與社會歷史學家的不同還在于,他不需要直接回答他的社會診斷,一切皆在人物、故事、場景等想象之中,充滿模糊意味的隱喻和人物故事孕育著多種理解生活的可能性。小說歷史敘事的目的就是把讀者帶回到歷史之中,重新回望并思索歷史,在文字的縫隙中,找到人性的多重可能性和歷史的某些癥結。
《蛙》就是這樣的一部充滿歷史敘事魅力的小說,小說穿行在建國后的歷史時代之中,小說敘述的是關乎國人生活重要方面的生育問題。中國作為世界上的人口大國,從人類生存發展的意義上,幾十年的計劃生育政策無疑是必要而成功的。中國又是一個有生育傳統的國家,計劃生育國策與國人的香火觀念、生育權利之間又是有矛盾的。當代中國生育問題對國人的生活影響是深遠而廣泛的,世界上沒有哪個國家有這么嚴重的人口問題。生育問題不僅僅是國家政治,也是老百姓生活的重要部分,不僅僅是人口數據的變化,也是飽含著普通老百姓血淚情感的歷史事實。作為小說家的莫言以深深的責任感,看到了這樣充滿悖論的歷史現實。
《蛙》的難度在于計劃生育是一項無可質疑的“國策”,表現這樣的“敏感”的社會題材,是不能超出這個基本前提的。如何處理這樣的重大題材?其文學的意義在哪里?莫言的處理方式是以大跨度的歷史年代進行對照,書寫在歷史的變遷中人們所受到的生育政策的影響,以人的命運變化寫歷史,以生育線索為中心串起了人物的愛情史、社會生活史、階級斗爭史、心理發展史、精神血淚史,以毛茸茸的人物故事呈現充滿悖謬的歷史黑洞和人性本色。姑姑(萬心)是小說的主人公,1950年代國家提倡生育人口,姑姑是一個接生能手,接生了數千個嬰兒,是受高密東北鄉人敬重的圣母般的人物。在階級斗爭年代,姑姑因為戀人飛行員駕機投敵受牽連,她成為社會的專政對象,受政治打擊和身心摧殘。在國家實施計劃生育政策的年代,姑姑是一個優秀的計劃生育干部,她鐵面無私,為工作鞠躬盡瘁,萬死不辭。她是個傳奇式的人物,她為革命工作犧牲了愛情,犧牲了自己的青春,她為維護國家的法律,赴湯蹈火般地迎接一個個的任務。這是個為時代犧牲的人物,在她光輝的歷史下,她受到身體上和精神上的重重傷害。作為計劃生育干部,姑姑成為非法生育婦女的敵人,頭上被人打棍子,走夜路被人砸黑磚頭,身上有很多傷疤,被人戳著脊梁骨罵,給她最沉重的精神負累的是她逼死了幾個懷孕的婦女,被人詛咒。她的晚年是在“罪感”中度過的,一個人仿佛受了歷史的欺騙,陷入矛盾的撕扯之中。她害怕青蛙,隱喻了她一生所背負的罪惡之源。姑姑的精神矛盾分裂癥是時代造成的,它隱喻了歷史現實對個人的巨大傷害。這個曾經的“政治斗士”,其悲劇如小說的敘述人蝌蚪所說的,她“太聽話了,太革命了,太忠心了,太認真了”。但姑姑不是一個簡單的“政治斗士”,她醫術精良,很有同情心,她不是一個冷血的人,在看到違法懷孕的小孩出生的時候,她作為婦科醫生的本能也會被喚醒,甚至在面對母牛難產的時候,她也會出手,她還不止一次地無私地將自己身上的血輸給病人。這樣一個充滿精神光輝的人物,最后變成了劇作家蝌蚪代孕生子的幫兇,曾經的正直品格,完全化解了。姑姑的人生命運和精神心理變化質疑的是時代對個人的壓迫,在大時代中,個人不過是一枝隨風的蘆葦,姑姑是時代觀念的受害者,是歷史運動的受害者。
除了姑姑,小說中的蝌蚪、小獅子、陳鼻、王肝等何嘗不是歷史的受害者。“蛙”所象征的生殖文化在當代社會左右了眾多人物的命運。蝌蚪作為一個劇作家,他最終也成為“香火”觀念的不自覺繼承者,追隨姑姑戰斗了一生的小獅子充當了觀念的幫兇。高密東北鄉最漂亮的姑娘陳眉外出打工在一場大火中被毀了面容,被迫與人代生孩子充當“孕奴”為父還債,又被出爾反爾的袁腮等人欺騙,精神上飽受摧殘。王肝、王仁美等女性在國家、家庭、歷史所構成的復雜困境中作為生育的“容器”丟掉了生命,有震撼人心的效果。
二
據莫言自己的講述,《蛙》的寫作有一波三折的經歷,早在2002年就寫了15萬字的初稿,主要是采取主人公坐在舞臺下觀看舞臺上上演他創作的話劇的方式展開構思,穿插主人公的回憶,再描寫劇中人的表現和觀眾的反應,可謂是一個多角度敘述表現歷史的構想,后來覺得自己這樣的寫作太過“混亂”了,可能會構成對閱讀者的折磨。②這篇小說后來采用了劇作家蝌蚪寫信的方式,以5封短信、5篇故事敘述加上一個劇本構成,既有多維的敘述角度,又有敘事上的明晰性,符合中國讀者的接受習慣,這構成了小說結構上的創新性。
《蛙》分為三種語言敘述故事,書信、小說講述、戲劇融為一體。內容上,三者相互映襯,書信是真實的,小說是虛構的,戲劇是真假混合的,小說以這種真真假假的方式切入時代,讓讀者深思,這不僅僅是形式上的新穎變化,而是引導讀者從小說表層超離出來,獲得更深層次的認識。如同小說中李手對蝌蚪所言:“文明社會的人,個個都是話劇演員、電影演員、電視劇演員、戲曲演員、相聲演員、小品演員,人人都在演戲,社會不就是一個大舞臺嗎?”現實和戲劇的內在本質被人物一語道破,在這里獲得了強烈的諷刺效果。《蛙》中蝌蚪寫給杉谷義人的書信是以一個文學青年向一個文學家請教的口吻寫的,涉及的主要事情是如何進行文學創作,如何將姑姑的事情寫成文學作品。這種敘述的方式極大地擴充了小說的內容,使小說有了多重意義空間。比如蝌蚪寫給杉谷義人的信中說:“在過去的二十多年里,中國人用一種極端的方式終于控制了人口暴增的局面。實事求是地說,這不僅僅是為了中國自身的發展,也是為全人類做出貢獻。畢竟,我們都生活在這個小小的星球上。地球上的資源就這么一點點,耗費了不可再生,從這點來說,西方人對中國計劃生育的批評,是有失公允的。”這是從政治層面上來講的,形成了對故事的補充和映襯。再如在另一封信中說:“十幾年前我就說過,寫作時要觸及心中最痛的地方,要寫人生中最不堪回首的記憶。現在,我覺得還應該寫人生中最尷尬的事,寫人生中最狼狽的境地。要把自己放在解剖臺上,放在聚光鏡下。二十多年前,我曾經大言不慚地說過:我是為自己寫作,為贖罪而寫作當然可以算作為自己寫作,但還不夠;我想,我還應該為那些被我傷害過的人寫作,并且,也為那些傷害過我的人寫作。我感激他們,因為我每受一次傷害,就會想到那些被我傷害過的人。”在這樣的段落中,說出了小說寫作的意圖,引導讀者去懺悔,去深入地思考小說故事敘述中沉甸甸的一面。小說的最后一部分是劇本,這個蝌蚪創作的劇本在內容上是小說故事的延伸,采取的形式是戲謔的,歷史上的高密縣令高夢九斷的案子是今天的,官府被買通,采取了一種遮人耳目的方式斷案,這個頗有寓意的情節戲謔了歷史沒有進步,在經濟發展的當下時代,政治黑幕并不比歷史上任何時代少。
《蛙》的敘述很緊湊,毫不拖泥帶水,故事的推進很快,沒有過多的冗繁的心理描寫和景物描寫,細節描寫和人物形象描寫很簡練,看上去像是一幅幅工筆畫。小說選取的是幾個不同時代的片斷性的故事,以幾個核心人物為中心,進行發散,小故事大時代,以少勝多,在20多萬字的篇幅中書寫大跨度的歷史時代。莫言早期小說中那種感官鋪張的“炫技”式寫法在《蛙》中有較大的改變。莫言有寬廣的世界文學視野,但他的敘述定位是中國式的,他采用的是中國式的講述,寫作老百姓喜聞樂見的小說,清晰的故事,個性鮮明的人物,中國當代歷史,中國的社會現實,都是中國讀者所熟悉的。
《蛙》的中國式敘述也體現在小說所塑造的人物的精神氣質上。小說所寫的人物多是高密東北鄉的奇人,小說以奇事來寫奇人,這與中國古典小說中那種適當神化、拔高人物的寫法極其相似。奇人,或是一種有獨特個性的人,或是有特殊藝術才能的人,或是有傳奇人生經歷的人。姑姑是一個奇人,精神上的血脈可以延伸到《紅高粱家族》中“我奶奶”式的奔放人格,潑辣大膽,敢作敢為,勇于擔當。姑姑的奇還在于她傳奇般的接生技術,那種敢于赴湯蹈火的工作熱情,以及聰明干練的工作方法。秦河、郝大手的奇在于捏泥人的手藝,王膽的奇在于癡情,袁腮的奇在于算卦、給人取避孕環等“奇技”。奇人奇事是中國傳統小說塑造人物的方法,塑造的多是類型化的人物,但莫言面對的是21世紀的讀者,他當然不能簡單地寫類型化的人物,而是在傳奇人物的個性中增加了多面性,比如上文分析的姑姑形象,再如劇作家蝌蚪是個性格曖昧的人。與奇人相聯系的是他們的奇事,陳鼻的經歷,陳眉代孕,蝌蚪的婚戀史等等都具有傳奇意味。《蛙》也不是簡單停留在傳奇故事上,還揭示了這些人物故事背后濺著血淚的一面,傳奇故事中有著深厚的心理基礎,還有飽滿、生動的生活細節,小說不是簡單地天馬行空虛構奇事,而是將嚴肅的社會批判與傳奇式人物故事的講述結合在一起。
莫言多次說到小說家的風格就是作品的語言風格,這部小說的語言創新體現在莫言自如地運用了多重筆墨。一是政治語言。這體現在文革時代的人物語言中,以姑姑的講話為代表。“姑姑嚴肅地說,你們年輕人,要聽黨的話,跟黨走,不要想歪門邪道。計劃生育是基本國策,是頭等大事。書記掛帥,全黨動手。典型引路,加強科研。提高技術,措施落實。群眾運動,持之以恒。這段姑姑的話很夸張,塑造了一個深受政治影響的人物形象,在字里行間隱隱地表達了歷史的揶揄。第二種是樸素、簡潔的敘述語言。“在河邊釣魚的閑人杜脖子親眼看到我姑姑從對面河堤上飛車而下,自行車輪濺起的浪花有一米多高。水流湍急,如果我姑姑被沖到河里,先生,那就沒有我了。”這段語言很簡潔,但很有神韻,很幽默,姑姑潑辣、豪爽的形象從敘述中呼之欲出。第三種是一種詩意化的戲謔語言。比如:“她眼里飽含著淚水,是因為愛孩子愛得深沉。”這段話是對艾青詩歌的戲謔,在嬉笑中蘊含了人物嚴肅一面。當然《蛙》的語言不只是這三種,莫言是個很注重語言的作家,他積極吸收了民間的生活語言,古典散曲的語言,注重語言的氣勢,小說中常有一些鋪排的感性書寫語言,有很強烈的個人風格。《蛙》的語言風格總體上向樸素的敘述回歸,作者有意壓低了那種鋪排的感性敘述風格。一個作家使用的語言不是通常的生活語言,而是經過提煉的一種個性化的語言,只有這樣的語言才能呈現一個獨特的藝術世界,莫言正是這樣一個有語言自覺的作家。
三
莫言的小說不是戴維·洛奇所說的“現代主義小說”,不搞純文學試驗,而是有現實的責任和關懷;不是向內轉去描寫人物的內心世界,而是有明晰的人物故事;也不是用開放性或含混性的結尾,而是有鮮明的傾向性。莫言的小說藝術建立在中西小說資源的基礎上,立足中國的民族歷史,積極吸收中國傳統小說的藝術形式,并對之進行當代化的改造和推進,以現代的思想和理性精神貫注其中,符合民族讀者的閱讀習慣,又給讀者以精神的滋養和啟迪。經過多年的寫作磨煉,莫言的小說在藝術上已經非常成熟,藝術個性非常鮮明,達到了自由創造的境界。《透明的紅蘿卜》對生命的疼痛感的表達,《紅高粱家族》對人性自由與生命本色的張揚,《豐乳肥臀》、《檀香刑》、《生死疲勞》等作品以大跨度的歷史變遷書寫人性之思與一個民族的精神之思,《酒國》、《紅樹林》、《天堂蒜薹之歌》、《生死疲勞》對現實的批判精神,《十三步》、《檀香刑》在敘事方式上的革新,等等,都給讀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蛙》的寫作建立在莫言多年寫作的基礎上,藝術上進一步推進,以更廣泛的人類意識和懺悔意識,在清晰的故事中蘊藏著對人類生存的深層思索。
我們不難看到《蛙》與莫言已有作品的聯系,如對“高密東北鄉”文學地域空間的書寫,對民間語言的積極吸收,對民間傳奇式人物故事的敘寫,對中國讀者閱讀習慣的尊重,等等。但《蛙》又是對莫言創作的一次推進和創造,莫言在積極地回歸民族傳統的時候,又在積極地發展傳統,對此,除上文已涉及的外,還突出的表現在小說意義空間的營造和對藝術手法的綜合運用上。
作為一部現實主義的小說,《蛙》在主旨上超出了故事本身的內涵,這是莫言在敘述上所采取的藝術手段所達到的藝術效果,其中主要是隱喻手法的恰當運用。這是小說中的一段:“蛙類并沒有什么可怕的,人跟蛙是同一祖先,她說,蝌蚪和人的精子形狀相當,人的卵子與蛙的卵子也沒有什么區別;還有,你看沒看過三個月內的嬰兒標本?拖著一條長長的尾巴,與變態期的蛙類幾乎是一模一樣啊。”這段話解釋了小說的題名,說出了小說的深層含義,它隱喻了生殖文化對中華民族的影響力。主人公蝌蚪的名字也有隱喻意味,一個講述生殖文化的劇作家本身就是生殖化的。小說的封面設計為在紅色的底色下站著一個孩子,又像是一個青蛙,有一股強烈的生殖氣息。書中的人物以人體的器官命名也隱喻了人的身體是生殖文化的產物,個人的生死悲苦與特定歷史背景下生殖文化緊密地聯系在一起。《蛙》提出了關乎民族發展的重大問題,在新的歷史時代,我們該如何反思我們的生育傳統?小說中姑姑嫁給郝大手的過程也是有隱喻意味的,姑姑被一群青蛙追逐,被青蛙撕去了衣裙,這件事說起來不具有現實性。但具有內在情理上的合理性,它暗指了我們每個人都是有罪的,姑姑對自己罪惡的懺悔通過自己的丈夫將那些被流產的嬰兒重新捏出來,以贖回自己的罪惡。有罪的人不只是姑姑,敘述者蝌蚪,接受信件的杉谷義人,等等,很多人都是有罪的,如莫言所說:“要把自己當成罪人來寫,他們有罪,我也有罪。當某種社會災難或浩劫出現的時候,不能把所有責任都推到別人身上,必須檢討一下自己是不是做了需要批評的事情。”③因此,小說就不僅僅是寫歷史,寫民間傳奇故事,而是在故事之中有深層的人性反思和文化反思,這就極大地擴展了小說的意蘊空間。
《蛙》在敘述清晰的故事,塑造鮮明的人物之外,也對人物進行適當的心理精神分析。通過對人物進行成長式的對照,對人物內心的精神沖突進行解剖,當然不是那種細膩深入的心理分析,而是一種在白描式的簡練的人物形象勾勒的基礎上,以人物富有個性的語言和簡練的心理描寫表現人物命運的心理機制。《蛙》的歷史跨度較大,人物的性格、心態前后有很大的變化,作者并沒有細致地展示人物內在精神脈絡,但給讀者留下了很大的分析空間。
如上文所述,《蛙》無疑是一部有批判性的小說。《蛙》在批判現實上是有自己的抱負的,但莫言批判的力度還是有限的,《蛙》對社會現實黑洞的揭示在多大程度上超越了新聞報道?多大層面上進入了對當代文化體制的深層反思?對人類的生存問題有沒有天問式的追問?莫言仍然是有所保留的,他自己也認識到了這一點。另外,《蛙》有懺悔的角度,但懺悔的靈魂并未被撕開寫,而是融入在一些隱喻性的情節設計之中。
任何作家都有自己的局限,莫言不是一個學者型的作家,他的思想沒有超出我們這個時代,但不容否認《蛙》是一部致力于創造的小說。莫言的創造是一種不斷積累的綜合創造,他直面歷史問題和時代問題,以小說的魅力去呈示那些歷史陳年舊事,啟示著讀者思考。在這個網絡寫作娛樂化泛濫的時代,在各種小說理論撲面而來的時代,執守小說藝術的創新是艱難的,但無疑又是必要而可敬的。
注 釋
①莫言:《大江健三郎先生給我們的啟示——在大江文學研討會上的發言》,《西部》2007年第9期。
②莫言等:《對話:在人文關懷與歷史理性之間》,《南方文壇》2010年第3期。
③楊桂青:《莫言 寫作時把自己當罪人》,《中國教育報》2011年8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