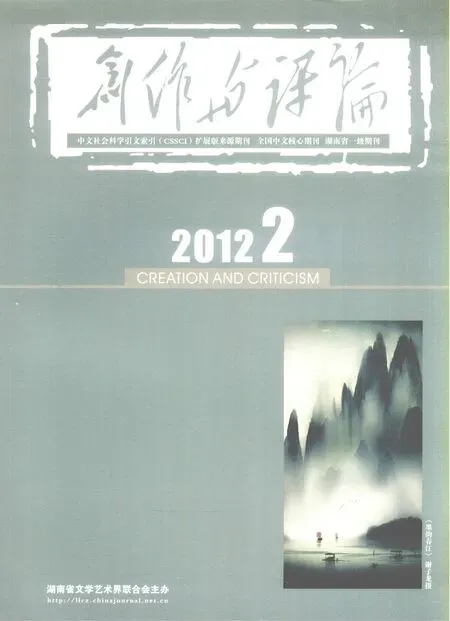匱乏中的繁復與反復——解讀張煒《你在高原》系列
■ 徐勇
一、繁復與反復
張煒的《你在高原》系列十部給人印刻最為深刻者,莫過于它的無處不在的繁復與反復。這一繁復和反復既表現(xiàn)為小說的出版發(fā)表上,也表現(xiàn)在敘述語言和情節(jié)內(nèi)容,甚至章節(jié)編排上。系列小說雖集結出版于2010年,但其實是張煒前此階段創(chuàng)作和出版的一次全面總結與回顧。這十部小說中,有些如《家族》和《我的田園》屬于舊作修訂后的重版,而后收錄在《你在高原》系列中;《橡樹路》則以單行本的形式,和《你在高原》(作家出版社)系列幾乎同時出版;有些如《憶阿雅》和《曙光與暮色》,則分別是此前《懷念與追憶》和《你在高原——西郊》修訂重版后的更名而成;而即使是系列名“你在高原”也是沿用作者此前的小說名《你在高原——一個地質(zhì)工作者的手記/我的田園》《你在高原——西苑》和《你在高原——懷念與追憶》)。若從小說的情節(jié)發(fā)展和設置來看,《你在高原》系列其實是在張煒早期長篇小說《柏慧》的基礎上的極大的擴充。其中,有些篇章如《父親的海》幾乎完全取自《風姿綽約的年代》中的同名篇章;《金黃色的菊花》和《窮人的詩》兩篇章,則均是《風姿綽約的年代》中相同篇章的縮寫。《如花似玉的原野》中的有些情節(jié)也被重新敘述后進入《你在高原》系列中。而《風姿綽約的年代》中“風姿綽約的年代”一節(jié)則幾乎被全部移入了《家族》當中。至于章節(jié)編排上,系列小說更是錯綜繁復:“你在高原”乃總的系列名,之下是各部小說名,而后分卷和章,再下就是各個具體的中短篇名如“父親的海”等。而事實上,各個中短篇很多都可以獨自成篇,很多如前面提到的《父親的海》、《金黃色的菊花》、《窮人的詩》、《風姿綽約的年代》等等,都曾以中短篇的形式發(fā)表或出版過。可見,如果不欲從張煒創(chuàng)作的整體上通觀,顯然是很難有效地把握這一繁復和反復的現(xiàn)象的,這是一個方面。
另一方面,這十部小說,其實可以當作一個整體來看。換言之,這十部小說大可看成一個叫寧伽的中年男性主人公的個人傳記。因為這十部小說的主體部分都是以第一人稱“我”——即寧伽——的口吻講述“我”和與“我”有關的故事。而之所以分為十部,是由于十部小說分別從十個不同的角度和側面進入,故而整個系列中,常常有大量的重復——情節(jié)、人物、結構乃至文字上的重復——,這無疑給人以絮叨和繁復之感,但如果換個角度來看,這種重復實則乃作者的有意經(jīng)營,毋寧說是作者數(shù)十年沉積于心底之訴求和吁求的表征。
二、尋找與追問
要理解張煒的這十部小說,僅從情節(jié)上考察,看來顯然是不夠的,因為在這其中有大量的情節(jié)互相重復交疊。在這里面,倒是有一些對立的范疇始終貫穿整個系列小說,這對理解小說十分關鍵。這些范疇有城市/野地、平庸/浪漫、定居/流浪、平原/高原、現(xiàn)實/歷史,等等。而事實上,恰恰是這些范疇的對立沖突和矛盾運動,起到了推動小說情節(jié)的發(fā)展——即敘述者“我”的行止:城市平庸而單調(diào)的現(xiàn)實生活,促使“我”不斷遠行(或重述歷史),而一旦“我”遠行到某一個地方,駐足不久,又再一次踏上了流浪的路途。如此循環(huán)不已。在這些范疇中,“高原”似乎又是理解的關鍵。“我的夢中有個高原。在這條通向高原之路,粉色的蘋果花紛紛落下來,它遮住了我奔波的身影,送我進入一個又一個香甜的長夜。高原……高原……我總能感到穿過遙遙旅途射來的那道目光,那是她的永恒的高原……”(《我的田園》)“她先我一步站在高原上。我突然明白了:我為什么有一雙永不停歇的腳。”“可她是誰?她從哪里來?她又為什么在高原上久久佇立?還有,我真的認識她嗎?”(《我的田園》)看來,“高原”毋寧說就是某一模糊而朦朧的目標,“她”誘使敘述者“我”不斷的追尋,永不停歇,至于這一目標到底是什么,為什么要追尋,敘述者自己也似乎不甚了了。
在這里,與其沿著敘述者“我”的思路去弄清追尋的目標“她是誰?”,不如反過來去追問敘述者“我”是誰?而事實上,敘述者追問“她是誰?”的意圖也是為了尋找屬于自己的語言——即“我”是誰?“我”從哪里來?“我”要到哪里去?因為,一旦弄清楚“我”所要追尋的目標是什么,她來自何方,又要到哪里去,也就能明白“我”是誰,“我”為什么要不斷地流浪和出走了。這樣也就能理解,系列小說為什么始終要以第一人稱“我”作為小說的敘述者并以有關“我”的故事貫穿始終。對敘述者“我”而言,似乎只有弄清楚追尋的目標——“她”是誰,才真正明白“我”所來何處。“我”之不斷的出走和流浪也似乎是源于因應“她”的呼喚;這似乎是一個循環(huán):是先有“她”的神秘的呼喚,還是先有“我”的不斷的出走。敘述者“我”翻來覆去的傾述,顛來倒去的出走,最終只是表明敘述者的迷惘,“我”既不明白“她”是誰,也不知道自己是誰。“我只有在這個時刻才發(fā)現(xiàn)自己又回到了原來。我明白:自己屬于一片無邊無際的野地,我只有與土地、土地上滋生的這一切面面相對時,才會感到內(nèi)心的愉悅。”(《我的田園》)讀到這里,忽然明白,敘述者一生不停的奔波,似乎總與童年時代的記憶糾纏在一起。實際上,童年時代在山林中的流浪記憶,正貫穿于《你在高原》系列的始終:那大李子樹,那林中的小茅屋,外祖母和母親,以及始終缺席的父親(父愛)。而這一切,某種程度上,又是源于某種匱乏:因為顯然,這一切美好的記憶很快就成為了歷史,因為父親的所謂不可洗脫的“罪責”,“我”被迫長期離家,從此浪跡山林,永難回頭;而且,美好的童年中的“故地”也正遭受毀滅性的開墾和破壞。可見,從這個角度看,“回到了原來”并不是要“原來”重演,而是要在記憶和敘述的回返中達到對匱乏的想象性解決。
在這里,“回到了原來”帶有重寫歷史的意味。因為“我”從哪里來,顯然涉及到歷史。而事實上,整個系列都一直在寫“我”的家族,乃至祖先的故事,這在《家族》、《憶阿雅》和《人的雜志》中有鮮明的表現(xiàn);而“我”要到哪里去,則顯然關乎未來。如果說歷史還能通過敘述的力量去追溯的話,未來則有賴于當下了。但問題是,敘述者“我”不屬于城市,也不屬于平原。這并不是說現(xiàn)實不接納“我”,而毋寧說是現(xiàn)實不接納“我”的歷史,因為,通過敘述的力量建構的有關“我”和“我”的家族的歷史,只是一部通過“我”的視角敘述和呈現(xiàn)的野史,并不為正史所認可:“我”的父親和外祖父進入不了歷史。而實際上,他們也已早已為歷史遺忘和歪曲,因此,對于“我”而言,要想進入現(xiàn)實也就意味著必須忘記家族前史,但忘記“歷史”,也就注定了“我”是一個無根之人。敘述者十分清楚,沒有歷史,也就難以安置現(xiàn)在的“我”。看來,這只能是一個無解的悖論:“我”能通過敘述講述歷史中的“我”(和“我”的家族)的故事,但這一故事只能存在于“我”的講述中,“歷史”于“我”似乎只是鏡像,“我”只能在“歷史”的講述中獲得完滿和自足,一旦進入現(xiàn)實即告破碎:“我”注定了要不停的流浪和尋找。可見,“我”之為“我”有著先天的匱乏。從這個角度看,正是這匱乏,促使張煒二十余年如一日地不懈寫作——也是敘述者“我”的始終絮叨不已,他的寫作客觀上就帶有彌補這先天匱乏的意圖之所在。
三、絮叨與孤獨
盧卡奇曾把小說寫作視為一項孤獨而歷險的事業(yè),這在某種程度上正符合張煒。張煒(敘述者)把他的孤獨化為不停的寫作和尋找,在他那里,寫作和尋找其實是同構的。在這個意義上,張煒其實是把孤獨的寫作視為一場對話和較量,他通過虛構和講述,既在與假象中的讀者,也在與目標“她”對話和較量。這從題目“你在高原”可以看出。“你”既是假想中的對話者(讀者),也是矗立在“高原”中的“她”,敘述者“我”雖不能至,但心向往之,因此,就有了敘述者的急不可耐,故而難免絮叨和重復;就有了敘述者想試圖說服假想中的“你”,故而出現(xiàn)不斷地訴說和表白。這似乎很反諷,張煒(和敘述者)的孤獨,固定在筆端,卻生出無限的絮叨。
這也決定了《你在高原》的文體形式,這是一種介于故事體和小說之間的混合文體。說其是故事體,是因為整個系列都是以敘述者“我”的所見所聞作為基礎,用本雅明的話說,就是立足于“經(jīng)驗”的講述和傳遞。在故事體中,還有一個因素不可或缺,那就是聽故事的人。連接講故事的人和聽故事的人的,不是故事,而是故事的基礎——共同的經(jīng)驗。故事表現(xiàn)在情節(jié)上雖然曲折離奇,但終究還在經(jīng)驗能理解的范圍內(nèi),故而能交流能被理解。在張煒這里,聽故事的人就是假想中的讀者“你”(也包括作為“她”的“你”)的存在。這里除了假象中的“你”的存在外,還預設了“你”與“我”的對話關系。我們擁有共同的經(jīng)驗基礎,故而能互相交流。但另一方面,通過敘述者“我”講述的故事,卻是明白無誤的“經(jīng)驗的毀滅”。因為顯然,我們之間經(jīng)驗之基礎的東部平原正一步步走向毀滅,現(xiàn)代文明正一步步侵襲著古老的平原;平原在萎縮,我們的共同經(jīng)驗也將蕩然無存。從這個意義上,這是一部以“故事”的講述的形式,完成的“小說”寫作實踐。張煒的寫作,希求的是與讀者的經(jīng)驗交流和對話,其結果,帶來的是交流的不可能。小說的寫作正是這種交流之不可能后的孤獨的文化實踐。“講故事的人取材于自己親歷或道聽途說的經(jīng)驗,然后把這種經(jīng)驗轉為聽故事人的經(jīng)驗。……寫小說則意味在人生的呈現(xiàn)中把不可言詮和交流之事推向極致。囿于生活之繁復豐盈而又要呈現(xiàn)這豐盈,小說顯示了生活深刻的困惑。”①“歷史”的先天匱乏,經(jīng)驗的破碎,“生活總體性”的缺失,邪惡之現(xiàn)代文明的長驅直入,張煒以他不倦的寫作,明白無誤地告訴我們這一點;但他同時又試圖以自身總體性的重建來抵抗這種缺失。這一努力賦予張煒的寫作格外地帶有悲劇性和挽歌色彩。但問題是,他的努力,他的通過把歷史與現(xiàn)實勾連和對接重建起來的,只能是他自己的總體性,這一總體性并不為他人和社會認同,敘述者的家族前史不為正史認可,敘述者的喋喋不休和奔波流浪也不為當世人理解,從這個角度看,張煒從事的,其實是“一個人的戰(zhàn)爭”(張煒語)。張煒的寫作雖然絮絮叨叨,其實從一開始就注定了孤獨終老。
這似乎是一種悖論:越是孤獨,張煒越表現(xiàn)出喋喋不休絮絮叨叨;社會越是變化莫測,張煒越是表現(xiàn)出二十多年如一日的堅韌;文化越是走向快餐化,張煒越是要越寫越長。這諸多矛盾對立奇怪地糾結在張煒的寫作當中,既相安無事又彼此互不相容。這與其說是張煒在考驗讀者的耐心,不如說他是在考驗自己,他是在拿自己的青春時光參與的一場豪賭。二十余年的堅守,十卷近五百萬字的篇幅,繁復的敘述,一己的呢喃,到頭來,都只能交付給素昧平生的聽眾,而事實上聽眾已演變?yōu)楣陋毜淖x者。畢竟,在聽眾和敘述者之間,可資交流的共同經(jīng)驗正日趨萎縮:這不禁讓人疑問,張煒以如此恢弘的篇幅建立起來的閱讀/對話機制還能持續(xù)多久?顯而易見,張煒其實是在以熱熱鬧鬧的文字,寫作最為孤獨的人生“體驗”。
四、成長等于流浪?
其實,如果把十部系列小說中重復(或重合)的情節(jié)和敘述文字刪掉,然后加以重組,《你在高原》系列大可看成是一個人的成長史,這就不妨從“成長小說”的角度來解讀這個系列。正如巴赫金在談到《巨人傳》之類成長小說時指出的:“這類小說中,人的成長帶有另一種性質(zhì)。這已不是他的私事。他與世界一同成長,他自身反映著世界本身的歷史成長。他已不在一個時代的內(nèi)部,而處在兩個時代的交叉處,處在一個時代向另一個時代的轉折點上。這一轉折寓于他身上,通過他完成的。……所以,未來在這里所起的組織作用是十分巨大的,而且這個未來當然不是私人傳記中的未來,而是歷史的未來。發(fā)生變化的恰恰是世界的基石,于是人就不能不跟著一起變化。顯然,在這樣的成長小說中,會尖銳地提出人的現(xiàn)實性和可能性問題,自由和必然問題,首創(chuàng)精神問題。成長中的人的形象開始克服自身的私人性質(zhì)(當然是在一定的范圍內(nèi)),并進入完全另一種十分廣闊的歷史存在的領域。”②可以說,《你在高原》就是這樣塑造敘述者“我”的,它把“我”放在“我”的家族前史,七八十年代中國的社會轉折以及二十世紀末的中國全球化進程這一復雜脈絡當中加以形塑,因而雖然始終講的是“我”的故事,但其實早已同家/國之間密切聯(lián)系在一起了。“家/國”的“前世今生”顯然內(nèi)在地決定了“我”的未來走向。
但事實是,敘述者/主人公“我”甫一出生,其實就意味著衰敗和下降:父親的難以洗脫的罪愆令“我”一家始終籠罩在灰暗之中,“我”的命運早已于冥冥之中由“我”的家族和先祖的命運決定了,“我”不過是再一次重復先人的人生軌跡;但“我”又似乎不甘于這種宿命,因而就有了“我”總是不停地流浪和出走。從這個角度看,這個系列又可以看成是當代的“流浪小說”。“我”的血液里先天留有先人流浪的稟性,因而從出生一刻起就注定了要不停地流浪。流浪任何年代都有,但流浪(漢)小說的產(chǎn)生乃至大量出現(xiàn),卻是近現(xiàn)代才有的事情。張煒小說中的流浪漢,內(nèi)涵極為復雜,這很像本雅明筆下的“游蕩者”形象,他們作為經(jīng)驗的被剝奪者,逡巡在現(xiàn)代大都市的邊緣地帶,他們其實是以破碎的經(jīng)驗對抗現(xiàn)代文明的震驚和巨大沖擊。顯然,敘述者“我”并非如三毛(《三毛流浪記》)一樣社會的底層或邊緣群體,也并非不被社會接納和認可,事實上,如果愿意,“我”可以輕而易舉地進入到社會秩序中去,可見,“我”的流浪漢形象更多是一種“心象”,是“我”的心靈不甘寂寞,“我”有家庭,有妻小,有親友,但“我”卻想著打破它們,沖出牢籠。“我”拒絕秩序,拒絕安定,向往野地。但問題是,野地茫茫,最終會把“我”引向何方呢?其實,早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中期,張煒在一篇創(chuàng)作自述中就曾這樣寫道:“我覺得我踏上了一條奇怪的道路。這條路沒有盡頭。當明白了是這樣的時候,我回頭看著一串腳印,心中悵然。我發(fā)現(xiàn)自己一直在尋找和解釋一樣東西,同一個問題——永遠也尋找不到,永遠也解釋不清,但偏要把這一切繼續(xù)下去。”③如果略去寫作時間,再把它隨便置于《你在高原》系列中的任何一部當中,其與系列小說中的文字敘述之間,簡直難分軒輊看不出任何區(qū)別。以此觀之,《你的高原》系列,其實還可以看成是作者的精神自傳,是作者早年創(chuàng)作追求的敘述實現(xiàn)。在這里,敘述者/主人公“我”某種程度上其實就等同于作者“我”。
但問題是,當作者在寫作中不知不覺混淆了這種敘述者/主人公“我”和作者“我”的區(qū)別時,他的寫作其實就已暗藏了種種危險。因為,這勢必造成敘述距離的消失,作者往往不由自主地隱沒于敘述者乃至主人公身上,其結果是,作品不可避免地變得沒有節(jié)制和感性泛濫;而事實上,一部成功的作品總是能很好的處理這種距離的。另一方面,這種混淆,也會造成認同上的混淆。因為寫作畢竟是虛構,現(xiàn)實主義雖能達到“仿真”“亂真”的效果,但實際上在這其中仍有距離的存在,而一旦作家在寫作中忽視了這點,反而可能導致效果上的“失真”。張煒的《你在高原》系列恰恰在這一點上沒有把握好。在小說中,“我”似乎總在尋找,但一佚找到,如換工作、辦雜志和開墾葡萄園等,“我”卻又在想著新的啟程(《我的田園》、《曙光與暮色》、《憶阿雅》等),如此往復,沒有窮盡。可見,尋找,對敘述者“我”而言,重要的并非目標和結果,而似乎是過程。既如此,又何必一而再再而三地尋找下去呢?而如果艱苦卓絕的尋找不是為了某一目標,這樣的尋找又有什么意義?難道就是“為了尋找而尋找”“為了流浪而流浪”嗎?這到底是敘述者/主人公的尋找,還是作者的尋找?事實上,這其實是以對沒有結果的“高原”的追求而犧牲了路邊的美麗“風景”:“我”并不“人道”。小說中,很多人物形象往往只如道具一般出場退場,無始無終,似乎就只為了形塑“我”的流浪漢形象,敘述者(抑或作者?)可以隨意棄之不顧。小說中“我”的妻兒因為“我”的永難安定而處于一種長期被離棄的結果,“我”之為“父”為“夫”的責任何在?而即使是像《我的田園》中的小姑娘鼓額和《曙光與暮色》中的姑娘小冷——這樣的形象在小說中還很多,當她們等待著“我”去救贖的時候,“我”卻突然消失得無影無蹤,這樣的信賴和依托,其意義何在?等等。這些雖然都是發(fā)生在小說文本內(nèi),但其實已不知不覺間從想象和敘述的層面顛覆了作者的形象及其文學實踐。
而最為致命的是,一旦敘述者“我”的尋找淪為一種無需結果和目標的永遠的過程時,張煒實際上通過這種寫作揭示出人生/敘述的荒誕之本質(zhì):沒有結果和目標的尋找,其實就是一種不斷的重復(或反復),重復(或反復)似乎注定要成為我們總也逃不脫的宿命。從這個意義上看,“高原”其實如同“戈多”,其有無早已無關緊要,對于我們而言,所能做的,似乎就只有翻來覆去的寫作和不斷的重復了。
注 釋
①本雅明:《講故事的人》,《啟迪》,北京三聯(lián)書店2008年版,第99頁。
②巴赫金:《小說理論》,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32-233頁。
③張煒:《一輩子的尋找》,《文學角》1989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