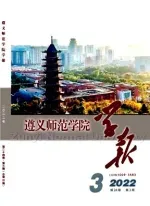論馮至詩的藝術特征
姚國建
(蚌埠學院 文學與教育系,安徽 蚌埠233000)
馮至早在上世紀二十年代就以獨特的個性,幽婉雋永的筆調,寫下了近百首新詩,分別收入了《昨日之歌》、《北游及其他》兩個集子,從此登上了中國的詩壇,成為當時沉鐘社最有影響、成就最突出的詩人,并被魯迅譽為“中國最杰出的抒情詩人。”[1]三十年代末他到昆明出任西南聯大外文系教師,并在那里創作和出版了令人耳目一新、顯示了詩人輝煌的藝術成就的《十四行集》(1942年)。此后,由于受當時抗戰氣候的影響,文藝界號召為抗戰而寫作,這與馮至的創作個性、藝術追求產生了沖突。經過痛苦的抉擇,他一度中斷了詩歌創作,轉向了“現實性較強”的雜文和隨筆的寫作。全國解放后,由于馮至那些具有現代主義特色的詩歌是屬于獨立化的個人寫作,不屬于那種革命派的詩歌,在那個崇尚浪漫主義和革命現實主義的時代,他的那些具有現代感的詩歌受到了長期的冷遇。半個多世紀過去了,今天,當人們超越了時空和種種偏見,站在詩歌藝術發展軌跡的歷史高度,重新審視馮至的詩歌時,不能不看到馮至的詩為中國現代主義詩歌的發展作出了突出的貢獻,特別是他的《十四行集》更是中國新詩里程碑式的代表作品。他的詩外觀樸實而充滿內在智慧,形式簡煉而包孕豐富內含,取材尋常而意境高遠,語言清麗而情味悠長,無論從思想內涵的開掘上,還是從詩歌藝術美的創造上,都達到了當時詩歌創作的高峰。本文結合馮至20年代至40年代的詩歌創作,對其詩歌的藝術特征作一些初步的探討。
一、質樸雋永的藝術風格
一個成熟的詩人總是有著自己獨特的藝術風格。風格是詩人在長期的創作實踐中逐步形成的,是詩人的主體精神通過獨創的藝術形式得以充分表現的,是詩人通過全部作品所體現出來的基本特色。它是詩人在漫長的創作實踐中所形成的精神體系與詩人在藝術創作中所習慣運用的藝術形式的高度統一。通過風格,我們可以看出詩人的創作個性。成熟的風格具有相對穩定性。法國文論家布封說過:“知識、事實與發現都很容易脫離作品而轉到別人手里,它們經過更為巧妙的手筆一寫,甚至會比原作還要出色些哩。這些東西都是身外物,風格卻就是本人。因此,風格既不能脫離作品,又不能轉借,也不能變換。”[2]馮至的詩,無論是早期的詩歌,還是后來的《十四行集》,都始終體現出一種質樸雋永的藝術風格。這主要表現在:
第一,馮至為人是樸實謙和的,性格是較為內向的,他不喜歡張揚和狂傲,而是喜歡靜謐的觀照和沉思。這決定了他在寫作時決不會狂呼濫喊地讓感情一瀉千里,也不會沒有形象依托、沒有迂回變化地赤裸裸地表露出來。他的詩不像郭沫若那樣以強烈的氣勢震撼人心;不像李金發那樣以晦澀神秘的意象折磨人。他的詩始終是質樸自然的,絲毫沒有矯飾、夸大和雕琢,也沒有過于激烈的情緒渲泄。例如寫于1923年的詩《不能容忍了》,單看標題,感情色彩異常強烈,似乎有一股激烈的情緒要渲泄而出,一吐為快,但馮至寫起來,卻對強烈的感情進行了有效地節制和冷處理,仍然采取了他慣用的樸實、平和而簡煉的表達方式。詩人創造了一個想象的境界,以平淡樸實的筆調,通過敘述“我”捧著自己“血紅的心兒”,到人叢中去尋找知音卻遭冷遇的事實,深刻地表現出在那個黑暗的時代,純潔真誠的心得不到理解、反遭譏誚的痛苦。全詩的感情不是外露的,而是凝聚在具體的情境中,卻比任何外在的渲泄更具有內在的力量。
第二,在詩的取材上,他沒有追奇獵新,也沒有刻意去關注時代風云、民族命運、國家大事等較大的題材,而是老老實實地從身邊的日常生活中選取平常渺小的事物,并以敏銳的感覺和深刻的洞察力,從中發掘出一般人所忽視的詩意。例如《我們來到郊外》(《十四行集·七》),這首詩根據詩人的注解,寫的是敵機空襲警報時,昆明的市民躲到郊外這一具體的事實。但詩人并沒有把這件事與抗戰的主題直接聯系起來,去強烈地表達對敵人的痛恨,對民族危亡的憂慮,對民眾苦難的關切。而是把關注的目光投向逃難人群的匯合與分開這一極平常的現象上,并且極冷靜地思索其中蘊藏的人生哲理。在他看來,人們由于同樣的“警醒”和“命運”,才像不同的河水流到郊外,“融成一片大海”,大家很容易凝聚在一起;詩人呼吁人們要愛惜這種共同的“警醒”和“命運”,珍惜這種危難情況下彼此關愛的凝聚力,不要等到“危險過去”,又回到“分歧”的現實中,“海水分成河水”,人們又各自東西,形成陌路。
第三,馮至深受里爾克、歌德等人的影響,注重追求詩的哲學意蘊。他的那些長于“沉思”的詩,外觀顯得自然質樸,實則含蓄雋永,耐人尋味。盡管他所選擇的都是日常生活中的平凡事物,但他特別注重激活自己對這些事物的獨特體驗,密切聯系它們與生命存在的方式、價值以及人的命運、追求和夢想等層面進行觀照和思考,并且注重尋找它們與自然、宇宙之間相通相聯的關系,努力從新的角度去揭示蘊藏其中的深刻哲理。例如《鼠曲草》,就從鼠曲草“躲避著一切名稱/過一個渺小的生活/不辜負高貴和潔白”,想到人生也應當像鼠曲草那樣,敢于否定和超越現實的“一切形容、一切喧囂”,才能默默地生存和奮斗,成就自己完美的人生。又如《我們站在高高的山巔》,則由人化為自然的遠景,自然的遠景又化成了人的生命這一情景,從而探討了人與自然息息相通、相互轉化的關系。再如《我們聽著狂風里的暴風》,通過寫狂風暴雨中人與物都孤單地存在,人與物之間,物與物之間都很難溝通,揭示了生命存在的本質是孤獨而寂寞的。他寫于三十年代的短詩《等待》,在無限廣闊的時空中,打通了人與自然、宇宙的關系,通過寫天上的星、海里的水對“你”漫長的等待和對“我”真誠的關愛,創造了一種人與自然、宇宙相互依存、相互關愛的美好境界,從而更生動形象地表現一種天長地久的等待、執著無言的深愛。
總之,從馮至的性格與氣質、取材特點、善于哲思的習慣,到他詩歌形式上的一些特征等等,都充分顯示了他的詩有著較為穩定的藝術風格,那就是既自然質樸,又含蓄雋永,讀后能啟人深思,耐人尋味。這也是馮至的詩迥異他人、自成大家的重要標志。
二、靈活巧妙的藝術構思
詩是講究藝術構思的。越是篇幅短小的詩,越是要在構思上嘔心瀝血,慘淡經營。陸游說過:“詩無杰思知才盡。”構思依賴詩人的藝術智慧,構思的好壞直接決定著詩作藝術水準的高低。馮至深深懂得這一點,并以自己的智慧,千方百計地在構思上下功夫,以便將自己從日常生活中捕捉到的詩意轉化成詩的藝術世界,大大增強作品的表現力和感染力。他的詩,從構思上看,大都是別具匠心、靈活巧妙的,其中呈現出一些鮮明的特點。
第一,從實境向虛境的轉折與升華。在詩歌創作中,實境與虛境相互結合,可以使詩虛實相間,增強詩的張力,拓展詩的境界,使詩意獲得升華。馮至的詩在構思上,常常是先寫一些實境(這些實境大都取材于他所熟悉的日常生活),作為詩的基石,詩的鋪墊,給讀者造成一種詩的實在感,具體感,然后將詩思突然轉入虛境(這種虛境常常來自詩人的頓悟或沉思),于瞬間突然拓寬了詩的境界,給讀者造成一種震驚感,意外感,使你在佩服詩人智慧的同時,不知不覺被引入一片新的精神領地,從中獲得意外的啟迪和審美的愉悅。如《幾只初生的小狗》(《十四行集·二三》),詩的前三節寫的都是實境。由于連落半月的雨,初生的小狗沒有見過太陽;等到雨過天晴,小狗的母親便銜著小狗去領受太陽的光和暖。這些都是生活中最平常的景象,不足為奇,但詩人卻在如實描述這個實境的同時,突然轉入詩的虛境:“但是這一次的經驗/會融入將來的吠聲,/你們在深夜吠出光明。”這就將現實與將來,現有的體驗與未來的行動一下子連接起來,使詩突然呈現出一片嶄新的天地,詩的精神境界發生了質的飛躍,直接進入了一個深刻的永恒的主題——“在黑夜中吠出光明”。可見,對光明的體驗將化成生命的血肉,化成潛意識中對光明的苦戀,也必將化成未來為光明而獻身的動力。全詩通過這種由實境向虛境的轉折和升華,實現了詩意由此岸向彼岸的穿越和抵達。
第二,借助想象創造獨特的意境。意境是指詩人主觀情意與客觀物象相互交融所形成的藝術境界。意境的創造將帶來詩歌的含蓄美。創造意境既要對主觀的情意進行藝術的提煉,又要精心尋找恰當的客觀外物,并且使二者水乳交融,有機統一。例如《我是一條小河》,就構思巧妙,把“我”比作一條小河,把心上人“你”比作“彩霞般的影兒”投入河水的柔波,創造了一幅迷人的意境,且隨著河水的流動,詩的意境也在不斷展開,不斷呈現出新的面貌:當“我”流過森林,便把那些碧綠的葉影兒裁剪成“你”的衣裳;當“我”流過花叢,便把那些彩色的花影兒編織成“你”的花冠;當“我”流入無情的大海,狂浪擊碎了花冠衣裳,“我”只有漂漾到無邊的地方,“你那彩霞般的影兒”,也和“幻散了的彩霞”一樣,暗示“你”和“我”已形神相隨,心心相印。詩人以新奇的想象,貼切的比喻,創造了優美的意境,形象地抒發了一種濃郁而美好的戀情。此外,他的《狂風中》、《雨夜》、《夜半》、《南方的夜》等詩也都采用了這種構思法。
第三,由自然界向人類界的巧妙聯想。馮至的許多富有哲理的詩,都是他善于沉思的結晶。聯想既是他沉思的推動力,也是他構思詩的重要手段。他常常眼光盯著自然界,心里想著人類界。在詩的構思上,也常常喜歡通過巧妙的聯想,把自然界與人類界聯系起來,于對照、關聯、比擬中表現人生的哲理。《威尼斯》就是由西方那座充滿著一個個島嶼的“水城”,聯想到它是“人世的象征”,表現了人與人之間要通過溝通與交往來擺脫生命的孤獨與寂寞。再如《原野的小路》,有感于原野里那“一條條充滿生命的小路”,是經過了“多少無名行人的步履”,才“踏出這些活潑的道路”,自然聯想到人類的心靈也有這樣的小路。這種聯想有效地將作品的主題拓展到人生的層面,它旨在啟迪人們,不要忘記了我們的心靈的小路,也是由許多人的步履踏出來的,若沒有他們的開拓,我們的靈魂還得四處漂泊,無路可循;在我們真誠紀念他們的同時,我們也要進一步守護并且拓寬這些心靈的小路,以便為后人留下更加寬闊的心靈之路。
第四,根據起、承、轉、合安排好詩的內在結構。前人作詩,講究詩的起、承、轉、合。馮至深受古典詩歌的影響,加上他寫的大都是精致短小的詩篇,因而他在構思中特別注意運用前人關于起、承、轉、合的寫詩原理,來安排好詩的內在結構,以便讓詩思的運行起伏有致,脈絡分明。例如《我們天天走著一條小路》(《十四行集·二六》),首先寫“我們”天天走著熟路,回到自己居住的地方,但林里還隱藏著許多尚未走過的生路,這是“起”。接著寫走在生路上“心慌”的感覺,這是“承”。后來望見“我們住的地方”,有一種異樣的新奇感和強烈的發現感:那個“我們”曾經十分熟悉的住地,此刻竟“像座新的島嶼呈在天邊”,詩人由此悟出,即使是身邊再熟悉不過的事物也還潛藏著許多未知的內涵,也在期待和呼喚著人們去進行“新的發現”,這是“轉”。轉出了新的境界,新的發現,使全詩的思想境界也發生了質的飛躍——由對個別事物的感悟進入了對人生普遍哲理的揭示。“轉”在全詩的結構中非常重要,轉得好,就能詩境拓寬,思想翻新。最后,詩人緊承“轉”的內在精神,作進一步的強調,提醒人們不要昏然不覺,熟視無睹,哪怕是自己最熟悉不過的發膚,到死時也還有許多未知的地方,也還會生出新的疑問。這是“合”。全詩就這樣在起、承、轉、合之中,把自己對平凡事物的感受與思考曲折有致地表現在詩中,使詩的境界不斷拓展而內在脈絡分明,情思跌宕起伏而又前后關聯。
第五,運用多種藝術手法,增強構思的靈活性和藝術感。為了避免構思的模式化,突出構思的個性化,多樣化,馮至還善于運用多種藝術手法,來增強構思的靈活性和藝術感。例如《蛇》的構思,就以精妙的比喻為主要手段來創造全詩的意境。在詩中,詩人巧妙地把“我”的寂寞比作“一條蛇”,“靜靜地沒有言語”,這種大膽的想象和新奇的比喻,確實前所未有,出人意外。全詩的境界也由此巧妙地展開:“我”在告訴心愛的姑娘,不要害怕,這樣奇異的寂寞,正是因為愛你而生;它在想念你頭上“濃郁的烏絲”,如同熱烈地思念故鄉“那茂密的草原”;它輕輕地游走到你那兒,正是為了要銜回你花朵般的“夢境”,以探究你的夢境里是否有愛“我”的信息。全詩就這樣巧妙地把寂寞比作長蛇,把烏絲比作草原,把夢境比作花朵,都是絕妙的比喻。正是依靠這些比喻,全詩的構思才顯得巧妙精致,虛實相生,不露痕跡。《夜半》一詩,本是要表達詩人對自己現狀的不滿和自責,本來也可以直抒胸臆,但詩人卻采用側面描寫的角度去構思,大量運用擬人的手法,創造了一幅奇特的“生命的狂歡”圖。在這幅“生命狂歡”圖中,詩人移情于外物,將桌上的文具全部擬人化了,它們一起行動,共同向主人發起了聲討,紛紛譴責主人的種種失職的行為。全詩運用擬人手法,把桌上的文具寫得栩栩如生,幽默風趣,從一個側面形象地表現了詩人對自我現狀的不滿,寄寓了詩人渴望回到那種充滿激情、充滿靈感、充滿創造的生命狀態。此外,像《橋》則運用了象征和對話體的方式進行構思;《在海水浴場》則運用了對比的方式進行構思,等等,這里不再一一論述。
三、淡雅含蓄的語言美
馮至的詩在語言上也體現出鮮明的個性。他不以詞藻取勝,不以夸飾見長,不以雕琢為能事,而是順其心意,追求一種淡雅含蓄、極富意味的語言,來增強他詩歌的藝術美。這與他的性格和為人,與他一貫保持的質樸雋永的藝術風格是合拍的。他的詩歌語言既來自他的生命和直覺,也經過詩人精心的選擇、錘煉和加工。同時,他的詩歌語言還明顯受到中國古典詩歌和外國現代詩歌的影響,因此,他的詩歌語言是一種具有很高的文化修養、很深的藝術功底的書面語言,具有很強的藝術表現力和感染力。
首先,他的詩歌語言是淡雅的。淡雅,即平淡而高雅。馮至的詩歌語言看起來是平淡的,清淺的,但這決不是直白、淺露、平庸、單薄,甚至口語化,隨意化。他的詩歌語言淡在自然、清新,不事雕琢,平淡而富有意味,是“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李白),是“一語天然萬古新,豪華落盡見真淳”(元好問),是“掃除膩粉呈風骨,褪卻紅衣學淡妝”(魯迅);雅在純凈、優美,淘盡雜質,脫俗而耐人欣賞。這種既保持了天然本色,又經過了詩人的選擇、錘煉和巧妙組合的語言,十分有利于表現馮至那種感情深沉、極富哲理的詩思,也使讀者從中獲得一種質樸、真純的審美享受。例如《別離》中的詩句:“我們招一招手,隨著別離/我們的世界便變成兩個,/身邊感到冷,眼前忽然遼闊,/像剛剛降生的兩個嬰兒。”詩中的語言都非常樸實,平淡,沒有形容詞,沒有感情的夸張和渲染,只是一種平靜的敘述,但這種語言組合在一起,卻極富張力和彈性,使人的目光要在詩行上流連往返,仔細品味和琢磨詩中潛藏的意味。“我們的世界便分成兩個”“像剛剛降生的兩個嬰兒”,似乎在暗示人們,夫妻二人整天廝守在一起,可能束縛了人的個性和潛能的發揮,暫時的離別和分開反而是好事,可使兩個人都獲得新的發展空間,有利于各自個性和潛能的發揮。這樣,面對離別,就不必憂傷,而應當感到慶幸,如同兩個人都獲得新生一樣;“身邊感到冷,眼前忽然遼闊”,這樣洗煉、清純的語言,也在暗示人們,離別雖然給各自帶來了冷清和寂寞,但卻為夫妻雙方都提供了新的更為開闊的生活舞臺,每個人都可以在這個舞臺上盡力拖展自己的才華。這首詩下面的一些詩句,如“把冷的變成暖,生的變成熟”,“為了再見,好像初次相逢”,等等,都是平淡而極富意味的。離別后,各自為了耕耘自己的世界,為社會作出更大的貢獻,以一種創造和超越的精神去看待別離,“冷”也會變成“暖”,“生”的也會變成“熟”。況且,這種“離別”的生活還會成為將來重逢時的美好回憶。一切的努力,一切的成功,一切甘于孤寂的堅守,都會使未來的“再見”變得更為溫馨和甜美,如同初戀般美好。此外,如“從沉重的病中換來新的健康,/從絕望的愛里換來新的營養”(《歌德》),質樸平淡的語言,概括了深刻的人生哲理。總之,在馮至的詩中,特別是《十四行集》中,到處充滿著這樣平淡卻耐人尋味的語言,它們深入淺出而又包含著豐富的情感和哲理。這樣的語言看似平常,但詩人在寫作時卻“經過了千錘百煉的功夫”(臧克家)。
馮至詩歌語言的高雅性,主要體現在他的詩歌語言基本是非民間化、非口語化、非革命化。民間的口語、俗語、俚語,革命化的政治術語,口號式的吶喊語,都沒有進入馮至的詩歌。他的詩歌語言,基本上是來自他生命的直覺和感悟,同時又經過了提純和加工的書面語言。他的詩歌語言雖然也受到了中國古典詩歌和外國現代詩歌的影響,但他卻有效地排除了其中的負面因素(例如深奧、晦澀、離奇、怪誕等)對自己詩歌的影響,而是取其所長,化為自己的語言營養。他的詩歌語言融會了杜甫的質樸、簡練、深沉、雋永,又汲取了里爾克、歌德等人的平和、超拔和玄遠,保持了一種獨立、純正、高雅的藝術品位。
馮至的詩歌語言在追求淡雅的同時,也注重追求含蓄性。所謂含蓄,就是對所要表達的思想感情不作直接、明確的表達,而是通過間接、形象的語言去暗示,讓讀者充分發揮想象和聯想,并結合自己的生活體驗和知識積累去思索、品味和感悟,從而收到言有盡而意無窮的藝術效果。在寫作中,他主要是通過多種藝術手法來實現語言的形象化,以取得以一當十,以少勝多的含蓄效果。第一,他的詩中運用了大量的比喻,增強語言的含蓄性。例如:“仿佛飛翔在空中,/它隨時都管領太空,/隨時都感到一無所有。”(《看這一隊隊的馱馬》)詩人用了一個比喻,把生命的存在與與虛無這樣一個具有哲學意味的觀點形象地表達了出來。“你的貧窮在閃鑠發光/像一件圣者的爛衣裳,/就是一絲一縷在人間/也有無窮的力量。”(《杜甫》),一個比喻就揭示了杜甫雖然物質貧困、精神卻富有和永恒。“你的熱情到處燃起火,/你燃著了向日葵花,/燃著了濃郁的扁柏,/燃著了行人在烈日下——/他們都是那樣熱烘烘/向著高處呼吁的火焰;”(《畫家梵高》)詩人用暗喻,生動地表現出梵高把生命的火焰、創作的激情全部融進了他筆下的畫面,從而熱情謳歌了梵高為藝術而獻身的精神。第二,用擬人。如:“在我們未生之前,/天上的星,海里的水/都抱著千年萬里的心/在那兒等待你。”(《等待》)通過擬人,溝通了宇宙和人的關系,使得宇宙有情,充滿對人類的關愛。“銅爐在向往深山的礦苗/瓷壺在向往江邊的陶泥,”(《我們聽著狂風里的暴雨》)運用了擬人,使無生物具有人類的“向往”精神,富有情趣和哲理。第三,用對仗。如《我只能……》,詩人一連用“空際的游絲”、“水上的浮萍”、“風中的黃葉”、“殘絮的飄零”等意象并置在一起,含蓄地表現了生命和愛情的漂泊不定感。第五,虛實結合。例如:“在山丘上松柏的蔭中,/輕睡著一個舊的希望。”(《希望》)希望本是抽象的,無生命的,詩人在這里用了一個動詞“輕睡”,便化抽象為具體,變無生命為有生命,增強了語言的形象感。
以上我們對馮至詩歌的藝術特征作了初步的探討和論述。對于這樣一位經受了時間的考驗,有著獨特個性和藝術風格的詩人,我們要以歷史的眼光,去正確看待和評價他的詩,通過比較他和同時代詩人所走過的不同的創作道路,去總結中國新詩發展過程中的一些經驗教訓。同時也要用現代的眼光去觀照他的詩歌,以便多角度、多層次地去發掘其詩歌的思想價值和藝術價值,從中汲取豐富的藝術營養。當前,在有關中國現代詩人詩作的研究中,馮至的研究還相對薄弱,甚至比較冷清。他的詩歌仍然是一座沉默的寶藏,我們熱切地期待著更多的有志者前去開采,以便讓他詩歌的藝術瑰寶不斷地顯現出來,并且閃爍出耀眼的光芒。
[1]魯迅.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序[A].魯迅.且介亭雜文二集[M].北京:中國人民出版社,2006.
[2]布封.論風格[J].譯文,195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