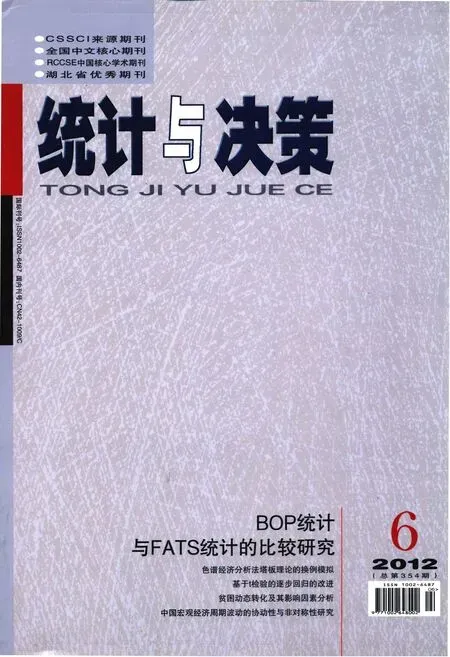企業家人口背景特征與企業社會績效的相關性研究
陳守明,范嘉斯,余光勝
(1.同濟大學 經濟與管理學院,上海200092;2.復旦大學 管理學院,上海200433)
目前,國內有關高管或高管團隊與多元化戰略的實證研究比較豐富,也有一部分學者對高管的人口背景特征與企業對外直接投資(FDI)進入模式選擇進行了探索(陳守明等,2010),但是對于高管與企業其他戰略選擇的研究還很不充分。另外,就企業社會績效而言,國內的研究也還不成熟。將這兩者聯系起來進行研究,在我國是一個鮮有研究者涉及的主題。本文首將企業社會績效作為企業的一種戰略選擇的結果,基于中國制造業上市公司的數據,檢驗高管的人口背景特征與企業社會績效的相關性,可以從一定程度上彌補國內在這方面研究的不足,進而對高階理論在中國具體情境下的應用作一點有益的補充。除此之外,本文的研究結論在某種程度上對完善我國企業社會績效的影響因素模型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1 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國內外關于高管人口背景特征與企業戰略選擇關系的相關研究中,企業家的年齡、受教育程度、職能背景、任期、社會背景、國際化經驗等是運用較為廣泛的幾個人口統計特征變量。結合要研究的主題,本文依據高階理論,著重分析企業家的年齡、受教育程度、職能背景、任期四種變量與企業社會績效的關系。
1.1 企業家年齡
高階理論認為,企業家年齡會影響企業戰略選擇。許多研究表明,越是年輕的企業家,越具有冒險傾向。對此的解釋認為,年齡較大的高管,無論是在生理上還是在心理上都缺少耐力(Child,1974),或者不容易掌握新的觀點,學習新的行為(Chown,1960)。雖然管理者的年齡看上去似乎與搜集更多的信息、準確分析信息的能力、愿意花更長的時間作出決策的傾向正相關,但是與決策過程中對信息的整合能力、決策信心負相關(Child,1974)。也有解釋認為,年齡越大的企業家,在心理上越安于組織現狀,抵制變革;此外,年齡越大的企業家越重視其財務和職位的安全性,任何會妨礙到這些安全性的行為都會被避免(Alutto et al.,1975)。企業社會責任作為一種戰略,是指企業除了對股東負責之外,還應對更加寬泛的一個利益相關者群體承擔責任。就我國的現實背景看,企業履行社會責任正處于逐步被企業家接受的過程中,對多數企業來講,每次承擔新的企業社會責任就是對原來做法的變革,而年輕人更愿意接受變革。于是,本文提出:
假設1:越是年輕的企業家,其所在的企業社會績效水平越高。
1.2 企業家的受教育程度
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受教育程度代表了一個人的知識和技能基礎。我們有理由認為,受過工程教育的人與在歷史或法律方面受過教育的人有著不同的認知基礎。而且,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他的價值觀,認知偏好等等(Hambrick&Mason,1984)。高階理論認為,高學歷意味著更強的信息處理能力和區別眾多影響因素的能力。在這里,高階理論強調的是受教育的數量而不是類型,這就為我們按學歷來劃分受教育程度提供了有力證據。顯然,擁有博士學歷的人與擁有大專學歷的人在思想、處理信息、承受不確定性和識別以及估計復雜情形方面的能力不同。此外,大量研究一致發現,受教育水平與創新能力存在正相關關系。
傳統的企業認為企業是以盈利為目的的組織,承擔社會責任不是企業家的主要工作。新的社會責任行為會對企業的財務績效帶來波動,企業家面臨新的不確定性。高學歷者具有較高的整合、分析信息的能力,更樂于承受不確定性。所以,本研究提出:
假設2:學歷越高的企業家,其所在的企業社會績效越高。
1.3 企業家的職能背景
為了在假設陳述中建立相關的參數,我們采用Hambrick&Mason(1984)對職能背景的分類:第一類,“外部職能”也稱“輸出職能”——營銷、銷售和產品研發,強調企業成長,開發新的市場機會,以及負責監督、調整產品與市場。第二類,“內部職能”也稱“生產職能”——生產、過程工藝及財務,旨在提高投入產出這一轉化過程的效率。顯然,分別來自這兩類職能領域的人員對企業及其所在的環境具有不同的導向。擁有生產職能背景的企業家通常強調有計劃的成長,傾向于通過內部發展來實現增長。因此,他們偏好高效率的運營,可能會對企業的自動化、設備更新、工藝改進等更感興趣,較少地關注企業與其利益相關者之間的關系。GUPTA(1984)提出擁有市場、銷售方面等輸出型職能背景的企業家在不確定性很強和不可控因素更多的環境中會更加游刃有余。因此,他們可以接受和處理由于承擔社會責任對企業戰略競爭環境所帶來的不確定性。此外,擁有輸出型職能背景的企業家接觸的利益相關者相對來說更為廣泛,例如,擁有市場職能背景的企業家除了要處理好與股東、雇員等利益相關者的關系,還要考慮到消費者的需求、政府的政策、社區利益等對企業競爭環境的影響,因此他們對于企業承擔超過股東利益之外的利益相關者的責任具有更強的意識。
綜上所述,本研究提出:
假設3:擁有輸出型職能背景的企業家更傾向于承擔社會責任,企業社會績效更高。
1.4 企業家的任期
基于CEO和董事長是企業中最關鍵且權力最大的兩個職位,同時考慮到一些企業家在CEO卸任后改任董事長,或者本來身兼兩職,卸任CEO后繼續擔任董事長,為了更好地反應企業家在該公司核心位置的“任職時間”,基于已有研究,我們將企業家的任期定義為在本企業擔任CEO或董事長時間的總和。
在任職初期,企業家的決策往往比較謹慎(Hambrick&Fukutomi,1991),為了建立企業與利益相關者之間的關系,通常會全面考慮對企業戰略選擇及其結果施加影響或者受企業戰略影響的利益相關者各方,主動承擔相關的社會責任,提高企業社會績效,以逐步建立企業聲譽和良好的關系網絡。隨著任職時間的延長,企業與利益相關者之間的關系逐漸穩定和密切,企業家的決策對利益相關者的影響力也逐漸提高,因此在戰略選擇方面企業家可以不必“遷就”所有的利益相關者,甚至采取一些更加創新、更加多元化的戰略,可能會影響一部分利益相關者的利益,企業社會績效因此略有所降低。于是,本研究提出:
假設4:企業家任職時間越短,企業的社會績效越高。
2 研究樣本與變量設計
2.1 樣本選擇與數據來源
為了控制行業因素的影響,本文在同一個行業內選取樣本進行研究,樣本選取范圍為我國滬、深A股制造業上市公司,根據中國證監會上市公司行業分類標準,2009年末共有957家制造業上市公司,剔除ST的上市公司后共有929家,然后我們采取隨機取樣的辦法從這929家公司中抽取200家作為研究樣本。根據本研究因變量企業社會績效的相關數據的缺失情況進行樣本剔除后,所獲得的最終樣本企業為130家,組成2009年度的截面數據。這樣,我們同樣控制了時間(年度)因素的影響。
本研究所用的數據來源:企業社會績效事件的識別來自于對上交所、深交所網站所提供的上市公司年報的閱讀與分析;企業家的人口背景特征及控制變量所涉及到的原始的企業財務數據的采集來自于對年報的閱讀,數據缺失部分根據新浪財經和清華金融研究數據庫披露的信息獲取。
2.2 研究變量測量
(1)解釋變量:高管的人口統計特征變量
由于中國上市公司的法人代表往往是董事長而不是總經理,在中國,董事長是事實上的企業家,在企業的重大決策中擁有更多的決策權,因此本文將企業家設定為董事長。
我們將注意力集中在企業家的年齡,受教育程度,職業背景和任職時間,Finkelstein&Hambrick(1997)認為這些特征最能影響高管的知識基礎、認知導向和價值觀。
X1:企業家的年齡=樣本年份(2009年)-出生年份
X2:受教育程度,參照陳傳明等(2008)的分類標準,企業家的學歷分為5個等級,即博士、碩士、本科、大專、高中及以下,并分別賦值5至1。
X3:職能背景,本文將其設計為虛擬變量,把擁有生產、會計、財務、法律、流程R&D等職能背景的歸類為throughput(生產型職能背景),編碼為“1”。擁有市場、銷售、產品R&D等職能背景的歸類為output(輸出型職能背景),編碼為“0”。
X4:任期,是指截止樣本年份(2009),高管在本企業擔任CEO和董事長的時間總和。
(2)因變量:企業社會績效(CSP)變量
關于企業社會績效(CSP)的衡量,本文從財務的角度建立一套分析企業社會績效的指標體系。根據上市公司年報的特點,我們主要從三大財務報表上選取反映企業對股東、債權人、員工、供應商、客戶和政府所履行的責任狀況的財務數據。值得說明的是,由于我國現行財務報告所披露的社會責任信息有限,其中環境責任和慈善責任等方面的信息披露不完整或者完全沒有提及相關信息,為了便于對樣本企業進行比較分析,因此所選用的企業社會績效指標中沒有包含企業對環境和慈善事業的責任信息。
之所以選擇財務角度來表現CSP,原因在于:第一,CSP是一個多維度的概念,包含了大量與企業資源、過程、產出有關的企業行為(Cooper,2004)。因此,在研究中引用CSP的不同方面就有可能得出完全不一致的結論。這就要求在理論和實證研究中,要注意強調CSP的某一特定方面,這一點很重要(Griffin et al.,1997)。這樣可以避免理論上的模糊性和在CSP衡量方面的困難(Pedersen,2007)。第二,結合我國企業的實際情況,目前還沒有規定公司提供專門的“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或者類似的“年度社會報告”、“可持續發展報告”等,自愿披露有關社會責任信息的公司較少,同時,也沒有獨立的機構或部門對企業社會績效進行全面的統計和分析。而公司對于Clarkson(1995)界定的主要利益相關者,即股東、債權人、客戶、供應商、員工和政府所承擔的社會責任中有很大一部分屬于會計基礎型信息,可以在財務報表中作為正式的會計信息來反映。
利益相關者業績評價指標體系由反映六類利益相關者的最具代表性的6項指標構成,具體見表1:

表1 利益相關者業績評價指標
我們先分別算出所有公司每一個指標的值,然后由高到低進行排序后進行五等分,按照數值由高到低分別賦予5分、4分、3分、2分、1分。5分為優秀,4分為良好,依此類推,1分為最差。
企業利益相關者業績的總得分(即企業社會績效得分)為衡量六類利益相關者利益的6項指標得分的加權平均數,即L=∑al,其中,L為公司利益相關者業績的總得分,l為各項指標得分,a為各項指標的權重。
(3)控制變量
研究企業社會績效時,通常將企業規模、行業作為控制變量,我們通過選擇制造業企業作為樣本來控制行業因素的影響。考慮到國內外大量實證研究表明企業社會績效與企業財務績效之間存在相關性,而且根據資源基礎理論,具有良好財務業績的公司可以為公司履行社會責任提供更多的資源,本文加入企業凈資產收益率(ROE)和財務杠桿來控制企業財務績效的影響。
①企業規模(Scale):企業2009年末的資產總額,再取其對數。
②企業凈資產收益率(ROE):提供資金假說認為財務績效影響公司社會責任,本文使用企業2009年的凈資產收益率來代表財務績效。
③企業財務杠桿:取2009年末的企業的資產負債率(AD)。
2.3 回歸模型
本研究通過回歸分析檢驗我國企業高管的人口背景特征與企業社會績效之間的關系。回歸模型為:

其中,CSP由上述反映六類利益相關者的各項指標得分加權求和后的利益相關者業績總分來進行量化。
3 實證結果與分析
3.1 描述性統計
董事長的人口背景特征變量、控制變量、企業社會績效的均值、標準差和Pearson相關系數如表2所示。從變量均值中可知,樣本企業中的董事長平均年齡為50歲左右,在陳傳明等(2008)的研究中,這一值為51.421;董事長的教育水平高于大學本科水平(本科賦值為3),在陳傳明等(2008)的研究中,這一值為4.189(本科賦值為4);董事長的任職時間平均水平為6年左右。從相關系數矩陣可以發現,雖然受教育程度與年齡之間,任期與年齡、受教育程度、職能背景都具有一定的相關性,但兩兩相關系數都較小,所以由于自變量的共線性帶來的影響也較小。
3.2 多模型回歸結果與分析
首先,把全部的控制變量引入回歸模型1,檢驗控制變量與因變量的關系;然后,在模型1的基礎上,每次分別檢驗1個自變量的影響,從而建立模型2至模型5,模型6是一個全模型,包含所有的自變量和控制變量。
首先,觀察僅含控制變量的模型1,從表3中可以發現,企業資產負債率(AD)通過了0.001置信水平下的系數檢驗,企業規模(Scale)通過了0.01置信水平下的系數檢驗,說明這兩個控制變量對企業社會績效的解釋力較好,加入這些變量有利于更準確地分析高管的人口背景特征與企業社會績效的關系。但是凈資產收益率(ROE)的解釋力較弱,這一點值得深入分析,但因為控制變量這不是本研究的主題,因此,在本文中不再深入探討。
接下來,我們分析本文主要研究的四個理論假設:
模型2在模型1的基礎上引入了年齡這一自變量,從表3中模型2和模型6可以發現董事長年齡與企業社會績效的關系沒有通過0.05水平下的顯著性檢驗。假設1沒有得到支持,也就是說越是年輕的企業家,其所在的企業社會績效水平越高的假設不能成立。可能的原因在于數據反映的我國董事長群體的年齡特征。從表2的描述性統計中我們可以看到,研究樣本中董事長年齡的均值為50.49,標準差僅為6.3,多數公司董事長年齡相近,處于人生和職業生涯的類似階段。因此,年齡對公司社會績效的影響不明顯。

表2 描述性統計:均值、標準差和Pearson相關系數矩陣
模型3在模型1的基礎上引入了受教育程度這一自變量,結合完整回歸模型——模型6的結果,我們可以發現董事長的受教育程度沒有通過顯著性檢驗,假設2未得到支持。我們認為受教育程度未能通過顯著性檢驗的原因可能是:中國企業家受教育程度的統計信息存在失真,比如一些企業家是成功以后再去讀MBA甚至直接用金錢購買的碩士博士學位;另外一種可能,比如在統計受教育程度的信息時,一些企業家的最高學歷仍然在讀,統計結果顯示的是其已獲得的學歷,這些情況都可能導致受教育程度無法通過顯著性檢驗,這有待在今后的研究中進一步進行討論。
模型4和模型6的結果顯示董事長的職能背景通過了0.001水平下的顯著性檢驗,假設3得到了支持,即擁有輸出型職能背景的企業家更傾向于承擔社會責任,企業的社會績效更高。原因在于擁有市場、銷售方面等輸出型職能背景的企業家在不確定性很強和不可控因素更多的環境中會更加游刃有余。因此,他們可以接受和處理由于承擔社會責任對企業戰略競爭環境所帶來的不確定性。另外,在我國輸出型職能背景的企業家更加堅信社會責任方面的投資會得到市場的回報。
模型5和模型6的回歸結果同樣顯示董事長的任期與CSP之間的負相關關系通過了0.001水平下的顯著性檢驗,假設4得到了支持,即企業家任職時間越短,企業的社會績效越高。
綜合上面的模型結果分析,我們認為企業家年齡與受教育程度對于企業社會績效的解釋力不強,而企業家的職能背景與任期能夠較好地預測企業社會績效的變化。
4 研究結論與展望
本文運用高階理論的思想和方法,以中國上市公司制造業為樣本,對企業家(董事長)的人口背景特征與企業社會績效的關系進行實證研究,得出以下結論:第一,擁有輸出型職能背景的企業家更傾向于承擔社會責任,企業的社會績效更高;第二,企業家任職時間越短,企業的社會績效越高。同時,企業家年齡和受教育程度未能通過顯著性檢驗。

表3 多模型回歸結果
本研究的理論意義是在中國情景下檢驗了企業家特征與企業社會績效的關系,豐富了高階理論的實證研究。研究的管理實踐含義也是自明的,有志于提升企業社會責任的投資者和政府主管部門可以多選擇輸出型職能背景的人擔任領導者,而且個人總的任期不能過長。
本文的研究是對高管個體特征對企業社會績效影響這個論題的初步探索,未來的深化研究的空間還很大。可行的研究方向主要包括:(1)在研究中引入中介變量。雖然本研究結論認為人口背景特征能夠對企業社會績效產生影響,但是關于人口背景特征影響企業社會績效的具體作用機制仍然是理論上的“黑箱”,這在某種程度上削弱了模型的解釋力和預測力。引入合適的中介變量有助于解釋高層管理者的人口背景特征對企業社會績效影響的機理。(2)我們還可以研究企業家人口背景特征影響企業社會績效的情境變量,考察這些變量對二者關系的調節作用。本文的研究只是企業家人口背景特征和CSP之間關系在我國情景下的初步考察,進一步的深化研究需要我們大家共同的努力。
[1] 陳傳明,孫俊華.企業家人口背景特征與多元化戰略選擇——基于中國上市公司面板數據的實證研究[J].管理世界,2008,(5).
[2] 陳守明,簡濤.企業家人口背景特征與“走出去”進入模式選擇——基于中國制造業上市公司的實證研究[J].管理評論,2010,(10).
[3] Alutto J A,Hrebiniak L G.Research on Commitment to Employing Organizations:Preliminary Findings on a Study of Managers Graduat?ing from Engineering and MBA Programs[R].New Orleans,1975.
[4] Child J.Managerial and Organizational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Com?pany Performance[J].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1974,(11).
[5] Chown S M.The Wesley Rigidity Inventory:A Factor-analytic Ap?proach[J].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1960,(61).
[6] Clarkson M.A Stakeholder Framework for Analyzing and Evaluating Corporate Social Performance[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1995,20(1).
[7] Dearborn D C,Simon H A.Selective Perceptions:A Note on the De?partmental Identification of Executives[J].Sociometry,1958,(21).
[8] Finkelstein S,Hambrick D C.Strategic Leadership:Top Executives and their Effects on Organizations[J].Australian Journal of Manage?ment,1997,22(2).
[9] Griffin J J,Mahon J F.The Corporate Social Performance and Corpo?rate Financial Performance Debate:25 Years of Incomparable Re?search[J].Business and Society,1997,36(1).
[10] Hambrick D C,Fukutomi G D.The Season of a CEO’s Tenure[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1991,1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