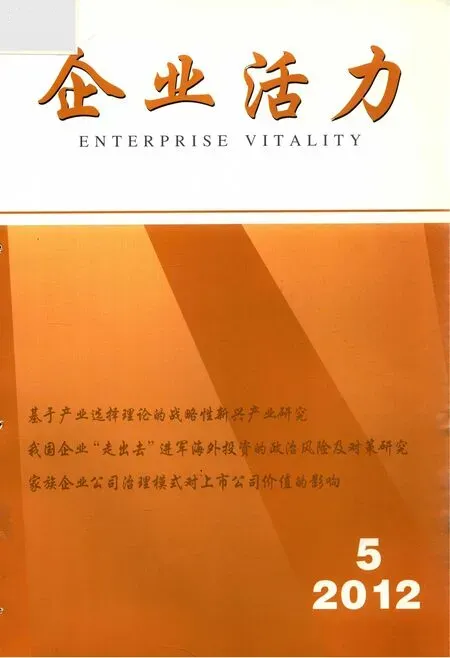基于復雜組織內個體差異的隱性知識傳播模型研究
□李中師 王麗萍
(1、2.浙江工業大學經貿管理學院,杭州 310014)
知識經濟的來臨使得知識成為企業生存、發展和獲得競爭優勢的關鍵性資源。對于知識的研究,Michael Polanyi[1]最早將那些無形的且不易被編碼的、較難與人共享、交流和理解的知識稱作隱性知識,相對的即為顯性知識。作為企業核心能力的主要表現形式[2],隱性知識在企業組織內能否順利傳播,進而能否被員工掌握轉化為生產力,將會給企業帶來截然不同的結果。隱性知識的傳播相對比較困難,因此科學地認識組織的隱性知識傳播規律,有效地控制隱性知識的傳播,對提高企業知識的管理水平具有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意義。
隨著知識管理研究的逐步深入,人們對知識活動的認識也逐步走向了兩個研究范式:信息網絡范式和社會網絡范式[3]。基于信息網絡范式的研究延續了數據、信息、知識等信息學的概念體系,以信息技術為中心,而基于社會網絡范式的研究主要是繼承了經濟社會學和組織行為學的觀念思想,該范式下的研究認為任何經濟實體都是嵌入在一個具體的、實時的社會系統中的,而知識的流動也通常存在于一個有邊界的社會網絡中,因此將知識傳播和知識利用放在具體的社會網絡中進行研究是比較合理的。
因此,越來越多的國內外學者對其進行了深入研究并取得了豐富的成果。大體上知識傳播的社會網絡范式研究可以分為兩類:局部研究和系統研究。局部研究,主要側重于個體之間的知識交換模式,如吸收能力、知識分享的效果和模擬,這些研究主要是基于認知心理學、社會心理學以及博弈論等[4]。例如Cowan和Jonard(2004)[5]提出了復雜網絡上的一種知識轉移模式——barter模式,并分析了網絡結構對知識傳播的影響。在此基礎上,Ping Yan和Xiuyu Yang(2009)[6]又提出了另外一種知識轉移模式——teaching模式,分析了不同的知識轉移模式對知識傳播的影響。系統研究,主要是基于計算機模擬和社會網絡拓撲結構對知識傳播的影響[7],從模擬結果分析網絡的結構特性對知識傳播的影響。例如鄧丹等(2006)[8]通過構建加權小世界網絡,考慮網絡的全局效率、局部效率和成本三個變量,分析了群體網絡中的知識共享問題。李金華等(2006)[9]結合復雜網絡理論,提出了一種群體網絡上的知識傳播模型。唐方成和席酉民(2006)[10]討論了網絡結構對知識傳播的影響,認為網絡組織的規模越大,連接節點數越多,知識傳播的效果越好。
這些研究成果對科學認識知識在組織內部和組織間的傳播機制發揮了很大的作用,并也為企業的知識管理實踐提供豐富的理論指導。但是,基于Vito Albino和Jeffery提及的影響知識傳播的因素(包括被轉移的知識因素、知識發送方因素、知識接受方因素、轉移渠道因素和情景因素)以及Andrews和Delahay[11]所認為的接受方感受到的提供方的可靠性和提供方感受到的接受方的可信度在知識傳播中的影響作用的分析,可以看出當前的研究還存在一些不足。具體表現為:其一,在宏觀層面上,沒有將系統研究和局部研究相結合(如網絡結構的差異和知識的傳播模式相結合)來研究其中的知識傳播規律;其二,在微觀層面上,知識發送方和接受方的個體差異對知識傳播影響的研究不足。
本文在現有隱性知識傳播的研究基礎上,通過構建復雜組織內的隱性知識傳播模型,綜合考慮了局部研究層次的隱性知識傳播模式和系統研究層面的網絡結構差異,分別分析了組織內部存在個體間知識轉移能力差異、知識吸收能力差異及個體間的信任度差異對隱性知識在組織內傳播的影響。研究結論在理論上,更加系統和全面地剖析了復雜組織中隱性知識的傳播機理;在實踐中,能夠更好地指導企業進行知識管理,促進企業內部隱性知識的高效傳播。
一、復雜組織內部隱性知識傳播的社會網絡模型
1.模型的基本假設
為了比較客觀嚴謹地研究隱性知識在組織內部的傳播規律,現對模型做以下假設條件:
(1)組織中的人數為常數,在知識傳播的分析周期內不會發生人員的流入流出;
(2)在知識傳播分析周期內不會發生連接關系的變化;
(3)組織中個體的初始知識存量隨機確定;
(4)在知識傳播過程中不考慮傳播成本(包括尋找學習資源以及教授、學習的時間成本等);
(5)組織個體均有很好的教授和學習動力,不存在“拒授”和“厭學”現象;
(6)在知識傳播過程中,對象個體不存在知識遺忘。
2.隱性知識傳播模型
采用Jackson算法構建的社會網絡結構可以看做是一個圖G(N,L),N表示所有節點的集合,L表示所有連接關系的集合。本文用一個整數表示隱性知識的擁有量,任意節點A∈N有Nk種不同的隱性知識,第i種隱性知識表示為A(i),i=(1,2,3,…,Nk)。跟節點A有直接連接關系的節點稱為A的鄰居節點,A的所有鄰居節點表示為Nei(A)。隱性知識的傳播是按一定的有限時間順序集t2∈(1,2,3,…)進行的,其傳播過程的流程圖如下:

平均隱性知識擁有量可以通過式(1)算得:

現有研究也已表明[11],組織群體網絡中的隱性知識傳播需要節點間頻繁的互動,知識分享的成功依賴于溝通的頻繁性和容易程度以及“知識發送者”和“知識接收者”之間整體關系的密切性。因此,對于組織內部隱性知識的傳播研究不僅需要考慮到“知識發送者”、“知識接收者”的傳播能力差異,而且也應考慮兩者之間的信任水平。
知識作為專家地位、個人威望和組織權利等社會資本的源泉。知識的傳播或轉移通常會引起個人獨有能力的擴散,并給“知識發送者”帶來機會成本和分享風險,進而影響其社會資本[12],因此知識傳播的成功不僅受到了“知識發送者”的知識存量、傳達能力等硬性指標的影響,還會受到其轉移意愿、保護意識的影響。“知識發送者”對知識傳播的影響程度大小可由式(2)算得:

其中,TAB表示節點A將其知識傳授給節點B的能力大小,CA表示節點A的轉移知識的最大能力,WAB表示A與B之間的信任度;
由于知識轉移能力的大小很大程度上受到節點的知識儲量和表達的意愿的影響,故:

其中,SA表示節點A的知識擁有量,DA表示節點A的傳達意愿大小。

TAB與TBA是前述流程圖中(1)的具體算法。
“知識接收者”同樣會影響到知識傳播的成功,已經被認識到的影響因素包括接收方的接受意愿、知識結構、知識存量以及吸收能力。“知識接受者”的接受意愿越強烈、知識結構越豐富,其接受知識的積極性就越高,知識傳播的成功率就越大。知識傳播的終極目標是知識的吸收和創新,所以知識傳播的效果還受到接受方知識存量和吸收能力的影響。“知識接收者”對知識傳播的影響程度具體可由
式(6)算得:

其中,LAB表示節點A向節點B學習知識的能力,XA表示節點A的最大吸收能力,WAB表示節點A與節點B之間的信任程度;
由于知識的吸收轉化能力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該節點的知識擁有量和其對于知識的接受意愿程度大小,故:

其中,SA表示節點A的知識擁有量,PA表示節點A的對知識的接受意愿度;
同理,

LAB與LBA也即上述知識傳播流程圖中(2)所表達的具體算法。
由于目前理論界和實踐中對轉移能力與知識存量、傳達意愿以及吸收能力與知識存量、接受意愿之間的函數關系均沒有一致的清晰認識,且該函數關系研究亦非本文的研究重點,故將CA,CB,XA,XB分別設定為某一常數。又因為前文模型假設中提到“組織個體均有很好的教授和學習動力,不存在‘拒授’和‘厭學’現象”,因此,CA,CB,XA,XB均為大于0的某一常數,且節點之間各不相同。
R.Cowan[5]等學者提出個體之間的知識交換可以理解為個體在經濟社會中的“易物”交易,即當且僅當節點的某一類隱性知識j(i≠j)大于其鄰居節點A的同類隱性知識,且節點的某一類隱性知識亦大于節點的同類隱性知識時,知識傳播(知識交換)才能得以達成。現假設節點A教授節點B隱性知識i,并且向節點B學習隱性知識j,該知識傳播過程(流程圖中(3))可以表述為下式:

Ping Yan 和 Xinyu Yang(2009)[6]基于某些企業為了鼓勵公司員工間知識的共享和傳播,對于有分享知識的員工給予一定的獎勵,提出了另外一種傳播模式——“教授”式傳播,即節點A沒有向節點B學習的隱性知識,但是節點A可以將其某些隱性知識教授給節點B。現假設節點A教授節點B隱性知識,但是沒有A向節點B學習任何隱性知識,該過程(流程圖(4))可以表示為:

一般來講,隱性知識的傳播是通過個體之間面對面的交往和接觸來得以實現的,在接觸的過程中必會占用一定的時間。因此本文假設“易物”式傳播的時間跨度是“教授”式傳播的兩倍,因為“易物”式傳播過程有兩次“教—學”的過程。故在本文的隱性知識傳播模型中,在同一時間,“易物”式傳播只能進行一次,“教授”式傳播最多不超過兩次。
在本研究中隱性知識的擁有量用整數表示,因此隱性知識的擁有量不會完全相同,故本文認為式(10)成立則A(i)=B(i)。

二、隱性知識傳播模型仿真
1.模型初始化
本文的仿真模型采用C語言編寫,在Matlab中對其運行結果進行分析。考慮一個有100個節點的組織群體,設定Mr=Mn=3,則可用η=Pr/Pn表示不同的網絡結構①Pr表示在備選節點Mr中隨機選擇節點形成新的連接關系的概率;Pn表示在備選節點Mn中隨機選擇節點形成新的連接關系。每個節點擁有5類不同的隱性知識且隱性知識量服從[1,100]的均勻分布;每類知識中各有一個節點為專家節點,專家節點的該類隱性知識量為最大值100。
各個節點的最大轉移能力C和最大吸收能力X服從正態分布,而各節點之間的信任度W服從[0.1,0.9]均勻分布。
2.隱性知識傳播模型仿真
采用Jackson的網絡構建算法,在考慮“易物”式和“教授”式兩種傳播模式共同運行,并且在不同的網絡結構環境下,分析節點的知識傳授、學習能力以及信任度水平的差異對隱性知識傳播效果的影響。穩定狀態下的平均隱性知識水平的仿真結果均是在同一網絡結構下運行50次,然后取其穩定狀態下的平均值。
模型一 假定各節點的轉移能力水平和吸收能力水平均為0.5,個體間無任何差異,信任度亦無差異,均為0.5,知識傳播模擬仿真結果如下圖1。
正如圖1所示,知識存量水平會隨著η的增長而增加,尤其是在區間[0.09,9.00],增長幅度比較明顯,當η的值超過9.00以后,知識擁有量水平基本保持不變。
由模型一可以看出,網絡結構對隱性知識傳播的影響,主要是在區間[0.09,9.00],也就是小世界網絡(the small-world network),主要影響了知識傳播的速度和平均隱性知識水平。在該區間,隨著η的增加,知識的傳播速度由快逐漸變慢,而知識水平呈現逐步增加。
模型二 假定各節點的吸收能力以及信任度水平較模型一均無變化,分別均為0.5,唯有各節點的轉移能力水平有差異。假定節點的轉移能力水平服從正態分布,為了體現不同的能力水平對隱性知識傳播的影響,本文選取兩組節點轉移能力水平均值分別為0.2和0.8的節點組進行對比分析。模擬仿真結果見圖2。

圖2 不同網絡結構下,不同的轉移水平對隱性知識傳播的影響
如圖2所示,隨著節點轉移能力水平的提高,隱性知識的轉移速度和隱性知識平均水平均有明顯的上升和提高。同模型一類似,節點轉移能力對隱性知識傳播的主要影響亦在小世界網絡范圍內。
模型三 假定各節點的轉移能力以及信任度水平較模型一均無變化,分別均為0.5,唯有各節點的吸收能力水平有差異。假定節點的吸收能力水平服從正態分布,為了體現不同的能力水平對隱性知識傳播的影響,本文選取兩組節點吸收能力水平均值分別為0.2和0.8的節點組進行對比分析。模擬仿真結果見圖3。

圖3 不同網絡結構下,不同的吸收水平對隱性知識傳播的影響
如圖3所示,隨著節點吸收能力水平的提高,隱性知識的轉移速度和隱性知識平均水平均有明顯的上升和提高。同模型一類似,節點吸收能力對隱性知識傳播的主要影響亦在小世界網絡范圍內。
模型四 假定各節點的轉移能力以及吸收能力較模型一均無變化,分別均為0.5,唯有各節點之間的信任度有差異。假定節點之間信任度水平服從正態分布,為了體現不同的信任度水平對隱性知識傳播的影響,本文選取兩組節點間信任度水平均值分別為0.2和0.8的節點組進行對比分析。模擬仿真結果見圖4。
如圖4所示,隨著節點間信任度水平的提高,隱性知識的轉移速度和隱性知識平均水平均有明顯的上升和提高。同模型一類似,節點間信任度對隱性知識傳播的主要影響亦在小世界網絡范圍內。
三、結語
本文構建了復雜組織內的隱性知識傳播模型,綜合考慮了微觀層次的隱性知識傳播模式和宏觀層面的網絡結構差異,分析了組織內部個體間存在知識轉移、知識吸收及個體間的信任度分別對隱性知識在組織內傳播的影響。模擬仿真的結果證實了如下結論:
(1)小世界網絡對隱性知識在組織內的傳播的影響最大。
(2)組織內部個體間的轉移、吸收和信任度的差異對隱性知識在組織內的傳播產生了正面影響,組織節點的平均轉移(吸收或信任度)越高,隱性知識的傳播速度越快,隱性知識在組織內的平均擁有量也越高。
如何提高隱性知識在組織內的傳播效果,作為組織的管理者可以從以下幾方面采取措施:首先,提供便利的場所(咖啡屋、棋牌室或者游戲廳),這樣是為了提供更多的個體之間的面對面的接觸機會,增加隱性知識傳播的可能性;其次,提高個體的學習能力和表達轉移能力,可以通過一些培訓課程以及實踐鍛煉來實現;同時,工作場所應盡量營造一種開放、自由的工作氛圍,以建立個體之間的相互信任,這樣有利于隱性知識的傳播;最后,合理的利益分配政策,形成公平、公正的激勵機制,如獎金的發放和員工績效的考核應考慮到員工個體在知識傳播中的影響作用。
本文通過隱性知識在復雜組織內的傳播過程進行建模,并分析了個體間的知識轉移、吸收能力和個體間信任度的差異對傳播過程的影響。由于時間和篇幅的限制,本文不能全面分析隱性知識的全部傳播過程,所以后續的研究可以從以下兩方面進行改進,一是在局部分析層面,遺忘機制可以加入到本文的模型中;二是在系統分析層面,可以研究網絡結構的演化(如員工的入職、離職和員工間關系的變化)對隱性知識傳播的影響。
[1]M.Polanyi.“Tacit Dimension”.New York:Doubleday&Co.,1966.
[2]H.Tua,Difficulties in Diffusion of Tacit Knowledge in Organizations,Journal of Intellectual Capital,2000(4):357─365
[3]馬費成,王曉光.知識轉移的社會網絡模型研究[J].江西社會科學,2006,(7):38─44.
[4]T.Yin and Q.Zhang.Dynamics Game Analysis in Work’s Tacit Knowledge Sharing Process in Enterprise,I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achine Learning and Cybernetics,2005,(4):2234─2238.
[5]Cowan R., Nicolas, J..Network Structure and the Diffusion ofKnowledge[J].JournalofEconomic Dynamics&Control,2004,(8):1557─1575.
[6]Ping Yan, Xinyu Yang.To Trade orto Teach:Modeling Tacit Knowledge Diffusion in Complex Social Networks. 2009.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Futur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Management Engineering,151─154.
[7]F.Tang,J.Mu and D.MacLachlan,Implications of Network Size And Structure on Organizations’Knowledge Transfer, Expert Systems with Applications,2008,34(2):1109─1114.
[8]鄧丹,李南,田慧敏.加權小世界網絡模型在知識共享中的應用研究[J].研究與發展管理,2006,(4):62─66.
[9]李金華,孫東川.復雜網絡上的知識傳播模型[J].華南理工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2006,(6):99─102.
[10]唐方成,席酉民.知識轉移與網絡組織的動力學行為模式[J].系統工程理論與實踐,2006,(9):83─89.
[11]Andrews K.M., Delahay B.L..Influences on Knowledge Processes in Organizational Learning:The Psychosocial Filter[J].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2000,37(6):797─810.
[12]柯江林,石金濤.驅動員工知識轉移的組織社會資本功能探討[J].科技管理研究,200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