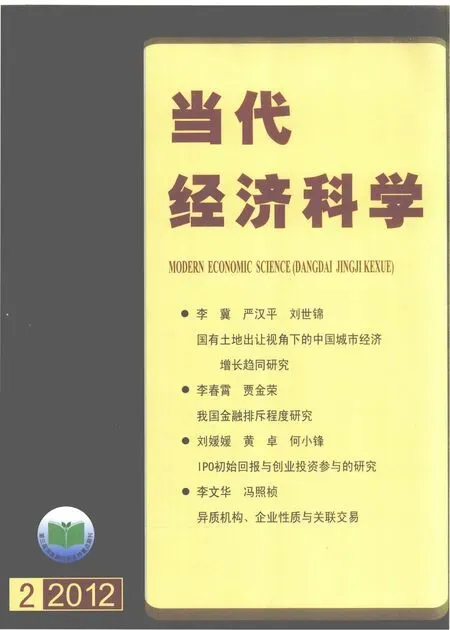國有土地出讓視角下的中國城市經濟增長趨同研究
李 冀,嚴漢平,劉世錦
(西北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陜西西安710127)
一、引 言
市場化進程開始至今三十余年以來,中國經歷了經濟的高速增長和體制的深刻變革。中國的實際GDP在1978~2008年間保持著年均9.8%左右的高速增長。但相比之下體制的變革則不太容易被直接度量。盡管如此,這并不意味著制度是不重要的。新制度經濟學很早即區分了不同要素在經濟增長中所起的作用,并認為資本投資和技術進步只是經濟增長的結果或本身就是經濟增長(North,Grossman& Helpman)[1-2]。而關于真正決定經濟增長的因素,Zysman認為經濟增長的路徑和軌跡由包括政體形態、產權制度以及分配制度等在內的廣義制度所決定[3]。甚至如Acemgofu所言,即經濟增長從根本上依賴于制度發展,制度先于經濟發展并決定經濟增長[4]。而在制度類型的選擇上,Rodrik&Waeziarg則認為有助于實現市場競爭和產權有效保護的民主制度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效率更高[5]。
如果說制度對經濟增長確實存在實質性的影響,那么中國當前的區域經濟差異的問題一定也可以從這一角度尋找答案。根據嚴漢平、李冀等的測算,中國省際人均GDP的Theil指數已經由1978年的 0.028 上升至 2008 年的 0.061[6]。如 Rodrik.et.al.指出的那樣,對于任何一個經濟體,要素對經濟增長的決定作用都能從世界各國或地區的經濟發展歷史中得到驗證[7]。而1978年以后中國市場化進程的歷史經驗則釋放出一個明顯的信號,即一旦制度創新使得某種生產要素能夠通過實現自由流動并進入市場化交易進程,這不僅可以實現要素配置的帕累托最優并獲取相應的最優報酬,而且會在推動城市化進程的同時影響經濟產出。一個不容否認的事實是,地方政府對工業建設用地實施低價協議出讓為各地區低成本實現資本形成和工業化創造了條件,而其對經營性土地實施的高價出讓則成了1994年分稅制改革之后,充實地方政府預算外財政收入的重要途徑。不僅如此,國有土地出讓在改變了農業土地用途的同時還極大地加速了城市擴張的步伐。因此,國有土地使用權市場化出讓的實施是否在很大程度上推動了經濟增長,不同地區在國有土地出讓方面的差異是否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趨同性產生了影響就成為我們希望考察的問題。
本文其余部分安排如此:第二部分首先根據國有土地使用權的市場化出讓影響經濟增長的三個主要途徑分別進行相關文獻的梳理和總結;第三部分給出了本文的實證模型,并對相關的數據處理、指標選取等問題進行解釋;第四部分對我國1999~2008年國有土地出讓對經濟增長的影響進行實證檢驗,并分別考察國有土地出讓在三種影響途徑下各自的影響力度;本文最后對國有土地出讓推動經濟增長的模式可能的消極作用進行了延伸性討論,并以此結束。
二、文獻述評
在新古典理論的視角下,國有土地使用權的市場化交易可以被視為一種資本形成和資本集聚的平臺或載體,從而為長期的經濟高速增長提供了條件。而包括政府公共投資、FDI甚至金融資本等在內的資本對經濟增長的推動已經得到了諸多文獻的證明(姚樹潔、馮根福等;王定祥、李伶俐等)[8-9]。但是,基于新古典理論視角的研究較少考慮制度變革所帶來的影響,因此其研究范式相對于我們所希望考察的問題,即中國整體制度變革背景下土地資源的市場化配置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無疑存在著固有的偏差。
考慮到中國經濟增長所具有的特殊制度背景,除了新古典增長理論框架下的資本投入已經得到了廣泛的認可之外,在解釋中國經濟增長的制度因素時,中國式分權理論、地方官員晉升錦標賽理論和地區競爭理論是被廣泛接受的三種理論框架。其中,中國式分權理論將中國的經濟增長歸結為經濟體制中(尤其是財政體制方面)所進行的分權改革,認為這直接改變了地方政府的激勵結構,并成為其實行促進經濟增長政策的主要激勵,由此衍生出了以Barry R.Weingast、錢穎一等為代表的第二代財政聯邦主義理論。不過,中國式分權并未對具有明顯集權特征的1994年分稅制改革實施以后中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進行解釋,而國有土地市場化出讓的大規模推行正是在這一時期,因此這一理論框架并不適用。而對于周黎安等所提出的地方官員晉升錦標賽理論,陶然等指出了其理論邏輯與實證研究方面存在的問題,并認為晉升錦標賽所產生的影響和后果在地區競爭的理論框架下可以得到解釋[10-11]。進一步,考慮到國有土地出讓行為的實施主體是地方政府,后者在不同類型的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中會采取差異化的行為,即以協議方式低價出讓工業用地從而爭奪制造業投資獲取增值稅等各項稅收收入,而以招拍掛方式高價出讓商住用地從而增加土地出讓金等預算外收入。因此國有土地使用權的市場化行為與地區競爭的理論框架極其契合。
如果按照地區競爭的視角,1994年分稅制改革的實施使得地方政府由于“利權上收、事權下放”而出現財政收入窘迫的境況,因此地方政府不得不為增加稅收收入而展開對制造業投資的競爭,因此低價出讓工業土地即成為必然;而高額的土地出讓金等預算外收入又使得政府選擇高價出讓商住用地。總之,政府具有相當強烈的主管征地沖動,這可以由近年來土地出讓收入占地方政府財政收入的比例得到證實。而土地出讓金及其相關收入所構成的預算外收入即為所謂的“土地財政”。至于地方財政對經濟增長的作用,現有文獻已經對其進行了詳盡的論述。嚴成樑、龔六堂的研究表明,政府財政支出對經濟增長的推動不僅來自于資本積累的提高,生產型公共支出所帶來的勞動邊際回報提高也能夠有效增加經濟產出,而生產性公共支出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存在地區差異[12]。而杜雪君等以及辛波、于淑俐則直接證實了土地財政對經濟增長具有顯著影響[13-14]。從上述文獻研究內容不難看出,在當前的中國財政體制早已實現中央和地方“分灶吃飯”的背景下,由國有土地出讓所帶來的土地出讓金及其他相關的預算外收入并不會被中央拿走,因此這一部分收入在地方政府總體財政收入中已經占據了相當重要的地位。正是依靠著龐大的預算外財政收入,地方政府才能夠擴大財政支出和公共投資的規模,進而后者能夠顯著推動經濟增長。
由此不難看出,在新古典理論、地區競爭理論以及城市化的視角下,國有土地出讓具有推動經濟增長的不同路徑。那么,國有土地出讓究竟會對不同地區的經濟增長產生何等影響,這種影響是否有助于解釋近年來中國地區間經濟差異,都是前述文獻所未涉及的,這同樣是本文所希望考察的問題。
三、實證模型及數據處理
(一)實證模型及指標選取
本文對傳統的兩要素CES生產函數進行擴展,使用附加人力資本H和土地出讓F的四要素CES生產技術模型替代廣泛使用的Solow總量生產函數模型,并將其與趨同方程相結合得到本文的計量模型如下:

對于(1)式穩態條件下有效人均產出水平的對數值為:


(3)式在ρ=0時的二階泰勒級數近似展開為:



又

其中,λ =(n+g+δ)(1-α -β-γ)


對(7)式兩邊求積分得:

對(8)兩邊同時賦以e為底的:

由(9)式不難得到:

令ec=b,并將Y=lny(t)代入(10)式不難得到:

由(11)式兩邊同除以beλt并經過簡單變換不難得到:
lny(t)= lny*- e-λtb-1,其中 b-1= lny*-lny(0)
因此有 lny(t)=lny*- e-λt(lny*- lny(0))
即

將(5)式代入(12)式并推導①此處推導較為繁瑣,故沒有列出,需要的讀者可來信向作者索取。,
可以得到:


考慮到政策實施可能具有的滯后效應,我們在(13)式中加入因變量的滯后項;此外,為了刻畫樣本中可能存在的地區差異,在(13)式中加入隨截面個體變化的ut和隨機擾動項ε(it),則(13)進一步變為:

(14)式是一個典型的動態面板模型,也是本文所要估計的基本計量方程。各個變量的含義如下:
1.因變量 Δpcgdpi,t。該變量反映了特定時期內各地級市的實際人均GDP增長率。為了充分利用有限的樣本容量,從而避免樣本容量過小可能導致的估計偏誤,因此本文設定t-T=1①設定t-T=1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樣本數據,以保證估計的有效性。。
2.核心自變量 Δpcgdpi,t-1。對于式中的核心自變量初始人均GDPyi,T,如果其系數β2顯著為負,則經濟增長率與初始人均產出水平負相關,趨同假說成立。最后可以根據β1計算不同區域的趨同速度λ。
3.控制變量集X:其包含的解釋變量為:
(1)基期人均對數值yi,T。地區的經濟增長率就可能與一系列的控制變量有關。通常是以投資率、人力資本等作為控制變量,由此測算出來的β系數反映的是城市經濟增長的條件趨同性。通過公式β1=-(1-e-λt),可以計算得到中國地級及以上城市的經濟增長趨異速度。
(2)資本sk(i,t)的對數值(經人口增長率、技術進步率和折舊率的修正)。選取固定資產投資占GDP比重作為衡量物質資本變量sk的指標。變量n則可以通過計算各期年末總人口的平均增長率得到。最后,對于其余無法直接觀測的變量,即衡量技術進步的變量和衡量資本折舊的變量δ,則遵循MRW的處理方法,即假設g和δ是常數,且分別等于0.02和0.03。下文中的變量 n、g和 δ也采取相同的處理方法。
(3)人力資本sh(i,t)對數值(經人口增長率、技術進步率和折舊率的修正)。選取教育事業費支出占GDP的比例作為衡量人力資本變量sh的指標,由于2001年后《中國城市統計年鑒》未將按“市區”統計的教育事業費支出列出,故統一使用按“地區”統計的教育事業費支出代替。
(4)土地出讓收益Sf(it)對數值(經人口增長率、技術進步率和折舊率的修正)。對于土地出讓收益Sf(it),現有文獻尚沒有相關的處理方法,考慮到地方政府在地區競爭中,為了吸引制造業投資,而傾向于對不同的用地類型采取差異化的出讓方式,即對工業用地普遍采取低價協議出讓的方式,而僅對部分商住用地采取市場化程度較高的招拍掛出讓方式,因此變量選取應當能夠全面涵蓋不同的用地類型的出讓情況,而國有土地出讓價則可以有效地反映這一點。基于此,本文選取國有土地出讓價款占財政收入的比例作為衡量土地出讓收益Sf(it)的指標。
(5)資本對數值、人力資本對數值以及土地出讓收益對數值之和的平方項。資本等要素的投入可能導致產業集聚和技術外溢等外部效應,人力資本的積累同樣可能產生學習效應和技術創新,而土地出讓收益的增加則有助于充實地方財政,增加地方支出,加速城市化進程。各個因素之間無疑會產生極其復雜的交叉效應。而加入三者之和的平方項則有助于描述這種復雜的效應。
(6)地區虛擬變量。考慮到我國疆域廣闊,不同省份之間的經濟結構、發展水平、習慣風俗等可能存在較大的差異,由此可以預期,國有土地出讓政策的實施在不同的地區所產生的效果必然存在顯著的差異。基于這一考慮,我們分別對分布在東部、中部、西部和東北地區的不同城市構造了虛擬變量。
(7)2004年國有經營性用地招拍掛出讓虛擬變量。盡管國土資源部于2002年5月即頒布實施《招標拍賣掛牌出讓國有土地使用權規定》,要求包括商業、旅游、娛樂、商品住宅的經營性用地必須通過招拍掛方式出讓,但是對經營性用地出讓方式產生實際效果的則是國土資源部2004年8月31號頒布的71號令,它明確規定了經營性用地采取招拍掛方式出讓的最后期限,即所謂的“8.31大限”。毫無疑問,由于直接影響到推動經濟增長行為主體——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讓決策,2004年的“8.31大限”具有非常顯著的非觀測效應,因此我們構建了控制這一效應的虛擬變量,將2004年之前賦值為0,2004年之后賦值為1。
(二)數據來源
本文收集并整理了中國174個地級及以上城市1999~2008年的面板數據,盡管中國的直轄市、副省級市和直轄市共計286個②這一數據來自于《中國城市統計年鑒2009》。,但部分城市在1999年之后發生了行政區劃邊界的變化,為了準確起見對其予以剔除;此外,由于統計本身的原因,部分城市個別年份的數據缺失,樣本中只保留所有年份數據均完整的城市作為觀測對象,因此最終的樣本容量為174個但為保持統計指標及相關口徑的一致,除各地級市的國有土地出讓價款數據來源于歷年的《中國國土資源年鑒》之外,其余的所有指標均來自于歷年的《中國城市統計年鑒》。從現有的統計數據來看,《中國城市統計年鑒》對地級市分別列出“地區”和“市區”兩項,“地區”包括市區和下轄縣、縣級市,包含了農村地區的數據,不能真實地反映城市的經濟活動;“市區”則僅包括城區和郊區,行政界線相對穩定,體現了城市中的經濟活動。由于2001年后《中國城市統計年鑒》未將按“市區”統計的教育事業費支出列出,故統一使用按“地區”統計的教育事業費支出代替。
四、實證分析
(一)估計方法的說明
對于本文所采用的動態面板數據模型而言,因變量滯后項Δpcgdpi,t-1的存在會導致其與不可觀測的界面異質性效應ui產生相關,進而導致參數估計的非一致性問題;不僅如此,因變量滯后項還會導致不可避免的模型內生性問題。為了克服上述問題,需要采取工具變量法對式(12)進行估計。Arellano&Bond提出了用一階差分GMM(first differenced GMM)估計方法,在假設干擾項ε(it)不存在序列相關的前提下,對式(12)進行一階差分,利用滯后的被解釋變量作為差分方程中相應變量的工具變量[15]。然而,Blundell and Bond、Judson and Owen 很快指出了這一估計方法所存在的缺陷,即DIFGMM估計量會導致部分樣本信息的損失,因此不適于小樣本分析,此外,當解釋變量表現出較強的序列相關性時,水平滯后項將會成為差分方程中內生變量的弱工具變量,從而導致估計結果有偏,因此需要尋求更佳的工具變量[16-17]。而系統 GMM(System GMM)估計方法則是克服弱工具變量問題的有效途徑,與一階差分GMM不同的是,系統GMM估計量采用差分變量的滯后項作為水平值的工具變量,相當于進一步增加了可用的工具變量,且估計過程中同時使用水平方程和差分方程,因此一般認為系統GMM估計量具有更好的有限樣本特征。考慮到本文所使用的樣本數量有限,結合面板數據的單位根檢驗結果(無法拒絕所有控制變量為一階單整的假設),因此為了有效克服弱工具變量問題,選擇系統GMM方法進行估計。此外,由于兩步(Twostep)GMM相比一步(Onestep)GMM而言更加漸進有效,且本文的動態面板數據的樣本容量相對充分,可以較好地避免避免小樣本偏差,因此我們采取Twoestep-System-GMM進行估計。
由于系統GMM估計不僅將水平值的滯后項作為差分變量的工具變量,而且進一步采用差分變量的滯后項作為水平值的工具變量,因此為了檢驗工具變量是否有效,本文使用Arellano and Bover提出的過度識別約束檢驗和自回歸(AR)檢驗[18]。
(二)實證結果的分析
1.單位根檢驗
為了增加檢驗結果的穩定性,本文利用Levin-Lin-Chu(LLC)、Im - Pesaran - Shin(IPS)、Breitung和Fisher-PP四種方法來進行面板數據的單位根檢驗。對30個地級及以上城市面板數據的穩定性進行檢驗,結果見表1。四種檢驗方法的零假設為序列存在一個單位根。
根據表1所顯示的結果,在針對各主要經濟變量進行的單位根檢驗中,LLC檢驗顯示lnyi,0存在單位根,IPS檢驗顯示資本、人力資本、土地三者之和的平方項與 lnyi,0存在單位根,Breitung檢驗顯示Sf(it)存在單位根,而Hadri檢驗則拒絕了每一個變量不存在單位根的原假設。因此,為了避免一階差分GMM可能存在的弱工具變量問題,我們選擇系統GMM方法進行回歸分析。
2.模型估計
由于系統GMM對不同類型的經濟變量采取了不同的工具變量設置方法,因此首先需要對不同經濟變量性質進行判斷。我們基于式(14)分別構建兩個不同的模型:在模型A中,我們假設除因變量滯后項 Δpcgdpi,t-1之外的其他自變量均為外生變量;在模型B中,則將除地區虛擬變量和2004年份虛擬變量之外的所有自變量均設定為內生變量。兩個模型的估計結果分別如表2所示。
從表2給出的檢驗結果來看,兩個模型中殘差序列均存在顯著的一階自相關,但AR(2)檢驗值均在0.10以上,因此不存在二階自相關,而模型A的Hansen檢驗值更大,這說明模型A對經濟變量性質的判斷在總體上更符合動態面板數據的估計要求。

表1 各變量的單位根檢驗結果

表2 模型估計結果
表2中的估計結果基本符合經濟學解釋。對于直接影響趨同假說是否成立的核心自變量yi,T,無論是模型A還是模型B,其系數均為正值且高度顯著,均通過了顯著性水平為1%顯著性檢驗。因此不難斷定,在整個樣本期間內(1999-2008年),中國地級及以上城市的經濟增長呈現出顯著的趨異性。根據公式β1=-(1-e-λt)計算得到,方程A和方程B的趨同速度分別為1.9%和2.7%。換言之,與部分以省際數據所做的實證研究結果不同(劉生龍、王亞華等;李冀、嚴漢平),中國的城市經濟增長呈現溫和的趨異[19-20]。
盡管我們的模型考慮到了政策的滯后效應,但無論是模型A還是模型B,LΔpcgdpi,t的系數均不顯著,表明從1999年迄今所表現出的政策短期時滯效應并不明顯,前一年的經濟增速對下一年的經濟增長并沒有顯著的影響。一般而言,經濟政策的時滯大約為五至十年,我國建國以來的區域經濟政策的演變與區域經濟差異的變動也呈現出周期大約為十年左右的階段性耦合,因此因變量滯后一期的影響不顯著也在我們意料之中。
在兩個模型中,資本變量sk(i,t)對數值的系數均為正,與多數類似的實證研究結果相同,投資對經濟增長均有著正向影響。然而,模型A中這一影響并不顯著,而在模型B中則高度顯著。正是由于變量性質的不同假設,造成了如此顯著的差異。實際上,前文已經說明,為了保證行政界限的相對穩定和城市經濟活動的真實反映,本文所選取的數據均為“市區”數據。而在地方投資方面,無論是以中央財政性建設資金為主要支持的水利、交通、能源等基礎設施建設項目,還是以銀行信貸投入為主要支持的鐵路、主干線公路、電力、石油、天然氣等大中型能源項目建設,區位布局多數以城市郊區為主,因此并不反映在“市區”數據中;此外,前期建設周期較長的大規模投資建設發生的若干年后,才會帶來的產出水平的提高。這也形成了投資對當期城市經濟增長的推動可能并不顯著的又一個原因。
人力資本sh(i,t)對數值的系數在兩個模型中均為正值,且通過了1%的顯著性檢驗,說明人力資本投資對于經濟增長產生了顯著影響。需要說明的是,本文對于人力資本度量選擇了投入法,即以教育事業費支出作為代理變量。從一般意義而言,投入法可能會傾向于強化人力資本推動經濟增長影響的估計,在時間跨度較短,樣本容量較小的情況下尤為如此。在其他的實證研究中,除投入法之外,對人力資本的度量主要根據受教育年限或是用知識存量價值指標[21-22]。但錢雪亞等認為,這樣的變量選取則傾向于強化在長周期中人力資本推動經濟增長影響的估計[23]。同時考慮到本文樣本容量所限,因此上述方法及相關的結論并不適用于本文。土地出讓收益sh(i,t)對數值的系數均為正,而在模型設定更為合理的模型A中,這一系數呈高度顯著,由此不難判斷,土地出讓收益的增加對這一時期的城市經濟增長產生了顯著的影響。在地方政府從土地出讓獲取的全部直接收益中,作為預算內收入的土地相關稅收(如耕地占用稅、房地產和建筑業營業稅、土地增值稅)所占的比重相對較小,而占據較大比重的則是與土地相關的非稅收入(如土地租金、土地出讓金、新增建設用地有償使用費等),后者作為地方政府的主要預算外財政收入,幾乎全部留存地方,由此不難預期土地出讓收益將為地方政府的城市建設提供重要的支持。
從兩個模型分別得到的估計結果來看,資本對數值、人力資本對數值以及土地出讓收益對數值之和的平方項的系數趨近于零,換言之,三者相互疊加所包含的城市化、知識溢出以及技術創新等交叉效應表現得并不顯著。一方面,該變量觀測值的數量級較小;另一方面,沒有任何一個變量能夠對上述交叉效應之間的內在聯系進行完整描述。盡管如此,估計結果仍然顯示,這種交叉效應盡管微弱,但仍與經濟增長存在正向的關系,而且高度顯著。
盡管為了區分不可觀測的地區差異,我們按照慣例以東部、中部、西部和東北地區設置了不同的地區虛擬變量,但估計結果顯示地區差異并不顯著,即相同的經濟政策及外生影響在不同地區產生的差異并沒有顯著影響各個地區的經濟增長。分稅制改革極大地改變了中央和地方的相對收支地位,卻使不同的地區面臨著相似的財政收支困境。因此,利用國有土地出讓充實財政收入,緩解財政收支缺口成為了幾乎所有地區的一致選擇。因此,地區虛擬變量不顯著也在預料之中。
相比之下,2004年國有經營性用地招拍掛出讓虛擬變量d2004則顯得極為關鍵。估計結果顯示,2004年國土資源部發布的國有經營性用地招拍掛出讓“8.31大限”產生了顯著的影響。在地區競爭的格局下,為了在“官員晉升錦標賽”中獲勝,制造業投資及其帶來的增值稅收入和GDP增長成為地方政府追逐的首選,而降低地價、犧牲土地出讓收益則成為主要的競爭工具;有限的制造業投資使得地方政府不得不退而求其次,為尋求經營性服務業及其帶來的營業稅收入同樣被迫放棄土地出讓收益,通過行政劃撥、協議的方式低價出讓土地;此外,土地出讓中可能存在的串謀行為也導致了這一問題。“8.31大限”使得經營性用地全面實行市場化出讓,顯著提高了地方政府在商住等經營性用地出讓中的收益所得,增加了地方政府進行城市發展和經濟建設的支出來源。
五、結 論
本文通過對相關文獻研究的回顧,總結了土地要素推動經濟增長的主要途徑,并運用四要素CES生產函數構造了動態面板收斂方程模型,使用中國174個地級及以上城市的樣本數據進行估計,主要結論如下:
第一,多數基于省際數據所做的實證研究結果均發現,1999年以來中國的地區經濟增長發生了絕對或相對趨同,且具有較高趨同速度。然而,本文基于地級及以上城市的數據所進行的估計結果則顯示,即使在控制了資本、人力資本、國有土地出讓等諸多因素之后,1999年至2008年中國的城市經濟增長仍然呈現出溫和的趨異。這意味著,與這一時期中國省區經濟差異的變化趨勢不同,城市(尤其是城區)經濟差異并沒有顯著地縮小。由此可以判斷,當采用更加細致的研究對象時,關于中國區域經濟增長趨同性的判斷可能會得到不同的結論。
第二,盡管對變量性質的差別化假設使得不同的模型在系數顯著性的估計結果中出現差異,但包括資本、人力資本和國有土地出讓在內的控制變量與經濟增長之間均存在正向關系。尤其是國有土地出讓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顯著正相關關系,有力地證實了我們基于經驗和文獻所做的判斷。在不區分用地類型的情況下,土地的市場化交易對地區經濟增長的影響得到確認,國有土地的出讓通過強化政府財政能力,可以顯著地推動地區,尤其是城市的經濟增長。
第三,地區虛擬變量不顯著而2004年份虛擬變量顯著表明國有土地出讓對地區經濟增長的影響不存在明顯的地區差異,但2004年國土資源部發布的“8.31大限”(當年8月31日后全國范圍內所有經營性用地出讓必須采取招拍掛方式)則產生了極大的影響。這一限令使得數量龐大的經營性用地擺脫了劃撥、協議等低價出讓方式,改變了地方政府為了競爭經營性服務業投資犧牲土地出讓收益的行為,從而對地區經濟增長產生顯著影響。
[1] North D C.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M].New York:W.W.Norton,1990.
[2] Grossman G M,Helpman E.Quarterly ladders in the theory of growth [J].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1991(58):43-61.
[3] Zysman J.Government,markets,and the growth[M].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3.
[4] Acemogfu D,Johnson S,Robinson J.Institutions as the fundamental cause of long run growth[R].NBER working Paper[J].2004,NO.10481.
[5] Rodrik D,Wacziarg R.Do democratic transitions produce bad economic outcomes[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05,95(2):51-55.
[6] 嚴漢平,李冀,王欣亮.建國以來我國區域經濟差異變動的空間分解——基于不同區劃方式的比較[J].財經科學,2010(11):86-91.
[7] Rodrik D,Subramanian A,Trebbi F.Institutions rule:The Primacy of institutions over geography and integration in economic development[J].Economic Growth,2004(9):131-165.
[8] 姚樹潔,馮根福,韋開蕾.外商直接投資和經濟增長的關系研究[J].經濟研究,2006(12):35-46.
[9] 王定祥,李伶俐,冉光和.金融資本形成與經濟增長[J].經濟研究,2009(9):39 -51.
[10] 周黎安.中國地方官員的晉升錦標賽模式研究[J].經濟研究,2007(7):37-50.
[11] 陶然,陸曦,蘇福兵,汪暉.地區競爭格局演變下的中國轉軌:財政激勵和發展模式反思[J].經濟研究,2009(07):21-33.
[12] 嚴成樑,龔六堂.財政支出、稅收與長期經濟增長[J].經濟研究,2009(6):4 -15.
[13] 杜雪君,黃忠華,吳次芳.中國土地財政與經濟增長——基于省際面板數據的分析[J].財貿經濟,2009(1):60-64.
[14] 辛波,于淑俐.對土地財政與經濟增長相關性的探討[J].當代財經,2010(1):43 -47.
[15] Arellano M,Bond S.Some tests of specification for panel data:Monte carlo evidence and an application to employment Equations[J],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1991(58):277-297.
[16] Blundell R,Bond S.Initial conditions and moment restrictions in dynamic panel data models[J].Journal of Econometrics,1998(87):115 -143.
[17] Judson R A,Owen A L.Estimating dynamic panel data models:A guide for macroeconomists[J].Economic Letters,1999,65(1):9 -15.
[18] Arellano M,Bover O.Another look at the instrumental variable estimation of error- components models[J].Journal of Econometrics,1995(68):29 -51.
[19] 劉生龍,王亞華,胡鞍鋼.西部大開發成效與中國區域經濟收斂[J].經濟研究,2009(9):94-104.
[20] 李冀,嚴漢平.中國區域經濟差異演進趨勢分析——基于政策導向和收斂速度的雙重視角[J].經濟問題,2010(11):14-18.
[21] Pritchett L.Where has all education gone[J].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2001,Vol(15):267-391.
[22] 姚先國,張海峰.教育、人力資本與地區經濟差異[J].經濟研究,2008(5):47 -57.
[23] 錢雪亞,王秋實,劉輝.中國人力資本水平再估算:1995 -2005[J].統計研究,2008(12):3 -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