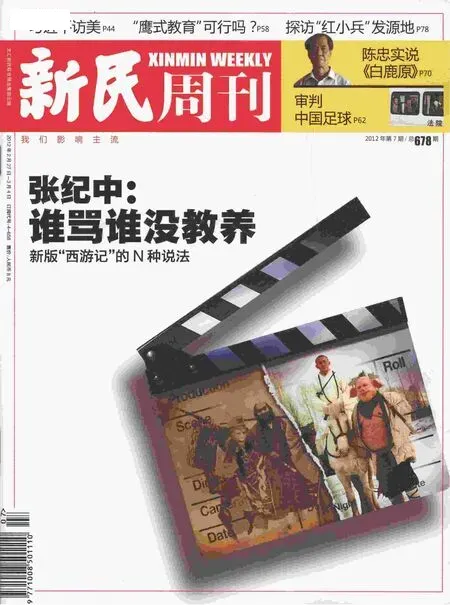我只是一個認真的攝影人
任曙林



上世紀八十年代我進入校園,是一個決定,在當時想了一段時間,但是思考的內容并不復雜,偶遇的高考似乎抓住了線索。當時比較了大學與小學,還是中學合適;在重點校與一般學校面前,一所中等水平的學校更合適。北京171中學具備了這些條件,而且離我工作生活的地方很近,就是它了。
進學校當然要先拿下校長,上詞兒唄,校方最終同意,我琢磨攝影本身也有一定原因。1979年的北京,照相還是比較新奇的事情,特別是專門去拍學生,好像還沒有聽說過。我反復保證不影響課堂秩序,他們也想看看這小子到底能耍出什么花活吧。開始校長推薦了一個特優秀的班主任,她怕干擾教學,拒絕了。有趣的是,兩年后,曾拒絕我的老師請我到他們班攝影,她也許發現了攝影的魅力。
進入學校還不算太難,難的是學生們的認可。那時的中學生普遍認為報紙上的宣傳假,記者是主觀臆想的同義語,特別是講到中學生更不是那么回事。他們經常嘲笑諷刺那些奇怪的所謂校園照片。在這種情況下拍攝,他們從心里看不上你,呵!又來了一位。那時的學生挺有禮貌,他們不一定躲你,但會用體態語言和表情的改變,強烈地表示他們的態度,這種抵制更可怕。一個個假象擺在眼前,你還拍什么呀。特別有意思的是,他們的后腦勺都長著眼睛,可以感到你要干什么,幾分之幾秒內,他們的體態已做了調整,這種不易察覺的變化其實差異很大,我進入的通道被堵死,只有放下照相機。怎么辦?解釋我不是那樣的記者?那真是傻了,只有靠時間,我有這個信心,有與拍攝對象相處的基本功。頭一個學期我幾乎沒拍出幾個膠卷,但我還是在校園里轉悠,極耐心且悠然地尋找著,與這幫學生打著持久戰。我并不傻干,我有我的專業素質:跑位,時機,進入幅度,體態語言和表情等等。學生們不傻,他們觀察出這位“記者”的不同,起碼好奇心使他們愿意了解我,但我并不去同他們聊天,這是我的原則。我無聲地干著我的攝影,我最終征服了他們,他們接受了這個外來者,我打開了進入他們的第一道關口。
我在校園成了透明的影子,慢慢地如入無人之境。這種感覺很迷人,時常你不拍什么,游走于學生中間也是一種享受。在彼此放松視而不見的前提下,種種感覺出現了,各種發現出現了,特別是眼睛跟著心思走時,相機不再束縛你的手腳,只是把你的所感凝固下來。我到學校沒有固定時間,只要還有學生在校園,哪怕是一個學生,也有可能有所發現,垃圾時間是不存在的。學生生活看似刻板,其間的細微變化都令你意想不到。他們的節奏一般大人們不清楚,也不想去弄清楚,自然認為他們簡單,沒什么過程與變化,一旦有點事兒,簡單的結論立馬得出,這也許是所謂代溝出現的原因之一。學校程序是固定的,學生們的狀態可是躍躍欲試。他們在限制中尋找自己的空間,表達交流自己的感受見識和發現。這是他們生存的必需,這是他們除了課堂學習之外,自由表現自己的天地,這恰恰成了攝影進入他們的通道。進入就是發現,兩者是同步的,伴隨著快門聲,我把他們的廬山面目一點點地留在底片上。
學校內容是十分豐富的。上學進校門千姿百態;早操早自習各顯特點;課間十分鐘眼花繚亂,年級不同,男女不同,性格不同;體育課與美術課我是可以參與的,何況還有不少室內活動;中午時光因人而異,吃飯談天,安靜中有一絲秘密色彩;下午的課程總有些異樣,也許是副課多吧;放學不一定回家,課外活動,課余活動,操場教室交相輝映。這往往是我最緊張的時刻,總是一層樓沒拍完,日暮就降臨了。夏日的黃昏,當最后一個學生離去,我往往要在校園里呆一會兒,不是回味今天拍了什么,而是人去樓空,另一種心緒升騰起來。失落?悠遠?彌漫在心中。我會在那一瞬進入另一種世界,在那個世界中沒有我,只有記憶的碎片來去飛翔。冬日的太陽落山早,經常有學生不肯早早回家,這時的教室是學生的天下,特別是老師也走了之后。你會感到像旋轉舞臺一樣,瞬間地或慢慢地,味道變了,氣氛變了,那已不是教室,你可以看到一個個鮮活的靈魂在躍動。一間教室也許只有一個學生,也許是一群,也許都是男生或女生,也有時就兩個人。這都無關緊要,緊要的是我需要調動所有的神經,靈活快速地游走,準確迅速地把握,而這一切的前提是不能對他們造成絲毫的干擾和影響。我與學生們的默契在這時發揮著重要作用,彼此心照不宣,彼此相互信任,我不是老師,也不算朋友,我只是一個認真的攝影人。(圖片均見《八十年代中學生》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