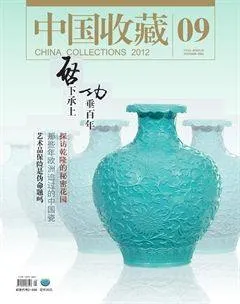開朗與平和是一種風格




8月初的幾場雨,讓北京的空氣清新了許多。暑期的北師大校園顯得頗為安靜,啟功先生生前居住的紅六樓宿舍藏身于北師大一個僻靜的角落,旁邊是一個小小的花園,幾位老人正在晨練,呼吸著北京難得的清新。在這個盛夏的清晨,記者帶著對啟功的景仰以及對先生為人處世的一些好奇,走訪了《啟功全集》編撰者侯剛先生和啟功內侄章景懷先生。
“人家喜歡是看得起我”
《啟功全集》編輯部與紅六樓僅隔著一條小道,當記者走進編輯部時,啟先生生前的助理侯剛正在埋首整理著手邊的文稿,記者的到訪使得這個陪伴了啟先生20余年的老人再次追憶起啟先生的才情和德行。
“我是1979年與啟先生相識的,那時我在北師大校長辦公室工作,經常到先生家通知事情。當時,啟先生在北師大不但給本科生上課,還主動承擔了夜大的課,教授古典文學,課程繁重,”說起啟先生,侯剛頗為動情,“啟先生給我的第一印象是非常平易近人。上世紀80年代初,啟先生在社會上已經頗有聲望,事務也越來越多,為此,學校打算給先生配助手,但先生卻婉拒了,他說:‘怎么能因為我的事,耽誤年輕人的前程。’后來,當時的北師大校長王梓坤就讓校長辦公室幫忙處理啟先生的一些日常事務,我也因此與先生結緣。”
1988年幫啟功先生籌備書畫義賣一事讓侯剛至今也感慨頗多。“當時,北京女孩擇偶有一句俗語——‘北大老、師大窮,惟有清華可通融’,就是說那會兒師大的學生生活困難的比較多,啟先生有感于此,向學校提出了義賣他的書法繪畫籌集獎學金的想法。”
從1988年到1990年,三年的時間里,啟先生創作了10幅畫,選出了100幅字。其實,侯剛透露,在三年的時間里,啟先生創作了不下500幅書法作品,但最終僅留下了100余幅,這其中有一個有趣的緣由。“有客人來了,正好趕上啟先生在寫字,于是就問他‘您這是給我寫的吧?’啟先生就隨口回答,‘你想要那就拿走吧’。”無奈之下,北師大校辦就在留學生公寓給啟先生找了一個房間讓他安心寫字,要不然連這100幅都很難湊齊。“張中行先生就曾問過他,怎么對自己的作品這么不在意呀?啟先生回答說‘人家喜歡是看得起我’。”最終,啟先生創作的這10幅書畫和100件書法在香港拍得160余萬元,并全部捐贈給北師大,設立了“勵耘獎學助學基金”,以“勵耘”命名是為了紀念啟功的恩師、北師大的老校長陳垣先生。
對啟先生的隨和與平易近人,侯剛頗為欽佩,“我們北師大的司機、食堂的大師傅、修電話的工人手里都有啟先生的書法作品,有的還不止一幅。”說到這里,侯剛想起了一件趣事,有一次,一場暴風雨使得紅六樓的電話線出了故障,啟先生著急地找到侯剛,侯剛立刻帶著電話工小楊去修理。修好了后,啟先生十分高興,主動提出要送一幅字給小楊。啟先生一邊寫一邊詢問小楊是否有對象,并向小楊許諾,等他結婚的時候一定要再送他一幅字。第二年小楊結婚后果真上門去拜訪啟先生,啟先生二話沒說,立刻寫了一幅字送給小楊,賀他新婚之喜。“啟先生就是這么隨和的一個人。”侯剛說。
北師大的“禮品制造公司”
在北師大,師生們都習慣把啟先生等幾位老教授居住的宿舍稱為“小紅樓”,從上世紀80年代初到2005年先生去世,啟先生在“小紅樓”里居住了20余年。雖然啟先生仙逝已經7年,但紅六樓啟先生的宿舍還保留著他去世前的原貌。
十多平米的書房,除了書桌和三套沙發外,都被書籍塞滿了。“這張書桌是九三學社的人送給先生的,他用了20多年,許多作品都是在這張小書桌上誕生的。”章景懷告訴記者。從1983年開始,啟先生的內侄章景懷就一直在先生身邊照顧他的飲食起居。
在啟先生生前,這間十多平米的書房常常高朋滿座,“經常是這撥剛談完,那撥就馬上進來了,他人緣兒特別好,”章景懷介紹,常來常往的除了張中行、馮其庸、徐邦達這些大學者外,“三教九流的人他都能跟人攀上話,他知識面很寬。有一次,一個制作筆的小伙子來拜訪他,他興致頗高地跟人談起了怎么做筆制筆,小伙子頗受啟發,回去用了三四年的時間寫成了一本關于制筆的工具書,還來找啟先生寫序,據說,制筆界正好就缺這么一本工具書。”
和啟先生共同生活了20多年,在章景懷眼里,啟功就是一個普通的老人,一個整天都樂呵呵的老頭兒。常有人問章景懷啟先生高壽的秘訣,他每次都回答說,啟先生是個佛面佛心的人,對物質生活沒有什么要求,寵辱不驚。
侯剛也認為,啟先生之所以能高壽,緣于他良好的心態。“雖然他一生這么坎坷,但他從不溫習煩惱,他曾對我說,過去的已經過去了,現在很短暫,但將來還很長遠。”
啟先生的幽默可謂人盡皆知,在侯剛看來,幽默也是啟先生高壽的秘訣。“有一次,我們學校一個修管道的小青年在路上遇見了啟先生,啟先生要跟他握手,小伙子一邊在衣服上擦手,一邊說‘我手臟’,啟先生笑言,‘手臟沒關系,只要不是黑手就行’。”侯剛還回憶說,當時,北師大的領導出差或訪問都要帶些禮品,而啟先生的書法自然是首選。此外,啟先生還給北師大加油站寫了不下20幅書法作品,每次加油站需要進油了,就送一幅啟先生的書法給油田,所以北師大加油站的汽油總能源源不斷。為此,啟先生戲謔地稱自己是北師大的“禮品制造公司”。
“啟先生是個性情中人,大家都知道他隨和,其實他也有不隨和的時候。”侯剛告訴記者,曾有一位空軍軍官來向啟先生求字,一進門就把自己的名片亮出來,說自己是什么軍銜、什么來頭,啟先生對這套有些反感,就讓他把名片留下,改天再給他寫。可這位空軍軍官非得當天就要,啟先生急了說:“你今天不派飛機來轟炸我就寫不了。”章景懷也講述了類似的一件事。有一次,一位高官派秘書來向啟先生索字,啟先生一反往常的隨和,對來人說:“我要是不寫,你們首長不會停發我工資吧?”
“做人誠平恒”
在大部分人的眼里,啟功是因書法家的身份而聞名的。“行文簡淺里,做人誠平恒”——這是掛在紅六樓啟功書房里的一幅書法作品,“這個字他寫了好幾遍,最終選了這一幅,他這一生也是這么做人做文的。”章景懷告訴記者,啟先生每天都要寫字畫畫,對于他來講,寫字、畫畫就是一種娛樂,“他癖嗜碑帖,臨摹了大量的碑帖,光唐人寫經他就臨了無數遍,大家都說啟先生字寫得好,殊不知他在這方面是下了大功夫的。”
跟隨在啟功身邊多年,耳濡目染,章景懷對書法也頗有些見地。“啟先生有時也會跟我談談對書法的一些看法,他說,寫草書就如同公共汽車中的大站快車,到小站的時候可以不停但必須遵循一定的路線。他的草書就是這樣練出來的,他真正懂草書。”不過,啟先生對自己的書法作品卻頗為隨意,他從不認為這些書法值錢,“他有一方印章,可以說是他心態的寫照,叫‘令紙黑耳’。”啟先生還有一方閑章叫“功在禹下”,因為大禹的兒子是夏啟,所以“禹下”就指“啟”。此方“調皮”的印章的用意也在強調他的姓。
除了書法家,啟功還是一位大學者、詩人,而許多人都挺困惑,啟先生每天既要教書,又要練字,還有那么多應酬,他哪來的那么多時間看書呢?“啟先生起居十分隨性,困了就睡,但他時常睡不著覺,或者很早就醒了,因此他的床邊總放著書,睡不著的時候就看幾頁書。除了書外,他的枕邊還經常放著些小鉛筆頭,有時靈感來了,就寫上幾句,他的很多詩都是這樣做出來的。”作為啟功身邊最親近的人,章景懷對啟功的“學問”是從何處而來的最為清楚。
在北師大從教70余年,啟功專攻古代文學和古典文獻學,對史學、鑒定學、宗教學很擅長,甚至對敦煌變文也有研究。侯剛說:“啟先生傳統文化的底蘊十分深厚,他除了寫字畫畫外,有時候還會唱詩,按照古代的唱法來吟古詩,他十分在行。”
說到做人的“誠”,章景懷和侯剛都不約而同地說起了兩件事,“啟先生跟人照相必定要平起平坐,要坐著大家都坐著,要站著大家都站著,絕不會別人站著,他坐著。”章景懷說,啟先生還有一個習慣,每次家里來了客人他都會把人送出門,然后再自己輕手輕腳地把門關上,以免影響鄰居。“他對錢財也沒有什么概念,同事、學生有困難,他都會熱心幫忙。他的大部分錢都捐給了北師大勵耘獎學助學基金。”侯剛補充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