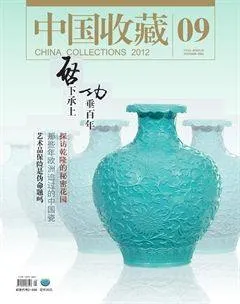忐忑
我對曾經火爆的歌曲《忐忑》從未感到過一絲喜感,既不賞心,也不養心。反而讓我時常想起親身經歷的一些事,心生忐忑。
頭一件,是由中國書畫引發的煩惱。我認識兩個收藏家,他們都握有齊白石作品數十幅,都以大藏家自居。如果各玩各的,當然相安無事。可我犯了個錯誤,鬼使神差,把他們聚到一起,結果引發沖突。
雖然兩個人都有十幾年的收藏經歷,但有所不同,甲某在地攤淘寶,乙某在拍場掐尖。
事情的起因是,我對甲某的藏品一直存疑,看他用辛苦掙來的錢沒完沒了買些不靠譜的東西,心里著急。于是懇請乙某幫忙鑒定。如果甲某的藏品的確有問題,就直言相告,免得一錯再錯。不料,我苦口婆心遠道接來的乙某,僅對甲某的幾件藏品提出疑問,并誠懇講明理由,反而被甲某粗暴地轟出門外。
我一直認為甲某算是個藏家,因為他夠癡迷,只是屈在囊中羞澀。如今,看他對別人的誠懇指點充耳不聞,稍有質疑即刻惱羞成怒,這大大出乎我的意料。我感覺,甲某的問題不在差錢上,而是差在對藝術品缺乏足夠的真誠。對他而言,東西的好壞無所謂,是否有人當真的買才最重要。令人忐忑的是,像甲某這樣的人目前在藏界為數不少。
另一件,是認識了開沉香店的汪琦先生。他雖然經營沉香,但他卻把香道當作一門藝術,潛心研究,著書立說。
汪琦與香結緣,是在十年前的一次日本之旅。他偶然走進一家經營沉香的小店,聽導游說,日本香道來自中國,但中國已經失傳,反而在日本完整保留傳承。這番話讓汪琦十分震驚,他請求店家演示香道,想探個究竟。店家恭敬地邀請他次日再來,理由是,做香道最少要用半天時間準備。第二天,看完香道儀式,汪琦被深深地感動。香道的文化核心不是炫耀沉香的名貴,而是合香過程的心靈體驗。從此以后,汪琦把“香”尊為琴書侶,形影不離。
這讓我想起,有個朋友去一位作家府上做客,面對條案上一枚奇石,主客席地而坐,開懷暢談一整天而興致未減。此刻的奇石,已幻化成一幅畫,一支歌,一首詩。沉浸在如此美妙的藝術感受中,誰還會關心這枚奇石價值幾何?
與汪琦交談時,他總是表示出無奈,多數買沉香的人,是抱著游戲態度,只關心沉香能否養生保健,能否保值增值。我由此對汪琦的孤獨產生敬重,同時對茶道、花道、香道生在中國而活在國外深感忐忑。
經常在電視里看到,文物專家對持寶人拿來的東西先說真假,再說價錢,很少說它美在哪里,丑在哪里。更有一些貌似的藏家,在拍賣會上買到東西后,立即在大腦里飛快計算,應該值多少,實際花多少,馬上送拍能掙多少?當人們開始習慣把藝術品直接用金錢來換算,把本來關乎心靈的東西當作大腦理財的工具,藝術品在人成為人的過程中正在逐漸失去作用。此刻,我們還能用“忐忑”掩飾忐忑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