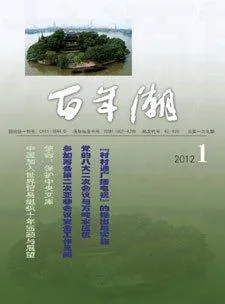革命曲折路 艱苦堪稱奇



中央紅軍長征本為二萬五千里,然而我因中途負傷離隊,后隨四方面軍進入河西走廊,故多走了五千里。事非經過不知難,三萬里長征路讓我艱辛備嘗,尤其是負傷離隊和西路軍這兩段,更是九死一生,永遠不能忘懷。
過草地負傷離隊
1908年,我出生于江西興國縣一個貧農家庭,自幼家境貧寒,只讀了3年書便中途輟學,當了7年多的裁縫。
大革命失敗后,中共興國縣委派人到我們老家一帶秘密宣傳革命,開展農民運動。1927年下半年,我借當裁縫的便利從事黨的地下交通工作,第二年加入共產黨。從此,我走上了革命道路,曾組織和領導過農民暴動,擔任過區蘇維埃政府主席、中國工農紅軍獨立第五師政委、瑞金縣委書記等職。
1934年10月,中央紅軍在第五次反“圍剿”失利后,開始長征。李維漢決定讓我參加長征,任中國工農紅軍總政治部地方工作部副部長。一路上我和鄧小平輪流共騎一匹馬,互相照顧。隨后我被調任中國工農紅軍第一軍團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長。紅軍從瑞金突圍,途經廣東南雄、湖南道縣、廣西全州等地,突破了粵、湘、桂軍閥的圍追堵截。我們工作部則一路打土豪、籌糧款,保證了大軍的食宿。經過三個多月,我們終于到達貴州的遵義城。這之后,我又回到中國工農紅軍總政治部做民運工作。那時遵義有“紅軍之友社”,成員都是知識分子、學生。我們退出遵義時,許多男男女女跟我們走。我負責帶隊,給他們講課。
我們在貴州轉了三個月的圈子,和蔣介石部隊周旋。1935年4月,我們從桐梓突圍,直奔云南。到了云南,我們如入無人之境,縱橫馳騁。后來因蔣介石部隊大兵壓境,紅軍又從四川迂回,渡過金沙江,飛越大渡河,到達四川西北地區的懋功與紅四方面軍會師。這期間,我曾任干部團民運組長,該團政委是宋任窮,團長是陳賡。當中央紅軍和四方面軍在懋功會師后,合編成立了紅軍大學,劉少奇任政治部主任,我在他領導下擔任過地方工作組組長。
1935年六七月間,紅軍開始了過雪山草地的艱苦行軍。當部隊進入四川松潘毛兒蓋草地時,不幸的日子降臨到我的頭上,我左腳嚴重中毒。由于整天整晚不是工作便是行軍,更可恨的是張國燾的反黨反中央使我軍行動更加緊張,這樣一來,不到數天我的傷口大發作,不能行軍,掉隊了。
領導對我非常關懷,毛主席的馬我騎過,劉少奇的馬我也騎過不少次,王首道更是我的救命恩人。負傷后第一次難忘的遭遇,是有一天劉少奇叫我騎他的馬走在前面,不料還未走二里路,就遇上敵人集中火力對我射擊。幸虧只是牲口受傷,而我遇到了一位四方面軍的戰士,他將我背回了本隊。
后來我的傷更加嚴重,有牲口也不能騎了,因此組織上給我一副擔架。由于天天爬山涉水,腳夫不是這個跟不上,就是那個掉了隊,四個腳夫只剩下兩個,不是張三叫苦,便是李四叫累。在時間緊迫的情況下,李維漢前來看過我一次。他說大夫對他說過,我的腳已經殘廢了,將來也不會走路了,沒有長期休息,傷口不會好的。為了安全,組織上決定留我在老百姓家休息。后來李維漢還寫了一封親筆信,勸我好好休息,痊愈后去找陜北蘇區,并寄大洋50元派蔡樹藩同志送來。就這樣,路過甘肅通渭時,組織上將我寄在了義崗鎮娃子川陳得倉、陳珍倉的家里。
與組織失去聯絡的一年
留在甘肅通渭時,我的病情惡化了,全身瘦得只剩下幾根骨頭,胡子頭發一樣長,滿身盡是虱子。安置我的同志對我說這家姓陳,因此我也改稱姓陳,取名陳先桂,并拜陳得倉做父親,組織上給我的50元大洋也全部交給了他。老農民見到錢非常高興。不料,組織上將我安排到他家第七天的晚上,由義崗鎮來了一個團丁,左手拿傘,右手提著馬燈,到我的住房檢查我。這位團丁似乎驚動了莊子上所有的人。他們都跑到我住房門口來,看我和這位團丁對話。這位團丁裝模作樣,腳剛踏到我房門口就問:“土匪”,你在紅軍干什么的,當什么官,哪里人,姓什么,傷口是什么槍、被誰打傷的?人們都瞪著兩個眼珠子望著我。這時我躺在炕上,很難受,但還是強打精神應對。我說,我是紅軍后勤部當裁縫的工人,姓陳,江西人。我的傷口不是打仗受傷,是過草地中毒的。這位團丁說我胡說,并問我打算要死還是要活。我說死活隨你的便吧,反正我病成這樣,看你怎么辦。他抬起頭四周探望,結果拿走我一床紅毯和一件毛線背心就走了,從此以后再沒有來過。我想當地的老百姓說不定還能記得當時的情況。
我到娃子川陳家,一直同陳得倉夫婦一床睡。由于我傷口日漸惡化,到他家里約有兩三個月之久都病得不能起床。接屎端尿、每天飲食全憑陳得倉的妻子和小孩們幫忙照顧。感動之下,我把身上僅有的一塊銀元都交給這位母親,作為酬謝。
陳得倉是個中農,當時年約50歲,是個做木工的人。他有個弟弟叫陳珍倉。他兄弟倆上有母親下有老婆和兒女,共十幾口人吃飯,都是在家務農為生。這個莊子離通渭城60里,到義崗鎮僅十來里,約十來戶,都姓陳,都是忠厚善良的農民,沒有一家是地主。他們都很擁護紅軍,經常將我軍和國民黨軍對比,和甘肅馬家軍對比。他們看到紅軍路過甘肅公買公賣又不殺人,認為這是了不起的好軍隊。這里群眾條件很好,但治病的條件很差,沒有錢也買不到藥,不衛生讓人嚇得吐舌。我實在沒有辦法,只好躺在床上讓這位陳得倉擺弄。他用土辦法,天天燒香,用艾葉灸、拔火罐,用尿洗傷口。
離開了部隊,離開了親人,一切都靠我這個孤苦伶仃的病人去和陌生人打交道。環境是陌生的,生活是艱苦的,病情是嚴重的,說話聽不懂,風俗習慣差異很大,真是讓人很痛苦。每當苦悶時,我總想著我家是貧農,我是工人,我無論如何是要革命的。革命事業是正義的,對我們有利。我還念著馬克思說過的話,一個革命者,不但要認識世界,而且還要改造世界。我在這種困難環境下,該是自告奮勇去克服的時候了。就從這些基本道理出發,我克服困難,堅持養病,下決心和當地老百姓打成一片,弄好關系。
真是謝天謝地,雖然終身成了殘廢,但在那極端困難的條件下,久而久之我的傷口竟然逐漸好起來了(當然痊愈是在1936年八九月間)。大約到了1936年二三月間,我雙手拄拐棍能去廁所大小便了。為了和群眾打成一片,我下決心帶病給娃子川百姓縫衣服度日。由于我會這門手藝,名聲一下子傳開了。為了把群眾關系弄好,我在大多數人家做工都未拿過他們的工錢。不少周圍百姓都派毛驢接我去縫衣,大約在娃子川縫衣服有一兩個月之久,隨后又到和娃子川相隔十里遠的獅子川的張家和楊家河的楊家、王家等戶縫了兩三個月。因為我是紅軍寄下的南方人,再加上會縫衣服,所以在娃子川一帶無形中成了眾人皆知的人物。
大概是1936年春夏之交,得到一個振奮人心的消息。因住在那兒消息不通,我和一個在通渭縣讀書的娃子川陳姓小學生交換條件,我替他縫了一套學生服,他替我要來一張《甘肅日報》。報載彭德懷率領陜北紅軍東渡黃河,占領山西臨汾、洪洞等可喜的消息。我從這張報紙里真得到很大的安慰和鼓舞,高興的心情難以形容。我將報紙放在口袋里,每當苦悶時,總是偷偷地取出來看好幾遍。
當我正在義崗鎮王家替他女兒縫嫁妝時,我紅軍二、四方面軍會師北上,路經此地,從此我就歸隊到紅軍三十一軍了。我到軍部時,遇到該軍做地方工作的干部,他們告訴我說,路過楊家河、獅子川時,就有不少老百姓向他們反映娃子川有個縫衣的人是紅軍里的人,為此,他們曾找過我。
祁連山上打游擊
三十一軍軍長蕭克和我在江西萬安、泰和一起工作過,彼此熟悉。他招待我吃了一餐飯,問了問我的情況,給了我一匹馬,叫我和李聚奎在當天的頭里走。我們走了不到幾天,在一個夜里渡過了黃河,到了甘肅河西走廊一帶。就這樣,我參加了西路軍,調至政治部民運部工作。我積極請求恢復黨籍,但因天天行軍,直到1937年1月左右,在臨澤縣屬的倪家營子戰場上,經過西路軍黨委決定,恢復了我的黨籍。經手人是張琴秋,時任西路軍政治部組織部長。
西路軍到了甘肅古浪、山丹、臨澤、高臺等地,遭遇到西北馬步芳等部騎兵節節包圍和嚴重的抵抗。我方死傷不少,殘廢傷號也天天加多。敵人還俘虜了我方不少的人。大約在1937年1月左右的一個晚上,馬匪騎兵集中力量圍攻我通向新疆要道的高臺城駐軍,董振堂率領的紅軍第五軍團全軍壯烈犧牲。
戰爭形勢十分嚴峻,加上嚴寒的氣候、糧草的困難和飲水的缺少,艱苦程度和過雪山草地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
到了形勢無法挽回的時候,西路軍領導徐向前、陳昌浩、李卓然委我為西路軍直屬殘廢營的政委。該營百來人,多是團、營、連的殘廢干部,也有個別當過師長的。新中國成立后曾任中央政府糧食部副部長的喻杰當時在該營任教導員。
后來形勢更加惡化了,上級決定主力由李先念率領向新疆方向突圍,而老弱病殘一律留在祁連山上打游擊,曾任軍委總干部部副部長的徐立清就是當時在祁連山上的總領導人之一。當環境萬分不利的時候,徐立清集合大家講話,要我們化整為零,自由自愿地分散為小型隊伍活動,當場每人發了不到一兩重的大煙土。根據這個指示,我和喻杰重新調整了殘廢營,在自愿原則下重新組織了20人左右為一隊。會議公推喻杰任隊長,我為黨支部書記。我們在祁連山上打了一個時期游擊,做少數民族群眾工作。這些民族很像是藏族,他們善良老實,從未和我們搗亂。
當馬家軍從四面向祁連山搜山的時候,我們的出路只能是突出敵人的包圍。我們決定偷偷越過高臺敵人的封鎖線,經過內蒙古邊境到我陜北根據地去。當天晚上,大多數人都順利地渡過了黑河,到高臺以東的東河岸來了。有一兩個女同志,一個小同志,渡河后掉隊了。我也差點掉隊,因馬失蹄,一家伙連人帶馬都滾到黑河的深水中去了。馬克思在天之靈保佑,我手拉著牲口的尾巴才浮到河東岸,跟上隊伍。當時氣溫大約在零下20度左右,皮帽皮衣、棉鞋棉褲全都浸得透濕,隨即結成冰塊,頭發胡子也結成一串一串的白雪珠。光腳板走過河沿的砂子地,雙腳凍得發紫,周身發抖。這是我永遠不會忘記的一條倒霉河,真凍得我好苦。喻杰等同志替我拾到幾根柴禾烤烤,稍稍溫暖了一下,大家又騎上餓瘦了的老馬向內蒙古邊沿沙漠地前進,找陜北根據地的希望可能實現了!
兵敗被俘
天不遂人愿。當晚,高臺城馬步芳駐軍就發覺了我們,馬上派了一連騎兵追趕。在漆黑的夜里,伸手不見五指,兩軍相遇。敵人喊殺連天,刀光閃閃。在緊要關頭,喻杰走在前頭,取出自帶的駁殼槍放了一梭子,帶領我們突破了敵人這一次的包圍。但我們整天整夜的行軍,不但人饑餓疲乏到萬分,就連靠著救命的牲口由于白天和夜里不停地行軍得不到休息,也餓得大叫大嚷起來。我們這支隊伍總共只有一兩支破步槍,幾發子彈,喻杰的那支駁殼槍子彈也打完了。我們陷在了彈盡、糧絕和人困馬乏的沙漠里。馬步芳的騎兵一直在我們屁股后頭追趕,到第二天的上午又追上包圍了我們。我們都被敵人俘虜了,當即被押送到高臺縣政府禁閉了一天。這大約是1937年3月左右。
被俘的當天晚上約12點左右,我們一個個睡得像死人一樣時,突然來了兩三個人,帶著馬燈叫我們集合站隊,當場一個個地審問我們。我們事先互相商量過對付的辦法,都一致回答是在后勤部休養的殘廢病號,也有個別的說是在后勤部當勤務的。當敵人問昨天誰打的槍時,喻杰說是因不慎槍走了火。第二天早上,敵人又讓我們在縣政府門口集合站隊,送我們到張掖去。這時有個高臺縣的縣長出來講了幾句話,主要說明送我們去張掖的理由。他還當場照例審問了我們一下,我們也按照前一天晚上說過的話答復了他。從高臺到張掖大概花了三四天時間。我們這些人大多是殘廢病號,而我是當時殘廢比較嚴重的一個,不能徒步,挨過馬家軍士兵不少的打罵,到了實在無法走的時候,乘著老百姓的送糧大車,痛苦地到達張掖城。
到了張掖以后,我們被禁閉在喂駱駝的一個露天的大院子里,由民兵看守。我們來之前,已經有一批被俘虜的戰士關在這里,加在一起約百來人,盡是些殘廢病號老老少少之類的人物。
我們在這個駱駝院子里住了15天左右,當刮風的時候,天上的雪花紛飛到我們身上。敵人只許我們每人每天喝兩碗像水一樣稀的小米粥。有些小青年餓得在地上滾。我也偷過老百姓喂牲口的馬料充饑。餓到很厲害的時候,有張掖縣的天主堂牧師前來施舍過兩次,給了每人一個不到二兩重的小麥面饃。牧師到我們跟前,讓我們向上帝禱告,在每個人的臉上畫符。我們心里悶著笑。
我們到了張掖后,始終沒有人檢查和審問過我們。這是與國內時局發生了根本變化分不開的。這時候西安事變已經有好幾個月時間了,國共內戰基本停止了。我們時常聽到一些馬家軍士兵和百姓說國共合作了,不打內戰了,抗日了,你們的祖宗積德,南京有命令不殺你們了,等等。這些話我們半信半疑。在我們被俘之前,特別在西安事變之前,他們殺過我們不少的人,但到了1937年二三月之后,沒有聽說過殺我們的人了。
輾轉回延安
西路軍幾萬人,除李先念率領幾百人到達新疆以外,不是犧牲,就是被俘,只有極少數人化裝逃回延安。比如,陳昌浩、徐向前在祁連山失敗后,是化裝成放羊的老百姓回到陜北的。李聚奎、朱良才也是化裝討飯回延安的。被俘虜的人,有一些經過中共中央交涉,先后送到延安,比如劉瑞龍、張琴秋、方強等同志,都是被俘后送回延安的。同我一起被俘的十幾個人也先后回到了延安,當然具體方式各有不同。喻杰是被馬家軍動員去抬傷兵,回青海的路上逃回延安的。此外和我一起被俘,一起押在張掖縣的程其興同志,新中國成立后曾在一機部工作,是和百來人一起由張掖送到蘭州轉送回延安的。我未聽見和看見過馬家軍玩弄所謂自首叛變等鬼名堂。
當時,我們被關的地方常有一些馬家軍跑來找年輕小鬼當他們的勤務員,也有人來找我們的人去做工的,也有動員去抬他們的傷兵回青海的。后來,住的我們旁邊的一位住家的馬家軍士兵,據說當過排長,請我去替他老婆縫衣服。因為我會這門手藝,在極困難的時候找到了生活出路,和我一起被俘的同志都為我高興,有些同志常跑進來向我要根火柴抽煙,有的向我要碗開水。過了大約三四天,一個晚上,我們的人跑進來告訴我說,他們明天一早就要整隊集合,每個人各背15天的干糧,徒步押送到蘭州去,問我去不去。聽說這是南京的命令,要將我們解送到南京去。當時我的腳確實殘廢不能走路,故未跟他們一起走,仍留在這家縫衣。
縫了好幾天衣服,我未得他一文錢,只請求他幫忙找到一家縫衣工廠。之后我就進這家工廠做工去了。這個廠子的招牌叫甘州東興軍服莊,就在張掖東大街,實際上是一個漢人叫喬東生私人開的廠子。這個廠子在張掖是手藝比較高明的,既能縫軍衣,也能縫中衣、西服、便服,約有縫衣機七八架,工人一二十名。廠長喬東生,甘肅合州人,曾和楊仲貴師傅一塊合作縫衣,后來他自己開辦了這個廠子,聘請楊師傅當工頭。楊師傅是四川人,思想很進步,天天都希望紅軍勝利,也很想跟我到陜北來。我臨走時,他給過我路費。
由于西路軍的失敗,當時有不少我們的人流浪在河西走廊各個地方,特別在張掖更是充滿街頭,有的替人做工,有的挑擔做小生意,也有的在街上討飯度日。不少女同志當了別人的老婆,亦有些青年小鬼替馬家軍當勤務員的。謝覺哉的愛人王定國當時也在張掖。她在張掖天主教堂進步分子高院長那里住著,還來過我這家廠子縫過衣服,彼此見過面。我們的人告訴我說天主堂的高金城院長很進步,很同情我們。因此,我下工的時候常常偷偷地跑到他那里去活動。我同王定國就是在高院長家里第一次認識的。
考慮到甘肅河西一帶有不少我們的干部流散在各地,高院長同情紅軍、共產黨,表現十分進步,八路軍駐蘭州辦事處就委托他設法輸送我們的干部回延安來。當時謝覺哉同志是八路軍駐蘭州辦事處中央代表,主持這項工作。王定國是在高院長那里找到蘭州八路軍辦事處的,我也是通過高院長才到蘭州辦事處的。張掖很多人都知道這位高院長同情共產黨。有一次我去找高院長,被喬東生發覺了,這位廠長連說帶笑地說我是共產黨,高院長也是共產黨,宋慶齡、馮玉祥都是共產黨,等等。由于高院長太紅了,據謝覺哉后來告訴我,這位好人1938年2月不幸被敵人在一個夜里活埋了。1949年,我軍解放張掖后,當地的人民為這位遇難烈士立了一塊紀念碑。
大約是1937年九十月間,我離開工廠到了蘭州八路軍辦事處。王定國比我先走了幾天,我后走幾天,到了蘭州辦事處我們又見了面。當時朱良才在蘭州辦事處工作,他原先在紅一方面軍衛生部當過政委,后在西路軍我們彼此認識。赴陜北中央組織部的介紹信,由朱良才當面交給我。朱良才找我談了幾句,委托我帶著其他幾位同志一同回延安。我們一行人由蘭州辦事處出發路經西安辦事處,1937年冬勝利地回到了延安,住在中央組織部招待所,從此結束了長征。我剛到延安的時候,就有同志告訴我,毛主席曾關切地問到我,“那個瑞金的縣委書記來了嗎?”1938年春毛主席到中央黨校參加畢業典禮,我特意去毛主席住處看望。
在我的革命生涯中,長征是最難忘的一件大事。我曾賦詩一首,以志不忘,詩云:
長征史無前,吾行三萬里;
革命曲折路,艱苦堪稱奇。
掛彩留通渭,不意去河西;
國燾反中央,罪責難清洗。
山丹被敵困,槍炮加飛機;
浴血倪家營,高臺苦戰激。
撤退祁連山,冰雪無寒衣;
偷渡黑山河,落馬險溺斃。
被俘落虎口,彈盡糧絕際;
患難同甘苦,喻杰在一起。
統戰紅旗展,絕路逢生機;
蘭州遇謝老,敗因深剖析。
輾轉去延安,富春是上級;
走訪王首道,難忘讓馬騎。
黨校見羅邁,百感熱淚起;
批判張國燾,上臺言辭激。
感謝救命恩,晉見毛主席;
紅軍指戰員,情誼多親密。
往昔崢嶸事,代代莫忘記;
年老甘讓賢,革命有后繼。
民族大團結,四化齊努力;
中華得振興,共同慶勝利。
(本文由胡嘉賓的子女,根據父親1956年、1976年、1983年自傳和1983年口述記錄稿摘抄整理而成,有刪節)
(責任編輯#8195;汪文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