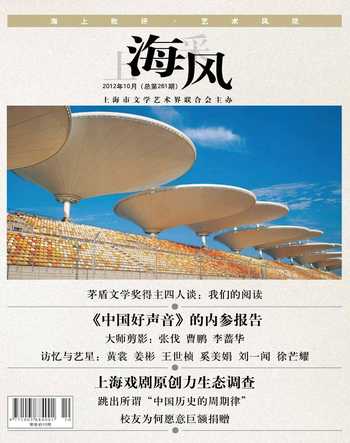中國好聲音從哪里來
千里光
若有人問,中國好聲音從哪里來,我會忍不住想起一首外國民歌,歌詞第一句就是“河里青蛙,從哪里來?是從那水田向河里游來”。我之所以不用“過江之鯽”來形容,是因為不想貶低當今的無數好聲音,我喜歡他們的歌。
那就像千千萬萬的小蝌蚪經歷了蛻變后的一次遠游。尾巴沒有了,腿出現了,于是一路蛙泳,一路歌。它們游出水田,穿越池塘,奔向河流。那場面壯觀又慘烈,因為真正能游到終點的總是少數。能成為中國好聲音的,應該是青蛙中的青蛙,特別牛的“牛蛙”。
竊以為,在中國,有兩樣東西是千萬不能自以為是的,其一是乒乓,其二便是唱歌。稍有涉足,便知道什么叫“山外有山,天外有天”了。民間乒乓高手多得不計其數,似乎隨便一個門洞里,都會冒出一兩個高手,把你打個落花流水。好聲音在中國,也是。
生活中不乏這樣的經驗,隨便的一個聚會,只要有麥,有唱歌,總有一鳴驚人的好聲音出現。平時看不出有多少藝術范兒,甚至靦靦腆腆的人,一上臺卻石破天驚,或渾厚如滾滾炸雷,或高亢如穿云裂帛;能將《青藏高原》最后一句“那就是——青——藏——高——原——”輕輕松松飆上去的,我們單位就有三兩個。
中國的卡拉OK業大概是世界上最發達的,分布稠密的歌廳,造就了無數的“青蛙”,哪怕再偏遠的地區,一踏進歌廳就感覺不到有什么地域差別了,歌照樣唱得時鮮,不僅和內地大都市接軌,還和港臺接軌,和歐美接軌。難怪有人說,歌廳是走向世界的搖籃。有幾次遇到縣委書記或縣長、局長親自K歌,別看他們平時金口難開,一張嘴卻出口不凡,貌似歌星下凡。讓人不由感嘆,人不可貌相。倒不是說他們相貌有什么不到位,而是實在出乎意料,明明不像會唱歌的,卻偏偏是個好聲音。
前不久看到《非誠勿擾》中有個來自加拿大的男子,已經過了不惑之年,說話帶有磁性,有位歌唱家夸他低音難得,為此他毅然放棄原先已有的事業,專攻低音。孟非要他當場唱幾句,他一卡緊喉結,一開唱,全場就沉默,無話可說。大家都知道他腦子進水了。我只能說他國外呆久,變傻了,只要他來國內參加幾次縣城里的卡拉OK,他就該明白自己原來是多么的蝌蚪。他最多只能說喜歡唱歌,或者說嗓音條件不錯,會唱兩句。那天,他想憑借自己未來“男低音歌唱家”的光環,牽手一位女嘉賓,結果卻慘遭冷遇,演繹了一出無人喝彩的“歌星滑鐵盧”。
這位加拿大仁兄的故事告訴了我們一個簡單的道理,擁有一副好嗓子,并非就等于擁有了好聲音。
那么誰能說得明白到底什么才是好聲音?是庾澄慶的High,很搖滾張揚的那種,還是劉歡的抒情,很安靜內斂的那種?答案應該是,風格因人而異,動人就好。所謂動人,囊括了喜怒哀樂;動人之極,大概就是汪峰說的“心碎”的感覺了。金志文的《為愛癡狂》大概就是一首“心碎之作”。那天,在他唱到“想要問問你敢不敢,像你說過那樣最愛我”時,我已經控制不住地流淚了。那時他還沒訴說北漂的經歷,但那種種的委屈、不如意都已經充斥在他的聲音里了,讓人們泛起陣陣酸楚,一邊想象著他的人生故事。有著類似經歷的楊坤,更是感同身受,哭得像個淚人兒了。以前聽楊坤的《無所謂》以及《那一天》我也有心碎的感覺。
這些“心碎之作”并沒有在敘述一個完整的故事,它不是歌劇,也沒有朗誦詞穿插,它只是借助旋律抒發情感,人們居然可以從歌者的聲音里感受到一種特別的氣息,甚至可以想象到里面的故事,進而產生強烈的共鳴。這便是好聲音的魅力所在。
那英在趙露落敗時鼓勵她說:想成為我,就多幾次生活磨難。
那英有點二,說話直白,但這話一語道出了好聲音之所以能成為好聲音的真諦。那英早先在山溝溝里呆過,她考沈陽歌舞團一連考了三次才錄取,而且很長一段時間,只是一名伴唱,直到有一天主唱生病,她臨時頂替,才從此由一名伴唱升格為主唱。所以那天她的和音王崇對著她唱《白天不懂夜的黑》的時候,她淚流滿面。那是她的歌,歌詞說,你永遠不懂我傷悲,像白天不懂夜的黑。
其實她怎么不懂,她就是從黑夜里熬過來的,知道伸手不見五指的那種恐懼和絕望。熬過黑夜的人才知道白天的可貴,他們的聲音里也就多了一份對生活的體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