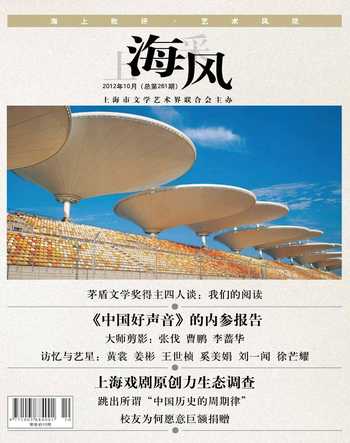1956年秋在上海
彭荊風
去過上海許多次,印象最深的還是1956年秋天那近40天的小住。
在20世紀五十年代的中國,1956年是個難得的安定歲月;沒有戰爭,鄰近的朝鮮半島的硝煙烈火,前兩年就停歇了,也沒有政治運動,1955年那場讓文學界心驚膽戰的“反胡風運動”并由此引發的“肅反”,也悄然結束了,人們又恢復了平靜生活!上海這座中國最大、最繁華的城市,也就能從容顯出它那特有的魅力!
新時代的上海,不同于舊中國那在表面繁華下掩蓋的貧困、混亂。
我1947年春夏曾經來過上海,一方面驚訝這城市高樓大廈之多,燈紅酒綠中富人的奢侈,又深感這城市的下層貧苦人境遇之慘,報紙上每天報道的是物價飛漲、路有餓殍。以致過了許多年,我對上海這大都市,都有著一種既感神奇又充滿恐懼的矛盾心情!
1956年上海的城市格局還是從前的樣子,老樓房、老街巷,并沒有增加多少新的建筑,熱鬧的還是那些老地方,但城市的精神氣質卻不一樣了,物資供應充足,價格又平穩,更沒有挨餓的人,給我的感覺是每個上海人都在安心地工作、學習,把他們的聰明才智以及這個城市多年形成的精巧細膩作風發揮得淋漓盡致。這時候來上海旅行,既可欣賞這城市傳統的大都市氣派,又可感受上海人在新的社會煥發出的為人民服務的真摯熱情,也就是今天所提倡的人文關懷;你問個路,那些大娘、大嫂會不厭其煩地告訴你,該去哪條巷口坐車,如果要省幾分車票錢,可多走幾步去另一條街坐車……
話語親切、周詳,聽得我們心里都是暖暖的。
那次,我是因為創作了電影文學劇本《蘆笙戀歌》,被中央電影局局長、老作家陳荒煤電召來上海參加為期40天的、有蘇聯專家講課的電影劇作講習班。
荒煤把這個講習班選在上海,也是因為上海是中國電影發源地,這方面的專家學者多。
那是新中國成立以來,參加的人數較多,時間也較長的一次電影研討會,半天看中外電影,半天討論,我還記得那次的同學就有海默、孫謙、徐懷中、魯彥周、黃宗江、公劉、白樺、季康、公浦、張天民、鄭秉謙……
在這以前,我剛剛在云南邊地一個景頗族村寨的竹樓里生活了六七個月,突然換了個環境,從整天云霧繚繞的山野飛臨這高樓林立、珠光寶氣的大城市,真是有些眼花繚亂。我和幾個年輕朋友,常利用中午、晚上的時間和周末的休息天,在街巷里盡情游逛,細細欣賞那些產生于各個時代,有的是洋場味,有的是古典情調,風格各異的建筑,大陸新村的魯迅先生故居,幽靜的長長短短石庫門,熱鬧的城隍廟、大世界,包括那名人聚集的萬國公墓……當時人還年輕,雖不是老饕,卻也愛吃,也就很關注那些經過一代又一代美食家篩選肯定過的精美吃食。
時過50多年,那次在“講習班”看過了哪些電影,我卻一部也記不得了,但老正興的鱔魚糊,陸稿薦的百年老鹵鴨腳、雞翅膀、大蝦的鮮美,卻是現在想起來還是垂涎欲滴,特別是那價廉物美的油炸肉餡餅……
當時,我們住在蘇州河邊的老新雅酒家。樓下就是熱鬧的大街,每天晚上華燈初上時,就有一個胖胖的中年人挑著一副擔子過來,在酒店樓下擺開攤子。這是一副精巧、整潔的木制擔子,一頭架著一口平底鍋,另一頭擺著各種作料的案板;他就在街頭切蔥、和面、調雞蛋、剁肉末,然后一邊做餅一邊煎餅。看來他是很有號召力,在他剛放下擔子時,就有人開始排隊了,雖然這要等很久,大家都很安靜、耐心,沒有人擁擠地亂插隊,更沒有人嫌他和面、煎餅的動作緩慢,他也決不會因為排隊的人多而匆忙潦草地減少工序,一定要把面和勻,煎得油香四溢兩面焦黃才賣給顧客;也不管你來得多早,排了多久,或者是天天來買餅的熟人,都是一人兩個,決不多賣給。
我那天從樓下過,也被這又香又脆的油炸肉餡餅引誘得加入了買餅的行列。從此每天都是常客。
有天晚上,我出去辦事走遠了,趕回來已是晚9時左右,最后的兩個餡餅已賣掉。沒有買到的人,也已嘆息地散去。他每晚上只做200個呢!
我當然也頗惆悵。問他為什么不多做一些?他笑道:這副擔子只能裝這200只餅的原料,做起來也很費力,馬虎不得呢!
當他知道,我是從遙遠的云南來。十幾天來,每晚都來排隊買餅,頗高興,就說:“你是出差的人,事多。以后,就不要排隊了,來晚了,我會給你留兩個。不過也不要太晚!”
第二天晚上,我剛加入排隊,他就認出了我,馬上把剛煎好的兩只餅遞給我。
隊伍里有了騷動,對他來說,這可是異樣之舉。他解釋道:“人家是從云南來出差的,幾萬里遠呢!來一趟不容易,優待,優待!”
隊伍里又安靜了,我連聲向人們道謝。
離開上海的前一天,我又回來晚了,這時候已近晚10時,上海的夜市結束得早,街頭巷尾已是燈火闌珊。我想,他那餡餅攤子也該早收攤了。行前卻錯過了這最后一次美食,真可惜!哪知道,他卻在已沒有人排長隊的攤子前,迎著秋夜的涼風悠然地吸著煙。見我來了,只說了句:“你再不來,我就該走了。”
灶里只剩下一些余燼的平底鍋上放著兩只微溫的餡餅。
我連連道歉,也告訴他,明天一早,我就要離開上海了。并為以后不能再吃到他的鮮美香脆的餡餅而遺憾!他卻爽朗地笑了,“以后再來嘛!你們公家人,出差的機會多!”
我想也是這樣。我親熱地握了他那滿是油的厚實大手。
但世事是那樣難以逆料。第二年就“反右”了,我在苦難中一泡22年;到20世紀八十年代初期再去上海,雖然街巷大致依舊,但經歷了“文革”10年,上海還沒有恢復它的活力,頗有“自胡馬窺江去后,廢池喬木,猶厭言兵”之感。有天晚上我專程去了老新雅酒家的樓下,哪里還有那個油炸餡餅攤,再找老正興的鱔魚糊、陸稿薦的百年老鹵,也失去了從前的口味。
我才恍然,這二三十年可不是平常的二三十年,許多人事都被沖擊得變了樣呢!
不過我對上海的美好記憶卻沒有變!我相信,優良傳統和美好現實總有一天又會融洽地結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