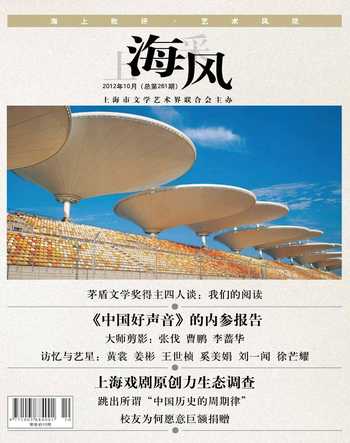劉一聞:敬畏傳統是一切之本
劉莉娜



劉一聞
1949年12月出生于上海,山東日照人。書法篆刻得蘇白、方去疾、方介堪、謝稚柳諸前輩教誨。20世紀八十年代嶄露頭角,并逐漸樹立起清逸典雅的個人風格,為藝壇所矚目。2005年9月在山東臨沂王羲之故居建立劉一聞藝術館。歷任全國第五屆書法篆刻展、第二屆中國書壇新人新作展、全國第六屆中青年書法篆刻展、首屆國際篆刻藝術交流展等多項大展的評審委員。出版有《劉一聞印稿》《劉一聞楹聯書法》《一聞藝話》《劉一聞刻心經》《中華民族印譜》等二十部著作。現為中國書法家協會理事、中國書協篆刻藝術委員會委員、中國藝術研究院篆刻藝術院研究員、西泠印社理事、上海書法家協會副主席、上海博物館研究員。
與書法篆刻名家劉一聞先生約在上海博物館見面,這本身就是一件太應景的事情:斑駁的青銅、古雅的字畫、精美的璽印……舉目所見皆是古韻的凝聚,歷史的沉淀,這些與我們要聊的主題正是相得益彰。但其實選在這里可并非我們刻意造境,完全是因為上博就是劉一聞每天都要出入的工作單位。
是的,劉一聞的另一個身份是上海博物館的研究員,這樣的雙重身份是不是讓你直接聯想出一位古舊周正的老學究形象?然而如果你看過他的印,你就一定不會這么想了——讀他的印,就如見到他本人一般:劉一聞祖籍山東日照,所以生得高大魁梧,身形可稱得上是“山東大漢”;而他又自幼生活在上海,幼秉家學,耳濡目染,為海派文化所浸潤,眉宇間和藹親切,說起話更是輕言慢語,一派謙謙。飽滿的額頭下是一雙明亮而熱情的眼睛,這讓他雖年過花甲卻依然精氣神十足,頭上絲絲縷縷的白發更為他平添了一份儒雅沉穩——山東人的大氣豪情,上海人的細膩雅致,在他的身上可以說得到了完美的融合。
不僅面相如是,劉一聞的作品亦如是。他的作品大多乘興使然,絕少有雕琢的痕跡,第一眼是簡約的,干凈的,下一眼卻是奪人眼球,攝人心魄。既有淋漓暢快的豪放之姿,又在謀篇布局間心細如發,這表現在印章上,就正是渾然天成,大有古風了。說道“古風”,據說還有個小趣事:大約十年前劉一聞曾陸續為幾位相熟要好的朋友每人刻制了一方“將軍印”,其中有一方印文為“長沙將軍章”,結果得了這方印的朋友一時頑皮,將印拓寄給了某市的博物館,假稱自己偶得了一方漢印,詢問博物館是否有意收藏。而月余后居然得到了博物館的回音,表示有意收購入藏,這雖是一樁趣談逸事,卻也由此可見其作品中古風之正。
中華民族印譜:56個不重樣的“族”
就在我與劉一聞先生相見之前的一個月,他剛帶著他的《中華民族印譜》原印原作赴臺北國父紀念館做了一次展出,在為期一周的展出時間內,寶島觀眾絡繹不絕,在當地引發了不小的轟動。劉一聞說,中華民族印譜的印章有57方——56方民族印加上一方刊頭印——全部漂洋過海搬去臺灣,說起來也不是一件輕松的工程,但是中間經歷了臺灣友人的積極促成、臺灣文化界的大力支持、以及普通臺灣同胞的熱情觀展,他覺得所做的一切都非常值得,更覺得這一切正是自己的這套民族印譜所承載的意義的最好體現——56個民族心連心,兩岸三地一家親。
說起這一套《中華民族印譜》,最早是劉一聞應出版社之邀、獻禮國慶六十周年的力作。作品由五十七方印章組成,除刊頭印《中華民族印譜》外,其余代表五十六個民族的五十六方印章,每一印都各以民族稱謂作為具體鐫刻內容。這些作品或清勁古淡或峻健典雅,可以說每一方印章都能從不同側面反映出劉一聞鮮明的藝術風格。而說起這套印譜的刻制過程,劉一聞感慨說,對于自己這樣一個“上班族”來說,其實所有的創作都是在業余時間完成的;而當時在2月接下出版社的邀約“任務”之后,因為要趕在當年8月的上海書展上首發,所以留給自己的時間非常非常緊。“我是個心急的人,一件事情在手里,總是盡早完成方才心安。”劉一聞笑說,“所以,關于56個民族的正稿還沒拿到,我已經按照新華字典后的附錄內容,選擇部分自己有把握的民族先刻了起來。”于是,他每日白天照常工作,下班回到家就潛心其中,構思、比較、奏刀,日復一日,竭盡心神。搞創作的最怕重復,而在這一套民族印譜中,56個民族的每方印章上都少不了一個“族”字,如何既保證民族族名印譜的連貫性要求,又能體現各印章間的獨創性差異?為了這56個不重樣的“族”字,劉一聞可謂費盡了心思。他又是個追求完美的人,每一方印章都盡可能精益求精:筆畫不夠美的、形態有雷同的、整體不和諧的、甚至就只是自己看不順眼的……全部磨去重來,即使再不舍得也毫不含糊。“我那一陣子幾乎是夜夜‘淚流滿面啊。”劉一聞大笑調侃,“倒不是心疼印石,而是工作量太大太密集了,結果用眼過度,導致流淚不止,到現在還留下了后遺癥。”劉一聞說,現在書中收錄的是56方印章,但他當時實際上刻了又廢掉的也有近10方了。
功夫不負有心人,在劉一聞“淚流滿面”地努力下,《中華民族印譜》如期出版了,看著自己耗費半年心血一刀一刀刻出來的作品印成了書,劉先生說自己還是挺滿意的。不過回頭再重新審視這一方方印章,他直言還有遺憾:“如果時間充足,本可以更好一些的。”
寄語年輕人:技巧為“匠”,意境成“家”
從臺灣回來的劉一聞依然很忙,因為他已受邀參加了將于11月正式開幕的“全國第十屆書法篆刻展”的評審工作。四年一屆的全國書法篆刻展,有著書法篆刻界的奧林匹克之稱,而今年上海首次成為主辦方,這對于上海的書畫界來說,既是迎接一份等待已久的喜悅,更要面對一次“居安思危”的自省。
這一次的全國第十屆書法展一改常規,破天荒地在上海和廣西設立了兩個展區展出。一直以來,入選全國書法展的人數之多寡,是每個地方書法界的臉面。而上海這個中國近現代書法的重鎮,近年來在全國同行中的表現不算突出,這次自然想借全國書法展辦到家門口的契機,將更多書法新銳的風采在此舞臺上展示。最終,上海入選全國書法大展上海展區的有18人、入選廣西展區的有7人,著實比往年有所增長。但身為上海書法家協會副主席、中國書協篆刻專業委員會副主任的劉一聞卻給一派歡欣的業內潑了一桶冷水。“今年上海的參賽情況雖然不錯,但這不足以讓我們沾沾自喜。”在劉一聞看來,上海是海派文化的發源地,又是本次展覽的主辦方,占一定的優勢是應該的。“我們的問題是,明后年上海不辦這樣的展覽了,是不是還能保持這樣的良好狀態?”劉一聞說,他作為多屆全國書法篆刻展的評委,深深感到中國書法正面臨被邊緣化的趨勢,除了毛筆書法的實用性被邊緣化,當今書法家群體的社會地位、文化修養、經濟能力和影響力等方面都趨于“邊緣化”,無法與前輩相比,更不要說古人了。
“自古以來,大書法家多為文化、政治、藝術等領域的精英。中國書法歷史的輝煌是整個民族文化大環境造就的。如今書法正在失去其過去所依賴的環境,所以這不是僅僅靠幾次培訓班和幾場書法展就能解決的。”在劉一聞看來,現在一些書法家的書寫技巧看似直追古人,但其實無法超越前人,是因為過分重視技巧,忽略了作品內在的精氣神。“我們很多人沒有把寫字和書法區分開,這兩者是完全不同的。寫字只是為了滿足日常生活的需要,字只要讓人看懂就行。但是書法是藝術創作,有很高的藝術境界,我們不能習慣性地從寫字的角度去欣賞書法。”在這次書法篆刻展的前期評選中,劉一聞甚至曾看到過有的楷書作品在技術上幾乎不亞于文征明,然而畢竟書法是一門藝術不是技術,本末倒置的結果就是“格調不高”成了當今書法的通病:“這么多場評審做下來,我看到的還是匠氣、俗氣之作多,大氣、靈氣、有精神氣的作品少。”
劉一聞認為,單純的刻苦練習只能提高一個人的書寫技巧,但“書法”不是“書寫”,只有在“書寫”的過程中融入了靈氣、體悟、意境等藝術成分,才能稱之為“書法”。“我們上海博物館的講解員都覺得書法陳列室最難講解,因為書法很難具體化,有的作品從寫字角度去看,并不怎么樣,但它內在是帶有很強的文化氣息和藝術高度的,這個需要我們用自己的修養和審美去讀懂它。”劉一聞認為,現在書法作品正在趨于格調低下化,其根源就在于如今的書法家普遍缺乏審美修養。而缺乏審美修養的一大根源就是“孤陋寡聞”:“古今中外的好東西要多看,不要幾十年就埋頭老師當年要你臨的帖。要放眼看世界,看中外藝術大師的作品。只有見多識廣,才體會得出審美品位的高低。”
隨著社會文化藝術教育的普及,公眾審美趣味正在迅速提高,如果我們的書法作品品位跟不上,就很難被追求高水準的人群和居所欣賞、接納,更不用說發揮引領審美的作用了。“如果一個書法家的審美品位還不如普通市民,那就不要怪自己被社會邊緣化了。”劉一聞很不客氣地說。
變與不變:“永遠要對傳統抱敬畏之心”
說到這一次寶島之行,讓劉一聞印象最深刻、感慨最深切的,不是號稱門檻奇高的“國父紀念館”對自己的一路綠燈,也不是市長親至所作的開展致辭,而是那些最平常不過的普通市民前來觀展時的一系列微小的動作——從他們取閱展覽宣傳冊開始,他們的動作就很輕,但卻很慎重,每一個人從工作臺上拿好自己的一冊之后,都順手把剩下的一疊宣傳冊重新整理、碼齊;而在他們看完之后,劉一聞注意到,也沒有一個人隨手丟棄,而是放回到之前拿的那張桌子上、認真按照之前的原樣擺放好。劉一聞對此非常感慨:“這些動作看上去確實很小,但我覺得折射出來的內容很大,那是他們對包括篆刻在內的中華傳統文化的一顆敬畏之心。”
時代在飛速向前,可是我們在追求速度的同時,卻不知不覺出現了審美的偏頗:現在很多藝術活動,都以淺薄媚俗為樂,以張狂怪誕為美;很多藝術活動熱鬧有余卻水準不足,這些總總日積月累,最終導致了公眾對藝術認知開始有所偏差。而在劉一聞看來,糾正這些偏差的一劑良藥,無疑就是“回歸經典”。劉一聞說:“現在很多藝術家只追求自己的作品是否獲獎、成名,卻對真正的學問一知半解,把古往今來的許多優秀作品都不放在眼里,更別談讀出其中的文化氣息了。”劉一聞認為,能否理解藝術作品是藝術家自身文化藝術修養的體現,尤其是古人的作品,包含著前人對中華精粹文化的感悟,有著濃厚的文化氣息。所以,要讀懂這些作品,必須具備一定的傳統文化素養。而劉一聞對傳統經典的頂禮膜拜,在圈內是出了名的。也許是家學淵源,其外祖公王獻唐先生曾為山東圖書館館長,也是中國現代史上赫赫有名的考古學家、版本目錄學家、金石文字學家,著名國學大師,一生著述極豐,在詩、書、畫、印等中國文人的傳統領域都有極其深厚的造詣。“也許是受家中氛圍的影響吧,我在還不大識字的時候就開始寫字了,而且的確是非常喜歡,一看到字就很興奮,天生的。”劉一聞笑著說。自幼時起,劉一聞最常聽到的,便是姥姥口中關于外祖公王獻唐的故事和傳奇,連同家中成箱的古書、字帖、印譜一起,伴隨劉一聞度過了難忘的童年時光。家學的滋養和耳濡目染,加上性好筆墨、篤學不倦,方才有了如今的劉一聞。
正因為切身體會到了從傳統經典中的收益豐厚,劉一聞提出了藝術家應該具備“為藝、為學、為人”之道,“為藝、為人大家普遍比較重視,但常有藝術家忽略了為學之道,其實我們現在就該補補傳統文化的課,書法之道最終還要從傳統文化中去找。”劉一聞坦言,海派文化的影響力不如從前,書法藝術也正失去過去所依賴的環境,“現在還能有多少人真正靜下心來寫字看古籍?如果藝術家本身的內涵功力不行,那么整個藝術界的基礎就會不扎實,就難以進一步發展。”
然而如果你因此就把劉一聞歸總到“守舊派”,那就又錯了。據說就在幾年前,一位老友在看到劉一聞六十歲之后作的一幅作品時,很是感慨——他居然仍在“求變”!對此,劉一聞笑說:“在創作上,我常常會有今是昨非的感覺。創作一件作品很艱辛,但也很快樂,得了好作品,自己看了也會很欣賞很得意。可是,過了一段時間以后再看,有時候我自己都會否定自己,所以說創作就是一件沒有窮盡的事情。”劉一聞說,創作有時還會出現審美偏差,如果一旦陷入這個偏差,作品就很容易走上下坡路,所以他時時都會警覺這一點,時時提醒自己千萬要有清醒的頭腦。“藝術的創作就是人對‘美的認識與體悟。”劉一聞說,只有自己感受到了美,才會在創作中表現這種美。而每個人的感悟不同,資質也不盡相同,有的人敏銳,有的人麻木。麻木的人就很容易一直不變,而敏銳的人則能時時將所見所悟的美體現在自己的創作之中。“我恰恰是一個比較敏銳的人,所以我常常會在感悟之后思索,思索之后表達,把那些新的美的體悟融入到我新的創作之中。可以說,在我這個年齡層中,就全國范圍內,我的創作能力也還是很靠前的。”
但是是不是每一次的創新都會帶來美好的改變呢?也不盡然。所以每當創新進入瓶頸,審美發生偏差的時候,劉一聞的辦法就是“停下腳步,回望古人”——是的你沒有聽錯,當“創新”遇到問題的時候,劉一聞給自己的一帖靈藥就是“回歸傳統”。“因為書畫藝術是一門傳承千載的傳統藝術,所以我們所有的向前邁進都要建立在對傳統的充分認識上。”在劉一聞眼里,創作上、技法上的難度都不是主要的,真正可貴的是思想上的高度。而很多時候,藝術上的求索就如同在荒山上辟一條新途,一半靠自己上下求索,一半靠仙人指路,披荊斬棘的艱辛與柳暗花明的快樂都是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正如劉一聞先生自己的一方印文:“道可道,非常道”。而此間之“道”,就是匠人與大家的分野吧。